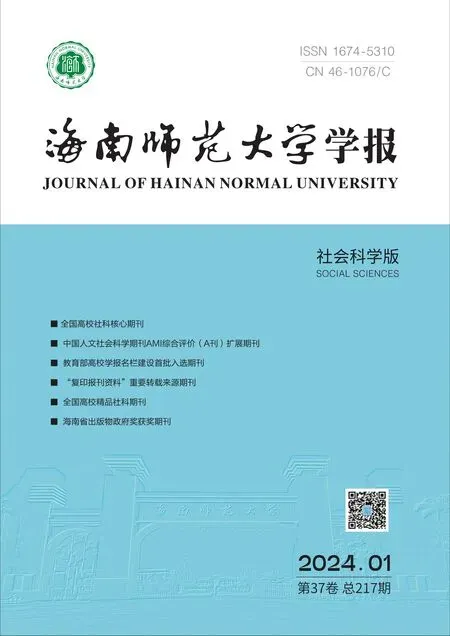论《呼兰河传》风景书写的视角与意蕴
苏晓芳
(厦门理工学院 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呼兰河传》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近年来对于这部作品的重视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1999年,中国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 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呼兰河传》名列第九。这部作品自诞生80 余年来,学界对于它的论述与解读,大多围绕其散文化或诗化的文体风格、回忆体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国民性批判中的反讽结构及对于女性命运的书写等方面展开。同时,《呼兰河传》也是萧红作品中读者普及程度最高的一部,小说的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三章第一节的部分文字分别以《火烧云》和《祖父的园子》为篇名入选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这两段文字的共同点是出色的景物描写,堪称小学生学习写景状物的文学范本。随着风景诗学的兴起,广泛征用相关理论和跨学科的视角来探讨文学作品中的风景书写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作家作品中的风景描写被放置在新的理论视域下进行解读。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有较为密集的风景书写,通过这些风景书写的文本细读,能够丰富对其作品内涵的理解与阐释。
一、背景与主角:不同叙事功能的小城风景
在小说中出现大量的风景描写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才发生的变化,中国传统小说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情节叙述,而较少景物描写。人物中心或情节中心作为传统小说最经典的形态,也培养了中国读者小说阅读的欣赏习惯和阅读心理,人们更关注故事本身,而不大关注场景,与核心情节无关的枝节内容,甚至会让读者厌烦。以致西方小说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时,林纾在他的汉译小说中为顺应中国读者的口味,对原作中大量的风景描写采用大幅删减的翻译策略,从而创造了译者“创造性叛逆”的经典案例。比如林译小说《黑奴吁天录》第32 章中,原文近两百字的景物描写,译者被缩减为一句话:“一路景物荒悄,似久无人行”[1]。
风景的发现是现代小说家的功劳,作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一种表征,风景书写不仅成为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能从背景走向前台,赫然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杜秀华指出,《呼兰河传》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认为萧红“认真地把呼兰河城当做小说的描写中心”[2],对它进行了性格刻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大胆选择。当然,此处所说的由背景转而成为主角的呼兰河城包括但不限于呼兰河城的风景。
小说发表时,茅盾在序言中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3]401。王科则说它是“典型的‘三无小说’”,“既无鲜明的主题,也无中心的人物,更无连贯的情节,”“是小说创作的别体”[4]。但读完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于呼兰河城的景观描述是完整而鲜明的,既有整体性的书写,也有局部的细节描述。小说一开篇就对呼兰河城进行了鸟瞰式的整体观照,这是一座不太繁华的小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5]5,而全城的精华就是两条大街的交汇处——十字街口,小说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十字街口的各种营生,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等。随后又将镜头转向十字街之外的两条街,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以及许多的小胡同。小说对于小城空间的描写基本按照由大到小,即十字街口——东、西二道街——小胡同缓缓推进,其商业的繁华度逐渐递减,小胡同里“连打烧饼麻花的店铺也不大有”[5]18,而只有一些走街串巷提篮子卖东西的小贩。
作为一个东北小城,萧红笔下呼兰河城不同于我们在其他现代小说中见到过的城市,从城市空间布局到市民生活方式,它确实是城市而不是乡村,但它跟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它是“东北‘县乡社会’的缩影”,“这种‘县乡社会’不同于关内的格局,‘城’与‘乡’几乎没什么距离:今日在‘街上’卖豆腐,明日可能就下到‘屯堡’种地;有钱人多数为有田产的地主,城居乡居两由之”[6]。小城在文化、风俗、人情等方面与乡村区别也不大。它更像是乡村与都市之间的缓冲地带,这里没有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城与乡的融合互渗更能体现20 世纪中国社会动态发展的样貌。而且,这类兼具城、乡二元特征的生活空间正是以后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小城镇的早期形态,因而《呼兰河传》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或乡土小说,但它所呈现的呼兰河城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社会学意义。
《呼兰河传》虽然没有中心人物与连贯的情节,其叙事脉络却非常清晰。十万字的篇幅分为七章与一个尾声,第一章通过对居民生活空间的描述来展示小城“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第二章写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小城的精神生活盛举;第三章回忆我与祖父的故事,第四章写我家小院里的生活景观;第五、六、七章分别讲述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故事。除了叙事,小说中有大量写景的笔墨,正如艾晓明所说,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一意孤行,恣肆叙事和写景”[7]。而这些写景的文字,特别是其中对自然风景的描绘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本朝说“小说随处都是自然的诗篇”[8];日本学者平石淑子在谈论萧红作品的魅力时,特别提到小说中“如美丽画卷般的风景描写”[9]。
这些“自然的诗篇”或“美丽画卷”有时是作为叙事的背景,有时则是叙事的中心。小说的第五、六、七章,可谓叙事压倒写景的章节,每一章都较为完整地讲述了一个人物的故事,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景物描写。如第七章讲述冯歪嘴子的故事,主人公登场之前,先有一段约六百字的文字展现冯歪嘴子所住的磨房外的景物: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5]132
……
黄瓜的细蔓生机盎然,恣意生长,逐渐爬上磨房的窗台、窗棂,开着花爬上房顶,“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那磨房里边的磨倌就见不着天日了”,将“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5]131-132在“我”看来,这磨房窗外的后园风景是磨房的背景,黄瓜秧、倭瓜秧蓬蓬勃勃地向上攀援,将磨房的窗子装饰得煞是好看。然而,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严实实,冯歪嘴子看不到后园的风景,有时他会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5]133仅仅隔着一个窗子,他却与这后园风景完全隔绝。此处对于后园风景的描写既是写实,展现冯歪嘴子的真实生活境况,又具有象征意味,身处社会底层的磨倌像黄瓜秧一样努力生存,“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5]132,冯歪嘴子白天拉磨、卖粘糕,夜晚打梆,但其生活处境仍旧如这被黄瓜秧遮蔽的磨房一样暗无天日。直到秋天来临,“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巴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的荒凉起来了”,“那些纠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5]134,磨房的窗子才显露出来。这样,“我”站在后园里就可以看到磨倌冯歪嘴子,看他喝酒、睡觉、打梆子,看他拉胡琴、唱唱本、摇风车。此时,窗子变成了一个取景框,“我”透过它来观看冯歪嘴子的生活。
呼兰河城因呼兰河而得名,城在河的北岸。《呼兰河传》中有不少关于河流的书写。第二章的放河灯、看野台子戏都是在河边进行。放河灯一段堪称“人间最美的祭仪”[10],七月十五盂兰会,黄昏,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人们就奔着去看河灯了。虽然这盛举“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5]6,但对于人们来说,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当月亮升高,数不清的河灯从水上放下来,人们听着和尚吹奏笙管笛箫,看着河灯从上流拥拥挤挤地往下浮来,“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河灯往下流去,越流越少,逐渐变得荒凉、孤寂,看河灯的人们的心情也由欢喜转而“无由的来了空虚”,而“河水是寂静如常的,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海水上边闪着一片一片的金光,而是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5]7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此情既是看河灯的人们的情,更是数年之后在遥远的南国穿越时空回望之人的情。
野台子戏也是在秋天的河边唱的,如果那一年收成好或是求雨成功,就要唱一台戏酬神还愿,且一唱就是三天。搭台唱戏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戏台、看台搭好之后,人们就呼朋唤友地前来看戏,这看戏并不是简单的看戏,而是一个内容异常丰富的社交场合:在媒人的指引之下,适婚男女的父母在戏台底下彼此相看;姑娘媳妇盛装出席、争奇斗艳;三姨二姑聚集在一起,传播各种飞短流长。野台子戏就像呼兰河城的狂欢节,除了看亲戚、会朋友、订婚约,也会发生一些溢出规矩礼法的事情,比如绅士之流也会趁人多眼杂偷偷调情,也有人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在戏台下边结下终生之缘。因此,野台子戏最精彩之处不在戏台上的表演,而是戏台下看戏的人之间的交流互动,那才是更令人难忘的戏剧。这戏剧以呼兰河边的一块平平坦坦的大沙滩为背景,这沙滩长达半里,又光滑,又干净。此时的呼兰河退隐在热闹的戏剧背后,直至夜里大戏散了,那些赶车进城看戏的乡下人在河边沙滩上住下来,他们燃火、煮茶、聊天,才感觉到“住在河边上,被河水吸着又特别的凉,人家睡起觉来都觉得冷森森的”[5]40。东北的秋夜自是比其他地方温度更低,用“凉”“冷”来描述近于写实,热闹之后的沉寂加重了人们体感的凉意,因而“冷”之上更添森然之意,这是人们的心理感受。此处写景,虽仅几笔点染,曲终人散的落寞感呼之欲出。
这类作为叙事背景的“自然的诗篇”在《呼兰河传》中俯拾即是,也是萧红小说创作的一个特征,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比较多见。有时长段铺叙,有时寥寥数笔,通过对自然的描绘,渲染出人物生活的环境特征,与人物的身份、境遇、心情形成一种映衬或对照,让读者阅读感受产生增值。在《呼兰河传》中还有一些风景书写是将风景从背景推向前台,让风景成为小说的主角。这种写法首推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火烧云”与“后花园”的描写,作家用整节的篇幅来写景。这两个小节独立成篇也是极为优秀的写景散文,但放在小说上下文中来进行阅读,却自有不一样的感受,“火烧云”一节所呈现的自由、热烈的风景为小城生活增添了审美的色彩;“后花园”则带着浓烈的乡土气息与童话色彩,如同小城中的一片梦幻乡土,写尽游子的乡愁。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写景章节。如小说一开篇就是呼兰河城的严冬风景: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5]3
地域化的风景在比较中彰显其特有的风貌,在写作这部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时,萧红正身处亚热带城市香港,漫长的严冬应该是此时的她对于故乡最醒豁的记忆,也是呼兰河城的特征之一,此时的大地、天空呈现一种混沌空茫的气象:
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5]4
第一章除了依照空间布局来展现小城居民的生活状态,还按照时间顺序书写小城的自然景观,此处时间顺序包含四季与晨昏。这一章共九个小节,从冬季写到冬季,其写景写出了季节转换中的生机盎然与荒凉寂寞;而六、七、八、九等四个小节则从午后写到夜晚,将小城日常生活风景的庸常与浪漫尽收其中。第九节作为第一章的收束,尤其绝妙,在这一节中,作家通过天地星月、风霜雨雪的变化,猪、牛、马、羊乃至燕子、蝴蝶、蛤蟆、虫子等的活动,来书写小城四季的夜晚。当然,写这四季的流转最终还是为了写小城中的人,写人们的顽强隐忍、逆来顺受,“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5]26;“受不住的,……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还没离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5]27。在呼兰河城,人与自然是同在的。
二、“朝花夕拾”:视角转换中的风景凝视
在萧红研究中有一个近乎定论的说法,那就是萧红小说叙事中的儿童视角,结合其性别,则进一步细化为女童视角,《呼兰河传》是儿童视角或女童视角的代表作。支撑这一说法的理由有二:一是,作品中呈现的是“我”童年时代的呼兰河城,而彼时的“我”是一个天真活泼且带几分任性的女童;二是,小说独特语言风格如多用简单句、多具象的细节描写等被视为出自儿童特有的心理与思维特征,甚至有人断言,“儿童视角成为理解作为小说意义存在的《呼兰河传》的关键”[11]。赵园认为,“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萧红“作品中最美的篇什”中都有“‘童心’对于‘世界’的覆盖”,这里的“童心世界”,是指“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比如保有世界形象的‘浑然性’的感受方式)以及表述方式(也是充分感性的),儿童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等等”。[12]219-220此处提及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都得经由一定的表述方式方能传达。那么,《呼兰河传》中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述方式是否都是儿童式的呢?
小说前两章对于呼兰河城全景式回忆虽然展现的是多年前的小城生活,但显然出自成人视角,那个四五岁的女童——“我”并没有在这两章中出场。第一章中以鸟瞰式的视角描画小城的空间布局,非成人无法胜任。介绍十字街口的药店“李永春”时说:“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5]5这里提及的城里人、乡下人对于店铺的记忆方式则显现叙事视角不仅是成人的,还是全知的。
一般而言,所谓全知叙事的叙述者通晓所有需要被认知的人物和事件,但并不出现在故事中,他们占据一个相对更为权威的位置,但也存在“失去了对情景的接近感,失去了亲切性和某种亲切感”[13]等缺陷。但我们读《呼兰河传》前两章,尽管看到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却不时能瞥见成年的“我”的身影。《呼兰河传》的写作始于1939 年的武汉,从1940 年9 月1 日开始刊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940 年12 月20 日,萧红在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并在12 月27 日全稿连载完。从萧红本人1931 年离开呼兰县算起,她已经阔别呼兰近10 年,此间未曾回乡,萧红的呼兰记忆也就定格于10 年前。写作此书时,萧红虽只有30 多岁,但重病缠身,蛰居香港,已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加之正处于战争环境,更添朝不保夕的恓惶。当她提笔回望故乡,很难保持一种真正的“零聚焦”状态,此时的“我”常常会悄悄地显露出来。如第二章回忆小城精神上的盛举,写跳大神的仪式,人们听着大神二神唱着的词调与鼓声,心里升起悲凉的情绪,感慨兴叹,以致终夜而不能已。接着,有一句景物描写:
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5]29
这句感慨,显然不是出自前文所述的请神的人家或邻居街坊之口,而是回忆此情此景的作者触景生情,自伤身世,油然而生的喟叹。
历来为众多读者与评论者所称道的“火烧云”一节也出自全知的成人视角,但其中变化颇为灵动。作者写火烧云,先不直接写天上晚霞形状与色彩的变幻,而写霞光中人与动物的样子: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5]23
然后变换视角,从看火烧云的人们的视角出发来看彼此互看:
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他妈的,你们也变了……”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5]23
喂猪的老头儿看到他的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乘凉的人看老头儿变成金胡子。视角的变化使看火烧云摆脱了“人看云”这一单一的观赏视角,而增加了“人看霞光中的物”“霞光中的人互看”等多重观赏角度,也为景物描写增添了动感与欢快的气氛。
小说的第三、四章,写“我”的童年生活,变成了第一人称叙事,那个四五岁的女童——“我”正式登场。这部分常常被“儿童视角”论者用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第三章的主角是后园、祖父和“我”,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中,“我”与祖母、父亲、继母及其他亲人的关系都比较疏离,与“我”感情最深的只有祖父。后园是“我”与祖父的秘密花园,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与祖父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后园中。后园风景是“我”童年的快乐源泉,也是成年的“我”记忆中的童年、亲情等最美好的承载物。这里种了很多花草、蔬菜,而且“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5]45,我在这儿自由玩闹,“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此时的“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后园中万物“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植物、动物都有自己的意愿,“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4]47。
但凡涉及童年回忆的作品,都容易被冠以“儿童视角”,张箭飞在论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景时说:“《从文自传》是作者关于少年时代的回忆。作为一个孩子,他对一切现象兴致盎然。大人繁重的劳作是他眼里的艺术,大人避之不及的场所是他的秘密花园,大人漠视的事物是他珍贵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风景是向孩子敞开的”[14]。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呼兰河传》的第三章中,后园的风景是向四五岁的“我”敞开的,因而确实存在一个童稚化的观看后园风景的视点,但关于“自由”的描述显然不太可能出自一个四五岁女童的认知,在这个童年的“我”后面始终隐藏着一个成年的“我”。这个成年的“我”不仅知道童年的“我”跟在祖父后面“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而且还知道童年的“我”用锄头的“头”铲地时,“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5]46
也正因为这个隐藏的成人视角的存在,艾晓明认为:“小说里混合运用了成人和儿童两种叙事角度。这个成人视角是超故事的叙事者,而儿童视角在故事内起作用”[7]。张莉也在叙事中感觉到“苍老和童稚,寂寞和热闹都在同一个声音里糅杂出现”[15]。这种成人与儿童视角的混用在第四章中表现得更加鲜明。第四章共五个小节,第一节写“我”家院子衰败的原始风景;第二、三、四节则依次讲述租住在我家院子里的几户人家的生计和生活;第五节回忆“我”与祖父从清晨到正午的日常生活。这一章有一个文眼,那就是“荒凉”二字。第一节中说:“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5]66在随后的四节,则分别以“我家是荒凉的”和“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作为首句。从第五节“我”与祖父的日常生活叙述中不难看出,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我”的生活都堪称幸福安宁,早上醒来,“我”就让祖父给我念诗、讲诗,一直到太阳出来。起床后“我”跟在祖父后面,看他喂鸡放鸭,老厨子为我们做好了饭,吃完饭听墙外街头各种热闹的叫卖。那么,“荒凉”的感觉实在不应来自回忆中那个四五岁的女童“我”,而是正在回忆往事的当下的“我”。这一章的最后一段继续书写“荒凉”: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5]78
这里体现的审美认知更带有成人化色彩,因此,即便是在童年的“我”出场率最高的章节都并非纯粹的儿童视角的写作。
《呼兰河传》也常被视为散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如果说小说的前四章偏重于写景抒情的话,那么后三章则近似叙事散文,叙述中心分别聚焦于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童年的“我”频频造访他们的故事空间,与小团圆媳妇搭讪,跟有二伯一起上公园,买冯歪嘴子的粘糕,“我”是他们故事的参与者。当然,一个四五岁的女童没有能力影响和推动他们的命运,因此,更多的时候,“我”又只是他们故事的旁观者或见证者。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故事,除了个别场景是“我”亲眼所见,大多数都是通过“我”跟祖父、老厨子、有二伯等一次次议论中呈现的,比如小团圆媳妇,将她如何嫁进胡家、如何挨打哭泣、胡家为她请人跳神驱鬼治病、用热水烫洗,直到最后死去。因此,四五岁的“我”虽然不是小团圆媳妇命运的推动者,却是这个故事的叙事推动者。在有二伯、冯歪嘴子的故事中也是如此。
这三章虽以叙事为主,但也有一些独具匠心的写景文字。磨倌冯歪嘴子的磨房的窗子临着后园,大多数时间,这个后园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世界,磨房的窗子如同这个美好的秘密花园的一道罅隙,它通向冯歪嘴子的世界。作家先从“我”的视角看到,后园的黄瓜蔓肆意生长,沿着窗子爬上屋顶,将磨房的窗子“遮掩得风雨不透”,然后变换视角,从磨房内感知——“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倌就见不着天日了”,“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至于“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5]131则是站在全知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即使在第三章以后,叙述里一直有全知视角”[6]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通过对小说各章节风景感知视角的梳理与分析,可知《呼兰河传》基本采用成人化的全知视角,这个成人就是作品中成年的“我”,而幼年的“我”——那个四五岁的女童——在更多的时候只是成年的“我”凝视与关怀的对象,“我”以洞悉一切的眼光端详着那个纯真任性的女孩,透过她的目光与行踪,重温儿时的时光,便有了一种“朝花夕拾”的珍重与叹惋,但每一个回忆片段结束、曲终人散时因感知回忆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如同一个隐藏的偷窥者终究没能藏住自己的影子。
那么,为何这么多人不断论证与强调萧红作品中的儿童视角?我想恐怕是研究者因为作家个人相对单纯任性的性格而造成的误读。比如有研究者从鲁迅先生在1935 年给萧红的一封信中找到了关于“儿童视角”的佐证,鲁迅在信中说“这位太太,到了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16],于是推断出“正是萧红身上这种一生未脱的‘孩子气’,使她首先获得了‘儿童的自由’”[17]。鲁迅与萧红之间有三十岁的年龄差,萧红视鲁迅为师长,写此信时萧红仅24 岁,鲁迅54 岁,以鲁迅的年龄与阅历从萧红身上看到孩子气并不足以证明萧红“一生未脱‘孩子气’”,更不能推断出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写作仍是“儿童视角”或“儿童思维”的。
三、怀旧与批判:多重意蕴的故乡书写
呼兰河城的原型呼兰县于1913 年设县,现为哈尔滨市辖的呼兰区。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黑龙江省的大县有‘呼、海、巴、拜’之说,呼兰实为首县”[18]。有学者将《呼兰河传》开篇对于呼兰河城空间布局的描述与20 世纪30 年代版《呼兰县志》进行对比,得出二者“完全一致”的结论[19]。因而,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萧红对于故乡空间做了还原,当然,出于创作需要或回忆的主观心理原因,这种还原也是有选择、有限度的,甚至有些是记忆的重组,原本记忆所提供的就是经过层层编辑的过去及其世界。
在风景书写方式上,除了写实性地还原记忆中的北国小城风景,《呼兰河传》中更多的风景刻画带有作家主体意识与情感的投射性,对于自然景物的描摹,更多的是为了透过风景的描写表达出内心世界的情感和思考。相对于外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20]15。《呼兰河传》中大量的风景描写就是这种“内在的人”的发现。于是,“风景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人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其上,赋予它思想情感,才有了风景和对风景的欣赏”[21]。
萧红喜欢将动物、植物、河流、大地、风、雪赋予人格化特征,写出它们的情感、动作,如“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5]4;如“老榆树全身的叶子已经没有多少了,可是秋风还在摇动着它”[5]121;又如“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5]71。她也喜欢将人物或自己的情绪、心理以视觉、听觉、触觉等外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人们看河灯时,“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5]30。灯光、河水、月亮所呈现的美好得令人晕眩的视觉场景是由人的心境产生的,正所谓“境由心生”,读者阅读此类场景时,可以逆向还原,由视觉描写而反推叙述者的心理与情绪。写粉房的工人住在破草房,逆来顺受地承受悲惨的命运,他们一边劳作,一边唱歌,“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5]70。这个句子中将听觉、视觉融为一体,与心理形成鲜明的反差,写实的仅有听觉感知的“歌声”,视觉中的“红花开在了墙头上”和心理上的“悲凉”都是由“歌声”衍生出来的。细细品读这类景物描写,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赵园曾说:“萧红要她的作品情境在虚实之间,在具体与非具体、特定与非特定之间,在历史与现实、在写实与寓言之间。”[12]232萧红对于呼兰河城的风景书写以儿时的故乡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融入自己多年的人生体验与想象。为呼兰河城立传,实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小说第一章中的“大泥坑”更像是一种象征与隐喻。东二道街上的这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不下雨时泥浆像粥一样,下了雨,泥坑就变成河,给附近的人家和过路的车马、行人带来诸多不便。却没有人去改变它,只是顺应它,甚至还享受起从泥坑中获得的两种福利:一是“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5]12;二是因泥坑的存在,人们可自欺欺人地将瘟猪肉说成淹猪肉,既便宜,也不算什么不卫生。对这个大泥坑的描述令人想到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思路,而这与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小说的基本表现方式和结构还是显示出儿童般的思维特征”[22]相去甚远了。
童年的小城风景具有多重面向,它是快乐无忧的,也是寂寞冷清的,它尽享生命的自由,却时常感觉到限制与危机。这一点颇类鲁迅的《故乡》。提起《故乡》,两幅画面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是,“我”回乡看到的“在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3]476;二是,“我”记忆中的“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23]477。今昔两幅画面形成鲜明的对照。不同的是,《呼兰河传》小城风景的多重面向是共时的,都是“我”记忆中儿时的小城。最能代表快乐自由的风景当然是“后园”,花开、鸟飞、虫子叫,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而“我”活泼好动,在祖父的庇护下自由生长,这里连天空都又高又远。
观赏火烧云一节对于小城风景具有特别的意义。火烧云并非呼兰河城或东北所特有的自然景观,属于非地域化的风景。作家以对云的色彩、形态等视觉元素细致入微的感知与辨识能力,运用丰富的想象,将视觉感知转化为精彩的文字,将稍纵即逝的火烧云描述出来,读者只需稍做还原,眼前就能浮现出一幅火烧云的动态画卷。然而,令人惊叹的还不止于此,小城中,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看火烧云,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5]23晚饭后,那些忙于生计的人们将看火烧云、辨认云不断变幻的形态当做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与乐趣。“晓看天色暮看云”,这是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闲适的、审美的生活,很难将这种生活乐趣跟“喂猪的老头子”联系起来。但在萧红笔下,正是这样的人将观看、欣赏火烧云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说中写到的深受大泥坑之苦却自欺欺人地享受着大泥坑所带来的“福利”而不图改变的人,以及“小团圆媳妇”悲剧中那些无聊的看客与闲人跟欣赏火烧云的男女老少看作是同一群人,然而,他们却真是同一人群。因此,不仅“我”的童年风景有不同的面向,小城中人也有不同的侧面,他们因循守旧,逆来顺受,但他们也乐观幽默,追求审美闲适的人生状态。所谓火烧云就是晚霞,在人手一台拥有拍照功能的手机的今天,人们看晚霞、拍晚霞并不足为奇,但在一百年前的东北小城,人们不论年龄身份,都不约而同地为这美丽的风景而驻足凝望,这幅画面比那绚烂变幻的火烧云本身更让人动容。
在记忆的重组中,田园牧歌般的美丽故乡是风景化的故乡的主要形态,然而,“现代性的风景是包含了‘反风景’的‘大风景’,是杂糅了风景、感怀、情绪、和现实遭遇的综合产物”[24]。所谓“反风景”是指被污染、被破坏的风景,常被视为风景的对立面或阴暗面,如闻一多著名的诗歌《死水》所描绘的那沟肮脏、绝望的死水即可视为“反风景”。《呼兰河传》中也有不少寂寞、荒凉的风景也是反风景,除了“大泥坑”,第四章第一节院子的衰败之状就是典型的反风景。院子里长满蒿草,胡乱放着一些朽木头、乱柴草、旧砖头,还有打碎的大缸、腐朽的猪槽子、生锈的铁犁头……所有人工之物都处于废弃状态,“什么都是任其自然,愿意东,就东,愿意西,就西。若是纯然能够做到这样,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风景”。[5]66现代风景书写不回避对于“反风景”的描述,并借由反风景中令人不适的景观来表现各种心灵创伤或情感隐痛。作为一个回忆性文本,《呼兰河传》的风景书写混杂着作家复杂的情绪与情感,既有眷恋,也有怨怼,因而也形成了既有对随着时间不断远去的童年生活空间的怀念,对这个北方小城风物、人情的眷恋,也有对记忆中破败荒凉景观的伤痛,以及对小城中人们愚昧、因循、自欺、颟顸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有学者认为:“《呼兰河传》所要讲述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灵魂漂泊者的思乡情怀。”[19]我们从作品的风景描写中能感受到这种“思乡”之情,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花花草草、稍纵即逝的火烧云、秋夜星光,乃至北方凛冽的风雪,都是能唤起乡愁的景物,而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精神返乡。这种精神返乡实际上是一次怀旧之旅,按照博伊姆的说法,“怀旧是时间上的距离和位移造成的痛苦”[25],此时的作家与定格于幼年时代的小城风景不仅有长达10 年的时间之隔,更有数千里的空间距离,其怀旧之苦非亲历者无法确知。
怀旧的痛苦在小说中被表述为“寂寞”,“寂寞”是作品中使用频次仅次于“荒凉”的词汇,“荒凉”的是风景,用了14 次;“寂寞”的是心情,用了8 次,还有一次叠用为“寂寂寞寞”。茅盾在给《呼兰河传》出版所写的序言中,更是用了28 个“寂寞”来描述和评价《呼兰河传》中展现的小城生活以及萧红个人的命运。茅盾认为:“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3]402虽然,已有很多文章对茅盾的“寂寞论”提出不同看法,但我觉得萧红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情绪以及由此推出萧红在写作此作品时的心境,用“寂寞”来概括是合乎情理的。从1940 年春萧红写给作家白朗的信中可以印证这一点,彼时萧红在香港,从时间上推断正是写作《呼兰河传》的时候,她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26]正如柄谷行人所说,“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20]15,深感寂寞孤独的作家面对眼前“恬静和幽美”的南国风光,勾起了她的乡愁,更加思念暌违已久的故乡风景,因而备感孤独寂寞。乡愁就是这样不讲道理,跨越遥远的时空,频频入梦的仍是故乡的风景,哪怕这风景有着如此多重矛盾的面向。
然而,萧红毕竟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作家,在一次次精神返乡时,对故乡小城的风景又始终保有一重批判审视的眼光,由于没有再次真正返乡,无法对小城进行今昔对比,审视的参照系只能是她多年外部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这就使她能够不断自由地进入与抽离那座童年的小城,以“内在的人”的眼光去发现小城风景的更多面向,启蒙立场的国民性批判也便成为题中之意。
从萧红的作品和她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能看出她喜欢看风景、写风景,除了《呼兰河传》,在《王阿嫂的死》《后花园》《黄河》等作品中都有不少风景书写,而在给萧军的多封书信中,她不仅坦言“自幼就喜欢看天”[27],而且常常分享自己在路途中所见的景致,如1937 年4 月25 日,她在火车上写信给萧军,“方才经过了两片梨树地,很好看的,在朝雾里边它们隐隐约约的发着白色”[28],如此文字在其书信中比比皆是。萧红一生只活了短短31 年,但有10 年的时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呼兰、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到最后客死香港,她看过了无数风景,这些风景都以或情景实录或借景抒情的方式体现在她的文字中。《呼兰河传》作为萧红一生小说创作的巅峰,其风景书写也是同类书写中的集大成者,每一次重读,都能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其丰富内涵与价值值得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