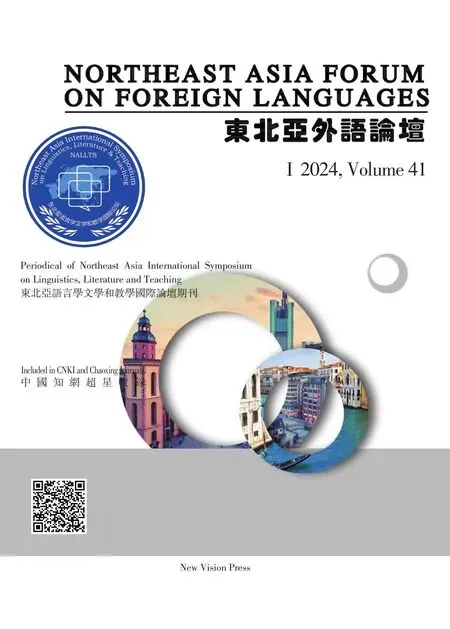《吃碗茶》中唐人街异托邦华人移民生存困境探究
李雅雯 曲 涛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一、引言
美国华裔作家雷霆超(Louis Chu)的《吃碗茶》(EataBowlofTea)被誉为具有“亚裔感性”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排华法案》废除后唐人街由单身汉社会向家庭社会转型时期的华人移民生活。国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它的历史意义和唐人街社区的文化转型;国内的研究集中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父权制度、中西茶文化的对比研究、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方面。目前来看,从空间视角对《吃碗茶》中唐人街空间进行分析解读的研究较少。米歇尔·福柯聚焦于研究空间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建立了空间哲学和空间政治批判相结合的理论模式,提出了“异托邦”理论。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以权力空间化对现代人造成的影响为立脚点,从空间角度来阐明现代权力的运作机制。本文将结合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唐人街对于三位主人公分别呈现出“危机异托邦”“偏离异托邦”和“补偿异托邦”的特征,探究权力的空间化所导致的华人移民的生存困境,体现了雷霆超对霸权压制和束缚的反抗,表达了他对处于困境中的华人移民的同情和关怀。
二、安逸与危机并存的“危机异托邦”
在《另类空间》中,福柯为了准确系统的描述“异托邦”的概念,对“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进行了具体阐述。“第一个特征,就是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福柯,2006: 54)。换言之,纯粹单一的文化是不存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的他者空间。在第一特征中,福柯认为异托邦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但是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危机异托邦和偏离异托邦。危机异托邦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异托邦形式:“这些地方是留给那些与社会相比, 在他们所生活的人类中, 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人的”(福柯,2006:55)。简言之,危机异托邦是由处于危机状态的特殊人群构成的,表现出空间的“他性”,不只是代表空间的概念,同时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事件紧密相连。
在《吃碗茶》中,对于第一代移民王华基,唐人街即呈现出“危机异托邦”的特征的一个空间。1848年,美国的“淘金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到美实现黄金梦。王华基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十几岁乘船只身前往美国打拼几十年。在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颁布并实施,其中一系列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华人移民成为白人社会中被排斥的他者群体。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加上自身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因此处于危机中的华裔移民在唐人街中构建了一个危机异托邦。文化为人类稳定生活提供了土壤, 第一代移民将中国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家庭理念和生活方式带到美国,在唐人街建立了一个美国土地上的中国文化空间,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维持着自身文化的稳定性,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因此变得稳定。《吃碗茶》中王华基在唐人街经营着一家地下麻将俱乐部,但是与一般印象中潮湿发霉、阴暗压抑的地下室麻将馆的氛围不同,“地下室里很清凉。不潮湿也不闷热,没有废弃地窖里的霉味”(Chu,1976:21),王华基每日在这里休憩喝茶、娱乐打牌,过着清闲安逸的生活。因此,受到排华法律等政策影响的第一代移民,认识到身份和文化的“他性”的危机,在唐人街中构建了一个提供庇护的危机异托邦,一个文化“舒适圈”。
唐人街作为早期移民的“舒适圈”,同时也是阻碍他们融入主流文化的文化“温床”。王华基在唐人街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滋养,也因此被传统的文化观念所束缚。“唐人街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几乎人人都互相熟知”(Chu,1976:113),众人在咖啡馆、理发店中公开议论别家的“丑事”,在社区中发生的任何“私事”都有可能变成众人谈论的“公事”。王家的“私事”也成为了整个社区议论的“公事”,而“公事”则涉及到一个人“脸面”的问题。中国人讲究“脸面”,一个人的“脸面”就是他在一个群体中的地位和名声。王华基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戴了“绿帽子”还无动于衷之后,对宾来大发雷霆:“人们会说是王华基的儿媳妇出轨了,而不是说王宾来的妻子出轨了”(Chu, 1976: 140)。在传统父权制观念中,“中国的家庭关系主导政治和经济活动,个人的名誉就是家族的名誉”(Kim,1982:102),王华基在宾来到美国后包办了他的工作甚至是婚姻,而宾来在被戴“绿帽子”后的无能表现,让王华基丢尽了脸面,他的名字会成为咖啡馆中人们口中的笑柄,他在唐人街社区中长久以来稳固的名声和地位都将崩塌,他感到无地自容。王华基想到离开社区,但又无法融入美国文化的主流社会,面临如此困境对于王华基如同世界末日降临,而昔日凉爽、安逸的麻将俱乐部内也变得“昏暗又空虚”(Chu,1976:143)。原本为王华基提供文化“温床”的危机异托邦,最终却变成了他想要逃离却无法脱身的牢笼。
三、“偏离异托邦”中的边缘化生活
“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福柯, 2006: 55),这些人往往是一批与规约社会文明人相迥异的异质人/边缘人,他们不适应、不符合规范,在常规社会受到压制和驱逐(纪秀明,2012:53)。排华法律种族歧视的政策将华人移民视为与疯子、罪犯一样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异常的个体”,他们的异位存在在唐人街形成一个异位空间——偏离异托邦,并在其中过着异于主流社会规范的边缘化生活。雷霆超在《吃碗茶》中主要描写了唐人街社会从单身汉社会向家庭社会转型时期的华人移民的生活,具体表现为在“混乱、无序”的秩序下的边缘化生活状态:唐人街华人社区中对违背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赌博、嫖娼、通奸等恶习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当社会伦理道德和法治力量不够强大时,人们倾向于借助家族的力量,甚至使用暴力手段维护利益。唐人街“偏离异托邦”形态中的“混乱、无序”的秩序是因为这个异质空间呈现着既封闭又开放的形态。“一些其他的异托邦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人们认为进入其中,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其实是被排斥的”(福柯,2006:57),唐人街是这样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异质空间。对于已经在唐人街安身立命的第一代移民,唐人街的封闭性更倾向于发挥着庇护的作用,但是对于第二代移民,这种封闭性更像是束缚他们自由发展的枷锁。
唐人街具有开放性。美国“淘金热”吸引了大量想要实现“黄金梦”的华人移民,他们期待着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前文提到,唐人街是无数华人移民到美后的落脚之地,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唐人街对外是始终开放的,但是对内却具有不可打破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产生可以从外部施压和内部控制两个方面分析。外部施压即在美国种族歧视话语和文化霸权的排斥和隔离环境中,华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囿于唐人街这个封闭的社区中,从事低等的工作,如洗衣工和餐厅服务员等,这类工作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从精神上削弱了他们的男性气概。不仅如此,中国餐馆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从早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而洗衣工每天工作17个小时,平均时间是美国工人的两倍多,很多华人移民认为当前的处境和工作都是暂时的,但长时间的工作压榨了他们休息和社交的时间,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工作和住所两点一线的毫无目的的生活。《吃碗茶》中宾来在下班后只能“和四面墙说话”,为了排遣单身生活的枯燥无味,宾来选择了和钱源一起去寻欢作乐,最后却导致结婚后发现自己性无能。列斐伏尔认为身体的表征体现着主体与自然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列斐伏尔, 2021: 63),性无能的宾来是唐人街封闭的特性,即美国种族霸权压制下华人移民的男性气概“被阉割”的受害者。
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除了外部权力的压制,在唐人街社区的内部,第二代移民还面对着从中国“移植”来的父权家长制的控制。“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被更大的社会环境所改变的封闭的世界,它是通过移植旧中国过时的行为、习俗和传统而存在,由唐人街的社会组织操纵的”(Li,1993:100)。因此,唐人街中的父权家长制,实际是“移植”过来的过时的、在封闭的异位空间中形成的畸形的父权家长制,体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宾来17岁来到美国,此后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父亲王华基安排好的,包括餐馆工作、住宿,甚至连结婚对象都早已物色好。当宾来表示想要等几年再结婚时,却遭到父亲的严厉反对,这时宾来意识到,他只能听从父亲,因为他无法违背传统。宾来没有积蓄,于是父亲便出钱帮他办理回国来回的手续,购置见面礼,操办宾来美爱二人的婚宴。在每一件人生大事上,宾来都服从着父亲的安排,在父权的控制下,他成为一个没有计划、没有想法、怠惰被动的人。在得知自己性无能后,宾来没有主动找医生医治,而是在美爱再三劝说下才肯去看医生。在美爱出轨后,他一直逃避,自怨自哀,最后是父亲王华基看不下去儿子的无能,为宾来“出头”报复。蒲若茜评论道,唐人街畸形的父权社会的威压,在某种程度上“阉割”了宾来的活力与男子气概(蒲若茜, 2009: 156),在畸形的父权家长制中窒息的权利义务关系控制下,宾来被“阉割”了作为男性的担当和责任,精神上也变得无能。
四、父权秩序理想下的“补偿异托邦”
福柯在阐述最后异托邦的最后一个特征时,提出了“补偿异托邦”的概念,他认为异托邦有创造另一个几乎完美的空间的作用,这是乌托邦投射出的理想空间,在远处实现,对现实进行补偿。福柯以南美洲创立的耶稣会会士的特别殖民地为例,“这些殖民地作为异托邦反映了殖民者的空间和秩序理想”(张锦,2013:129)。1882年的《排华法案》中因考虑到妇女劳工,于是将女性包括已在华人的妻子拒之门外。留在中国的“金山客”的妻子,只能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和丈夫团聚,她们接受着从美国寄来的资助,却不曾了解唐人街内的现实生活,对唐人街和在外打拼的丈夫抱有着美好的幻象。她们送自己的女儿去上学,希望女儿学好英语以后有机会能嫁给“金山客”,到美国去生活。1943年《排华撤销案》通过,华人妻子被允许进入美国,当她们生活在这个“完美空间”中,才发现唐人街是一个封闭的、畸形的父权社会,反映了男性对空间和秩序的理想。在《吃碗茶》中,雷霆超通过对美爱这个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在从单身汉社会向家庭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在唐人街的生存困境。
美爱在进入唐人街之前,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向往:“她将会快乐,非常快乐。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Chu,1976:66)。但是在唐人街的生活打破了她的幻象。她期待着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宾来的性无能无法满足她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她想要工作和社交,却因为丈夫的反对只能每日呆在公寓里。控制女性的活动空间是使女性服从于男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对女性活动空间的限制与对其身份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Massey,1994:179)。和美爱结婚让宾来感到了一种“占有的感觉”并且“让他拥有了尊严”。宾来以“妇女聚在一起闲谈会生事”为由反对美爱出去工作,限制美爱的活动空间,其实是为了确保他对美爱的控制,确保美爱作为他的“占有物”能够一直让他“有面子”。美爱以为在新的环境中可以追寻自由和平等,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发现唐人街依然是由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且对于女性以更严格的标准评判,她们不应该像男人一样有性的要求,而应该忠贞不渝,为丈夫侍奉父母,同时完成传宗接待的任务。然而唐人街社区中男性的赌博、嫖娼等越轨行为却可以被包容。在美爱眼中,唐人街这个补偿异托邦的完美空间幻象被打破,现实是以男性对于空间和秩序的理想为主导而建立的父权制社会,而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美爱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只能作为在男性眼中有价值的“附属品”努力实现作为“女性”的价值:传宗接代。安稳舒适的生活隐含着对女性的控制;看似温暖的关切和问候背后,是对美爱的逼迫;在这片美爱以为的崭新富饶、自由平等土地上,她却生活在旧传统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歧视、压制和束缚之中。
五、结语
唐人街是权力空间化的产物,具体来说是美国种族主义霸权和中国旧传统父权家长制的空间化的产物。雷霆超笔下的三位主人公的身份不同、处境不同,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美国种族主义霸权和畸形的父权家长制所压制和束缚着。雷霆超在《吃碗茶》中真实地再现了两代人包括女性在唐人街的生存困境,但在结尾中也展现了他们走出困境的美好愿景。第一代移民王华基意识到自己已经尽了作为父亲的义务,不再以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为由控制宾来,他也因此得以摆脱传统父权制对于父亲这一角色的约束,离开了纽约唐人街;第二代移民宾来在离开了父亲的控制后,变得成熟,不再怠惰,在积极主动地寻医喝药后,恢复了性能力;美爱得到宾来的原谅,二人一起在旧金山开始了新生活。但这看似完美的结局,其实未能完全打破权力的框架。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作为主流社会的“他者”,父子二人两代移民的新生活,也不过是在另一个地区的唐人街展开,因此想要打破美国种族霸权的排斥和隔绝,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而美爱,在旧金山的公寓里,开始了等待丈夫回家的新生活。这个结局没能超越霸权的束缚,也没能打破传统的藩篱,但这恰恰体现了雷霆超作品中的真实性,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超越同时代“唐人街”叙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