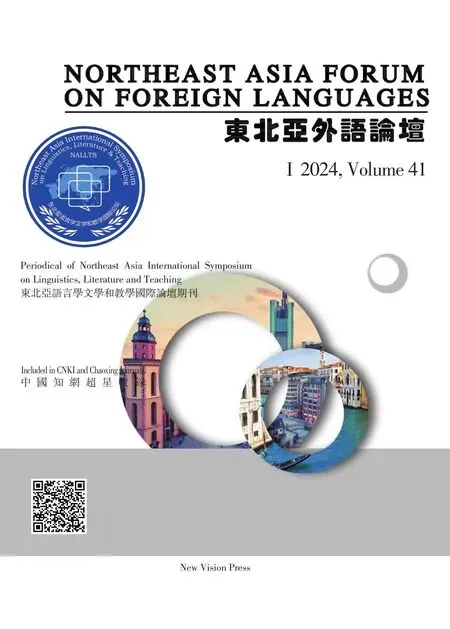福柯权力理论视域下《天秤星座》中的历史书写
陈莉丽 刘 丹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00 中 国
一、引言
唐·德里罗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揭露当代物质繁荣背后人类的生存危机是德里罗小说一贯的出发点。从《白噪音》(1985)到《天秤星座》(1988)再到《地下世界》(1997)、《大都会》(2003),德里罗的作品始终反思社会阶层的撕裂、消费主义的蔓延、意识形态的控制,批判技术统治和生存空间的挤压。
《天秤星座》对于肯尼迪遇刺做出大胆而又细致的虚构推测,尽管作为一部后现代的政治小说,它无法成为后人研究这次遇刺案的“呈堂证供”;但作为一部编史性元小说,作者与文中受雇撰写JFK遇刺秘史的尼古拉斯·布兰奇(Nicholas Branch)身份的重合,使得这部小说在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同时,也展现了历史小说新的呈现方式和解读的可能性。唐·德里罗记录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一个性格不稳定的天秤星座的冒险人生。奥斯瓦尔德自诩为“历史代言人”,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怀揣盲目的憧憬,但却最终成为历史的棋子,身陷看不清的局中局。不管是受人摆布的奥斯瓦尔德,还是精心布控的几位中情局特工,都相信自己不过是顺应历史,顺势而为。常年向反卡斯特罗组织提供经费盖伊·巴尼斯特在对肯尼迪进行抨击时说到:我深信空气中有一股力量,迫使人们采取行动,这力量就叫“历史”或“必然”(DeLillo, 1988:48)。
以往对于《天秤星座》研究大都集中在“编元史”小说的特征探析、新历史主义解读以及后现代文本创作特点上,往往忽视了知识与话语,权力与主体对于文本的建构价值。本文将思考历史如何发展、历史的力量如何催生历史事件、人类从启蒙运动中走出,高举着理性主义火炬,能否照亮历史前进的道路,解释历史发展的波折?继承尼采的史学观点,福柯终生质疑理性主义为人类发展勾勒的美好前景。即现代社会并不比启蒙时代更加高级,更不是线性发展的结果,相反,福柯断言,在现代性中,人将消失或终结(福柯, 2016: 392)。
二、权力欲望下的多元历史建构
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尼古拉斯·布兰奇负责撰写总统遇刺的秘史。面对越堆越高的证词和档案,布兰奇对于自己“编写历史”的重担感到心惊肉跳,他要对那恐怖的七秒钟进行抽丝剥茧的调查,要顺着子弹弹道的轨迹追溯躲在阴影之下的人们的生平。手边的每一本卷宗、每一盒录音带都有无数的暗示。肯尼迪遇刺后,奥斯瓦尔德也遭到枪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干扰历史正常情节的死亡案件。布兰奇深谙历史的运作,只将其看成“一首辉煌的史实”(DeLillo,1988:41),并且认为实在有必要去编造一个精妙的阴谋,好让每一次历史的断层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只需剔除不合逻辑的史料,润色牵强的记录,留下最为流畅的版本。
和布兰奇一样,德里罗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在创作《天秤星座》前走访了奥斯瓦尔德生活过的各个城市,例如新奥尔良、迈阿密沃斯堡和达拉斯。德里罗沿着奥斯瓦尔德的步伐一丝不苟的收集文字、语音以及视频资料,也曾做苦役般研读沃伦委员会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在整本小说中几乎见不到作者的评论,他如局外人一般刻画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肯尼迪遇刺后,官方媒体对于诸多细节始终秘而不宣,枪手的数量,枪击的次数,枪击的地点以及总统身上到底有几处伤口。电视影像开始代替官方报道,给了观众更多解读空间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困扰。人们逐渐感觉到历史在被操纵,“真实”一词也开始面目模糊。二十五年后,《天秤星座》发表,为这件迷案编织了复杂可信的脉络,但德里罗也再三强调这本书的核心并非通过小说的手段“发明”一段历史,恰恰相反,作者只是运用小说的“虚构特权”以及这样的历史事件实现小说的多样性(DeCurtis, 1988: 50)。
“历史的动力是争取承认”(Jameson, 2009: 89)小说主人公奥斯瓦尔德在袭击肯尼迪之后,强装镇定地走在达拉斯的道路上,走在幻想被凝视的惊恐下,他为他“英勇”的行为感到骄傲和后怕,但同时他又生出这样一种渴望:他很想写一些有关美国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DeLillo, 1988: 269)。这里所谓的短篇小说就是个人对记录历史的渴望。奥斯瓦尔德被形容为“生活在小房间”的人,出生于社会下层,成长在贫穷的单亲家庭,是历史洪流中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有书写历史的野心,也需要历史语境下的话语权。在小说结尾,作者不无感慨地说到“这名字(指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属于历史”(DeLillo,1988:305),这似乎是对奥斯瓦尔德愿景的一种回应和肯定——从俄国回到美国,奥斯瓦尔德虽已结婚生子,但当他走在空荡的达拉斯市中心时,却仍然感到无比的孤独,这是一种被历史抛弃的孤独感,在他看来,唯一解局的办法就是“达到一种境界,即他和周围发生的真实斗争不再是分离的。而这所谓的境界人们将其称为历史”(DeLillo, 1988: 165)。
话语对客体的塑形内在是一种暴力性的构序(韦宇婷,2021:50)。话语对历史的构建本身就是权力的扩张,人们常常将话语和权力放在一起称作“话语权”。就此,福柯首先对传统编年史里的话语单位提出了质疑,因为在他看来,话语单位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介绍了“忧郁症”定义的历史转变,从16世纪“并不损害理智整体”(Foucault,1965:118)到17世纪将忧郁症的归结为“忧郁气质”(Foucault,1965:118)再到18世纪詹姆斯在《医学大辞典》中首次提出“大脑功能的紊乱是这类疾病的根本原因”(Foucault,1965:123)……由此看来,不同时代相同的话语单位不能替换理解,运用到历史话语单位上,可能就会犯下类似刻舟求剑的错误。因此,面对卷帙浩繁的档案,不管是具有强烈指涉性的布兰奇还是作者德里罗本人,都不否认历史无法被真实还原的命题。
三.文本构建中的叙事霸权
“故事当中还有故事,法官大人”(DeLillo,1988:296)——这是奥斯瓦尔德的母亲玛格丽特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她表示自己无法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为刺杀案盖棺定论,她需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甚至需要写一本书来向观众介绍奥斯瓦尔德的一生。面对案宗之中的不实之词,以及秘密警察偷拿文件的行为,她说自己感到愤慨、无奈又好笑。戴维·费里,负责联络奥斯瓦尔德的前东航高级飞行员,也有着类似的论调,他深信肯尼迪在和卡斯特罗正在秘密通话,猪湾入侵的失败是因为肯尼迪故意的不作为,而“历史正是他们背着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总和”(DeLillo,1988:213)。
福柯认为,传统史学并非在用历史构建历史,而是动用人的意志筛选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的认识的规律(韦宇婷,2021:47)。启蒙运动为人类历史带来理性主义,更为历史的书写树立了标准:历史的编撰要合乎逻辑,表达理性,足够客观并且要顺应“进步发展”的大纲。与西方传统史学家不同,福柯认为线性的进步史观本身就在否定其客观性,只是沿着理性主义预设的方向对历史进行铺设,这是一项浩大的欺骗工程,最终呈现为宏大叙事的霸权。美国带着“应许之地”“山巅之城”的荣耀,从英属殖民地到国家独立,从南北战争到美苏争霸,似乎应验了进步史观的卜卦,但实际上无数历史片段被宏大叙事的网筛遗漏,沦落为民间野史,直至无从考察。奥斯瓦尔德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人物,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在他身上没有稳定的特质。他既有严重的阅读障碍,又熟读各种社会主义文献;在青年时期,他既狂热的迷恋马克思,又毫不犹豫地加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既蔑视国内盛行的消费主义,又无法忍受俄国物资的贫瘠;右翼的艾德温·沃克将军是他的死敌,被怀疑与卡斯特罗暗中勾结的肯尼迪却也得吃他的子弹。这些曲折的心理,连同奥斯瓦尔德的日记、生活过的街区,参加过的战斗一起被历史抹去了痕迹。与宏大叙事那样的“大历史”相比,“小历史”拥抱历史问题,将目光投向边缘领域的边缘人物,暴露历史的断层和偶发事件,天然地抵制克罗齐所阐述的“语文性历史”,是对兰克倡导的实证主义的偏离和突破。
故事当中还有故事,历史当中还有历史。原本不起眼的小人物奥斯瓦尔德站在天平的一侧,打破了美国社会在冷战局势下辛苦维持的社会平衡,在沃伦报告中成为枪杀总统的犯人。大历史和小历史此刻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当人们刚才震惊与悲痛中缓过神来的时候,却诧异的发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的运作竟然如此简单,各种阴谋论喧嚣尘上,其根源是对大历史的怀疑。小历史的语焉不详不单是刻意遗漏的结果,在1942年,西方哲学家亨佩尔(Carl G.Hempel)提出覆盖定律(Covering Law)。他认为一切突发的、偏离轨道的历史事件,只有在被纳入普遍规律之后,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覆盖定律下,小历史成为自然科学因果分析模式的牺牲品。小历史亦或被遗忘,亦或被宏大的理论拽进历史的旋涡难以自表(Hempel,1942:245)。显然德里罗拒绝掉进叙述的陷阱,脱离小历史,历史就会不接地气,如同空中楼阁,规格庞大但根基不稳,使人目眩眼花不知所云。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书中,将批判定义为“一种我们自身的历史的本体论”(Foucault,1988:136)而要批判的对象不仅是话语和档案,也是人的思想。无独有偶,德里罗的《天秤星座》在R.G.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定义下也更像是一部思想史,因为他认为理解并重新演绎历史人物的思想才是把握历史的前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Collingwood, 1946: 303)。从这个角度来说,德里罗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操作手段。
四、刺杀者与秩序解构
“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滩上的一张笑脸”(福柯,2016:392),这是福柯在其代表作《词与物》的结尾对人类前途和未来世界做出的预判。在《天秤星座》中,各种角色在一系列的阴谋与计算中、在对构建秩序的盲目崇拜里,一步步地丧失其主体性。福柯讽刺人类为构建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即反对世界的有序化。尼采的“上帝已死”,为“超人学说”腾出地盘,但福柯,尽管声称自己是坚定的尼采主义者,却更向前一步,表示“人也已经死了”。福柯的这番论断与其说是一种事实判断,更像是将人从世界中心位置拽下来的企盼。《词与物》的中心话题就是“人为何让自己成为了研究的对象,世界的中心”,福柯的答案是人通过语言、知识和理性为世间万物确立分类原则,孜孜不倦地为物制定秩序,使相异者趋同,驱赶“非理性”使其登上“愚人船”。然而现实却是,世界没有先天的顺序,真正的历史是让事件凸显出来,打断精心美化过的流畅度,暴露历史的断层和缺口,展现异质和疯癫的存在。
如果说奥斯瓦尔德试图刺杀沃克将军是完全的政治行径,是由于针对卡斯特罗的立场不同,那么他对于肯尼迪的敌意就显得更为复杂些,是政治之外的因素,甚至是“历史之外”的因素——比如梦,甚至是星座的运动或形象,这也是这本书被称为天秤座的原因之一。二十四年来他一直感到愤怒和沮丧,加上车队会经过他工作的大楼这一巨大巧合,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奥斯瓦尔德最后的刺杀行为(DeCurtis,1988:50)。如此一来,这一事件的“本源”似乎就无从谈起,更无法套用类似“政治分歧”“经济衰退”“阶级矛盾”这样看上去合乎逻辑的解释模板。
福柯后期对现代性的批判逐渐从知识转移到了权力,研究视角也从知识考古学转移到了尼采开创的谱系学。谱系学是对形而上学的史学传统的彻底批判,是对追求历史“本源”的放弃。“本源”在谱系学中被“出现”和“来源”代替,力图击碎单线条的起源观,因为一个事物可能有多个“前项”,也可能有多个“后项”(高德胜,2013:254),前项与后项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在时间上往往是共存的,有时前项的生命甚至要超过后项。因此,与本源相比,“出现”和“来源”能更好地标记谱系学的对象。而真正的历史颠倒了事件的爆发与连续的必然性之间的通常的确立的联系。“考古学所要描述的,不是井然有序、浑融无间的统一状态,而是离散状态的话语空间”(郑鹏,2012: 131)。当权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通过话语分散在关系网络之中,史学家无权决定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是重要的,因为事实并不等同于事实判断,但史学家却往往倒果为因,在掌握话语权之后编纂“知识”。奥斯瓦尔德在年轻时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不同社会制度的论证让他陷入迷茫和痛苦。局促狭窄房间里的电视传来美国对其国民的承诺——美国民众将生活在巨大的物质进步中。现实和理想的落差下,人们开始追问宏观叙事的开端,是盲目的自信还是精巧的骗局?历史的种种插曲是否就应被当作无法理解的东西被忽略掉?谱系学家就是要去追问历史的意外与巧合,打探隐秘的失败和未曾预料的成功,过问传统编年史无人关心的注释,但不去人为的串联因果,或者暗示历史背景的影响,这样的工作必然是枯燥但道德的。埃弗雷特和布兰奇构建叙事中的失败,暗示对特定事件的控制和了解从来都不是绝对的(Thomas,1997:124)。在一段偶发的历史中,奥斯瓦尔德并不是刺杀事件的象征性人物,他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相反,他成为了可能性的模板(Rankin,2019: 157)。随着密谋者推进刺杀肯尼迪的计划,奥斯瓦尔德的角色变得清晰:“‘如果奥斯瓦尔德不合作怎么办?’‘我们制造自己的奥斯瓦尔德。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354)。
五、结语
面对历史,尼采问道:是谁在说话?福柯也说:面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时,他有什么权力强加自己的偏好(朱梦成,2021:51)。对于官方历史的质疑从现代主义开始就已经存在,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官方叙事的怀疑更加深入和广泛(Stamenković, 2019: 143)。《天秤星座》作为一部编史性元小说,既因为小说的题材规避了这种诘难,也因元小说固有的指涉性特征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谦虚地贡献了自己的版本。小说通过一次政治危机敬告读者现实世界没有先天的秩序,偷袭,疾病和战争会经常光顾人类历史,人的优越性也将在一次次灾难中被彻底抹去,人应走下自己搭建的神坛,走出对自我的凝视。大历史和小历史享有同样的地位,历史中心的人物也不应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正如天秤两端的砝码,一旦失衡,就会打破历史貌似稳定的幻象。对于已发生的事件,没有真相,只有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