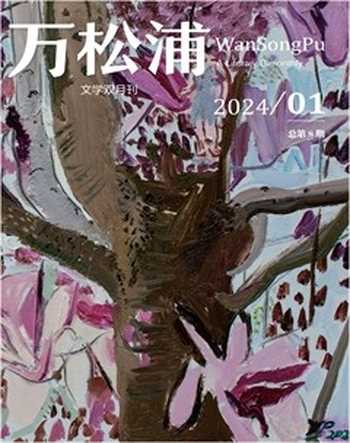沉默是最高的表达(组诗)
走进山林
脱下文明的外衣
向着树木走去,向着突兀的石头走去
与草丛里的蚂蚱、蟋蟀平起平坐
在蜗牛缓慢移动的屋顶上跳高
舔舐即将滴下的柔软的露珠
我的腰肢因此纤细
手脚像风一样灵活
山林间遇见一群自由的野猪
它们对我的造访颇为好奇
远远地将我打量
而后轻甩着尾巴悠哉离去
也许它们把我当成一棵竹子
不会因风吹草动而影响心情
我想追上前去请教出路
并打听泉水的秘密
翻过一个山头
只见被惊扰的蜥蜴
一只一只,闪电般一晃
不见了踪影
种菜的和尚
山后几间小屋,门全部敞开
迟迟不见主人前来迎接
听说种菜的是个和尚
已有八十多岁
鹤发童颜
每天从几十米外的河里
挑水浇菜
踌躇之间
一只瘦弱的小狗走来
像礼貌的酒店门童
善意地透知我的来意
扭过头看向远方
那是一片深不可测的菜地
远远望去
像一个幽深的梦
鹭
香山教寺的湖心船
常常栖息着几只白鹭
它们静静地守护着九月的黄昏
一次又一次经过
总也忍不住驻足凝视
很想知道它们对世界的看法
它们与船融为一体
也是整个静止的湖面
生动的开关
鹭有时是白色的,有时是灰色的
每次停留
都觉得自己白了一点
或者灰了一点
放生池
灰色的团云向天边逃逸
鱼群从湖底泛起,一轉身
甩出越来越清晰的人间
蝴蝶轻轻叼着花粉
鱼鳞捧着夕阳的余金
虔诚的山楂树双手合十
沿着山梯倒影
将流泪的白云抱在怀中
莲花耸动,像消失的空气宁静
飓风像个孩子,涌入花蕊
大干世界藏在每一滴水中
倒置的山顶镀着金边
天越来越黑了
远去的雨使竹林更加鲜活
随手撇下的食物
令鱼唇开花
一口一口将池水咬皱
原本平整的湖面
布满了坑坑洼洼,发亮的吻痕
随后又被夜色抚平
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依旧沉默
仿佛一个无法老去的梦
遗弃的夜晚
夜色灌满了山前
石头间每一道缝隙
唯独还未完全到达这里
静谧的山里
亮着一盏小灯
我知道它依然在等待
等待无疑是人生重要的事情
这个房间孤零零地醒着
骄傲地守在这遗忘之地
他也在等待着
天亮一定能看到蔷薇
花香已经冲破夜幕封锁
送来了宝贵的消息
黑色的雨被小灯
昏昏地照成金色的珠帘
必将洗亮
平静而又明亮的指尖
山中小草
风用巴掌将小草扇弯了腰
又被月光的手掌扶起来
它的呻吟比白云低
眼睛比夜晚还要黑
它们卑微地爱着土地
点缀着山的衣襟
从来没有
作为大山之子
该有的骄傲
头顶滚动夏雨,雷鸣
它们压制着身体里的猛兽
是的,即便是小草
也有表达的欲望
短暂的一生被生活无视
当本分活着都成为奢望
无声的不满汇聚成飓风
堵住黑色刻薄的嘴唇
溪哥
鱼竿不能阻止的教训
雷声也不能
钓钩沉下就要迅速扬起
在天空划过一道弧线
像蛰伏的蜂子列队而出
成为桶中一种实际的存在
雨点砸开溪面,露出
事物的本质
又被溪水覆盖
仿佛重复发生的前车之鉴
已被时间所遗忘
我看到的不是诗意不是远方
饵料中细小的铁
明明知道却又故作失明
自由自在的“溪哥”
只因善于忘记灾难
变成雨中一只只飞翔的银梭
虚无的死亡
气性很大的鱼
选择憋气而死
只愿意做溪中的君子
不做敌人的囚犯
也许它认为那叫气节
吞下泡泡不吐
翻起白色肚皮
决不让布下落网的人遂愿
不知死亡能带来什么
——除了决绝的宣誓
我无法诠释这样的道德
对于恶劣的天气有什么意义
但我将一切看得很重
只要都能拒绝诱惑
族群也不会有灭顶之灾
山中茅屋
石蹊小道在山腰間
缀成整齐的盘扣
常在夕阳周身逡巡
眼望苍天
凝固成虔诚的烛台
取来山泉洗净脸颊
用竹林拭净身体的欲念
云霞变幻
像日出一样平常
在蝉声中稳稳安睡
顽石
厌倦了交际场的喧嚣
躲在山中,活成一块石头
与鸟对话,离白云更近
不知不觉听懂了泉水的冷冽
追求成为令人膜拜的石像
最后回归诗心
变成不通人情的顽石
风吹不动,雨也无法使其漂浮
落日
山寺像情人一样寂寞
野花如思念灿烂开放
追寻落日的人
始终牵挂着朝霞
褪去光环的人生
用黑夜洗心
拾得一粒粒微笑
在河边激起串串水漂
石壁
每一次醒来
天空都亮了三分
名利如云
不如石壁上深深的苔痕
天鹅的羽毛脱离了肉体
却获得了自由的新生
就如这人迹罕至的秘处
不知什么是心病
忘记,再想起此身
高僧原是梦中人
蜗牛
弱小的生命也有影子
沉重的背负分明前世吾身
何妨放下一切
像一头真正的耕牛
一头撞破万里云
等雨
天上遗落的镜子
染上世间一粒灰
擦拭反而愈发模糊
何时才能不再苦涩
只待细细山雨
冲销沾染的
百年烟尘
经霜的季节里想你
诵经的声音剥下十月层层枯皮儿
露出清凉而富有弹性的小脸
凝霜的屋顶被浪子般的阳光
温柔地褪下娇羞的白色衣衫
只有我知道,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藏着一个小小的你
我不能做出想你的姿态
就怕
想你的时候
日子就变短了
以至于来不及告别
山下一块墓碑
横溪村的流水洗刷青黑色石头
布满青苔的生平渐渐显示
修桥、铺路、助学
人的一生压缩成几行文字
见证着一个家族曾经的富裕
浓缩的中国式道德
在冰凉的石头上静静地躺着
也许墓碑主人也曾有过烦恼
也有屈辱和愤懑
但被立碑者取舍后
只留下温情和善良
不管做过什么
每个人都将面对同样的结局
不管风光还是卑微
都会在结束的时刻
低于一坏黄土
或只在一块石头上
留下淡淡的痕迹
当然,也有人“活过”一生
只是“活着”
连一块墓碑都不会有
就像溪水中透明的虾米
清风吹拂竹林
未曾泛起一个涟漪
问山
在这不断寻找归宿的世上
谁能长生不老
为何总是想着千年以后的事情
一片热血都付与光阴
最终逃不脱时间的刑期
不如放下吧
听一听竹林在耳边私语
比情人的呼吸还要甜蜜
让我静下来的是壮阔
壮阔是最高的沉默
我为何来到这里?
每到来一次,我都忘记一次
归田园居
双脚蹚堂开起起伏伏的霞光
晨露纷纷在草尖上蹦极
喧闹一夜的蚂蚱
忽然懂得光阴珍贵
告别昨日月亮
如同告别曾经的光辉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锄头翻开松软而又湿润的歌谣
交响着潺潺流淌的溪声
被我一并种进泥土
辣椒与南瓜孕育丰收的九月
此刻乔装打扮
让篱笆有了该有的样子
铁器与木器
展示真实之最
它们不会嫉妒也不屑谎言
只要给予充分信任
即便腐了朽了
木柄都会发出新芽
饮酒
有时候
蔷薇都含着酒的精魂
鼻尖一旦靠近
会引发轰然的醉意
有时候,放下所有
会突然找回真正的自己
竹林外的湖水
每一层波纹都藏着生活的本真
水能载情,山可藏真
懂酒的人只会被云霞醉倒
回归自然
满头白霜也会随风悄然而逝
变成纯真可爱的孩子
当你深入理解了归隐的陶渊明
就会明白
一滴酒如何重新变成长长的麦穗
一段情怎样随徐徐清风回归初见
南山上的石头像面镜子
一次次逼真照见那些迷失的过往
(王长征,诗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