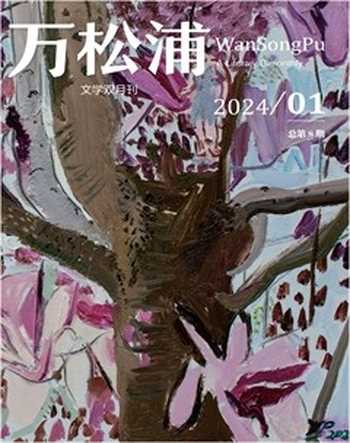上昆仑(组诗)
上昆仑
唯有,被历史冷白过头的山峰
才配称昆仑
唯有,凝聚万里
不再寻求高蹈的群山
才配得上昆仑
高蹈本是万山西行的步履
是史书中,蛰伏至今的
一阵罡风
传说叠成的纸船。在大地上
用方块字,堆积在一起
我从未见过如此浩渺的
白色的帆
在号令万物,包括春天
唯有,给山川重新命名的山
才配称着昆仑
在平处撑帐篷,放牧那些
唤不出名字的花朵
昆仑是一顶时间的毡
用没有颜色的风,裹成的
帽子
我用渺小,浩渺的渺
在地上画出日月的光芒
禾口寒鸦
我咳嗽一声,就掉一个旧体字
写的
仰望
拖着患病的群山,上昆仑啊
唯有昆仑,才能用过去
给我
指未来
夜宿苍溪读陆游《梦至苍溪》
先生,高速路的药片,让利润
的想法,一多,再多
至此境,我方恍然
饮涨价油的汽车与我,会不会
是先生,和那头骑着的驴
遗在江畔的残梦
江火似白话诗,如街边的
烧烤摊
一收,便关灯
终敌不过淹死过月的,水深
江面泊满我扶不起的高楼
的倒影
似自助餐里的鱼头,一般的
口形
越统一,越没有宋词的味道
像是同质化的新诗坛,猿啼
与月落
穿一样的制服
胭脂的名字,皆似外邦
好在县名里的苍
与酒店门口,刻的先生的
诗
还有点古风,只是
吹也不对
不吹也不对
先生,我只有独行至江边
摸着
摸不到的黑
读你的诗
因为,苍溪那么多
写白话文的兄弟
都去了异乡
先生,你的梦在诗里
是一面镜子
即便碎了
每一片都应该藏有真相,比如
回家的小哥,是不是
正在快递自己
新面壁
新修的寺庙,都是劫后的古树
结出的果实
来的,未必是来生,蚂蚁
在地上拼命
写黑字
火烧过的时间,趴在木柱上
用化学的漆
和普通话的佛号,缠在一起
一个,不放过一个
山深至寺院,便无路可去
像是噙着佛号飞走的鸟
刨根的人,一茬一茬,不过是
刨自己的先前
桂花
攥著西药片的老人,拼命地
掩盖寺庙的气味
长椅上斑鸠的跳跃太累
与现今的
汽车数目相似
狗只吃机制的盒装狗粮时
桂花落在老人肩上
秋天是一笼硕大的肺炎
被桂花的小火星薰着
孪生的气味,一个在宋
一个在视频中坠落
我和斑鸠坐过的长椅
都是等声响的
小注脚
汽车的籽,驶出小区的皮壳
大风在垃圾场,填埋
废旧汽车的
种子
我在桂花香翌年的春天下
等种子
老人和药味的真相一起飘
兔子在飞
寺庙再新,既是现实
也有未来
摘苹果的妇人
苹果园上方的那块天凉了,苹果
就不再长了
装着苹果的拖拉机走远了
像是把那块天也运走了
在路边,头越低的玉米
叶子越干
与光缆上的喜鹊们一道
用沉默,把时间还给了大地
此时,天空即使晴朗
我们的注视,也是无比的虚伪
印刷术
飞机在控制天空,成为青鸟
信件上标注清晰的叛徒
晴空岂止万里
照排的年纪越少
文字的身躯,堆积越高
把飞机想象成一支笔在天空上
的书写
是一种复辟
那么,我们便是它排出的蛋
依次排着,重生,并且单纯
术不是一只中性的鸟
活字与否
印出来都黑得一塌糊涂
即便捅破
也不会成为繁星
字越来越简化,多年前的
拣字工
从历史教材的排版车间的
窗户望出去
飞机像一枚铅字的牙
正在寻找自己说过的错别字
它们将相互指责
油松
抬着云朵棺木去墓地的油松说
不要讲话
你们昨晚已经死了
护林的飞机正在与斑鸠谈判
可是,葬礼比死亡本身
还令人
窒息
还好,即使冬天死去,我随身
携带的
生长过的万物,树一样,还
剩有骨架
油松,依旧用针,救治你们的
遗言
坐在高铁对面的坡上
整个下午,阳台上的我
与眼前的高铁,始终
隔着一只乌鸦的聒噪
茶水在杯中吓得发抖
移来的紫荆
也是坡上曾经的亲人
高铁的口号
把满山喊成空洞,不断来回
直至茶残
夕阳,许是救治过大地的
丹丸
乌鸦是好乌鸦,只是声音的
铁棍
把树枝们长出的天空
搅黑了
出伏
俗世中的白鹭,被凉风一刀
再繁华的秋天,满是死亡的
笔画
江河的胆,越来越小
岸上不停加秋衫的我,像是
孤悬的小魂魄,抑郁
且强迫自己喝时间的大药
河在蜕皮,碳排放把地球吹得
比哀愁还大
古人用农耕把时间种得再长
词牌的叶子,如今
也是出伏即黄,由不得我
就像白鹭羽毛的匕首,一抖
工业过的大地便满是伤痕
包括,我的年岁
和匕首自己
立雪亭前
怀揣的雪,用于时间转折时
掩盖真相的布景
可以断臂的风,在试探虚无的
深浅,飞出一只鸟
风就呕吐一次
可是山峦的胃,依旧似夕阳
光辉且没落
血点化过的亭子,被风
吹成老痂
战火揭一次,历史就假装
阵痛一下
直到把高处的飞机,痛成
一只失明的大鸟
立雪亭前,我尚不知自己是
站着的风
躺着的痂
抑或,僧人慧可
臂上流出的最后一滴血
乘车来的我,不敢乱想,只是
寻不见那断臂刀
公元1573,酒曲
帝国硕大的木船,在余晖中
边璀璨
边与独眼的夕阳,谈羽化
夕阳在江面漂
高梁在坡上红
我在漆黑的江边生火,煮饭
想着救活一首断气的歌
红嘴鸥,给河山配放大镜
给1573的明朝找窖池
鸥说,时间万不可流浪
否则,会窒息在历史的瓮中
大浪即使没淘尽我等,也是
仅余一片酒帆而已
饮过酒的江鸥,把夕阳衔成
一粒紅高梁
既然流水怀孕,不如让她
在泸州,生产永世的酒名
帝国云散,高梁幻化成曲
酒一淋
便是水上漂的我,小声
哼出的酒曲
落叶
金黄的落叶,像是一片片
来不及逃走的阳光
被风,驱赶到楼房南面的
角落
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
抗生素一滴一滴地
流进血管,躯体像是银幕
自带观众
死因需要越来越多的表述
爱越来越单薄,如同
我们再三肯定水
却无法说出它的来历
汛期
汛期来临
走在前面的水像是天空的树
坠落的口号
碾压机相互吞食
直到庞大成瘫软的胃口
轰隆隆的水既是钢铁
又是末途,可是
我不敢说出这水要像人一样
会死
(龚学敏,诗人,现居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