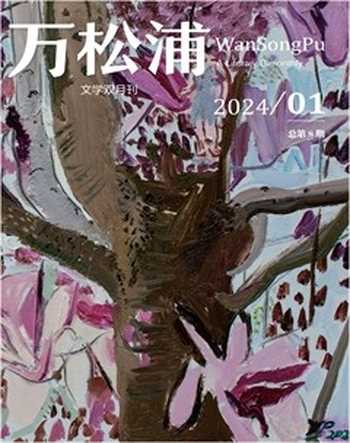谁曾回到过故乡
1
落地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自以为纸上熟悉的凤凰城到底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幸好向导小麻安排好了行程。见我急着先要去沈先生的故居,她又说:“很少有人去沱江下游看看沈先生的墓地。”她看出了我是有这种访旧心思的人——在她努力介绍一座古城诸多迷人细节的时候,我只说是为了一个人的故居而来。看来她也是懂得一些深情的,并非只是把此行当作看外人面色行事的工作。
她又像是写一篇文章般荡开一笔,开车带我去了大山深处的苗寨。这让人感觉很有意味,使我想到前人写文章时花大片的文字去铺陈,末尾似乎也不十分关心所谓目的。乡人汪曾祺的《受戒》就是这样子的。之所以在湘西一定会想到他,是因为我自益阳辗转凤凰,正是因为沈先生是他的先生。我们不像那辈古人那么深情和执着,眼下凡事都要想好了目的或者意义,所以我们的生活和文章总不能那么意蕴恒长。高速的办法让空间不再是阻碍,但时间又总会是借口。所以我们也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過许多种类的酒,却难以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
一路上的崇山峻岭被抛在身后,赶路的时候把日色都忘记了。人们总是按照时间刻度去生活是糟糕的态度,按照日色的黑白其实最为妥当,就不会无端地被束缚或者截断。溪水边钓鱼的人,脸上有自得其乐的快活。他如果抬起头,就可以看见南方的长城巍然屹立。可是这种对我而言闻所未闻的景观就在他们的日常里,比一棵草木还要稀松平常。那些游历经过的鱼才是他们想要的风景。我也是一条赶路的鱼,可是我不在水里,也进不了他们日色一样平和从容的目光。那些水清澈而纯净,没有一点点世故可言。鱼在水中遁藏或者赶路,偶然成为人们钩上的惊喜。流水常给人一种悲伤的意境。我暗暗记下这里的名字:廖家寨。这里的山距离凤凰城不远,我把它想象成沈先生的茶峒。对于一个平原上的赶路人而言,这里有着无尽的陌生和孤独。
我来寻沈先生的山水,是一个冒失的不速之客。这年的清明,我蜗居在城市之中的日子里,也曾去寻他学生汪曾祺的墓。城市里没有山水的阻隔,只是红绿灯所构成时间上的路障。我刻意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打听具体细节,只在网络上找到了地点,并且用导航计算出精确的到达时间:四十二分钟。虚无的网络也有点无中生有的诗意。汪先生当年出走高邮老家,恰好四十二年没有再回故里。京郊的福田公墓里到处都是鲜花。他的墓前有先来者奉上的浓茶。没有一朵花不会凋零,烟酒茶一生所好的心意,才更会被永远铭记。当年他是从高邮辗转上海等多地到昆明见到了沈先生,选了他所有的课程。在此之前,他在小城里就知道这位先生:“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
他赶这一路千山万水见到沈先生,是得了一生的福气。
暮色侵袭而来,两面群山下的稻田里草木丰盛,水稻已经长出了一些气势。平原上的这个季节麦子才黄,秧苗还在等着布谷鸟的叫声远去才能去投诚水土。这算不算也是赶路的前人,在等自己的后生一程呢?汽车还是赶不过夕阳的急性子。进城的时候已经灯火辉煌。实景剧《边城》开演的消息提醒声在手机里不断地响起,但我仍然决意先去先生的墓地。川流不息的人海之中,没有人理解有一个访客一定要走到沱江下游拜谒的心念。小麻并不催促我,只按照我的心意在不断地赶路。丢掉汽车从此岸下得坡去,沱江的水孕育起一些寒凉的氛围——它们也是懂得抒情的。流水如时间一样匆匆地过去,横渡江水的脚步声,就是一篇文章的高潮迭起。在汪曾祺生活过的平原上,这样的河无法有江的称谓。但这一天的匆匆赶到,让繁华的沱江在我心里有着无尽的辽阔。
到达彼岸拾级而上,走过据说暗含先生年岁的数十坡台阶,葱茏的草木和虚浮的灯光里安卧着一块静默的石头。先生比他的学生要多一点叶落归根的心安。他像一颗流浪的石头回到了沱江边的故土。远远的歌声绵延而来,被演绎的《边城》中的翠翠着了盛装,在江面清风中翩翩起舞,我背对着流水就像罔顾时光远去的事实,在一块石头前面诚心跪下,用自己家乡的办法认真磕了四个头。清明的时候,我在福田公墓也是这样表达敬意的。汪曾祺的墓碑上写上了故乡的名字,可是他没有能再回到家乡。沈先生的石碑上只有一些他生前喜欢的句子,无须再刻名讳和籍贯,也能说明他是从这里出发的孩子。他已经从出走时就把一切交给了山河,这里是他一生最美的边城。
《边城》的剧目在群山之中上演,它不用等一个迟到的赶路人,它也要像江水一样赶路。旖旎的灯光里,那个熟悉的故事在无数华美的服饰和词语中被反复演绎。在苗家人祭祀的盛大场景中,我起身离开了比现实更伤感的故事,我知道天保和傩送注定不再归来。一个人的离开不该被一次次地提起,也许忘记才是最恰当的记忆。无名的山川或者确切的文字,对于一个想着归家的游子而言,不会有任何的慰藉可言。可是他们一生注定因流浪而留下英名。
他们的一生都在脚下的路上奔走。一个十四岁离开家乡从戎,一个十七岁奔赴云南求学。沈先生说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是对一个总在赶路的人而言,谁又曾回到过故乡?
2
我在见到小麻之前,本是打算自己走一趟凤凰城的。我误以为有这点自以为是的本事,但我并没有把《边城》读透。从磁悬浮的列车上被放逐,双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我就像是失去了磁场护佑般慌张无助。汗水随着疑虑的脚步奔袭而来。路边林立的湘菜馆,没有办法解释我饥饿的疑虑。最后在一家空荡的餐厅前停下,琢磨着这样可以不用暴露自己无助的难堪。大姐用朴实的方言问我点菜。我慌张地在纸上指了两样:笋炒腊肉、血粑鸭。转而又想到主食,好在平原和湘西一样都吃米饭的。我们那里的人走得再远,见再多美食在眼前,倘没有一碗米饭,心里是难以踏实的。吃饱的人才不容易想起家乡。不知道湘西人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情绪。
腊肉是见过的,饱含着十足的烟火味。黝黑的光阴痕迹包裹着清亮肉片的条分缕析。人们是用时光把时光腌制起来。平原上也有类似的方法,但只用粗鄙的海盐,形成不了表面那些庄重的形式。盐就像是一种隐喻,而烟火是直抒胸臆。这是不同人们的想法,但都是为了抵消时光的腐蚀。就如写字也是为了抵抗时光,但不同的人用各自的办法。素白的笋,青绿的蒜,与腊肉的烟火在一起生长,可以想象出灶上热烈火苗上的跳动。其时师傅的手一定是焦躁的。我抵达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刻,莽撞的到来扰了他片刻的消闲。蒜还没有断生,油水裹挟着生分,这样对待一个突然的造访者也恰当。肉内里满是烟火味,肥而不腻的肉白更清口,可以调和瘦肉吸附过分古怪的气息。山水不同脾性,一道菜中自有线索。这是道下饭的菜。大姐上了一盆饭,这是合乎我心意的。我们上桌只说吃饭,可见菜才是配角。形式多样的配角就像繁复的修辞,最终却似乎只为一口饭。这时候应该独饮一杯,但酒也是煽情的配角,一口饱腹的饭才是正题。但那些形式和过程是生活与表达的策略。直奔主题的事情会显得唐突莽撞。所以要说很多话或者起很多心思,这些“顾左右”的铺垫,终为了一句想说也可以不明说的话。
平原的锅台上常见咸肉。会做饭的汪曾祺却讲了南方的做法:鲜肉与咸肉同烧。这大概是他在沪上的见识。这个城市对他无有太多美感可言,也许就剩下一个食客眼里的味道可堪敷衍记忆。这种做法也不是沪上人的创造。他们嘴上言语里瞧不上的江北,其实多是自己的祖籍,许多味道正是从记忆里过江南下的。江南人用酱,也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办法。那很有些腊肉熏制的形色,但缺少烟熏火燎的深刻。烟是火的最后一口气。人们舍不得它变成轻浮虚幻的炊烟袅袅,便把它留在生活的肉身之上。美感又多从异味而来,这是各种不同血性人的无奈创造。无奈有时候是独特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夸夸其谈的慧心。咸肉的做法多矣,炒是最爽利的形式。湘人用竹笋炒食是靠山吃山,平原用慈姑相佐是靠水吃水。慈姑肉片也会配青蒜叶。咸肉和慈姑片长成的时候,也正是青蒜最好的时节。这道菜是等节令的,要有寒冷的气候配合演绎。开了春一切都會变味。这一点不如腊肉沉默坚忍的脾性。所以汪曾祺和沈先生比起来,少一些决断与坚忍。当年在沪上形势艰难到要自断性命,沈先生写信给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地,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湘人嗜鸭,不知道这是什么缘由。鸭子要靠水。旱鸭子据说有古怪的狐臭味。人也要靠水。水尤其给写字的人许多福荫。水上有云彩一样变化的纹。鸭子也是水上的波纹,是沱江或者大运河的波纹。血粑鸭有种血腥的壮烈。湘人有自己秘密而独到的想法。血与糯的融合就像是一场奔赴,在黏腻中穿插了杀伐与果断。鸭肉和青红椒成了配角,蕴藉的血粑给味觉以足够的安慰。这同样是一道下饭的菜。下酒菜多只是酒的臣子,下饭菜才有米面一样熬饿的主见。就像是一名战士,只有充满自我的血性才能刚毅决断。小麻后来给我讲了个血粑鸭的故事。说某年沈先生卧病不起在家中,医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门前站了位道士问口饭食,桌上问先生的母亲家中是不是有人被灾病所扰。主人遂如实相告。道士告以偏方:以鸭血与糯米制粑共鸭肉同炒可治其病。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念想。我以为血粑鸭是一种更古老的办法。沈先生一定早早就吃过这种菜食,才能生出那种远走他乡的血气和壮怀。此后无论走到哪里,连沉默也能显出坚毅。
运河边的人们也嗜鸭。汪曾祺的高邮由来是鸭乡。高邮鸭蛋是一个天然的词语,就像双黄蛋独有其妙。汪曾祺笑言与本乡的秦少游及双黄蛋齐名。麻鸭入爨方式多可单独成宴,尤以一碗清冽的鸭汤与河水一样明媚可喜。落在沸水里的鸭,比水上的鸭子更见情义。但这还不足以显得多情。做饭的人手上必须有深切的心思,这样形式单薄或繁复都可以表达情浓,不然食物就只剩下煮熟和充饥。就像是湘人血粑鸭的深切,乡人也有修辞丰富的办法,同样也取用暖情的糯米。八宝葫芦鸭味道在内里。鸭子是要吃粮食的。鲁莽的它们不像鹅简素,但自有血气方刚的特性。把肉身和粮食一起同做生出特别的意境,就像来处便是归途的隐喻。八宝葫芦鸭取整鸭去内脏,空腹中填八宝糯米饭,封口后居中扎成葫芦状,油煎后上锅蒸熟。这些都不仅仅是手艺,更像是生活里神秘的法术。
这些故土的方法何等美妙,只有游历他乡后才会懂得。汪曾祺是做饭的人,不过多是家乡菜见长。老家的菜能见出自己的来历和秉性,就像沈先生和汪曾祺都写水上的鸭子。血粑鸭是湘西人的热烈,葫芦鸭有平原上的蕴藉。这些意味在游子们的脸色上是分明的。汪曾祺自述小时候喝够了咸菜慈姑汤,似乎对这种苦味的土产已没有好感。但他去给沈先生和师母拜年,还是特意炒了一盘慈姑肉片——他心里到底还是觉得那些苦涩的物事可靠。沈先生吃了两片,对他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
他们都懂得水土的苦楚实诚可信,也都是流浪的慈姑。
3
我后来想想,未曾看完《边城》的演出就离场,是自己不够深情。那些歌声实在太美了,比翠翠身上的盛装更华丽。可我又不大相信翠翠会着那么艳丽的红,让眼前的山水显得妩媚而失真。我曾听过那些陌生山歌一样的故事,在无数个令人心悸的深夜里盘旋,至今依然令人心生疼痛。
我在村庄生活的日子里,除河流以外简直乏善可陈。后来河流确实也成了我的福地,虽然我又狠心地离开了它们。其时我躲在黑夜里不敢多言,以至我后来说过很多话,并写下很多字,都是为了忘记那些无边沉默的夜色。河水也不言语,静默地与时间对抗。广播是个无情的外人,它一遍遍地播着既定的节目。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迎来沉默的都是一部广播剧。我似乎从来没有完整地听过它的全部。有时是从梦中醒来听见老人的讲述,有时是在女主角呼唤中睡去,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女孩在渡口涛声中守着爷爷和黄狗。
我本不知道那涛声是茶峒江水里的。也是到了十数年之后的大学课文里,我才知道那些呼喊来自边城。此时我已经通过十年寒窗,经历像《受戒》里小明子和尚学徒般的生活,拿到了一生受戒的度牒,从此只能做一个守望与书写河流上一切的苦行僧。汪曾祺《受戒》的河流里是撑船的小英子。沈先生的翠翠也有一条船,靠着手中的横缆来往于彼此两岸。她大概没有过从上游到下游的经历,只死守着非此即彼的诺言在等待。小英子的船误入河水深处,起码问了小和尚一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日后在纸上看见小英子,她就像是一朵雪白的栀子花:“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小英子唱的歌里开的正是栀子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
不知道为什么,边城中或者平原的河流里,总是有这样动人的歌声。翠翠嘴里的歌声一直没有唱出来。茶峒的日子似乎到处都是歌声,但就是听不清一句歌词。也许正如故事里的大佬所讲:“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歌声不能当作饱腹的饭食,姣好的面容也和歌声一样虚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翠翠哪里是纤弱呢,她自是一只心里明亮的小兽。像那江里的水,深到一篙子不能落底,却仍然是清明透亮的,甚至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江上清风明月给她无边的澄澈,照彻着等待茶峒天保或者傩送远走后的日日夜夜。
所有的人都决意走了,从此也不再归来。小麻与我讲他们关于沈先生的传说:十五六岁的翠翠与爷爷一起守渡,无意间认识了在此过河的沈先生。懵懂年纪的翠翠唱了一首山歌打动他,此后他就每天来渡河,一来二去就生了感情。后来沈先生的母亲生病危在旦夕,想看到他结婚生子,就给其介绍了当地的阿妹完婚。五十年后,他又回到了湘西,回忆起当时和翠翠的点点滴滴。无意间又走到了翠翠家门前,看到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满脸皱纹。翠翠为了等他一直没有结婚。沈先生临走时,请工匠打造一件名为“凤回头”的拉丝工艺银器送给了翠翠……我宁愿相信这不是银匠人为兜售手艺而编织的故事。凤凰到茶峒有一百五十公里山水之远的阻隔,但我也相信江边一定有一位为他唱过山歌的女子,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等着他未知归期的“凤回头”。至于翠翠是真人还是虚构,抑或是张兆和、周铭洗或者高青子的化身,一切并不一定需要再被证实。如果非要追问,在一九四八年《边城》重版的“新题记”中,沈先生似乎已说得很清楚: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唯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稀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受戒》里的小英子,唤出了心里萌动的情绪,但也不知道最后水泊深处的荷花到底有没有结出带有苦心的莲子?小明子与河水都没有给出准信。许多年后,汪曾祺听老家人来信说被认为是小英子原型的大英子殁了,他回话说:“她去世了,我知道了,人老了。”汪曾祺当年一家避难在《受戒》里所讲的庵赵庄,认识了赵家的姑娘大英子。此后回城,大英子去汪家做过几年“大莲子”——这里人如此称呼女用人。汪曾祺的早年是有些佛缘的,这就为他日后写小明子等一众和尚生出了许多独特的意味。长辈们为了让幼年的汪曾祺更好地养活,给他在和尚庙、尼姑庵、道士观都记了名,还求取法名“海鳌”。为他求取法名的帖子,一直贴在父亲汪菊生的卧室中。一张高八寸、宽五寸的梅红纸,中间写着一行字: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左边一个“皈”字,右边一个“依”字。尽管汪曾祺在《受戒》的题目下写过一句“这个小和尚不是我”,但是文末的那一句“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可以看出他对那段日子和那些人的深情。
汪曾祺游走他乡后,大英子也常进城去看看汪家人。知道汪曾祺回过高邮,就有点责怪汪家:“曾祺回来怎么不告诉我?我们同龄,都属猴,他的生日我记得,我们都是有孙儿辈的人了,有五十多年不见面了。我还有他一张小照,下次曾祺回来一定要告诉我。”
下次是什么时候呢?下次,也只是一种梦境,翠翠或者小英子都是在无尽的等待中成为歌声的。离乡的人始终只能是一个过客,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而谁又能再回到等待他们的故乡?离开沱江的时候,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们都是这天涯海角的过客。心里又总有歌声在不断被唱起:我是远方外来客哟,今日來到凤凰城哟,不会唱歌莫拦我哎,让我进寨歇歇脚哟,哟喂!
(周荣池,作家,现居江苏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