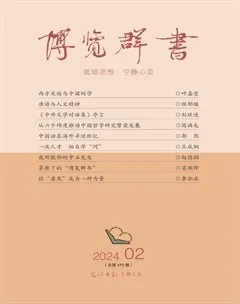流淌在《史记》长河中的文化初心
原昊
在中华优秀文化的长河中,《史记》是一部独具魅力的典籍,它被尊奉为“史家之绝唱”,是公认的史学瑰宝的典范,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它被称颂为“无韵之离骚”,对后世文学影响至深,备受韩愈、桐城派等古代散文名家推崇。从空间的角度观照,《史记》是一座高峰,太史公凭借悲情的人生经历、宏大的史学审视目光、高超的文献驾驭能力以及精湛的史学编纂笔法,使该书成为中华文化史中的一座巍峨山峰。从时间的角度观照,《史记》是一座时光长城,这座时光长城纵跨五千余年,可视为由两段组成,前一段是太史公所编纂的《太史公书》,书中记录了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三千余年历史,后一段则是《史记》成书之后经历的流传、补写、研究、考辨、点校、注释等两千余年的长久历程。在时空交融中,《史记》已不只是一部史学典籍,其整理及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史记》学”专学博然兴盛、长久不衰,其已然成了一条长河,而在这条长河中流淌的,是古往今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初心,赓续不断,历久弥新。
《史记》编纂中两代太史公的初心寄寓
《史记》是司马談、司马迁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典籍,其编纂初心源自司马谈,其编纂也肇始自司马谈。司马谈是西汉王朝的太史令,主司天文历法,兼管典籍档案,顾颉刚先生在《司马谈作史考》等文章中,通过细读《史记》文本,发现了司马谈的编纂痕迹,如《刺客列传》篇末“太史公曰”记载公孙季功等将荆轲之事告诉“余”,而公孙季功作为秦末汉初人,可知“余”为司马谈而非司马迁,《郦生陆贾列传》“平原君子与予善”、《樊郦滕灌列传》“余与他广通”等中的“予”“余”均为司马谈,由此可知,虽无法明辨司马谈编纂的具体篇章,但司马谈编纂《史记》并将遗稿传与司马迁,并嘱托儿子“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明言“父子相续纂其职”,足见承续的不仅是太史令的职官和父亲的史传遗稿,更是编纂完成史学巨著的文化初心。这份传承被司马氏后人所铭记,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直言“《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既肯定父子相继成书之说,其自身也为《史记》进行注释及订正工作,所撰《史记索隐》与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共同成为《史记》最为著名的“三家注”,传承了司马氏家族初心,也扎实推进了《史记》的发展。
明确了父子相继成书的说法,我们便可知晓作为《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中的太史公,实际上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而这里,读者容易对《史记》书名产生一个理解误区。《史记》的书名,粗略一瞥并按照惯常可理解为“历史的记载”或“历史的记录”,但这种常见的文言翻译及理解对《史记》书名来说过于宽泛,也容易造成理解的偏差,这一问题的迎刃而解需要从《史记》书名简化的过程谈起。在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最初编纂之时,该书被称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自序》),后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太史公》(见《汉书·艺文志》),再之后被简化为“太史记”(见《风俗通义·正失》),再后来,大约在东汉桓帝时,又缩减了一个字,称“史记”且通行,沿用至今。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史记》书名中的“史”是“太史”二字的缩写,而非“历史”二字的缩写,这是一个容易划过的基本问题。
古人拟想的司马迁的画像中,也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略微留心。其一,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牵连,遭受宫刑,正是这一刑罚之故,使得在古人拟想的司马迁的画像中,太史公没有蓄须,与我们惯常印象中长须髯髯的史官不尽相同。其二,在古人拟想的画像中,太史公身着“右衽”的衣服,这是典型的汉服,我们不禁想起《论语·宪问》篇中孔夫子评价管仲的话“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由此,我们有感,初心不仅存乎于内,也在服饰等方面现乎于外。
司马迁秉持着史家初心,在《太史公自序》中直言自己对于历史文献与口传故事的处理方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并在梳理史料、整齐故事方面展现出超凡的能力。金德建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梳理太史公所见之书,这种梳理不但有利于更加清晰掌握《史记》资料的来源,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成为《史记》的“艺文志”,有助于了解西汉图书存佚情况。此处略举一例,《史记》编纂过程中,司马迁参考了记载王侯士大夫世系的专书《世本》,而《世本》一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亡佚了,仅有清儒从《史记索隐》等汉唐文献辑出的《世本》文句,但我们无须过于遗憾,因为《世本》世系记载的主体已被司马迁采入《史记》之中,赵生群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太史公已将其(《世本》)资料系统吸收写进了《史记》。因此,《世本》实际上是名亡而实未亡。”而清儒所辑出的《世本》文句,还包含《史记》未采录或存在差异的说法,与《史记》等文献进行对读,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先秦两汉时期世系类图书的文献面貌。与绘声绘色的史传故事相比,《史记》一书在记述世系传承,多为套路式的记录,格式死板、言辞枯燥,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太史公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旨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为司马氏家族,至少是司马谈及司马迁父子,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甚至明言其“借史的形式”发表“一家之言”。而司马氏的观点,不仅集中体现在每篇“太史公曰”的史评段落中,也分散在史传的谋篇、人物的择取以及故事的筛选等细节之中。
《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每部分的第一篇,都寄寓着太史公独特的匠心。“本纪”的开篇《五帝本纪》,固然有“五帝时期”位列夏代之前的原因,但《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叙述起点,更是战国时期极为兴盛的黄帝大一统观念的客观呈现,且与司马谈崇尚黄老不无关系。故而太史公参考《世本》《五帝德》《帝系》等文献,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始,以《五帝本纪》为《史记》之始,这个思路也同样落实在“表”的开篇《三代世表》。“书”的开篇是《礼书》,学界对《礼书》是否为司马迁所作存在较大争议,但从《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想通过《礼书》探讨礼的古今之变,而今传本《史记·礼书》“太史公曰”前半部分倒是符合这样的思路,也与司马迁的笔法近似,也可以用存疑的态度阅读及使用。“世家”以《吴太伯世家》开篇,“列传”以《伯夷列传》开篇,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嘉伯之让”“让国饿死,天下称之”,赞颂吴太伯与季札、伯夷与叔齐的谦虚让位,特别是《伯夷列传》除了寥寥几笔夹叙伯夷、叔齐故事之外,主要篇幅都是司马迁抒发的颂赞及感慨。加之“本纪”开篇《五帝本纪》中的尧舜禅让故事,可见太史公十分赞赏“谦让”的政治道德,也让我们体会到《史记》布局谋篇的匠心独具以及潜藏其中的本真初心。
《史记》设立《孔子世家》,使孔子在“三十世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司马迁授业于孔子后裔孔安国有关,与司马迁曾前往孔子故里实地寻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人生境遇,使其对孔子的艰难与坚守有着强烈的共鸣,孔子达到极高的思想高度,其思想学说凝聚而成《论语》《春秋》,都让司马迁对《史记》寄寓极大期许,《孔子世家》末尾的“太史公曰”引述《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并旗帜鲜明地表达“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愿望,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司马迁也希望《史记》如《春秋》一般寓含褒贬,自己如孔子般,在礼崩乐坏的境况下,“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
《史记》设立《陈涉世家》,《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陈涉对暴秦的发难与商汤、周武对桀、纣发难相提并论,足见太史公对革除失政失德者、开创历史新局面者的推崇。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同样体现在《刺客列传》等篇章的创设以及荆轲等刺客形象的成功塑造。太史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而刺客拥有崇高理想,大义凛然甚至不惧牺牲,太史公欣赏“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报任安书》有言:“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所以《刺客列传》中“义不为二心”的豫让、《管晏列传》中管仲与鲍叔牙都成为讴歌的对象。太史公反对侵伐、反抗暴政,故而形象丰满、刻画细致的荆轲,正是在太史公强烈情感支配下,在参考《战国策·燕策三》等典籍并结合好友的详细口述基础上成功塑造出的形象。
司马迁父子重视血统,陈正宏先生察觉到《太史公自序》介绍三十篇世家的“叙录”,大约三分之二的总结里都有以‘嘉字开头的话语,展现出对血统的重视,“(司马迁)所‘嘉的,几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以历史学家的特有方式,向众人昭示,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还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向善的情感与道德”,这是中肯的结论。
《史记》整理研究中文献学家的初心传承
作为产生于西汉时期的古典文献,《史记》在流传过程中版本情况复杂,正文、注文没有句读,更谈不上现代标点,这不利于珍贵史学遗产的阅读及使用。20世纪50年代,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国家启动“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出版工作,由以出版见长的中华书局牵头组织,大批专家学者为珍贵史学遗产的点校整理凝心聚力、鞠躬尽瘁。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点校本,于1959年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之第一种出版,该书由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等先生承担点校和编辑、审读,此外还聚集了叶圣陶、王伯祥等大批学者的智慧,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从《史记》点校本《出版说明》《点校后记》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所收《整理史记计划》《史记校点说明》《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以及顾颉刚、宋云彬、王伯祥等先生的日记之中,前辈学者在《史记》点校整理全过程中的辛勤付出清晰得见。太史公父子纂修史书的文化初心,在《史记》点校整理工作中得以传承。
为弥补“二十四史”点校本存在的标点偏差、排印错误以及校勘缺失等缺憾,并更好吸纳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国家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史记》点校本修订工作由赵生群先生领衔,方向东、王华宝、王锷、吴新江、曹红军、王永吉及苏芃先生参与修订,修订工作自2007年开始,历时八年完成。据修订本《史记》的《修订前言》《修订后记》及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史记》修订本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例如撰写校勘记3400余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800余字,改动标点6000余处,改正排印错误300余处等等。《史记》修订本不但对原有点校本做了拾遗补阙工作,将《史记》点校整理水平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同时也将顾颉刚等先生的文化初心传承赓续。《史记》修订本卷首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对这份文化传承概括如下: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始,至21世纪全面修订再版,五十余年间,一代又一代学者如同接力赛跑,前赴后继,为之默默奉献,倾尽心力。点校本的学术成就和首创之功,以及其间展现的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为学精神,将泽被学林,彪炳史册!
赵生群先生对未来的《史记》整理工作有着前瞻式的设想:“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面世并不是一个句號。接下来比如开展对《史记》三家注复原性整理、《史记》历代版本资料库建设、《史记》汇校汇注汇考等工作,还要做一个《史记》新注甚至新的翻译本。”《史记》深度整理工作不会终止,潜藏其中的文化初心,学者也终将牢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及自身拥有博览群书的优先条件:“当时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时至今日,电子文献使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到远超太史公的便利阅读条件,而且经过学者的努力,古往今来的《史记》研究成果也都呈现在读者面前,悉心查阅、仔细展读便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当品读《史记》厚重的研究成果,在慨叹古今《史记》整理、研究、传承与弘扬的成就之时,我们更应静心感受流淌在《史记》长河中的炎黄子孙的文化初心,体察古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不忘初心、传承文化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领略史书编纂、古籍整理及史料考证等工作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历程上所取得的坚实成就。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大庆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