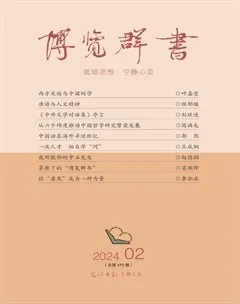茅檐下的“博览群书”
莫砺锋
从读书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66年在苏州高级中学毕业以前,我爱好数理化,一心盼着将来当个工程师。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后,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成天钻故纸堆,几乎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夹在其间的13年,从苏南的赵浜生产队,到皖北的汴河农具厂,我一直栖身于茅檐之下。我在辛勤劳作中度过了十年青春,靠种庄稼与做螺钉养活自己。务农、务工之余,我也不废读书。关于当年的耕读生涯,数量不多,内容却极为庞杂,毫无学科倾向性可言。单从后者来说,不妨戏称“博览群书”!
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爱文学,但是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却是长于理而短于文。1962年,正在一個江边小镇读初中的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全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前者名落孙山,后者却以参赛者中唯一的满分获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进苏州高级中学,也即名震遐迩的“苏高中”。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高中的语文老师教得极好,老师也鼓励大家读课外书。校图书馆里有数万册藏书,我课外阅读的范围迅速扩展。我从高一就立志要报考理工科的院系,仍然广泛地阅读各类文科课外书。到高三时,我已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但我在学科选择上更加偏向理科,生平第一次亲手触摸到那些实验仪器,使我对物理、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至于数学,则一向是我最喜爱的课程。我高一时在苏高中的礼堂里近在咫尺地聆听数学家华罗庚的报告,那种兴奋心情至今难忘。1966年初夏,我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面临高考。学校里让我们填写高考志愿的草表,我的前三个志愿分别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自动化控制系和数学力学系。没想到还没有走进考场,高考就被明令取消,到了1968年秋天,全部“老三届”中学生都奉命“上山下乡”,我也卷起铺盖,来到太仓县的赵浜村插队落户。岁月荏苒,我在茅檐底下度过了整整十年的“耕读生涯”。我都读了些什么书呢?又是怎样读书的呢?
下乡的头一两年,我对学习理科还未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道坎就怎么也过不去。我被迫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从此只读文科书。我在农村读书纯粹出于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单调,很无聊,很苦闷,总想弄点书来读。那时村里连张报纸都没有,更没有获取图书的任何渠道。城里的图书馆早已贴上封条,书店里较有价值的文科书籍都出于六位作者之手,即“马、恩、列、斯、毛、鲁”,这些书便成为我的首要阅读对象。我下乡时先后领到两套毛泽东著作,四卷本、一卷本都有,还有当时人手一册的语录。我把四卷本读得滚瓜烂熟,语录则倒背如流。我没弄到鲁迅全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倒是几乎读遍了。马列的原著也读了一些,《资本论》和《哲学笔记》我没敢碰,《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哲学之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读得较熟。
两年后我把能够弄到手的“六位作者”的著作全都读完了,我的书源顿时陷入枯竭。不久,我从生产队会计家借到一本《气象学教程》。我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就老是读它。书中凡是与现代科技相关的气象学知识,我日后都忘得精光,因为村里连个百叶箱都没有,我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气象测量仪器,对“锋面”“锋线”等术语只能诉诸想象,对“百帕”“千帕”的感觉也没啥差别。读完全书,倒是记住了好多观云识天气的民间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当时村里的农活都是用镰刀、锄头来干的,耕地则用牛来拉犁,与现代科技毫无关系,我也就没有产生阅读其他农学书籍的兴趣。同样出于无奈才读的一本书是《新名词辞典》,是邻村的一个知青送给我的。虽然是一本辞典,但所收的词条很有意思,我从头读到尾,津津有味。《新名词辞典》把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都列为词条,我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从此害上了对雨果的单相思。还有一条关于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的词条,说这首长诗抒写了对美丽的立陶宛故国的哀思,我看了也无限神往。我直到如今尚未读过此诗,却对立陶宛充满好感,就是受这本辞典的影响。
我四处借书,简直是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能借到什么书纯属偶然,它们的性质及出现的顺序则杂乱无章、毫无规律。但总的说来,大概分为几类。第一类是中国古书。部头较大的有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和一本《太平天国史料集》,此外就是《古文观止》、王伯祥的《史记选》,马茂元的《楚辞选》等选本。那本《经史百家杂钞》已经残缺不全,无首无尾,但书主人视若拱璧。我借到手后还没来得及抄录,便被催讨索回。《太平天国史料集》倒相当完整,主人也不催着讨还,我便把较喜欢的文字抄录下来。其中如石达开的《檄文》《复曾国藩书》等曾全文背诵。钱江的《兴王策》也深合我意,我甚至认为钱江是太平天国中最有见识的一个人物,可惜洪秀全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由于到手的书太少,“书当快意读易尽”,无可奈何只好反复地读,而古文、诗词正是最耐反复阅读的。读来读去,许多文字便熟读成诵了。《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孙子兵法》曾全书背诵。一本《古文观止》,我曾背过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我寻觅《论语》的过程。我下乡不久便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读到《论语》的六十来则条文,钦佩之余想读全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用心搜求,也只在其他书中找到寥寥数则。七年之后,书店里终于出现了一本《论语》。该书题作《论语批注》,翻开一看,“有朋自远方来”被译成“有没落的奴隶主从远方来进行反革命串连”,令人捧腹。然而《论语》的原文俱在,一字未删。于是我从《子张》篇中读到了:“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我不禁热泪盈眶,一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那块巨石顿时落地。原来一年前我父亲去世,为了向大队书记借用拖拉机运送父亲的遗体去火化,我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给书记送了两包香烟。事后我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心里又委屈又窝囊。一年后我读到孔子关于“亲丧”的话,如释重负。后来我看到伊塔洛·卡尔维诺关于经典作品的十四条定义,尤其是其中的第五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觉得这条定义虽是针对西方经典而发,但也仿佛是为《论语》量身定制的。
第二类是欧美书籍和苏联书籍,也包括若干沙皇时代的俄国书也算在内。当时这两类书都很难弄到。有人告诉我在某些北京知青手中流传着不少“黄皮书”或“灰皮书”,身在江南农村的我对那些神秘的出版物毫不知情,至今未睹真容。我能到手的这类书主要是从苏州知青那里辗转借来的,它们在我手上总是匆匆而过。外国小说最受知青群体的喜爱,每一本都在众人手上快速传递。有一次我借到一本司各特的《皇家猎宫》,主人只答应让我看一天,我点上油灯连夜阅读,总算在天亮时分读完了这本400来页的长篇小说。杰克·伦敦的《毒日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死屋手记》等小说都是这样匆匆读完的。只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例外,两书都是繁体竖排的老版本,爱读的人不多,传入我手后很久无人前来索取,我便从容地读了两遍。非小说类的书会在我手中停留较长时间,比如苏联科学院院士敦尼克等人编撰的《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它篇幅浩繁,内容复杂,我读得头昏脑涨,苦不堪言,花了几个月才啃完那两巨册。读完全书后似懂非懂,将信将疑。我保存着一本读书笔记,除了摘录原文外,也记了一些我的“存疑”,比如关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的“只有存在,没有非存在”,书中大加批判,我的“存疑”是:“我认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这句话实质上是一种同义反复而已。”又如关于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书上说“霍布斯错误地认为‘词就是人们按照相互间的同意而制定的符号”,我的“存疑”是:“这个观点错在哪里呢?难道说词不是符号吗?”想法相当稚嫩,但都是我边读书边思考留下的痕迹。还有法国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知青朋友都嫌它枯燥乏味,我却读得拍案叫绝,把许多词条抄在笔记本上,至今熟记在心。比如“魔鬼”:“上帝一句话就能使他化为乌有,然而他禁忌这样做。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又如“牧师”:“这是些受托牧放上帝的羔羊的人,他们大公无私地履行这一委托,只留给自己剪羊毛和屠宰那些羊毛不能令他们满意的绵羊的权利。国王是这些宗教牧师的狗,专咬离了群的或不让剪毛的羊。”我还在读后感中称扬此书:“冷嘲热讽,锐利难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由于书源枯竭,下乡五六年以后,我终于把我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所拥有的中文书都借来读过了,再想借到别的书难于上青天。迫于无奈,我重新捡起丢开多年的英语,心想学好了英语就能弄一些英文书来读,而英文书比较耐读,不会很快读完。我家原有的英文书屈指可数,只有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和薄冰《英语语法手册》比较像样。还有一套四册的英文版《基本英语》,是多年前亲戚赠送的儿童节礼物,书中的插图多取自幽默杂志《笨拙》,我曾经浏览,却从未细读。一时弄不到合适的英语教材,我便翻出这几本尘封已久的书来一一细读。不久,我辗转借到一套大学英语的教材,虽然只有许国璋编的前四册和俞大絪编的五、六两册(当时我不知道后面还有七、八两册),我还是如获至宝。为了及时还书,我一边读课文、做作业,一边用印刷体把全部课文一笔不苟地抄在软面抄上。如今我还保持着那两本“手抄本”,用作教导我的研究生刻苦读书的“革命文物”。后来我有幸结识了一位返乡务农的中学老师徐学明先生,他对我喜欢读书非常赞许,不但义务为我批改英语作业,还主动借给我不少英文书。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伊索寓言》,中文还是雅致的文言,我把英文与文言分别译成白话文,两相对照,获益匪浅。使我大开眼界的是《拜伦诗选》等原版英文诗集。以前我读外国诗歌,都是读的中文译本。拜伦的一曲《哀希腊》,马君武的译文与苏曼殊的译文差异极大,令我疑惑不已。借到《拜伦诗选》后赶快翻开《唐璜》,找到《哀希腊》那一节,才明白原来译诗其实是一种再创作。虽然马、苏二人的译笔都堪称惊才绝艳,但都与原文出入较大。我还借到若干册英文版《苏联文学》期刊和英译《别林斯基哲学文集》等,虽是从俄文译成英文的,但文字流畅,引人入胜。最珍贵的是一本英文版《世界短篇小说名著》,书厚如砖,字小如蚁,书中生词极多,我边查词典边阅读,进度很慢。作为练习,我曾把其中毛姆的《雨》、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斯托姆的《茵梦湖》等篇译成中文。还有一篇中国古典小说,当时不知其原名,也勉强译成中文,多年后才知道那是“三言”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这本《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陪伴我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寂寥岁月,就像书的主人徐学明先生一样,永远令我怀想。
我的“博览群书”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环境一有变化,也就戛然而止。查阅1977年的读书笔记,我先是缓慢地读完了《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接下来快速读完一位新朋友借给我的三本书:刘祚昌着《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任炳湘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和《袖珍神学》,然后开始细读自己购买的《论衡》。我对王充向无好感,又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刺激,在读后感中常有讥讽王充之语,比如《逢遇篇》:“此篇无新意,一言以蔽之曰:遇不遇,时也。”《命禄篇》:“一言以蔽之曰:富贵在天。”《吉验篇》:“取《红楼梦》中之一言以蔽之:满纸荒唐言!”最后在《偶会篇》后记曰:“暂停于此,日后再读。”为何才读了全书的八分之一就暂停?笔记未记原因,也未署日期。现在回忆,好像是在该年九月,农具厂刚订到一份好合同,我得加班加点赶制螺钉。也可能是当时传来了高考恢复的消息,我就张罗着报名、备考了。1978年4月,我进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读本科,课外阅读的书单中除了前文提到的几种雨果小说外,其他如《英国史》《英美概况》等都是老师布置的英语专业参考书。1979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唐宋诗歌”方向的研究生,导师程千帆先生为我开列了一份书单:必读书是《文选》《选诗补注》《古诗源》《古诗笺》《诗比兴笺》《唐宋诗举要》《今体诗钞》《万首唐人绝句选》《千首宋人绝句》《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宋诗精华录》;选读书是《中国史学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两唐书》《宋史》。我在程先生的严厉督导下疲于奔命,再也没有精力旁览他书。我的“博览群书”就此画上句号。
回首平生,感慨万分。在农村“博览群書”的阅读总量其实很小,内容又杂,学到的知识零零碎碎,但我仍很珍视那段经历。当年的书源虽像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但毕竟是源头活水,它的陆续注入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天光云影共徘徊”。我从书中结识了许多可敬的师长和可亲的朋友,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促膝谈心,为我排难解惑。即使我终生没进大学而一直留在农村种庄稼或造螺钉,那段读书生涯也依然值得留恋。
(作者系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