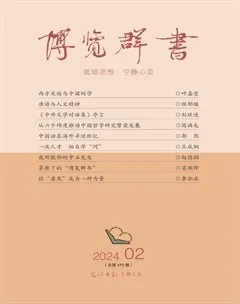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论语》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张庆利
《论语》记载了孔子许多有关教与学的论述,体现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而其中记录的孔子教育过程中的片段,更是弥足珍贵,深入挖掘,庶可见其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影响。《论语》中有如下两则教学片段,今天读来,仍觉意义深远: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这两则记言都是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弟子提问,孔子作答,然后弟子谈认识,孔子进行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完整的教学互动环节的记录。虽然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语文”的概念,但在这两段对《诗》的征引、疑问、说解与联想中,从其中涉及的内容与原则、方法与步骤、风格与特征等问题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其对当今语文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思想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孔子的教育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并重,而德行为先。这两则材料中,子贡问及的正是道德的问题。贫穷的时候不谄媚别人,富贵的时候也不骄傲自大,这是孔子经常提到的一个道德层次,他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要求以“仁”的方式获得富贵,去掉贫贱。他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认为花言巧语、谄媚作态,是不仁的表现。但这是基本要求,所谓“富而无骄易”(《宪问》)。孔子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引进以“礼”约束的更高境界,子贡则联想到了《诗》中的话语。子夏问及《诗》的理解,又从孔子的解释联想到“礼”的意义。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主内,礼主外,礼的教育是德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雍也》中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但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文质彬彬”谈的是君子风范。“质”强调内在的品格,主要是指其所具有的仁、义、智、信、勇等;“文”强调外在的修养,主要是指其礼仪等方面。《论语》中的“君子”具有多种品格特征:好学精进、乐观向上、过而能改、谦虚谨慎、言行合一、团结协作、胸襟开阔、任重道远、正道直行、礼乐情怀、忧患意识等,都是重要之处。
“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首先,要有向道精神。“道”是信念,是理想。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可见对“道”的规划和忧虑是“君子”之人的突出品质。孔子曾憧憬地表白:“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可见他一生都充满着向道的精神和求道的热情;他的弟子子夏也说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可见“道”是孔门一直的追求。“向道”就要有胸怀天下、安定天下的责任感,有开阔坦荡的胸襟,有任重道远的担当意识,还要培养正直品行,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其次,要有优良品质。孔子重视学习素养,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的新局面,把引导弟子学习作为第一要务,《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把“好学”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和作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声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论语》具有丰富的学习思想,对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都有具体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孔子重视求实品格,他认为仁人志士必须实事求是,因而君子之人要言行统一,要先行后言,不能言过其行。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古人不多说话,就是因为怕做不到。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要言语谨慎,行为敏捷。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孔子理解别人的过错,并认为君子之人善于改过迁善,“过则勿惮改”是君子的重要条件。认识到错误,并且积极地去改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吸取教训,从而成就君子的品格,正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为此,他特别赞赏颜回“不贰过”的精神!孔子崇尚谦逊作风,孔子认为君子从不因为别人不理解自己而不高兴:“人不知而不愠”(《学而》),而总是担心自己能力不及人之所望,经常从自身方面思考增强其能力:“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他们从不骄傲自满:“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所以能夠团结协作而不结党营私:“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另外,要有礼乐修养。孔子认为“礼”是立身、立业、立命的重要根据,因而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乐”为“德之光华”,发于内心,感人至深,具有“移风易俗”“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的作用。因而孔子非常喜欢音乐,在齐国听到舜时的乐章《韶》,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而且深深感慨:“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他非常重视乐教,认为修身从学《诗》开始,以礼立身,通过乐来成就中正平和之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礼与乐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正如《礼记·文王世子》中所说:“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这是“君子”之人的重要条件,也是家国之治的理想境界。
文化的承载与弘扬离不开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语文学科是个综合学科,承载更加厚重,责任更加重大。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语文”的概念,但在经典阅读的教育中,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强调中,其培养目标明确地指向了君子人格。
启示之二,经典阅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基础。在孔子的时代,《诗》具有特殊的功用。不仅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领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道理,而且可以“兴观群怨”具有多种审美意义,可以“赋诗言志”进行沟通与交流,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礼体现着规范,也是一种修养,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可言、可立,便具备了“君子”的基本条件。从教育的角度,《诗》则是一部可以认知名物、可以提升道德、可以学会表达的经典教科书。不只是《诗》,儒家教育中的《书》《礼》《乐》《易》等也都是经典之作。
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总有那样一些著作,她以不多的语言,给人无尽的启迪,不断被阐释,让人们常读常新;她以不变的姿态,却涵容着历史的变迁,不断被证明,成为准则,成为典范,“秩秩德音,洋洋盈耳”(《史通·叙事》);她以不争的经验,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记忆,不断被唤醒,又不断被印证。这就是经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们的存在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在人类的精神长河中如点点白帆,通往过去,也驶向未来。
这些经典的主角或创造者都是一个一个的文化大师,他们用不寻常的人生创造了不朽的经典。《论语》中的孔子,以蔼然长者的形象,怀着博大的胸襟,“有教无类”地播种智慧,“诲而不倦”地布施仁爱,带领弟子们由北到南贯通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传送德政;描绘《道德经》的老子,站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大道之巅,在“惚兮恍兮”的世界中探索着不可名说之“道”,阐扬着“自然无为”的帝王之术,构造出“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孟子,高扬着“大丈夫”的气概,驰骋天下,睥睨王者,意气风发,雄辩滔滔,坚持“民为贵,君为轻”,始终为民众争取着一席之地,全身充满着“至大至刚”的凛然正气。“衣弊履穿”“钓于濮水”的庄子,他以精神世界的丰满充盈,对抗着生活的贫困,抛开了名利的物累,超越了生死的限界而奔向“逍遥游”的辉光!写作《史记》的司马迁,靠着巨大的力量,以一人之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贯通历史的构建;带着理性的情感,拨开传说的迷雾,从蒙昧混沌的洪荒梳理出民族发展的脉络;凭着高超的技巧,描绘千百年中遽来遽去的人物,把再现的历史叙述得入情入理。就这样,经典展露了它最本初的端倪,带着世人穿梭在历史的长廊。千年稍纵即逝,而经典岿然不动。
在《论经典》一书中,作者詹福瑞曾论到经典的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累积性,谈到“教育之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认为“经典传播的主要形态之一,是学校的教育”(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这些经典,揭示了人间的至真情性,带领我们从人类发展的成败得失中寻求历史智慧。以《周易》《诗经》《尚书》《三礼》《春秋》《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为代表的中华元典,不仅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宏观的文化价值,而且,就个人生命来说,它们探讨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对每一种人生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韩愈自幼刻苦为学”,从“佶屈聱牙”的《尚书》、“正而葩”的《诗》、“奇而法”的《易》、“浮夸”的《左傳》、“谨严”的《春秋》,到《庄子》之论、屈原之辞、《史记》之录、扬雄和司马相如之赋,无不涉猎,而且“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这才有了“闳其中而肆其外”(《进学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辉煌成就。
对于文学经典的选编,早已有了历史的经验。南朝萧统编的《文选》,便是成功的一例。萧统看到了文学的发展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因而希望通过“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方式,编选一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选》,对前代文学进行总结,同时作为时人学习的典范。此书一出,盛极一时。唐代便有了“文选学”,出现了像曹宪、李善等选学家,以及《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等经典注释本,《文选》几乎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书,北宋甚至有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而《文选》既重文采、又重情思的选录标准,诗文并重、汇聚各体的选录原则,以类划分、时代相次的编纂体例等等,创体开新,蔚为大观,也为后代“国文”“语文”类教材的编纂开了先例。清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古文观止》,上起春秋,下讫明末,选录文章220篇。编者认为所选文章均为古文中的精华,因以“观止”称之。这个选本,当时即获赞誉,吴兴祚作《序》称其选“简而该”,其评“精切而确当”,能够“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这绝不仅仅是长辈对“从子”“从孙”的偏袒过誉,而是揭示了它足以“正蒙养而裨后学”的价值。虽然这只是一个文章选本,但由于其选文的精粹、注释的精当、评点的精要,使其本身就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对文章的学习与写作至今仍有重要影响。
当然,经典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实用,更重要的“而在文化”,所以朱自清称之为“经典的大路”“经典的海”,号召“亲近经典”(《经典常谈·序》)。
启示之三,启发联想是语文教育的专业特征。孔子重视启发式教学,他曾经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愤,是指经过了努力、经过了思考、却没有完全透彻地理解的思维情形;悱,是指虽心有所悟、意有所会、却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思维情形。这时候,师者一言点化,便如当头棒喝,又如醍醐灌顶,使之豁然开朗,粲然深思。由此可见,启发不是简单的提示,而是思想的引领。启发的目的是引起联想,使之达到贯通而彻悟。“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无疑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层次,但却不是最高的层次,所以孔子引导子贡追求“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更高层次,而子贡则由此联想到《诗》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这一段话,有的《论语》本子作“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意思更加明了。有了朋友间的切磋琢磨、相互砥砺,所以才能够虽贫穷而一心向道,虽富贵而深明礼敬。“绘事后素”是讲先有纯白的素娟,才能绘出最美的图画,这显然不是对子夏问《诗》的正面回答,但子夏却由“绘事”后于“素”,联想到了“礼”的问题,内含着有了仁的底色再加上礼的修养就达成了君子人格之意。
在《论语》的记言中,孔子经常采用譬喻的方式,引发听者的联想。比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北斗星为众星辰环绕与簇拥,以此为比,以德治政的显着效果和重要意义昭然若揭。再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雍也》)“輗”与“軏”是套牛马拉车的关键,没有輗、軏就无法套住牛马,也就无从拉车;诚信于人来说正是这样的关键,不讲诚信,人便无法立身。再如:“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水”与“山”虽然不是对“知(智)”与“仁”的界定,但却可以让听者在对水之灵动和山之厚重的联想中,体悟到“知(智)”与“仁”的品格。《论语·雍也》中还曾记载,子贡曾向孔子问道:如果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可以称为仁人?孔子回答说:不仅可以称为仁人,甚至都可以称为圣人了!他接着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能近取譬”讲的是能够从身边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就是行仁之方、晋圣之途,但如果把“能近取譬”用于语言表达中,也是让人联想、引人思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吧!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孔子十分重视启发学生联想和想象。在《论语·先进》记载的那篇有名的《侍坐》中,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他先以不要“以吾一日长乎尔”而不言打消弟子们的心理负担,又提出弟子平时总说的“不吾知”的话题,这种启发既有针对性,又消除了弟子的顾虑,所以弟子们才能畅想未来,高谈其志。
聯想与想象是心理活动方式,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运思方式。没有联想就无法将已有知识与经验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没有想象就会使其创作缺少创造、没有灵魂,通过联想与想象,“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晋·陆机《文赋》)。
当然,联想需要积累。可以说,积累是联想的宝库,阅读、经验和思想是积累的途径,而背诵则是积累的重要方式。前引两则材料中,从孔子“始可与言《诗》已矣”的话语可见,此时子贡、子夏二人尚未开始学习《诗》,但二人却对《诗》非常熟悉,不仅记诵在心,而且可以随时运用:子贡由孔子道德的教诲联想到了《诗》句,子夏由《诗》句的认识联想到了礼仪。记忆的积累,丰富了他们联想的资源。我国古代的教育十分强调背诵,无论哪一个时期,背诵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始终。古代的一些识字课本,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几乎都采用整齐的韵语,甚至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的形式,都是为了朗朗上口,方便背诵。朱熹指出:
学者观书,先须读行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则非为己之学也。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谈到中国古代教育时说:
国学生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熟记历代名家所作的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2000多年,已经养成大家于古文书有特别的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发生了一种崇视敬爱的心,这实在是中国人的特色,这种聚焦成功的大资产,以供中国著作家任意地使用,在文辞的修饰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效果。
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岑参5五岁开始背书,9岁便能写文章;柳宗元4岁时已经熟读了十几篇古代辞赋,13岁时已能写出相当不错的文章;李商隐5岁开始背诵经书,7岁学习写作;司马光,五六岁就能熟练背诵《论语》《孟子》,七岁熟读《左传》;苏轼十几岁时,就能熟读背诵《庄子》《史记》《汉书》等。毫无疑问,背诵可以促进联想,联想是想象的基础,想象是联想的升华。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论语》蕴涵着丰富的语文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提供了典范,值得深入总结与有益传承。其实,又何止《论语》,每一部经典,都是一方宝藏,值得我们“永无止境的”“无限的”阅读、诠释与借鉴。
(作者系文学博士,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