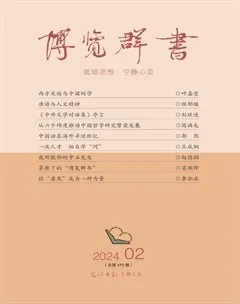中国话在海外寻迹断忆
我从2000年开始关注海外中国话,至今还坚守在这片蓝海里。20多年来,我一直被海外华人对母语教育的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感动,被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资源富矿所吸引,被海外中国话研究的广阔前景和不断出现的成果所激励。我探寻着,摸索着,不断有新认识、新发现。在朋友们的督促下,我试着写了一些回忆文字,刊载于《中国语言战略》2023年第一期,全文两万五千字。为了让更多的人对中国话在海外的情况有所了解,这里选取一些段落,重新整理,尽量删除学术化的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踏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2000年3月10日晚,我第一次踏上槟榔屿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兴奋、好奇、希冀,使命感,这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这时开始,我将走上一条对中国话在海外的追寻之路。
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迎接新的世纪并能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当时的一个响亮口号是“背靠大树,面向大海”。大树,就是中华文化;大海,就是海外,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我此次到槟城,就是受学校委派,协助位于槟城的韩江学院筹备中文系合作项目。赴马之前,远在新西兰的同门师弟孙德坤提醒我,马来西亚可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好地方,那里有很多民族,语言多种多样,多元文化并存,应该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实验场。有机会到被学界称为语言景观风景线的马来西亚,体验那里的语言生活,对我来说更是机会难得。这是兴奋点所在。
3月10日,我一大早从南京出发,经香港转机,晚上8点30分抵达槟城峇六拜国际机场。3月的南京春暖花开,而3月的槟城却是挥汗如雨,这是槟城给我的第一印象。从峇六拜机场到达厅出来,宝清夫妇已在等候,当晚就住在他们家。
宝清姓张,当时是韩江学院传播系系主任,跟南京大学合作的项目由她临时负责。她先生叫木锦,姓黄,是学建筑的,在槟城一家公司从事槟城古迹建筑修护的社会工作。从机场到他们家,20分钟的车程。木锦开车,边走夫妻二人边介绍马来西亚的相关情况。他们两个跟我说着非常标准、流利的异乡中国话,他们称之为“华语”。这种话我并不陌生,但都是从在南京大学读书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那里听到的;第一次在国外听到,是那么的亲切动听。
木锦祖籍福建福州,他的祖父在二战前来到马来亚,经营咖啡店。“咖啡店”是马来西亚华语中的一个有特色的词语。咖啡店不一定只卖,有茶有咖啡,还有其他饮料,除此之外,还有小贩卖的面食、简餐和小吃。大家在那儿喝茶聊天,进行餐叙。在槟城的乔治市五洲茶室,我见到了木锦的父亲,也是一口华语,没有木锦和宝清说得那么标准,乡音重一些。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福建省地图,地图上标着他的家乡。木锦的父亲出生于中国福州,十几岁时随木锦的爷爷奶奶来到马来西亚。他告诉我,中国一开放就回老家探亲了,木锦的姑姑及亲戚堂兄妹都在福州闽侯。一个“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后来把用“去”中国还是“回”中国作为认同转换的一个标志,就始于此。
说说槟城
槟城,旧称槟榔屿,简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州联邦州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北部,以槟威海峡为界,分成槟岛和威省两部分。自1786年开埠后到现在,槟榔屿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槟城的中心城区又称乔治市,位于槟榔屿的东北。岛上40%的人口居住在这里,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城市,也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传说早在1405年,郑和曾踏足槟城。槟榔屿西南区的峇都茅至今有传说中的“郑和三保公脚印”。
实地生活加深了我对马来西亚华文使用状况的了解。来槟城之前,我对它并未有深入的了解,但心里惦记的是槟榔屿。到槟城的第二天,我问宝清,槟榔屿在哪?她笑了,你就在槟榔屿。我明白了,这就是郁达夫笔下的槟榔屿。
槟城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城市。各种民族、各种宗教代表性的建筑随处可见。其中许多古老的宗教建筑城内充满华族风情。在街上有许多古老的会馆,最古老的乡会是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1801年),最古老庙宇是大伯公庙(1799年)及观音亭(广福宫)(1800年)。槟城还是一个多语多言社会。语言有四种:马来语,这是马来西亚的国语;英语,是马来西亚的通用语;华语,这是受华文教育的华族的通用语;泰米尔语,大多数新马印度人的母语。大多数槟城华人懂两种以上语言,不包括方言,有者甚至懂四种以上。受过教育的则四种都用:马来语,其中混有汉语方言、英语乃至泰米尔语成分;英语,包括正宗英国英语和非正式的“槟城英语”;华语;汉语方言,主要是福建话,但已经形成槟城特色,也有客家话等。面对不同的人,华人会运用不同的語言进行交谈。人们在不同场合会自如地说出不同的话。我深深地被那里华人超人的语言能力所折服。
华社以外的成员也多少会用一些汉语方言。例如,一些土生土长的马来人、印度人,也会讲福建话和简单的华语。我经常光顾的一位卖福建面的摊主不是华人,但他能讲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还会跟我讲简单的华语。不过,我2019年再次到槟城,看到的事实是,年轻人已经不使用福建话,福建话将退出。
在槟城期间,我住韩江中学宿舍,常听到校园里学生的读书声。老师在教室里边讲课的声音不时地传到我的耳朵。看到了学生各种各样的活动,学校运动会响起的中国运动员进行曲,只是《长江之歌》被改成了《大河之歌》。我想进课堂听听中小学的课,但是被校长婉转地拒绝了。在韩江住了那么久,一直没有能够进课堂听课,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才知道,在海外听课是大事,都不让随便听。如有考察团客人提出听课,要事先报有关机构批准。
给马来西亚华语打分
多年后,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会想起研究海外中国话?为什么热衷于用“华语”这个词?这得回到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参加记者会。2000年3月中旬,在我到达马来西亚槟城正好一周的时候,韩江学院举行了一次记者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记者会这个词。那个时候国内习惯说记者招待会。写到这里,想到一个小故事。国内一些人常批评海外华人用语不准确;结果,海外一位语文界的朋友反唇相讥,你们的记者招待会也不准确,记者招待会没有招待啊。
在答记者问的環节,有记者突然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语言学家,那你看看我们的华语能得多少分?我问他,用什么标准?北京的标准、台北的标准还是马来西亚的标准?记者说,不管什么标准,就说你自己的感觉。我说,那就七八十分吧。
第二天,马来西亚各大报都发了记者会的消息,我对马来西亚华语的评价也上了报。有的还用了《郭熙:大马华语不俗》的标题。报道登出的当天,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当地朋友,是一家华文小学的校长,给我打电话。他说,郭教授,你这个说法不对,太过分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语怎么可能有80分?最多30分。发音也不标准,词汇也不标准,语法到处是错的,你看报纸上到处是错字别字。意思是说,我对大马的华语肯定过了头。后来,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跟我讨论。很久以后才知道,在我之前,几乎所有到马来西亚的中文学者都说马来西亚华语不标准。而在马来西亚华语台播音的陈天然先生不仅批评华语发音的现实,对华人这一称说,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实际上,我当时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临时应对,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来不及。中国国内都用“汉语”这个名称,而且还有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到了马来西亚,看到他们都用“华语”,我感到很新鲜;而且,那里的“华语”不包括方言,相当于我们的“普通话”。于是,后来在槟城的一次演讲中,我阐述了普通话和华语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海外华语等,间接回答了为什么给马来西亚华语打80分。我说,推广华语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解决了各个方言群体之间的沟通问题,这应该是评判语言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仔细想来,我当时关注华语看似一个偶然因素使然,其实有必然性。我本来就是做社会语言学的,比较关注语言的变异变化和发展,特别重视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功能。我原来做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研究,那是河南话在省外,现在关心的是中国话在海外。
搜集海外华语资源
2016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首任主任李宇明教授邀我加入推动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2017年,海外华语资源库项目正式签约。2019年,我们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收集与整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先后获批。
搜集海外华语资源有多种渠道,其中很重要的观察和访谈。访谈是半结构化的。有规定动作,这是必须要问的;还有一些是自选动作,访谈中的意外发现,提纲里边没有的,可以随时去追踪。有一次,东南亚一位海外华校的校长回顾历史,讲到了当时受中国“文革”影响的情况。比如,那时唱的红歌,唱的样板戏,他们都学唱了。我想到“文革”中各地用地方戏移植样板戏的事,就问当地是否有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是自己重新谱曲唱的,还给我唱了《红灯记》的一段。这是很难得的资料。
访谈时间也比较灵活。按研究计划,每个人的访谈至少一个小时,事实上我们的访谈都会大大超过。
资源存在于多个方面。其实,国内其他方面也可以搜集到很好的语言资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在北京华文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建设华文教学实态库。对每一节课全程录像,这对于研究华文教学,研究学生在学习当中各方面的成长,都有重要价值。可惜的是,我离开以后这个工作不仅没有继续,而且还因为储存力受限,后边地把前面的覆盖了。一笔珍贵的资源自此不复存在。资源永远都是宝贵的。
获取真实语料
我们做访谈有三个目的:一是获取信息;二是了解历史;三是搜集语料,希望把各地华人说的话真实地记录下来。这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都需要“真实”。访谈中,被访谈人年事已高,因为记忆等原因,张冠李戴之类难以避免,这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靠的情况。这里只说说语料的事。
国内曾经有过一个大规模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规定调查员必须说普通话。其实这种做法是欠妥的。最理想的做法是调查人跟被调查人说同样的话,同样的话容易获取认同感,有归属感,有助于被调查人说真话。我和徐大明教授曾带学生到包头做过语言调查,为了获取真实语音材料,我们在座谈会上掩盖了自己做语言调查的身份,请他们讲述企业的历史。
这样的故事在海外华语资源搜集中再次发生。在马来西亚居銮,我们遇到了所谓的居銮华语。此前已经从文献中看到这方面的研究,知道那里的一些华人说带有四川口音的华语。因为最早在那里推广华语的老师是四川人,结果就影响到了居銮华语。在居銮,后来形成了两个华语社区,一边带四川口音,一边不带。再往后来,居銮华语成了社会变体,一部分人在一些特点的条件下才说。现在,这种居銮华语已经式微,只有少数人会说。
我们很想把这种华语记录下来。为了保证被调查人说居銮华语,我们不再直接问话。因为我一说华语,他们自然就要用马来西亚正式华语回应,不再说四川口音的华语。怎么办?我把要问的问题写成条子,让当地的南京大学校友孙福盛帮我用居銮华语口音问。确认这种华语的源方言需要《方言调查字表》,但我们没有带。我立即发微信到国内要。第二天,我让被调查人用居銮华语念方言字表的音系代表字。居銮华语的声韵调系统很快出来了:来源正是四川话!
跟时间赛跑
对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总会(通常称董总)前主席郭全强的访谈表明,我们的工作是在跟时间赛跑。
海外的华文学校都是华人自己出钱办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语传承是靠董总和教总(董教总)维营的。郭主席是马来西亚我第一批要访谈的人。他90岁,做了40年华文教育工作,一定有很多故事,尤其是没有人知道的故事。事前,我已经通过教总王超群主席帮我联系好,定于2019年3月中旬前往居銮访谈。正准备南下居銮,得到了不好的消息:郭太太说,郭主席身体不好,不便接受访谈。郭主席身体一直不好,从健康这个角度,是不宜让郭主席再激动、再兴奋。怎么办?他离开董总以后,20年基本上就没有再发过声,也没有公开留过任何的话。这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不能进入我们的资源库,将是一大遗憾。
到居銮以后,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下决心要试一试,哪怕是见一面,短短地留一段视频,留一段录音也好。我找到居銮高中的廖校长,详细介绍了访谈郭主席的目的和意义。还举了陆庭瑜先生的例子。廖校长被我的介绍所感动,表示他会想办法。很快,事情有了转机,郭主席愿意见面。郭主席的孙子在居銮开一间咖啡店,郭主席每天在医院做透析后会去喝咖啡,我们就创造了一次咖啡店偶遇。主席如期而至。我介绍了来意,同时也架好了摄像设备。但咖啡店人多,非常嘈杂,于是主席约我们去家里。听说是中国来的,明白了我们的意图,郭太太也积极参与访谈。两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从中国到马来西亚以及后来从事董总工作的来龙去脉。廖校长说,他从来没有听过郭主席讲这一段的珍贵的历史,更是非常感动。
2019年10月28日,郭主席溘然长逝。幸运的是,我们最终还是留下来他老人家最后的视频和音频,连同他那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段口述对于马来西亚华语传承研究非常宝贵,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谈及的。
海外华校实行“一校两制”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海外华文学校的汉语拼音和简体字是从大陆中文老师开始的。事实表明,不能跟着感觉走。
2018年,我和杨万兵一起到北美做访谈。美国和加拿大有很多中文学校。校长有大陆来的,也有台湾来的,还有香港来的。在洛杉矶,访谈伍校长的时候,我问到学校里边的相关情况,包括教什么汉字,如繁体字,还是简体字;是教汉语拼音,还是教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早期的海外华文学校多由台湾同胞兴办,自然是教授没有经过简化的汉字,他们称为正体字;同时,教授国语运动中推行的国语注音符号。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人开始到海外去,接下来就有了孩子到学校读书的问题。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当时的华校去。这时,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大陆人的孩子希望学简体字,学汉语拼音。这就产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就做出一个决定,实行双规制,同时提供正体字和注音字母班、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班,由家长自行选择。满足不同的需求,提升了家长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后来,隨着年级升高,学繁体和注音字母的就越来越少,最后,全部都使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了。
了解到这个情况,我当时就开玩笑说,原来海外华校早实行“一校两制”了。其结果是从一校两制开始,最终走向统一。后来,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语文顾问汪惠迪先生提醒我,香港姚德怀先生主编的《语文建设通讯》采用的是“一刊两字”:来稿用简体就用简体,来稿用繁体就用繁体,以照顾全球华语区的不同作者和读者。当年程祥徽先生建议的“繁简由之”实在是特殊环境下的一大发明。我由此还想到了马来西亚一些华文报纸的“一报两字”:标题用繁体,正文用简体,方便不同群体的读者。“一校两制”“一刊两字”都由“一国两制”仿拟而成。炎黄子孙的聪明智慧可谓无处不在。
东马发现“坟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墓地都叫“义山”,这也是我多年以来形成的印象。但是,在东马沙巴州,历史上的北婆罗洲,却有一个“津侨坟地”,而不是“津侨义山”。
我做海外华语研究多年,知道东南亚华人语言的主体是闽粤客三大方言和“华语”,也知道印尼棉兰有“川音国语”,马来西亚有居銮华语;然而,直到2013 年,在跟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总会张景程会长的一个见面会,收到他撰写的《华北祖先南下北婆罗洲沙巴同乡族谱》,才知道在马来西亚这个布满中国南方三大方言的地方还有个曾被称为“山东村”的地方,这里说的是一种北方话。
2019年3月,我和王晓梅、祝晓宏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为期3周的海外华语资源调查,那个挥之不去的沙巴“山东村”自然就成了这次田野调查的重点。办完入关手续,推着行李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身材高大,脸色稍黑泛红的“山东村”甲必丹。甲必丹是个音译词,意为首领。早期华人甲必丹由殖民者任命,协助处理华侨事务。沙巴目前有百多位华人甲必丹,张景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沙巴期间,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在编撰《华北祖先南下北婆罗洲沙巴同乡族谱》(108户族谱)的时候,甲必丹做了大量的访谈,也有很多的录音,但是这些录音带现在全都没有了,很可惜。甲必丹亲自开车,陪我们进行了4天调研。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包括他们的祖辈当年为什么来,怎么发展,前前后后,大体上弄清楚了山东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轮廓。我们终于明白,所谓“山东村”人,更多地来自河北和天津,我们看到的“津侨坟地”,是“山东村”的公共墓地。我们也弄明白了,老一代说的所谓山东村话,实际上是天津话。
后来,我们又去了沙捞越。这次东马田调颠覆了我以往对马来西亚的认知。我原来自认为已经很了解马来西亚,现在发现我们对马来西亚了解差得太远。我很多场合讲到这个故事,就会揭自己的短,出自内心地进行自我批评。写到这里,又想起一件往事;2000年首次槟城之行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马来西亚华语里“卫生所”指殡仪馆,有朋友不相信,写文章批评。我当时没有拍照片,无以证实。后来汪惠迪先生前往槟城,专门拍了照片寄给我。我第二次去槟城,又专门拍了数字照片。这些都是书房里看不到的。用汪惠迪先生的话说,田野调查才能看到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作者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