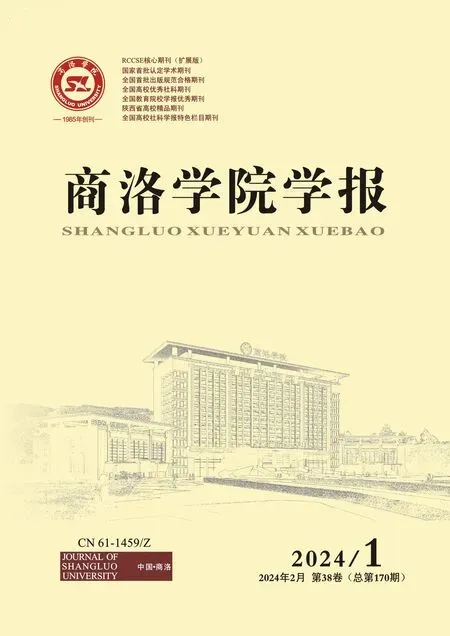汉代书法理论述论
葛稳罡
(1.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65;2.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苏淮安 223003)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璀璨的瑰宝,也是中华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和民族能像中国这样,把自己文字的书写铸就成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而且这门艺术深入人心,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华文明一直赓续至今,仍熠熠生辉。林语堂认为:“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1]他指出:“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1]沈尹默[2]30曾说过,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梁启超[3]也指出,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还有很多名家同持此论,不一一列举。诸贤一致赋予中国书法如此崇高的地位,足见书法魅力之强,价值之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然而就书法艺术及其理论的产生、发展,特别是作为书法成为一门独立艺术诞生期的汉代,学界对其书法理论的钩沉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就此作较为系统地述论。
一、汉代书法理论的溯源辨析
从目前能掌握的文献来看,中国书法理论诞生于汉代,准确地说是西汉末,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不过一种理论不能凭空产生,它必然源于对此前众多实践的理论总结。这就先得厘清中国书法诞生于何时,将此辨析清楚,汉代书法理论的溯源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都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书法也不例外。而在没有艺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能不能被称作真正的艺术,这又值得商榷。因此对于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诞生问题历来就存有争议,莫衷一是。总括起来存在两说:一种认为,书法艺术的诞生与汉字同源。另一种则认为,书法艺术诞生于有书法理论出现之时,即汉代。
持第一种观点者似乎也论据凿凿,作为一种艺术理论的诞生,首先应该源于与这门艺术直接相关的实践活动的产生。书法是关于汉字的艺术,与汉字有着牢固的不解之缘。汉字诞生,人们就去书写,于是书法艺术就诞生了。很多书法史在触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不作准确界定,但大多从汉字诞生之时说起,冠以“书法的萌芽”“书法的起源”“书法的雏形”“汉字之美”等含糊其辞之类名头阐述,在讲到汉代及其后书法时则忽然艺术气息浓郁起来。照第一种观点来说,书法的诞生可溯源到有刻画符号的新石器时代。伊斯特林[4]提出,图画文字的最终形成,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或者甚至在铜石并用时代。从目前世界上的考古实据来看,这一观点基本成立。汉民族的文字雏形——刻画符号,也大致产生于这一时期。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已出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距今有6 000 多年。郭沫若[5]认为,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了带有刻画的陶器,这些刻画有的很接近象形文字。仰韶文化之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陶器上的刻画字符,已经很类似殷墟甲骨文了。经过2 000 年左右的文明演进,公元前14 世纪左右开始出现甲骨文,以及与之同步演进、并驾齐驱的那些呈现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都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所以,如果认为中国书法与汉字的滥觞、演进、成熟同步,那么中国书法艺术则已有6 000 多年的历史。
持第二种观点者则认为,没有艺术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还不能被称作真正的艺术,最多只是一项技能而已。这一观点古人早有论述,元代韩性在《书则》中指出:“三代之时,书以记事,未始以点画较工拙也。”[6]元代刘因在《荆州裨编》中说:“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6]元代郝经在《陵川集》中态度更明确:“夫书一技耳,古者与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计夫工拙,而不以为学,是无书法之说焉。”[7]也就是说,在没有书法理论出现的先秦时期,尽管有一些字在今天看来书写得很精到,而且很美,也很有艺术性,甚至今天还有人作为范本去临学,但那时的书写活动还不是独立的艺术,只是停留在“技”与“工”的层面,未达到“法”与“道”的境界,因此不是书法艺术。
综合上述两种说法,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说法,即中国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应该以书法理论出现为标志,确切地说是汉代。至于汉代以前漫长时期内的那些书写实践成果都是汉代书法艺术及其理论形成的必要基础和准备,当然汉代书家、学者们对前代与当朝人们书写实践所作的总结、思考和理论升华,是形成汉代书法理论的关键。从此,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演进,不断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
二、汉代书法理论的钩沉梳理
从现有史料来看,中国书法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汉,蓬勃发展于东汉。两汉时期既是书法理论的发轫、发展期,也是书法艺术实践的重要奠基、开创期,这是中国书法成为一门独立艺术门类的明显时间标志。
(一)书法理论的第一声春雷——西汉扬雄的“心画说”
开中国书法理论先河者是西汉末的扬雄,他发出了“心画说”的第一声春雷。扬雄(前53—18),汉代著名辞赋家、思想家,著有《法言》《太玄》等。他在《法言·问神》卷五中提出:“书,心画也。”[8]虽然从史料上看不出扬雄是书法家,《法言》也不是讨论书法的专著,但他提出的“书,心画也”这句极其言简意赅的话,确是目前能看到的有关书法理论的第一句名言。文字虽简短,但意义重大,可谓振聋发聩。这让一项原本纯停留在指腕间的技术一下子被注入了灵魂,强调了“心”在艺术创作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了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而应是心手相应的创作行为,不仅是肢体动作,更是精神活动,它需要融入书写者当时的性情、志趣和情绪,同时也是书写者过往长期学养见识、襟怀操守积淀的自然流露。
(二)第一篇书法专论——东汉崔瑗的《草书势》
扬雄虽然发出了中国书法理论的第一声,但那并非书学专论,而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则是中国第一篇书法理论专论。崔瑗(78—143),东汉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在书法上,其师法杜度,后世并称“崔杜”。张怀瓘《书断》云:“瑗善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9]崔瑗不仅善写草书,还善于研究草书,能洞见草书之势,窥探草书之理,撰有《草书势》。《草书势》原本已佚,现传文本源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仅286 字,语句个别地方或经卫恒润色删改,但其基本内容和观点应遵循原貌。文章尽管很短,但由于是第一篇书法专论,所以文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都是首创性的,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全文绝大部分采用规整的四言句式,符合汉魏时简约古朴的风格。
《草书势》中首先谈到文字和书法的起源,起句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10]698,指出书法随着文字的起源而产生。随后用短短几句略述了从初始的“鸟迹”文字演变到汉隶的过程,基本符合上古文字演进的客观实际。因为典籍增多,政局又多动荡,官方业务繁忙,官吏还要抄写大量文字,所以只能动用很多辅助书写的隶人,于是形成“惟作佐隶,旧字是删”[10]698的状况。文章顺势进入主体部分,专谈草书。“草书之法,盖又简略”[10]698,说明汉字的变迁是顺应社会实际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有着删繁就简的趋势。隶书相对古文字已变得简捷,而草书又在隶书基础上更追求简略,因而草书顺势而生,即“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10]698这充分体现出崔瑗书法要求变创新,不能墨守古式的主张。这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不仅是书法,乃至所有文艺形式都在秉承。
《草书势》最精彩处当属对草书形态、意境之美的生动表述,他写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黑知)(黑主)点(黑南),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杜伯揵毒缘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10]698这段话与其说是精妙的论述,不如说是精美的赋文。他用铺陈笔法详细展示了书法造型艺术的特点。
概而言之,在崔瑗看来,草书形态有如下特征:一是有别于篆、隶中规中矩的平整之势,而是有俯有仰,非圆非方,书写非常自由。二是草书充满强烈的动态感,文中用多种物象予以形容。三是草书的字与字之间、点画之间互有呼应,顾盼生姿,即所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四是草书是讲求整体布局的,能营造一种气势和意境,即所谓“状如连珠,绝而不离”“远而望之,()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
(三)第一篇书法批评——东汉赵壹《非草书》
赵壹(122—196),东汉辞赋家,在书法史上也声名赫赫,其《非草书》是历史上第一篇书法批评文章,中国书法批评史也由此开启。赵壹写《非草书》的目的是出于“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对当时过于狂热的习草书风尚予以降温,他以严密的逻辑摆出了反对时人尚草书的几点理由。
1.习草书不是正业
赵壹分析了草书的起源与本质,以此来说明草书非“圣人之业”。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乃是因为秦朝末年“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古为隶草,趣急速耳。示简易之指”[11]170而形成的。这里透露出草书源于秦末,其发展是一个删繁就简“临事从宜”的过程。这与崔瑗所说的“草书之法,盖先简略”观点一致,符合客观事实。但赵壹接着又说草书“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11]170,只有仓颜、史籀之法才是正道,应当为世人尊重。显然赵壹是以弘扬儒家经典为“正业”的立场来批判草书的,而且也流露出他对正统文字观的坚守。
2.时人习草背离初旨
赵壹指出“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11]170。在赵壹看来,草书产生的机理就是简易便捷的,书写就应该“易而速”,如果“难而迟”是不正常、不正确的,有乖本原。他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后世对草书书写速度问题也一直持有争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草圣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10]698,文中“匆匆不暇草书”的意思是匆忙之中来不及写草书。这种说法既反映了张芝等草书家的观念,也反映出东汉草书书写的普遍现状。但这种说法又似乎违背常识,因为在诸书体中,草书的书写速度应该是最快捷的,在匆忙之下要完成书写,草书当是首选,而张芝却说“匆匆不暇草书”,这很反常。对此苏轼即提出异议,他在《论书》中说:“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12]其后,赵构《翰墨志》又云:“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13]370从李白盛赞怀素写草书《草书歌行》中“须臾扫尽数千张”的诗句可看出,怀素创作速度是很快的。同样,苏涣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有“兴来走笔如旋风”、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也有“满座失声看不及”之诗句,这些都佐证了草书创作速度很快的客观事实。所以,就此而言,赵壹对当时草书书写现状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
3.草书非人人可强学
赵壹指出:“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係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11]170说明草书与人禀赋密切相关,并不是纯粹苦学而致。他以杜度、崔瑗、张芝草书名家为例,指出他们“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11]170。后学者无其才禀而专事苦苦模拟,终难有成,弄不好就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增丑失节。显然,赵壹对上述几位书家未置厚非,似乎还略有褒扬,而对不具天赋的仿摹者的做法给予了尖锐讽刺和坚决否定。
4.草书无实用价值
赵壹明确指出:“且草书之人,盖技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经,试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11]170-171他站在儒学道统和经世功用的价值立场,认为这种雕虫小技根本没什么实用价值,不值得耗费精力、大下功夫,而应该精研儒学经典,立德建功。
(四)由点到面的多向散发——东汉蔡邕及其系列书论
从扬雄的只言片语,到崔瑗、赵壹的单篇书论,标志着汉代书法理论已经出现,并蔚然成风。紧接崔、赵之后的蔡邕又对汉代书法理论有了更丰富的承扬和发展。蔡邕(133—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曾拜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在书法上,他精于研习,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六经文字,蔡邕等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刻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成为官方教科书和书法范本。据说,他曾在鸿都门见工匠用扫帚写字而获得灵感,独创了“飞白”书,对后世影响甚大。同时他在书法理论上造诣很深,留下了《篆势》《九势》《笔论》《笔赋》等书论著作。《笔赋》一文,严格来讲是赞美毛笔的赋文,应作文学作品看待,与书法理论关系不大。上述这些书论原作均已佚,历来对其真伪争议颇多。《篆势》一文在《后汉书·蔡邕传》中提及原文已佚,现本见于《晋书·卫恒传》所载卫恒《四体书势》,《蔡中郎集》《全后汉文》等对此文亦有记载,可信度相对较高。《九势》和《笔论》见于宋代陈思的《书苑菁华》中,《笔赋》则见于唐代欧阳询等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以上诸文由于与作者年代相隔久远,或有被后人改动之处。《四库提要》云:“《隋志》载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注曰梁有二十卷,录一卷。则其集至隋已非完本。《旧唐志》乃仍作二十卷,当由官书佚脱,而民间传本未亡,故复出也。”[14]这说明蔡邕的文章早在隋朝之前即有遗失,唐宋离东汉时间久远,且社会变迁很大,因此《四库全书》不收《笔论》《九势八字诀》,或有一定道理。对此,沈尹默在《论书丛稿》中指出:“因其篇中所论均合于篆、隶二体所使用的笔法,即使是后人所托,亦必有传授根据,而非妄作。再看后世之八法,亦与此适相衔接,也可作为征信之旁证。”[2]39所以综合来看,蔡邕书论诸文,其思想相对统一,文风较为接近,内容比较符合蔡邕所处时代的认知和其本人思想,还可视为蔡邕真作。有些书法史家将蔡邕说成是汉代书法集大成者,笔者以为,这一评价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无论其书法实践还是理论都尚难堪此誉。但就上述他的那些颇有争议的书论来看,很多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其观点具体说有四点。
1.继承并发展了崔瑗的“法象”观
蔡邕把“法象”“象形”的美学思想作了很好的发挥。在《篆势》中他提出“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字画之始,因于鸟迹”[10]697,说明文字书写来源于仿效鸟兽的足迹。随后用“或龟文针列,栉比龙鳞”[10]697等一系列生动的自然形象来比喻篆书“法象”“象形”之美。在《笔论》中他提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接着又用了“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等系列形象比喻,最后得出结论,“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15]30这些表述充分表明了书法是形象艺术,强调书法表现自然物象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审美依据、审美价值。正如《书法美学思想史》中所言:“反映了人类从生存本能发展起来的,以生命气象为美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要求。”[16]
2.进一步丰富了“势”的内涵,提出了“力”的概念
“势”这个说法由崔瑗提出,但他并没有作具体阐述。蔡邕在《九势》中具体阐述了“势”,并提出了“形势”和“力”的概念。他说:“书法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15]38“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15]60“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15]69-70“势”与“力”是书法艺术表现中的基本要素,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观。“势”是“力”的目标效果,“力”是呈现“势”的必要手段。《九势》在谈具体笔法时也强调了“疾势”和“涩势”,也就是说,正是由“力”强弱疾缓的变化,形成“势”的多样化的矛盾统一,这一直以来是书法中难以把握的理论和实践双重要领。
3.强调了书写者精神状态的重要性
蔡邕在《笔论》中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15]30“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5]25这应该是蔡邕长期书法实践的精妙体会,非常难得。它显示了书法艺术创作与作者的精神状态、情绪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最佳的书写状态就是专注和放松的自然融合,既屏息静气、排除杂念,又散淡随意、任情恣性,而这一状态是偶得而易逝的。
4.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笔法问题
书法理论中经常提到笔法,而首次具体阐述笔法的就是蔡邕。但他并未在《笔论》《笔赋》中谈笔法,而是在《九势》一文中论及。《九势》内容很短,只有一百余字,但逻辑井然,按照“总—分—总”的基本议论文结构行文。除去前后的“总”,中间主体部分具体谈了结字、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等九个方面的笔法。在文末他总结道:“此名九势,得之虽无师授,亦能妙合古人,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13]7
三、汉代书法理论的价值评论
汉代书论资料直接存于同时代文献的较少,多散见于后人的辑录文献,所以历来有真伪之争,且作者也存有多说。但在没有确凿考据实证的情况下,只能基本遵循约定俗成之说。就前文所钩沉梳理的几位汉代书法理论家的书论资料及其主要观点综合来看,汉代书法理论受当时文风影响,都以单一的赋文形式呈现,议论风格并不明显。但内容已渐丰富,由宏观到微观,内涵渐趋深入,对后世影响巨大,很多观点一直沿用至今,其宝贵的价值不言而喻。具体说有三个方面。
(一)成为书法艺术真正诞生的时窗标志,开创了中国书学和书论的框架模式
汉代书法理论的出现,才使得原先仅是一项书写文字的技能有了理论的升华,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这是汉代书法理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尽管最先发声的扬雄仅说了极为简短的一句“书,心画也”,但这也是开创性的标志。而且他这句话在其后的两千余年来,一直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如同“诗言志”“诗缘情”之于中国传统诗学、文学一样,成为书法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不二法门。书法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内核,不再仅具有实用性,而是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属性,开启了此后魏晋书法走向尚美重韵、抒发个性的书学之路。崔瑗《草书势》极具奠基意义,其以“势”论书的赋文书法品评形式,后世效仿者很多,如紧接其后蔡邕的《篆势》《九势》,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字势》《隶势》等,唐代高骈更是写了与崔瑗同题书论《草书势》。尤其是唐代孙过庭的《书谱》,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具体表述上都效仿崔文。《书谱》中有一段对书法多姿多态之美的描述,与前文所引崔文极其相似,明显受到《草书势》的影响和启迪。孙过庭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他用他高妙的草书作品印证展示他的理论,算是崔瑗理论的发扬光大者。
(二)奠定了多种书体,有效发展了新书体
汉代是中华文明中最具奠基性的朝代,这从汉族的人种、民族、语言、文字及服饰等均以“汉”冠名可以看出。汉代对汉字、书体的奠定、发展贡献是空前绝后的。整个两汉四百余年间,汉字经历了篆、隶、草的变革,即便是楷书和行书虽在汉代没完全定型,但也有了发展的雏形,比如出土的汉简中很多手写体已经有了行书的影子,再比如汉末曹操留下的“衮雪”二字已经基本是楷书,没有汉代的奠定也不可能到三国时就有成熟的楷书出现。这一方面是汉代人书法实践开拓创新的结果,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他们的理论研究密不可分,这其中也包括文字大家许慎对汉字造字和字体的精细而系统的研究总结。从书法角度讲,最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书论有效提升了草书的书法地位,使其成为最具表现力的书体。作为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专论《草书势》,不是论甲骨、金文、篆籀、隶书,并且作为生活在汉代的崔瑗不选择本朝最通行的汉隶来研究品评,而偏偏选择草书,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看来并非偶然,而应有其必然产生的缘由。笔者认为,草书最能体现笔墨变化的丰富和精妙,也最能彰显书写者的情怀和个性,是最先摆脱实用趋向艺术审美的书体。选择赞美、探讨草书艺术,是符合书学客观发展内在逻辑机理的。在众书体中草书艺术表现力最强而创作难度又最大,它不仅对书写者的控笔运笔技能、点画结构技巧和空间布局设计等要求很高,而且对书写者的学养胸襟、气度性情和艺术灵感有更高的要求,甚至对笔墨纸张等书写工具都很有讲究。尽管难度很大,但由于草书深受书写者和观赏者喜爱,审美需求强烈,因而长期以来,各种层次的书法比赛、书法会展,草书作品数量均最多,几占大半,这种倾向在未来书法的发展趋势中仍会愈演愈烈。究其根源,早在草书及其理论诞生之初已见端倪,而崔瑗就是洞察并把握这一倾向趋势的第一人。《草书势》中对草书生动的描述,既是崔瑗对他所处时代已有的草书创作实践的总结描述,更有他理想化草书艺术境界的想象,因为其描述中已明显具有大草、狂草的瑰奇宏博气象。从现存的汉代章草作品来看,似乎还达不到他所描述的意境,所以这也为后世草书创作和草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范本和启迪,唐代张旭和怀素的狂草则是崔瑗所想象描摹的草书艺术境界的绝好实践样本。与崔瑗《草书势》观点相反的赵壹《非草书》的出现,似乎也并不影响草书的蓬勃发展。从《非草书》中能明显看出赵壹的基本立场,他作为儒学卫道士的形象也跃然纸上,这与他《刺世疾邪赋》中“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17]的愤世嫉俗精神一脉相承。对于《非草书》也要辩证看待。一方面,书法是艺术,评论艺术要有艺术眼光,要能把握艺术趋势。赵壹文中的立场观点说明他对艺术的本质及其特征缺乏认识,对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艺术潮流预见不够,因而导致此文沦为守旧陈腐的政治说教,缺乏远见卓识的艺术视野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非草书》在书法史上的独特价值。赵壹在批判草书时所列举的很多事例,如实展现了东汉时期人们热爱草书的现实,有些区域例如凉州地区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这充分说明,草书在那时已经相对成熟,有人以此为业为好。并且书法已不仅有其实用功能,它还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书法艺术已经进入自觉期。
(三)产生了许多新观点,持续影响后世
汉代书法理论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草书势》用了“法象”作为观书品书的总领,别开生面。“法象”初见于《周易·系辞》中,《系辞·第十一章》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18]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概念。“法象”观念被崔瑗用来论及书法,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书法要取象于天地万物,遵循自然之道,而非书者随意乱写。强调书法特别是草书应是生命主体精神和宇宙整体意识的一种感应契合,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一脉相承。这种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历代书法理论家在品评书法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会以天地万物之象来比拟形容书法之态势。蔡邕《篆势》继承并发展了崔瑗的“法象观”,文中的许多形象比喻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篆、隶、草、行等诸体皆适的点画线条艺术造型的圭臬。虽然赵壹的总体立场不可取,但他的某些观点和提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有些至今仍有宝贵价值。比如,他对草书产生的现实原因和大致时期的表述。他提出“书之好丑,在心兴手”的观点,强调人的天赋、气质和草书艺术的密切关系,因禀赋才情不同而各有面目,不能东施效颦式地强学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传承的。《九势》中所阐述的“势”与“力”的问题很具开创性,至今人们在品评书法作品时还经常会用“气势”“力道”“笔力”之类的概念,这应归功于蔡邕。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蔡邕在《笔论》中对书写者精神状态重要性的精妙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从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的《兰亭集序》《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创作实情,可得到实证。这三件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均是在类似于蔡邕所描述的状态下书写出来的,而且作者自己也难以复得。再比如蔡邕在《九势》中对笔法较为系统的阐述,极为经典。这是他揣摩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书法实践,而提炼创立的理论。除第一个方面讲结字原则,其余八个方面都是讲如何用笔,这些笔法理论虽未尽括所有笔法,但涵盖了最基本的笔法要领,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人们品评书法优劣的核心标准,这应该是蔡邕书法理论中最具实质性贡献的部分,对后世书法创作实践和书法理论批评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汉代书法理论虽体例单一、观点零散,未形成体系,但其开创性和影响力无可替代。纵观两千余年的中国书法史,尽管历代书家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均屡有发展、创新,但都能从中找到受汉代书法理论影响的因素,换句话说,汉代书法理论就是整个中国书论史的理论原点。对汉代书法理论的文献考据、整理和理论阐发,都还需要不断深入加强,这也是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