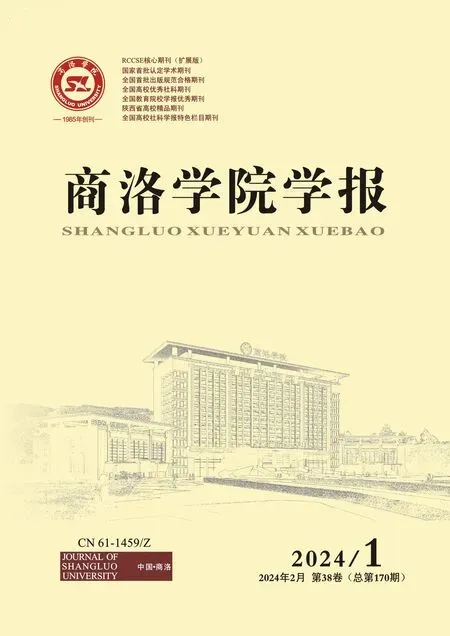论陈彦小说《喜剧》的戏剧化书写
熊英琴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
陈彦的创作发端于戏剧,作为当代著名剧作家,戏剧也成为陈彦的文学标识和艺术根据地。在继承陕西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陈彦以小说题材的重大突破开掘出“戏剧小说”的独特范式,并形成其正大宏深的艺术气象。《喜剧》是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秉持了陈彦文学一贯的艺术追求:“扣人心弦的情节与冲突、饱满的人物形象、个体命运与时代历史的复杂勾连”[1],《喜剧》的戏剧化书写也达到全新的高度,尤其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其时空叙事的场景化、语言表现的舞台化等层面的戏剧性建构与艺术美的呈现,为当代文学奉献了一种不拘一格的戏剧化小说样式。正如吴义勤先生所言:“陈彦是一位成名已久的出色戏剧家,又是一位晚出却又成熟的个性化小说家。他兼有两种文体优势,将之融为一体,使之灵活互动。”而“《喜剧》是戏剧性、抒情性与写实性叙事的融合,其中戏剧性占据统御叙事和抒情的主导地位,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的戏剧化设置决定了小说的叙事架构和情感表现特质。”[2]由此,考察《喜剧》的戏剧化书写、陈彦对小说戏剧化写作范式的深化,以及跨文体、多媒介文本建构对当代文学表现维度的提升与传播方式的拓展等,于今天的中国小说之理论与实践,均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性与价值力。
一、陈彦的跨文体写作
一直以来,小说式戏剧或小说的戏剧化是文学史的常见现象,小说与戏剧的文体互渗首先源于它们自身持有的叙事艺术属性,尤其以时空情节刻画人物、反映时代或寄托理想等文学表现特质。罗伯特·弗罗斯特曾说“任何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富有戏剧性。”[3]小说通过语言媒介向读者讲述已发生的事情,戏剧则是舞台演员直观展现的集语言、动作、舞蹈、音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单从传播方式和观演关系上二者就有明显的区别。然而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大众传媒技术之飞速发展所营造的超大戏剧性语境,戏剧化渐已成为新世纪人们的文化现实和生活表征。与此同时,文学的戏剧化传播、小说的戏剧化书写亦或小说戏剧电影的跨界融合发展也成为媒介时代媒体艺术生长的新姿态。质言之,以当代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已步入“文备众体”[4]的新征程。作为文体学家,陈彦亲身见证并积极参与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主角》《喜剧》立足多媒介的戏剧性和戏剧美创建,更是达到一种难得的新高度。
陈彦小说的戏剧化有其历史合理性与文体必然性。即陈彦小说的戏剧化书写,不仅是他作为剧作家转型小说领域的浑然天成,也是其跨体写作意识和媒介融合理念的自觉选择。方长安[5]认为,不同文体体式相互渗透、相互激励,以形成新的结构理论,更好地表现创作主体丰富而别样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夏德勇[6]认为,小说文体吸收其它文类的文体手法,以丰富自己的文体或改造已经自动化了的文体,借以产生陌生化的震惊效果。《喜剧》与《主角》《装台》一样仍是戏曲舞台内外人物的生命故事,相当分量的剧场和戏剧表演构成小说的内容叙事,陈彦不仅着重塑造了戏剧演员、剧作家和导演等行业人物,舞台、演出等戏剧活动更成为小说情节驱动和人物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但《喜剧》在借鉴戏剧文学写作结构、叙事方式、语言策略等方面,“更多采用了与人物身份和内在精神更具一致性的喜剧手法,在充满强烈戏剧性和喜剧性的叙事调性中,将严肃性的社会问题和悲剧性的人物命运呈现出来”[7],而明显区别于《主角》等,创构出陈彦“戏剧小说”经验的新范式。
随着近年跨媒介叙事、表演性理论的介入和探讨,“戏曲小说”[8],“戏剧—小说”[9]等概念被运用于贾平凹《秦腔》、莫言《檀香刑》、陈彦《主角》等戏剧化小说的分析研究中:“在中国,戏曲的元素贯穿于古典、现代与当代小说中,一方面反映了戏曲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体现出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戏曲的熟悉和喜爱;另一方面,戏曲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叙事与主题的需要,包含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乡土生活的一种怀旧情绪。与此同时,随着20 世纪初话剧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它也成为小说家们写作的资源和素材。”[10]作为由戏剧到小说的融合性作家,陈彦不仅学习接受了世界文学潮流中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法,更保持着情节结构和叙事功能的戏剧思维意向,呈现出一种向中国叙事传统的回归姿态和独特性。而促成陈彦叙事意识内质转化并艺术定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戏剧文化,即传统艺趣意识对现代小说思维的沟通。具言之,其主要表现在陈彦小说艺术对戏剧精神的吸收、对戏剧独特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的借鉴,也包括作家有意识的跨体理念和媒介思想。
二、人物塑造的戏剧化
相比《主角》以忆秦娥为中心所连带的秦腔艺术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和人物命运,《喜剧》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发展具有更强的戏剧性。其中,区别于《西京故事》《装台》《主角》的严肃的正剧式现实主义手法,陈彦对《喜剧》的人物塑造创新性地运用一种“美丑对照原则”以强化小说的戏剧性和喜剧感。“美丑对照原则”由法国作家雨果率先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之作。作为兼通戏剧的小说家,雨果小说的戏剧性特征向来突出,陈彦曾公开谈及他对雨果及《巴黎圣母院》的喜爱和推崇,《喜剧》则借鉴了雨果戏剧性的小说技法。比如喜剧表演艺术家“火烧天头上寸草不生,长得奇险诡谲,是前抓金、后抓银的形貌……最终把一颗脑袋,就结构成了可以直接用来讲物理、天体、数学的棱形。加之他嘴大、耳大、鼻子大,眼睛却小如绿豆”[11]5-6的人物奇丑外形设置,与之对丑角艺术精诚所至的内在坚守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关系。根本上,“美丑对照原则”根源于事物自身裂变发展的矛盾性结构属性。
贺加贝、潘银莲、潘五福等人物群像均体现出鲜明的“美丑对照原则”。作为《喜剧》的核心人物,贺加贝极具喜剧天赋和表演能力,但作家并未将其塑造成一个拯救或传承民族喜剧的艺术英雄,反而以偏执又痴绝的思想方式、行为表现和命运走向深度诠释了戏剧性扁平人物及其脸谱化图式。小说中,贺加贝出场即设定的性格形象似乎并未发展变化,在忙碌到跌落谷底、迷失自我的演绎生涯里,他几乎从没冷峻反思过自己的戏剧事业、爱情婚姻甚至人生目标,他迷恋万大莲、生病罢演、抛弃潘银莲、跳楼自杀等一系列举动均遵从“热爱万大莲”的感性逻辑。换言之,他没有忆秦娥一般久经生活考验而完成人格飞升和艺术淬炼的内在精神与文化境界,每一次的演绎改造也是外力推动。事实上,他缺乏父亲火烧天那种内在能动性,以及忆秦娥、刁顺子所具有的强大精神擎力或性格能量。对此,陈培浩[1]指出,后两位让我们悲悯或敬佩,他们是有精神力量的,差别只在程度。而贺加贝更近于一个被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很难激发读者的共鸣或同情。这也正是贺加贝形象近于扁平而缺乏超拔之气的根本原因,却又同时造就了他偏执的深刻、痴绝的可敬和悲戚的无可替代性。
潘银莲是《喜剧》里非常特别的人物,她的个性骨气誓为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同时带着陈彦“小人物”的光辉而初心不忘,因此格外惹人怜爱。曾有学者提出,如果潘银莲没受伤会怎样?潘银莲形象的价值其实在万大莲,根本上她是活在万大莲“影子”中的人物。根据“美丑对照原则”,主张将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有效地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两个事物相反的本质特征。只有增大两者间的反差,才能更深刻地突出两个人各自不同的特质。从这个角度,潘银莲羞于人言的“缺陷”恰好与她跟万大莲几乎无差的外在美构成巨大落差和遗憾之悲,这个缺憾不仅昭示了她作为万大莲替身的可能性,也根本决定了她之后被贺加贝抛弃的必然性。何况,即使潘银莲没受伤,她也缺乏万大莲秦腔花旦的艺术魅力,虽然陈彦无意塑造另一个徒有其表的万大莲,甚至赋予她民间喜剧朴素恒常的真理光辉,但作为艺术性塑造人物、反映生活的有效方式,潘银莲“伤”得绝妙且必须。正是作家这意外的神来之笔,增加了《喜剧》故事的戏剧性、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小说内蕴的深刻性,由此亦可见作家一流的文学功力和悲悯仁心。而这样一个自尊自爱的“小人物”最终带着孩子离异回村的悲伤结局无疑进一步加深并强化了小说整体的思想内质和精神寓意,令人读后慨叹不已。
三、时空叙事的场景化
不同于《主角》既以时间推进主人公忆秦娥的生命史和秦腔发展史,又以情感、心理和诗词唱词开拓出多维内蕴空间,使小说叙述保持一种急缓相济、张弛低回的宽阔与浩荡节奏。《喜剧》是时空交融的综合性文体艺术。《喜剧》在“情节编织、矛盾构设、心理冲突的剖析、人物塑造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等方面更具有动作化特征,即使心理发掘也具有突出的激情特征,给人紧张、急促、兴奋与压抑的感觉。”[2]《喜剧》的时空叙述不是组构式,而是融通式,即把情节的起伏、心理的跌宕和人物的命运以焦点透视的方式集中以一个个场景故事架构出来。并且《喜剧》的场景叙事常常在人事叙述中嵌入自然或时代地理,将戏、艺、人和历史传统、生活世界、城市景观融合一体。根本上《喜剧》的场景化叙述所营建的是一种文化生存空间和生命伦理记叙,并突出表现于戏剧化场景和场景戏剧化等多维度。
(一)以戏剧性场景串联叙事
当场景用于叙事文学,它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内发生的行动……为事件的展开提供了时间和空间。”[12]《喜剧》不仅关涉贺加贝等戏剧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更是探讨喜剧艺术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代难题,因此小说多次聚焦戏剧人舞台表演现场,以及喜剧演绎大起大落失重发展的戏剧化场景。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记叙之重从没放在喜剧演员的声、台、行、表,而是贺加贝、万大莲,以及火烧天、潘银莲等人物形象背后的心理、生理、情感、欲望等命运纠葛和现实肌理。比起贺氏喜剧坊《大豪斯里的分居日子》《玛莎拉蒂的吻》《千万别上厕所》等剧,作家更意在贺加贝跟万大莲演出爆火的《扇坟》或贺加贝跟潘银莲表演《罚赌棍》被赶下台等情节之后的深层关碍,仅一个场景就凸显出潘银莲的人物心理、贺加贝的现实处境,以及疯狂索要快乐的喜剧观众:“几天过去,她还记得台底下那喊声:‘让潘金莲滚下去!(他们故意把她叫成潘金莲)’‘让赝品滚下去!’‘让假货滚下去!’……看着观众涌动如潮水,她又不敢下去,怕真有冲动的闯上来,打了加贝咋办?她甚至都想把道具火钳或吹火筒递给他一件,但又怕观众受刺激……那阵儿,她感到,用什么求天告地的方法都无济于事。观众就是愤怒了,狂躁了,找茬了,要怒斥你,甚至大有要放你血的架势。”[11]222-223
(二)以场景的戏剧化叙述浓缩时空
除了喜剧舞台内容的场景化、喜剧行业自身的戏剧化,陈彦也擅长以“如在目前”的场景叙事和时空结构一幕幕推进喜剧人的戏剧人生和命运交织。从戏中的艺术场景到戏外的现实情景,《喜剧》虽关注的是舞台上的“角儿”,但他们也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以场景写命运,亦以场景写生活,陈彦能运用写意的方式把生活中所有的“物件”变成可以表现人物心理及所发生事件的“道具”。因而《喜剧》的场景化叙事不仅增强了小说空间的历史感、时代感,也丰满了小说人物的生活真实和命运感。此外,陈彦尤善细致绵密地铺设细节,以场景物景情景事景刻画人物心理、行为动作或为后文伏笔埋线。譬如小说开头写贺加贝出场:“天快黑时,他看见廖俊卿溜进了万大莲的房里,还随手关了房门。那咯噔的一声,就像被针扎一般,让他很不是滋味。尤其是该开灯的时候,房里始终没有灯。关键是几个小时过去,里面依然漆黑一片,他就知道问题大了:廖俊卿可能得手了。”[11]1既见一个卑微暗恋者蹴在暗恋对象门前整整一晚欲抓现行的荒唐景象,也不乏插科打诨式诙谐幽默的语言所营造的欢快轻松气氛。正是作家杰出的语言能力赋予叙事文本活泼泼的新鲜感和即刻性,保证了小说叙述的在场感、动作性和镜像美,以及一种悲喜互参的艺术韵致与戏剧美效应。总之,《喜剧》的戏剧化场景叙事和场景化戏剧策略不仅从细部夯实了故事的时空结构,也从中观和宏观等维度保证了小说的厚重感、框架性和整体性,达到一种“叙事性动作强,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充满传奇性”[13]的独特艺术效果。
四、语言表现的舞台化
一直以来,“戏剧”是陈彦透视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文化思考的重要载体与窗口。“历史—美学经验、时代现实经验和人的情感、心理、欲望等主体经验,不仅构成《喜剧》的基本内容,也形塑了小说的文化立场和叙事肌理。”[14]《喜剧》的戏剧经验书写首先得益于数十年来作家对剧团生活的熟稔与热爱,转而成为小说家后陈彦以《主角》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殊荣,不应忽视剧作家陈彦曾在戏剧领域取得的光辉成就尤其是其杰出的戏剧专业能力。这种能力显著体现并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比如题材选择的舞台聚焦、人物塑造与故事性的并重,叙事方式和方法的戏剧化及语言表现的舞台化、动作化等。同时对对话性记叙的热衷,对唱词、台本、宾白、诗词曲的整练编排均可见陈彦对戏剧与小说的融通与新创。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认为,小说与戏剧根源相通——“每一部优秀的小说里其实都包藏着一部话剧”[15],并在《檀香刑》等作品中尝试以戏剧叙事策略融于小说语言规则,从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戏剧式小说语言。陈彦小说《喜剧》的戏剧化书写达至新高,其中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语言表现的舞台化及其艺术性创构。
(一)对话式叙述
对话技法原属戏剧,戏剧甚少叙述,主张以对话来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戏剧性对话不停留在对生活内容的言说,而是要指涉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冲突,由此写好对话历来是对作家功力的极大检验。中国传统小说向来重对话,“旧小说中叙述与描写很少,而以对话为最多。”[16]20 世纪台静农的《拜堂》、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及鲁迅的《阿Q 正传》《药》《示众》等小说均采用了对话式叙述。鲁迅在翻译西班牙小说家P·马哈罗《少年别》的附记时强调,这是“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形式的小说”[17],并亲身倡行戏剧化小说写作。谨承传统的陈彦台词功力极好,《喜剧》《主角》等小说的对话书写精准、精彩又不失典雅。尤其《喜剧》的对话不仅展露了人物复杂的个性特征、心理欲望和人格思想,也注重营设对话间性的矛盾和张力,用“对话”处理人物间的现实关系、运命走向或精神冲突,同时亦在叙事密度的调控与梳理中营造了一种笑中带泪的叙述氛围。所谓“言为心声”,语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来是立显的,比如潘银莲最后一次找史托芬时控诉:“你们的确聪明,你们能把丝毫没意思的东西,弄得将观众笑翻在地……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人(贺加贝),包装成了疯子……除此之外,已是非不分、麻木不仁,甚至想方设法地帮着作弄、坑害我,你有罪!你们有罪!!!”[11]364-365数句之间就把潘银莲悲剧命运的根源、贺加贝自我迷失的缘由,以及整个喜剧行业颠倒发展的时代境况全部抖落出来,她入木三分的形象赫然矗立。
(二)动作性对话
《喜剧》小说语言的舞台化不仅以对话式叙述推动故事,还体现在对话深处的动作性。动作性对话“要求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且“适合于他的身份,阶层,年龄,籍贯,性别”[18],包括那些意涵丰富的“潜台词”。作为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喜剧》“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19]“动作性对话”强化了陈彦小说的文质冲突和戏剧性。以十足的“戏味儿”推动故事情节走向,《喜剧》的多文本写作“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20],且“对话”以其精彩的伏笔和动作性对潜在的人物命运与矛盾冲突进行了立竿见影的引爆与抛出。总之,陈彦小说使不同文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小说与戏剧交融、混用以丰富故事情节安排方式;通过叙事逻辑、叙事张力的调度更换延长阅读期待、增加审美快感;剧中角色的交替出现,方便作家的人物赋形更方便读者直观;叙述视角多重切换,并以戏剧/戏曲穿插使小说文本具有独特的韵律感和节奏美等,均极大增强了《喜剧》整体的艺术性和美感。
五、结语
曾有无数作家打破小说与戏剧文体之间的壁垒,让小说拥有戏剧艺术的审美与优长。《喜剧》叙事以喜剧表演艺术家贺加贝为主线,牵引出喜剧人和喜剧行业的生存现实与时空情状。小说人物主要包括台前的角儿贺少天、贺加贝、贺火炬、万大莲、廖俊卿等,幕后的戏剧工作者南大寿、镇上柏树、王廉举、史托芬及生活圈层的潘银莲、潘五福、草环、武大富、郝麦穗等。而《喜剧》文本本身就是一帧精彩纷呈的戏剧,非常适宜舞台剧、戏曲和影视剧等跨文体改编(这个工作已在进行)。且小说不单将戏剧唱词引入小说文本演绎戏剧人的人生故事,包括戏剧相关的创作理论、术语、行话、表演程式等,甚至以喜剧为本体深入反思戏剧行业的时代发展及其现代化症候。因此,戏剧在陈彦小说中不仅是一种美学装置,更是一种主体观照,它所承载的文化思考与现实批判在媒介权力甚嚣尘上的今天具有催人深省的意义。
在小说戏剧化的路途上,不同作家会有不同选择,本文以《喜剧》为例着力探寻陈彦跨体写作展现出的小说戏剧化的审美特征与魅力效应,剖示陈彦“戏剧小说”的艺术独特性及其价值意涵。徐岱[21]认为,虽然小说的个体化阅读方式令其具有严密的程序结构,但相对而言小说仍旧是一种较为自由的艺术形式。而正因其自由的形式,使得小说可以与包括戏剧在内的其他艺术形式相交融,并以此建立其独特的艺术表现优势。总体言之,《喜剧》延续了陈彦小说长期以来所秉持的文学创作理念,充分汲取了戏剧的外型机理与内在意寓,从而具有了戏剧艺术的精神品格和戏剧化的美学倾向,并显著体现于人物塑造的脸谱化、时空叙事的场景化和语言表现的舞台化诸层面。然而,陈彦小说的戏剧化书写不论作为其剧作家身份的本色展露或意外回归,均昭示出陈彦对戏剧行业的由衷坚守和永恒热爱,其凝聚着当代小说的知识、道德、思想、文化与艺术经验,也镌刻着一代文学家对民族文化传承和戏剧现代性的回眸与深思,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典型性、象征性和时间性的隐喻与召唤价值,包括媒介思维等,值得更多期许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