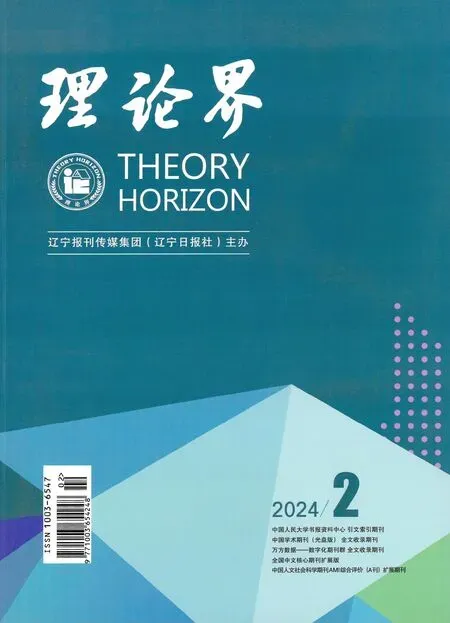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楼庭坚
引言
中国传统在近代的现代转化是近代史领域中经久不衰的中心议题。然而,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方的解释框架。在这些历史叙述中,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根深蒂固。例如,我们熟悉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了“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模型,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则阐述了“传统—现代”(Tradition-Modernity)模型。在西人的笔下,西方是确定的、已知的,中国是静态的、被动的,现代化仿佛是西方“示范”、中国“接受”的“连续性”的单向旅程。这固然与其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有关,也是一种“后见”与追认。回到历史现场,国门洞开,世变日亟,身处“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近代学人对传统与现代的切肤体会,或是一个更值得切入的角度。其中,钱穆(1895—1990)与胡适(1891—1962)各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思考记录。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前者土法炼钢而成大学者,能贯通,能深耕,著述遍及四部,以经学研究起家而精于诸子学、理学、史学;后者兼受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实证史学影响,“科学方法”名扬四海,于中国哲学(思想)史、明清小说、禅宗史诸领域皆有开风气之功。二氏大相径庭的治学方法,与彼此相去甚远的文化观念有关。钱氏特重民族传统与精神,相信善用此中独有的文化特质与历史潜力,“正可在此时代之黑暗中放光明”;〔1〕胡氏致力于以评判的态度再造传统,认为“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2〕有趣的是,二氏的关怀皆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说是其途虽殊,所归为一。
在今人的历史书写中,钱穆与胡适各自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位列近代思想谱系的两端。在当时,二氏虽亦有交往,后终成陌路。钱氏以为胡氏一派治学不崇文化精神:“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3〕胡氏则在日记中称钱穆等“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4〕当然,二氏丰富的学说意蕴与思想光芒并不能在简单的定位与意气之争中展现,实际上,当一名学者被贴上标签,其不幸也自此始。笔者将利用二氏中英文著述与档案资源,细致梳理其对传统的看法与文化认同,揭示两条不同的通往现代之路。
一、绵延抑或断裂:钱穆与胡适对传统的看法
承认本民族固有传统,是钱穆论学的整体基调。他常将“传统”与“文化”连称作“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中,他曾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是人类各方面生活的总汇,具有长时间的绵延性。一民族的生活在绵延的时间中演进便有了文化,此文化也成了该民族的“生命”。〔5〕由此,文化传统与民族生命相联结,文化的根据到了“历史”上。钱氏曾说胡适对国故“虽未作一笔之抹杀,但既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有文化之传统,则意义已偏”,〔6〕姑不论此言当否,但于此可见钱氏对文化传统之重视。在《国史大纲》开篇,钱氏更是直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齐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7〕唯历史传统能绵延持续,方“谓之有生命、有精神。”〔8〕唯对此民族文化大体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9〕
文化传统的绵延演进,钱氏称作“现代化”。在体现钱氏学问最后进境的《晚学盲言》中,钱氏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句,称这个“因”(也就是沿袭)就是传统,这个“损益”就是当时的现代化。显然,钱氏是从“常”与“变”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与现代化,因此,秦汉以降儒学的发展损益虽有不同,皆可谓因于孔子而求现代化,而整个文化传统,就是五千年所积的人文化成。他进而批评“西化论”者变革故常。在他看来,在过往历史的不断演进中生成的传统,是现代化的活水源头。这正如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所言:“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10〕
传统“生命”的现代化体现在个体的“小生命”中。钱氏称其人生自昨日婴儿至今日耄老,有一贯穿其中而不变的线索即“生命传统”。它“实常在今日国人所提倡之‘现代化’一词中”。〔11〕如同文化大传统需在历史记忆的保存下方有生命,若不记得此身何来,亦将失去自我,“必打破传统来求现代化,则我之现代乃在台北之外双溪,而我犹忆我乃从无锡之七房桥来。”〔12〕钱氏又说,心内之记忆可由自己作主,身外之遭遇则非自己能作主,二者分别对应“性”与“命”。人皆可在自己的心性上努力,这是人生最大的自由、平等。个体的记忆是小生命之所系,民族的历史记忆则是文化生命所在。唯注意民族精神,“乃可了解此一文化体系之意义与价值”。〔13〕钱氏认为较之西方,中国绵延的历史是“同体”而非“异体”的,中国人的态度是反观自身,“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里面。这样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14〕故中国文化太看重人生而忽视了外在尤其是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观念的科学精神、民主政治、个人自由。中国文化想要实现现代化,当在经济、政治、知识三方面学习西方,如此不仅可以容纳西方科学文明,“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15〕
要之,钱氏特重本国绵延的文化传统,以之为民族“生命”。其现代化主张要求根植于传统,不照搬西方,不然“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亦学不像他人。”〔16〕
再来看胡适。“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7〕胡适《先秦名学史》此语,可说是其毕生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的体现。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胡适抛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哲学在宋明时期未对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如今中国已与世上其他思想体系相接,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方法可以补中国所缺的方法论,那应该如何消解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使现代文化的精华融入中国自己文化的精华中呢?胡适彼时的看法是先秦儒家以外的学派对科学方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度,从“非儒学派”中可以找到适合哲学与科学生长的土壤。
此后随着胡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开,他对近世哲学的认知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中心关怀仍在找到适合现代化的传统资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1919)中,胡氏盛赞清代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因为考据学发达,西洋思想输入,而今日学术思想的源头在清代学术与西洋学说之中,“我们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8〕到《戴东原的哲学》(1925),胡氏更说清代的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功绩甚伟,今日中国思想可走的路便是继承致知穷理之遗风,修正戴震、颜元之说,“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19〕
胡氏从先秦“非儒学派”找到了逻辑学,又以清代的考据学对接西方科学方法,可说是积极发掘传统资源了。然则时人眼中,20 世纪30 年代前后的胡适已经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化身为“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了。钱穆便批评他道“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20〕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1929年胡适应《中国基督教年鉴》之邀,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按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的解释,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抗拒西化、选择折中、全盘西化三种文化主张,以为抗拒西化之论已经不存在,折中之论为变相的保守论,故应该“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21〕这其实是其一贯秉持的“反对调和”“反对盲从”观念的体现。在《独立评论》第142 号的“编辑后记”中,他也解释说其全盘西化论是出于文化有“惰性”的考量,“惰性”下旧文化自会与西方文化折中调和成新文化,故而“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22〕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在传统中开出新文明呢?胡氏的英文文章《中国的思想》(Chinese Thought,1942)〔23〕给出了答案。此文将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一千年的上古时期也就是古典时期,百家争鸣,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由精神的传统在此奠定;公元后第一个一千年的中古时期,佛、道盛行,中国面临把民众从宗教狂热中解救出来的挑战;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由于朱熹的理学重致知精神与格物方法论,中国思想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成功摆脱中世纪的影响。到了清代,科学的方法论产生了。可以看到,宗教在胡适处是现代化的负面要素,诸如“(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24〕之类的论调在其著述中屡见不鲜。胡适之意昭然:先秦时期留下了理性、自由与怀疑精神的火种,尤其其中的怀疑精神是一个文明国家发生深刻而彻底的文化变革的前提。〔25〕当吾人排除传统中的愚昧、迷信成分,恢复理性精神,对接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这个古老的传统将以新的面貌发扬光大。这也是胡适晚年《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1962)演讲的核心观点:外来文化的传入不会有损接受一方思想的价值与性格,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后的结晶表面虽看似带有西方色彩,实质“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26〕
要之,钱穆认为绵延的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生命”,文化的演进是“现代化”,因此,当一边根植于传统,一边吸取西方科学民主精神,否则“现代化”就是无源之水。胡适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合吸收现代文化的土壤,其西化论调即是此关怀下的策略性主张。他特重先秦的怀疑精神,否定中古宗教的价值,希望以理性主义对接西方的科学思想,建立一个吸收西方而恢复理智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钱氏思想中的传统是连绵的,而胡氏思想中作为“现代化”资源的传统则有中古时期的断裂。
二、普遍抑或特殊:钱穆与胡适的文化认同
钱穆论史,特重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阐发。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说历史研究有“特殊性”“传统性”“变异性”,其中最当注意的是“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历史为传统之表,文化为传统之里,故文化体系亦贵在特殊。文化研究当求其异,而非求其同;当寻其长处,而非寻其短。钱氏并不高抬某一文化以使之具备“普遍性”价值,而认为采纳不同个性的文化的优点,方能建构理想的世界文化,“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圭臬,硬说唯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27〕
基于此观念,钱氏称胡适对于中国文化只是贬低,胡适把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当作“世界各民族一种常识的理想境界”是极深的偏见,并说按胡适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中国文化则只是一种最普通的常识见解,无理想、无道路、无成就、无价值,主意只在不向前。”〔28〕在某种程度上,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正是二氏之间巨大的观念鸿沟。在钱氏眼中,中西文化天然有别,中国文化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中国人主张向内凝聚,西方人主张向外扩展。〔29〕这反映在学术特性上是中国重贯通,求达乎于道,西方重专门,受限于各人才性与职业需求;〔30〕反映在观念系统上,世界可分为“物世界”与“心世界”,西人崇物,中国则不贵物之多,而求心之安,“使此心自由自在,不为物缚,不受物占,清明在躬,虚灵不昧,也自会领略到人生寻乐真谛。”〔31〕
钱氏又认为,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便在于以人配天,达“天人合一”之道,也就是心物合一。人类可以通过后天之心了解先天之性,进而知天。这犹需由心出发,“主要更在于心对心,此乃人类最大的自由。”〔32〕钱氏学说一个很特别的点便在于以心性阐明“自由”。按钱氏《湖上闲思录》,他以“自由”的反面为“干涉”,可见他所言的“自由”近于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概念即免于干涉的自由。在《人生十论》中,钱氏从由“我”作主的角度对“自由”作了抽丝剥茧的考辨。
他援用了实用主义宗师詹姆士(William James)对“我”的三个分类即“肉体我”“社会我”“精神我”,称前两者都不得自由,唯“精神我”是我心自由自在的知觉。他又说到教育学大家斐斯泰洛奇(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的“三情状”的“道德情状”具备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由人类德性产生,此道德力量下人不觉有自己,所感者唯有德性。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正可与之相发明。钱氏以为,儒家的安身立命便是指将种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人类自心自性也就是“道德情状”上,“无论如何,人类若要尊重自我、自由、人权、人生,则必然该尊重人类的自心自性,而接受认许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在承认此理论的基础上人类方可追寻自由,这是“中国儒家精神之最可宝贵处”。〔33〕
要之,钱氏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发,在中西比较中,他认为西方重“物世界”,中国重“心世界”,文化理想在天人合一。他并不以“自由”价值为西方之“殊相”发展出来的普遍性价值,而从孔孟之心性论去讨论自由,并以为尊重自心自性是自由的前提。以心性证悟其本,再以治平之道尽其用,是为今日学术之康庄大道。〔34〕钱氏心声呼之欲出:“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35〕
较之钱氏,胡氏在中西比较中,更喜用“文明”一词而非“文化”。按胡氏的定义,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36〕这界定很带有实用主义色彩,须知杜威在《哲学的改造》对真理的界定就是结果显示的功效。〔37〕胡氏又秉承师说,以哲学为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如此,文明便是民族回应冲突的成绩了。针对当时普遍以中国重精神生活,西方重物质生活的风气,胡氏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中表达了相当的不满,称东方文明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充分承认物质享受的重要而以理智精神进一步求精神的满足,故反而是理想主义的。在《漫游的感想》(1927)中,胡氏进一步发挥此观点,以“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38〕区分东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文明视人为牛马,未必能称为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增进了人类幸福感,反而有生成“精神文明”的可能性。在《请大家照照镜子》(1928)中,他更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39〕这些论断很容易被误解,然结合语境,用意却昭然:吾人不能以对精神文明的重视为物质落后的借口,唯有彻底认错,死心塌地学人,方能尽快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现代国家。
胡、钱二氏同在追寻现代性的路上,而沿途的风景是不同的。钱氏处的“现代”并非一个共相,按其说,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且中国文化独具特色,乃至为天下先。胡氏则认为世界文化有一自然的趋向,即“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40〕此方向以科学增进幸福,以社会化经济制度提高生活品质,以民主解放思想。显然,胡氏所求的“现代”是一元的,自由民主是中西共存的普遍性价值。反映在学术上,钱氏的治学思路如其《中国思想史》所言:“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期。”〔41〕不以西方思想为宇宙真理之大全,方能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思想史之地位。胡氏的哲学史研究则有明显的以西释中之倾向,他推崇的是章太炎以“佛教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寻出一个条理系统”〔42〕的思路。这点虽在胡氏以“思想史”观念代“哲学史”后改变,然其在中国传统“找(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东西”的问题意识则未易。
要之,钱、胡二氏同追寻通往现代之路,然钱氏更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胡氏则倾向于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并建立普遍性认同。在治学中,钱氏注重对传统命题进行现代阐释,胡氏更致力于寻找西方问题的中国经验。
结语
作为独树一帜的学术大家与思想巨擘,钱穆与胡适开辟了两条迥然有异的通往现代之路。钱穆就像他颇为赏识的每到一处即兴建寺庙,随后飘然往他处再建,如是反复的虚云和尚。胡适则如他反复提及的佛典中的救火鹦鹉,看见曾经居住的陀山,心下不忍,以水浸湿羽毛,飞而洒之。二氏皆可谓力小任重,愿力宏大。他们各自所尽地寻找传统之“特殊性”以为国故招魂、充分吸收西方的“普遍性”价值以再造传统的努力,使国粹终得保留与发扬,并留下了自由主义的火种。“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相较于将前贤们列入各种思想阵营,总结其思想结晶,完成其未竟之志业,或许方是吾人肩上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