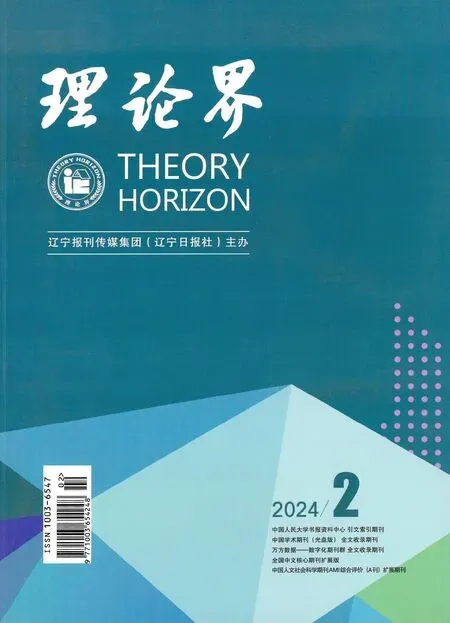美的标准能否造就标准的美
——对康德“美的理想”的当代思考
韩 钰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阐述了美学范畴中诸多概念的内涵,也为美学的边界领域做了划分,他使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起来。直到今天,学者仍在尝试对康德“美的理想”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意义辨析。尽管如今康德的美学思想受到现实的挑战,他的很多理论也被很多学者加以审视甚至批判,但总体而言,康德建立的现代美学理论和关于美的概念至今仍对人们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看法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当代的研究者和理论家在很多时候都无法脱离康德本身划定的美学范畴另起炉灶,足见其智力工作之有效,理论统摄力之强。
当今的社会文化面临同质化与多元化交织的复杂状况,不同社会圈层、文化群体及学科领域都发表过对美的问题的不同意见。有关美的问题早已溢出学术讨论或艺术创作的范畴,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生活中,人们渴望美、追求美,但有时却会迷失在对某些固定的、单一的标准之美的追捧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让我们以康德关于“美的理想”的论述为出发点,检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对当下生活中的审美状况进行反思,这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康德对“美的理想”的论述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为“美的理想”专设一节。在正式讨论“美的理想”之前,他先对美的种类做了区分。康德认为美有两种,一种是不基于概念的无目的的自由美,另一种是基于概念的有条件的依存美。前者以同人无利害关涉的自然物为代表,后者则是人类社会中有目的和对人产生意义的各类事物,包括人的形体本身。在此基础上,康德将自由美总结为纯粹的趣味判断,将依存美视为美的非纯粹趣味判断。〔1〕
在康德看来,人类社会中依存性的美数量众多,而纯粹的美则有限。以概念和目的为前提的依存美在体现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包含了理性和道德的因素,具备“有利害”的应用目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审美无利害”和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因此,有人认为他对依存美的肯定似乎“突破了他对美的严格规定”。〔2〕康德对美的分类体现了他“解决内容和形式的矛盾问题,并对美的内容和现实性进行强调”的用意。〔3〕由此,依存美被康德确定为“美的理想”。
“美的理想”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审美的规范观念,其次则是理性观念。〔4〕康德认为,“理想”意味着“一个符合观念的个别存在物的表象”。〔5〕每个人对于美的观念只在各自的意识中形成,其来源是主观的个体情感而非客观概念。它无法通过确定的定义被固定下来,需要经由人的想象力进行表象的描摹和显现,由此就产生了关于美的规范。美的理想是一种在感性形象中呈现的理性观念,这种理性观念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含有内在的目的性。这种美的理想内在于人本身,诉诸人的形体,可看作对“以人为目的”的最高价值的探索和追求。
二、美的标准:想象和技术在“美的理想”领域中的互逐
想象是理念的中枢环节,是人的一种先验能力。事物的存在有其时间连贯性,要想全面而完整地认识某物,不能单凭其某一时刻呈现的表象,还要对它存在的整体过程有所认知,而这种对事物“非当下”状态的思考需要经由想象才能达成。借助想象,人类才有可能对一个事物的完整表象拥有感知。康德认为,想象具有创造力,产生想象力的前提是事物自身的存在,唯有借助已存在的对象,才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换言之,在美的理想中,不存在对美的“凭空”想象。想象力以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方式运作,不过我们知道,它的运作以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离不开感性材料基础和人的认知观念。康德设想“同一种类许多个体的一致性的中间值可以成为衡量全体的普遍标准”。〔6〕这说明他认为通过想象力将人所见的同类感性材料相互叠加,就可以运用类比的手段从中得到某种直观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就构成了“美的理想”的基础。
这种标准的建立并不简单。以对人类面容建立美的标准的活动为例:个体接触的人数量有限,长相各异,每个个体经想象所得的“美人脸”也各自不同——这不意味着人们对彼此眼中的美人定然持否定态度,而是表明了这种标准的灵活性。将公众想象的不同“美人脸”呈现出来,我们有可能看到介于某个范围内的近似美,但很难达成完全确定的共识标准。就像“明眸善睐”“唇红齿白”“浓眉大眼”……都是公认的美人标准,但是多亮的眸子最清澈,什么样的红唇最有吸引力,眉毛浓到什么程度最好看……这种对五官的语言文字描述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概括性,但在现实中这种所谓的标准往往只可体会而难以量化,很难切实地明确下来。大体上人们对美的认识遵循的是非固化的近似标准,这种标准不是一条线,而是某种尺度或范围。
这解释了为何仅有美的规范无法成就“美的理想”——因为它只是想象力在一定的经验范围之内形成的一个模糊标准。不同的人对美的认知不同,因此,这类标准只能是相对的。基于这种认知,康德认为“美的理想”应当超脱想象力所凭靠的经验,借助理性进一步达到共性标准。
人力有限,想象力所依托的经验实体也存在一定的范围。正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尝试利用技术手段突破对人的限制。技术作为人的延伸,顺应人想要提高自己能力的诉求,为实现人的意志而持续发展。康德“以平均值作为衡量全体的普遍标准”的设想与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基本逻辑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尽管我们可能不清楚在“同类材料的叠加类比”中,想象力是如何运作继而产生美的规范的,但随着科技发展,对某种标准性规范的追求似乎变得越发可行。
在漫长的关于“美的真理”问题的讨论中,美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探讨问题背后的真意。同时,现代科学以一种实证方式逐渐进入这一话题,试图测量、描述甚至归纳出现实的审美标准。在20世纪末,已有秉持进化论的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人的审美标准形成于进化过程中,脸部的平均性、对称性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对健康与否的判断构成了对面容美感的认知基础。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在大量实验得出的数据基础上宣称:人类在感知领域对面容美存在高度一致的辨别标准,而这种标准与年龄、种族、文化等具有相对性的社会经验无关。〔7〕这表明有些学者试图说明,整个人类群体在根本上共享同一套有关美的客观标准,他们认为,对海量数据的归纳可以证明美不是主观的或相对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美的影响不过是在其主旋律上叠加的附调。
递归神经网络领域专家尤尔根·施密德胡贝(Jürgen Schmidhuber)于1998 年分析了人脸各要素的几何特征,以各要素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为参考探讨人脸美丽的标准。〔8〕学者开始借助计算机程序学习并总结人脸的吸引力规律,利用科技为美制定范本。2002年,中国新闻网转发的一则报道称,美国某网站用计算机合成了号称“梦幻级的脸蛋”,她“拥有丽塔·琼斯的媚眼,凤凰女茱莉亚·罗勃兹的金发,珍妮佛·洛佩兹的颧骨,蒂雅·李欧妮的鼻子,和安吉丽娜·朱莉的嘴唇。”〔9〕这张号称集结“50万民众心目中最美五官”的合成图片一经公开就激起哗然一片,因为它不仅不美,看起来还很不协调,令人大失所望。
2015年,面貌对比(facial mapping)领域专家克里斯·所罗门(Chris Solomon)利用电脑程序制作“世上最美的男女面容”。他的程序参考不同的嘴唇厚度、鼻子长宽度以及发际线高低等数据,以各色男女明星的面部特征为样本,最终生成的模拟人像容貌清秀,比2002年的那张“最美五官”好看得多。〔10〕尽管因为选取的都是欧美国家的白人明星,所罗门团队被质疑缺乏整个人类群体面孔数据的普遍性,但将这组图片放在技术发展史中,能够让人意识到随着合成技术手段的发展完善,随着人脸样本数据库不断扩容,“标准的美”越来越可能通过技术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技术的进步刷新了人对科学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随着机器识别的精度变高,通过足够多的面部数据分析和对关键点数据的采集,甚至加入人工智能领域对数据的学习和创造,技术领域对于美的标准的建构在21 世纪朝着愈加精细化的方向走去。
在《判断力批判》中,审美活动作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出场。感官获取感性材料,想象力对之进行加工并生产新的表象,同时知性能力归纳和综合想象力提供的繁杂表象。在自由游戏中,想象力和知性共同被激活,达到和谐一致的境地。传统的审美观认为想象力可以自由地无限延展;而现代科技则致力于对“美丽密码”给出客观定量的标准。信息学研究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分析的三个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这种转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局限身边的个体样本,而是全体数据;(2)由于海量数据带来的信息混杂,我们能够得到的分析结果往往是宏观的,因此,我们不再关注精确性的意义;(3)我们对事物及事物间内在因果关系的认知转化为一种简单的相关关系认知——这正是机器处理数据的方式。〔11〕
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康德设想的想象力在审美活动中所发挥的整合重组功能持续向前推进。相对地,自由延展的想象力也有被新兴技术吞并和取代的风险。具体而言,计算机庞大的存储量和运行速度为感性材料数据的处理提供了足够高效和全面的技术支持,消解了时空带来的人力限制的束缚,给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但与此同时,技术基于工具理性的运作方式在审美活动中渗透各个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作为人对于美的看法,反而限制了想象力的自由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在技术参与下对现实的美的问题进行探讨,有可能将导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并达到某种确定的标准。在此过程中,我们对美的认识是否不再自由,我们对美的判断会更加全面还是趋于狭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随着技术进步变得更为复杂。
三、经验条件:多元景观的审美情境
机器学习以目的为导向,技术将关于美的普遍标准作为处理数据的初始设定,它将运用各种方式去接近这一结果。尽管达到某种普遍性的审美理想或许会成为人类对美的认识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多元文化共存、审美旨趣各异的现实情况也将持续存在。在论及为何不能将经验范本作为美的理想时,康德指出,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经验,不同时代的人也有着不一样的趣味,因此,关于美的经验具有相对性,没有必然的普遍性。传统的美学很少考察经验性的审美现象,也不太顾及美和艺术在不同民族和历史时空中的具体情境,更多从观察者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将复杂多元的审美现象作为材料隐没在其构想的一般标准之中。这种居于客位的研究视角没能从特定的文化情境出发,解释本地人对美的认识和想法。
审美普遍性能在多大程度上通约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原则?它是否只是其他文化在当下对某些文化的某种妥协?对相关问题的反思从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始。很多人类学家对小型社会进行田野调查时尝试对当地居民的审美活动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发现不同社会中人的审美判断受到其所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塑造,也就是说,对美的认识和判断具有文化的相对性,人所栖居的意义之网以他所处的实际文化情境作为背景和编织原料。人面对不同的审美对象所产生的关于美的判断无法脱离情境。“要想按照任何普遍的标准来衡量美的价值和形式,那将是困难的”,〔12〕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存在于具体的文化场域之中,从美的发生发展到对美的认识鉴赏活动也都寓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具有强烈的情境性特点。可以说,将美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情境中去理解和审视是一种必要步骤,非此不能得到关于美的真正知识。
对文化相对性的认识引入了审美的情境化问题。正因为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图景,在分析具体的审美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面对具体情境。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主客体和文化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完整的审美活动。对特定文化情境中具体文化关系的重视正是对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的尊重和确立,在“人是目的”的终极理念指导下,作为一般性原则而被抽象出的美的概念,被拉回到人的审美实践活动中去检验和纠正。同时应该明确,关注具体的文化情境并不是对建立美的理论的抛弃,而是要求我们在考量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
四、人是目的:当美的理想照进现实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逐步发现了大写的“人”。始于14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发端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肯定了信仰中的人的独立性地位;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则以人的理性作为内核,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及其认识能力。“美的理想的提出,表明康德美学在本质上与人的生存和人性有密切关系。”〔13〕康德的美学吸收欧洲思想运动的成果,他认为任何美的经验在发生的过程中都暗含一种目的,这种目的的最终归宿指向人本身。这是康德始终以人为目的的目的论的体现,这一理念作为前提贯穿了他有关美的论述。
人即目的,人非工具。这句话以一种笃定的姿态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为中心和起点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强调人的价值,有的学者将之视为康德伦理学中“最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性的成果之一”。〔14〕将人从宗教和欲望中解脱出来,这在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从这一点看,“人非工具”理念同其所诞生的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拉扯的张力是推动人们不断认识自我和所处环境,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但也应当承认,社会生活中以具体的人为工具的实践活动实际存在。为了达到一些实用目的,我们常常将人本身作为工具或手段去使用。人类学家在工作中对研究对象某时某地的文化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他们的个人体验,包括处在现场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境感知”,都是辅助他们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身体成为将田野带回案头的载体。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辩证看待康德的“人非工具”论,认为“人是理想中的目的和实际生活中的手段的统一体”。〔15〕
目的和手段之间确实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可以互动甚至互换的,这不意味着“物成了主体和目的,人成了客体和手段。”〔16〕因为归根结底,现实中的“物”的目的看似是在通过人去实现物的主体性,实际上还是经由物的实现而服务于人。这种类型的人的“物用”仍以实现人、发展人和解放人为目的。康德的主张并非对物的主体性的漠视,而是穿透生活实践中“人—物”和“人—人”关系直达人类活动的本质,在这个层面上,就不必一味追究在某个活动的具体环节中,个体的人究竟是否曾作为工具或手段了。
后殖民时代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解构了西方经典美学体系,还其他文化和艺术的持有者以自我解释的空间和主体性地位。但现代社会对商业化和大众性的过度强调反而成为又一套普遍话语,将社会文化生活兜头纳入,再次搁置了处在不同情境中的多样化审美主体和对象。人的身体在对美的追求中一度被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或者符号用来彰显特定的理念或美的理想。奥利维耶·阿苏利(Olivier Assouly)认为,“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17〕学者周宪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审美追求同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消费观念联姻后,理想的人体美在市场中以一种“美的神话”的姿态被不断生产,“美的脸庞和身段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人人争相竞夺的文化资本……”〔18〕无数商业广告通过活力四射的俊男美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标杆诱惑着大众进行消费,在此过程中,理想的美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符号象征,无论是被表述为“追求健康”“做更好的自己”抑或诸如此类的其他口号,都离不开消费社会理念的主导。
实践中也出现了反思,消费者开始思考为何只有拥有“理想身材”的模特,才有资格出现在面向公众展示的广告和舞台上。〔19〕在此背景下,“大码模特”等新兴商业代表人出现,这同时也催生了新一轮对“审美资本主义”的批判。阿苏利认为享乐促进了消费的多样化,多样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带来审美品位疆界的模糊,品位由此囊括了更多的文化和差异。“……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20〕这也说明了,无论是在理念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让美的理想回归“人本位”是一直以来的主旋律。从“把身体视为承载理想的手段”到“将身体还原为身体本身”,解放人和突出人的根本目的被再次达成。
康德对审美的看法在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中展开,他关注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快感。在主客体的关系框架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具有中心和主导地位,康德重点强调人的趣味判断和审美感受的形成。人通过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平衡来寻找和定义自身。审美实践是人同所处文化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建立互动关系的一种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不是目的,审美才是目的。对美的标准制定被规范和统一在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理想之中,而不再是一个静止、孤立的问题域。
余论
在当代社会,人类社会的诸多要素被资本化和商品化,人们对文化的认知也以技术话语的方式被结构和组织起来。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试图超脱传统,以一种批判性反思姿态介入生活世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失去往日灵韵,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认为在商品活动中,审美化成为某种经济上的策略:“一旦同美学联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21〕借助资本和技术带来的便利,关于人类本身的探讨在各个学科领域持续进行,其中不乏以生物学为基础从物质角度对美的感受的探讨。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助力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中成为一种风潮或“刚需”,但在传统的人文学科比如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等领域中则体现得较为有限,偶有借鉴,往往也仅限人文社会领域各个学科之间的互通有无。
尽管仍然有学者认为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这三个对象进行边界明确的划分非常必要,但笔者以为,如果人文科学推到极致后仅存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就正如同自然科学缺少科学理想的指导和伦理的规约一样,其后果都是不可想象的。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相异并不代表其研究的断裂和思维的不可通约。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研究,都植根于人的主体性结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根本上来说都离不开人的发展。
现代科技已突入文学艺术领域,并且以其特有的技术路径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参与到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探讨甚至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来。而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这头,尽管学者承认技术改变甚至塑造了人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这种影响也在对社会文化领域发生无孔不入的渗透作用,除了将技术手段作为工具辅助人文研究或对数字时代中的人文发展路径的现状进行探讨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坚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新技术时代下的文化现实,借助新的材料提炼和更新理论思想,寻求美学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