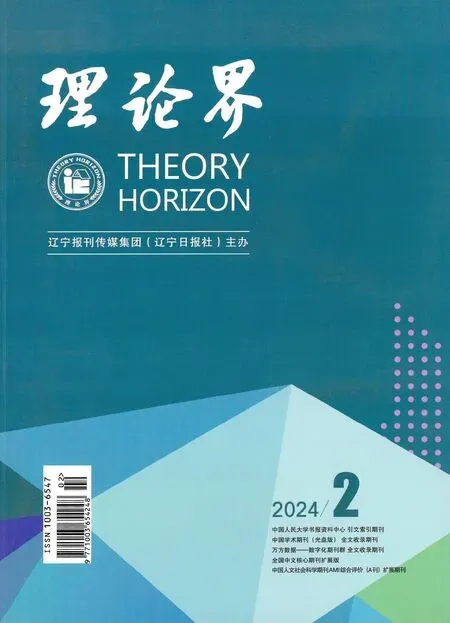善由何而来
——约翰·菲尼斯的解释
唐东哲
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不仅是新自然法学派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更是法哲学家中伦理学著作颇丰的一位。他的伦理学思想不仅为他的法哲学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作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说明,而对于善由何而来这一基本问题,菲尼斯立足于当代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这将带领我们在当代的话语下重新审视一些伦理学中的古老而经典的问题,并从中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善并非来自事实
正如菲尼斯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哲学体系是在解释阿奎那哲学的过程之中建立的,两个文本是可以相互阐明的。〔1〕而阿奎那的哲学导师是亚里士多德,并且其伦理学大多是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释过程之中建立的,这样菲尼斯在谈到善时,不可避免地就首先要对亚里士多德的善概念进行一个讨论。下文将指出,正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由何而来的考察,菲尼斯提出了自身独特的解释。
毋庸置疑的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真正意图是确立个人生存的真正目的或善。然而,这个主题下却包含了两个子问题:第一,善是什么?第二,善由何而来?在菲尼斯看来,在对亚里士多德善理论的研究中,善是由何而来的问题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菲尼斯所说的善的由来的问题,也即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握善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关乎善本身为何的内容上的问题,在逻辑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占据着一种优先性。但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研究者产生了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亚里士多德将善不仅置于自然秩序之中,并且置于人生意义及完满状态的实现之下,这就使善不可避免地和许多其他概念发生了关联,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将其和“欲望”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将其和“自然目的”——理性功能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零散的片段中,亚里士多德又将善和我们的实践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在善的来源这一问题上,基于这些不同的关联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路径。
第一种解释认为,善来源于我们的自然欲望。阿德勒(Mortimer Adler)认为,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解读的过程中,可以区分出两种欲望,一种是“获得的欲望”,另一种是“自然的欲望”,前者用“想要(want)”来 表 达,后 者 则 用“需 要(need)”来表达,这样一种需要来自我们的人类本性。〔2〕在伦理学中,我们共同的人类本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欲望,而这些自然的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即是真正的善,因此,善是通过我们自然的欲望来把握的,凡是自然的欲望所指即是真正有助于个人完满的,而自然的欲望是植根于先天的本性之中的。举例来说,就知识是一种善来说,求知的欲望即是根植于我们本性中的自然的欲望,因此,知识是一个真正的善。但是菲尼斯却指出:亚里士多德虽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反复提到了“善是可欲的”,但是这样一种善是通过一种先天的自然的欲望被我们所把握的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是值得我们欲求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善的任何一个段落中也并没有说,这种善是由我们的一个先天的欲求所确立起来的。阿德勒的这种解释视角也影响到了理论家对阿奎那哲学的解释,麦金纳尼(Ralph McInerny)认为,阿奎那的善是原始欲望的对象。〔3〕无论如何解释亚里士多德哲学或是阿奎那哲学,在菲尼斯看来,上述做法都是从“事实”到“价 值”的 非 法 推 论(non sequitor)。一般认为,在休谟以前的哲学家不曾留意这个问题,然而菲尼斯却质疑,虽然休谟公开宣称了这个逻辑上的真理,然而他却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理的。菲尼斯宣称:“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也会乐于承认不能从事实推出价值”,〔4〕这一点将会在后文得到解释。
第二种解释认为,善来自我们的自然目的。这样一种解释普遍地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在识别善的方法中最为主要的,它的立足点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一贯的一个推理:每个活动都指向了一个善,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完善,而我们在这里所寻找的是属人的特殊的活动,也即是理性的活动,因此,人的善在于理性活动的完善。在这样的一种基于“目的”的推论中,人类的特有功能扮演着关键角色。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亨利·维奇(Henry Veatch)认为,寻找人类理性活动的目的是识别善的真正方法。处于后休谟时代,维奇不可能无视休谟所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像菲尼斯那样为亚里士多德辩护,在他看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出发,我们不必要在自然秩序之外去发现善和价值”,〔5〕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善早已在自然秩序的目的中建立了,而人的这种自然目的实现就如同一颗橡树种子朝向橡树的实现那样。
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基本立场是一样的,即主张亚里士多德是从自然事实出发推出道德价值,也正是因此,菲尼斯认为第二种解释同样是不合理的。第一种解释不仅是一种从“事实”到“价值”的非法推论,更为危险的是,它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视为近代道德主观主义的来源。这种解释包含在霍布斯的以下论述中,“凡是我们欲望的对象就是善,而凡是我们憎恶的对象就是恶”。〔6〕这样一种解释不仅质疑了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善的客观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使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衣钵的阿奎那所提出的自然法理论失去依据。但是,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一无是处。首先,霍布斯正确地指出了,欲望在道德上有一种积极的能动作用,亚里士多德也会承认,欲望直接地推动了我们的行动,但是菲尼斯会否认的是,伦理学中所讨论的欲望是一种先天的、独立于理性的自然欲望。相反的是,这样一种欲望是经由了理性审视的欲望。其次,维奇在解释亚里士多德时明确区分了两种目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虽然他宣称道德目的早在自然目的中得到了建立,但是他也提出,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物,这也使人在追寻善的方式上不同于自然物追寻善的方式,这样一种不同就表现为“人类的特有功能”,因此,理性在把握善的过程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二、善来自实践理性
菲尼斯在上述的批判中表明了自身的立场:我们不能够从自然事实的立场前进到道德命题。同时,菲尼斯也表明了在把握善的问题上,有两个因素不能够被忽略,一个是欲望,另一个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这两者都是错误的结论提供给我们的有益提示。菲尼斯在对这一问题提出自身的理解时,充分地考虑了这两个因素,并尝试把它们融入一个前后融贯的体系之中。在菲尼斯看来,善来自实践理性的构建,实践理性在运作的过程中把握“可欲的事物”,这一可欲的事物即是善,“理性是实践的,这不是指一种实现原始欲望的方式,实践理性的首要功能是识别什么是可欲的,这些可欲的形象不是一种我偶然感受到的东西或一种独立于理性的欲望的对象,而是一种可能的行动或者行动所指向的目标以一种可欲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使我们觉得拥有什么、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是有意义的”。〔7〕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谁也不会愿意一生都处在儿童的心智阶段,即使他一直能从令儿童愉悦的事物中得到最大的快乐”。〔8〕在这一表述中,菲尼斯发现了另外一条构建善的理论路径,“没有人会愿意成为什么”这一表述并不是告诉我们要用一种诉诸大众的、流俗的思维模式处理伦理学上深远的问题,而是在说,对常言的留意可以将我们的哲学视角转向实践生活。在伦理学中,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人类实践的一些基本经验稍加留意,而偏偏要在一种事实的命题中去寻找善呢?从出发点来说,善来自实践领域。菲尼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道德命题不是从事实命题中推论出来的,自然而然,在构建善的问题上,菲尼斯的出发点就不是一个对人性的描述或者尝试对一个自然目的下某种定义,而是从真正的生活之中,在真正实践的领域之中去发现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被菲尼斯称为“机遇”或善的来源的世界,这种机遇是“一种能够提升(完善)一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处境的东西,以及作为应当被追求的东西”。〔9〕这也是菲尼斯在善的构建理论上的出发点,一个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可能性的世界。那么从这个实践的世界出发如何去把握善?从能力上说,我们通过实践理性构建起善。在菲尼斯的体系之中,实践理性是一个在外延上极为丰富的概念,它不仅被用来发现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也被用来确定如何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好生活。而善就是被实践理性所把握的,无论菲尼斯是否承认,维奇都给了他以足够的启示,维奇虽然宣称人的目的早在自然的秩序中建立了,但是他又认为,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物,如果这个目的或善是被理解的呢?换句话说,如果善是被我们理性所把握的呢?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方式。一般来说,实践理性能力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语境中是一种获得道德上的判断的能力,虽然这样一种判断完全不同于理性在纯粹思辨领域中的运用,但是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获得一个道德上的“真”的判断,这一点是有共识的。那么,这样一种“真”的判断的内容是什么?是关于手段的还是目的的?对实践理性的解释更多的是将其理解为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发现手段的运作,持这一种观点的不仅包括了亚里士多德,也包括了当代的学者,在麦金纳尼看来,“实践理性从目的开始运作,并且寻找达至目的的手段”。〔10〕在这种观点下,实践理性不在于构建善,而是在于发现一些实现善的手段。但是,在菲尼斯看来,实践理性的运作不仅在于确定实现善的手段,实践理性有着更为基本的运作,即构建善,“实践理性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运作不在于限制、限定或否定,而在于促进,并因此是积极的:亦即寻找和建构那些为人们所追求的赋予我们的行动以理性目的的可理解的目的”。〔11〕实践理性具体把握善的方式如下,我们在生活的、实践的经验世界中留意到了我们有一些对于某些对象的倾向,例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我们总是喜欢不停地提问,并且意识到我们会因为获得正确答案而感到高兴,无法获得正确答案而感到苦恼的倾向,这种对倾向的留意给我们的实践理性提供了材料,进而实践理性将倾向所指向的对象理解为一个在未来能够有助于我们个人完满的一个对象,也即是说,当我们留意到我们有一种对知识的倾向时,我们通过实践理性把“知识”构建为一个将在未来有助于提升我们个人完满的一个善。从结果上说,实践理性将善理解为可欲的(desirable)。实践理性通过构建的方式确立了一个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善,这样一个善本身就是被我们设想为可能会增进我们的完满,因此,这样的一个善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欲的”,一旦我们将一种可能性理解为一个能够增进我们的完满的状态时,这种可能性将会使我们产生欲望从而导致我们的行动,这样一个欲望完全不同于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始欲望,这种欲望依赖理性而存在,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阿奎那所使用的“理性的欲望(rational appetite)”的术语来表达,但是菲尼斯对此的解释并不是传统的解释,也即是说,理性的欲望是实践理性对原始的自然欲望的一个修正,而菲尼斯所谓的理性的欲望是由实践理性所产生的欲望,在实践理性把握善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一种对善的向往和欲求。
三、菲尼斯的辩证法
罗素曾以一种诙谐的方式调侃辩证法的论证,“某个结论之所以被看作真实的东西接受下来乃是因为它能够从公认为虚假的、相互不一致的前提中推论出来”。〔12〕任何一个辩证法出现的场合就意味着某个哲学家要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立场进行一个调和。有趣的是,菲尼斯处于和阿奎那一样的矛盾的境地,只不过这个境地不再是13世纪经验主义和神学信仰之间的矛盾,而是后休谟时代和前休谟哲学之间的矛盾。菲尼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的第一卷就谈道,“休谟宣告了一个逻辑上的真理,那即是我们不能从一个事实命题推出道德命题”,〔13〕这也表明了菲尼斯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即在后休谟时代谨慎地对待“事实”与“价值”的问题,但是这将使菲尼斯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就要抛弃对阿奎那哲学的传统解释。在菲尼斯的伦理学中,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辩证的矛盾,我们既然不能从一个事实命题推出道德命题,但是就如我们所展现的,为什么在实践理性把握善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一个看似事实的“倾向”因素。
实际上,在菲尼斯的伦理学中,“倾向”已经不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人性因素了,而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人性因素。我们对本性的言说不是一种经验的归纳或者哲学人类学上的假设,只有我们先把握到了“善”,我们才能够言说我们的本性。正是因此,在“人性”和“善”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从认识论的秩序而言,我们只有先把握了善,才能够言说我们的本性;从本体论的秩序而言,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我们人能够追求什么。菲尼斯在辩证阐释的过程中,已经转换了“人性”的内涵,它不再是作为独立于道德的一个事实,而是一种被善所刻画了的人性。这种转换改善了自休谟以来人性学说在伦理学中的尴尬地位。在伦理学中,我们如果不先把握和理解了善,那么获得一个人性上的判断就是不可能的。同时,菲尼斯承认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人性学说,但是这样一种学说并不是伦理学所要考察的课题。伦理学对人性的考察不是建立在经验的观察之上的,而是完全建立在对善的实践性理解和把握之上的。因此,这样的一种人性学说也被菲尼斯称为“实践的人性论”。菲尼斯接着为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作了辩护,就如上文提到的,菲尼斯认为这两位大哲学家都没有从“事实”前进到“价值”,菲尼斯提出的具体理由如下:亚里士多德所有关于人性的论述都包含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之中,这两门学科也是实践的学科,它们不是关于一种纯粹理论的学科,也即是说,其中对人性的描述不是一个事实的描述而是一个实践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论的秩序:为了能够把握像人类这样一种动态实在的本质,人们必须首先去把握他的各种能力,而为了把握这些能力,人们必须首先去把握这些能力的各种活动。为了去把握这些活动,人们必须首先去把握这些活动所指向的目的。这也表明了,在伦理学中,对善的把握和理解具有一种优先性,而人性学说依赖对善的理解,阿奎那的所有著作所持有的一贯立场也是一样的,“为了能够把握像人类这样一种动态实在的本质,人们必须首先去把握它的各种能力,而为了把握这些能力,人们必须首先去把握这些能力的各种活动,而为了去把握这些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去把握这些活动所指向的目的”。〔14〕因此,在菲尼斯看来,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伦理学中,不存在从一个事实的人性学说推出道德上的善的过程。但是,菲尼斯也同意维奇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确实给出了一个从事实命题到道德命题的论证,这就是基于自然目的的论证,但是在菲尼斯看来这只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方法中所采取的一个。
麦金纳尼曾批评菲尼斯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作了过分的区分,以至于将伦理学和关于自然秩序的知识完全割裂开来。〔15〕但是菲尼斯并不认为,那种事实上的人性说对于我们进行伦理学的研究毫无用处,虽然它没有直接参与到伦理学中,但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考。菲尼斯承认的一点是,并非我们关于人性的所有知识都是来自一个实践上的理解,也没有说这种实践的人性论可以完全独立于描述的人性论,实际上,“在对人类事物的描述性解释和用实践的观点去考察人类行动之间有一种相互依赖”。〔16〕在菲尼斯看来,如果我们对人类现状缺乏足够的描述和了解,我们就不太可能在把握善的问题上取得成果,而一个错误的事实的人性论描述可能会阻碍我们在实践领域去把握真正的善,我们如果认同休谟的观点,“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永远不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感情”,〔17〕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去运用实践理性以一种主动的、构建的方式去把握善。因此,实践理性是伦理学的起点和核心,在这一点上,菲尼斯是和康德一致的,但是菲尼斯所谓的实践理性和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为了自身而行动的,而至善就是实践理性自身的卓越发挥。但是在菲尼斯这里,实践理性的首要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独立于实践理性的善,一个有可能提升我们的完满的机遇或可能性,而我们的行动是在善得到建立之后展开的。阿奎那将关于人的所有行动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人的行动(actus hominis)”,一类是“人性的行动(actus humani)”。所谓人性的行动,指的是人是其主宰的行动,而人对其行为的主宰在于在理性指导下的意志的行动,具体而言,人性的行动在于它是经过理性考虑的意志的行动,而意志的行动的对象是目的和善,也正是因此,所有的人性的行动都是为了某种善。虽然这种善在执行的秩序中是处在最后的,但是在一个人的意愿的秩序中却是在先的。这也表明了,在伦理学中,对善的把握处于一个优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