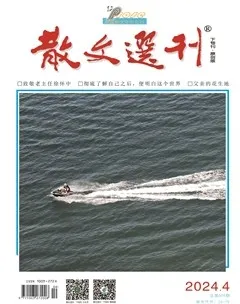家乡那片油茶林
罗平

我家的后山,有一片油茶。
上世纪70 年代初,家乡的父辈们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在生产队老队长的带领下,全组老老少少几十号人连续奋战两个秋冬,凭着锄头、铁锹,把一百亩荒山开发成了油茶地。后来,农村实行了责任制,先是水田和旱土,最后是林地也全部分配到人到户,县里还发了个林权证。我家分到了一片油茶林地。从此,父母就把这片油茶地当作宝贝一样侍候。一到冬天或春天,父母拿上弯刀、锄头,带领我们兄妹到茶林里清除杂草杂树,然后把茶树下的土地翻挖一遍。父亲告诉我那叫“垦复”。我们兄妹的手掌磨出了一个又一个血泡。父母常常督促我们:“多干几天,就好了。”似乎对儿女们没有一点一丝的疼爱之意。我和妹妹常常委屈得想哭,就时不时偷偷懒。父母却装作没看见一样,只是时不时骂几声:“又想偷懒。小时候不吃苦,长大后有苦吃。”就这样,油茶地被父母整理得像“一封书”“一槽糖”一样(衡阳方言,意为土地整理得条块分明)。油茶树也一年比一年长得茂盛,长得粗壮。
油茶收成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全家过年有没有新衣裳穿,我们兄妹3 人读书上学交不交得起学费。每当油茶丰产丰收时,父母的脸上露出的笑容就像冬天盛开的茶花,因为孩子们的新衣和学费有了着落。每当看到母亲从衣柜里最底层,拿出用一块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纸币钱来给我们去交学费时,每当过年可以穿上新衣裳时,才知道父母为什么总是那么狠心,要我们兄妹去为油茶割草锄地,因为后山那片油茶林是父母的希望所在。那片油茶林养育了我们。
垦复油茶地虽然辛苦,但也给我带来了美好的童年时光。每年春天,我们在父母的带领下,一边清除杂草杂树,一边挖土整地。茶苞、茶耳便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水果”。油茶树上长出来的茶苞和茶耳有淡黄色的、紫红色的,也有粉白色的,吃起来又脆又嫩又甜,还散发着淡淡的茶香味。每当我采摘一捧鲜嫩的茶苞或茶耳,父亲便会高兴地说:“既可止口渴,又可饱口福。”如今,有时在梦里,我还梦见自己在家乡那片油茶林里采茶苞、吃茶耳,醒来时,发现枕头上已浸湿了一大片,不知是贪吃的口水,还是思乡怀旧的泪水。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捡茶籽和榨茶油。
捡茶籽,正是寒露时节。父母说:“茶籽要呷寒露水,出油率才高。”寒露时,温差很大,早晚很凉,中午很热。捡茶籽,是个辛苦活,也是个体力事。早上,吃完早饭,父亲便挑上箩筐,母亲便背上背篓,让我们兄妹提篮携袋,一家人上山捡茶籽。山地很陡,茶树很高,要爬上树去摘采,有时还很危险。母亲在采摘茶籽时曾在茶树上摔下来几次,幸好只是皮外伤。一家人在树上采的采,在地上捡的捡,采满几背篓或几筐后就转运到山脚下来。因为早晨气温低,天气凉,我们都是穿着毛线衣,中午却要穿短袖衫。有时看见父母,背着或挑着沉甸甸的茶籽,两腿在微微颤抖,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父母的不易。于是,总想多为父母分轻一些重量,但父母不肯,说:“细俫子、细妹子身子还没长老成,莫把身子压坏哒。”宁肯自己担多些、挑重些,也不让我们兄妹多背多挑。
茶果下了山,一筐筐、一篓篓紫红乌红的茶果便晾晒在门前的禾坪上。在秋阳的暴晒、秋风的吹干下,茶果便裂开了壳,一粒粒一颗颗乌黑的茶籽便爆裂出来。一家人便开始褪壳分果。茶籽榨油,茶壳可以冬天取暖,可以用来熏腊肉。母亲说,用茶壳熏出来的腊肉格外香些,色泽金黄,又有看相。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每年母亲都会用茶壳熏一些腊肉让我带回城里吃。
茶籽晒干后,父亲便去村里一个小榨油的作坊榨茶油。榨油的过程很复杂,全靠人工,也是传统工艺。
榨油小作坊的主人是本村人,榨了几十年的油,手艺好,只收加工费。先把茶籽用一口大铁锅炒熟,用一个半机械化的圆槽磨成粉,然后上蒸笼把茶籽粉蒸熟,再用铁圈模铺上稻草,填上茶籽粉,做成一块一块茶籽饼,最后上榨,用一根大木头撞击木榨加压。在父亲一次又一次用木头的撞击下,金黄剔透的茶油便流了出来。父亲便接上第一碗茶油交给母亲。母亲在家开始忙碌,杀鸡剖鱼,准备用一年一度的第一碗茶油做一顿饭菜。一家人围坐一桌,喜气洋洋,热热闹闹。茶油煮出来的菜是那么的香,那么的甜。香了农家小院,甜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那些年,生活还很艰苦。茶油虽然是自家产的,但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母亲很省俭,也很有打算,计划着一年全家的用油,用一个陶土搪子装好,余下的便隔三岔五提到集市上去卖,作为一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母亲有时也很大方,有亲朋好友来了,过年过节了,都要给亲朋好友送上一小瓶,说是让他们去煮个腥味菜,也尝尝鲜味。
油茶全身都是宝,除茶油可吃,茶壳可烧外,茶枯(麸)也是个“宝”。那时候,没有什么洗发水洗发精,也没有什么洗衣粉洗衣液,母亲便把一个一个茶枯(麸)敲成一小块的,煮熬成茶枯水,可以洗衣,可以洗发。每当我们穿上母亲用茶枯水洗的衣裤,身上总是有股淡淡的茶籽的清香味。特别是用茶枯水洗头,一头秀发乌黑发亮,随风飘逸。难怪家乡的妹子都长得水灵漂亮,山里的后生都生得雄壮伟岸。也许,他们是茶油养出来的、茶枯洗出来的缘故吧。如今,常常有人问我:“你搞了几十年文字,还是一头乌黑的头发,是否有什么好秘方?”我总是笑着回答:“也许是家乡的茶枯水洗出来的吧。”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很少回家帮母亲捡茶籽了。但母亲却总记得,每次我回乡下时,都要裝上一大桶茶油让我带回城里吃,总要让我带上几块茶枯回去洗发。后来,县里发展油茶生产,村里把荒山全部种上了油茶,还成立了油茶合作社。母亲告诉我,村里好多乡亲都以土地入股了油茶合作社,乡亲们都靠油茶致了富。
家乡那片油茶林,已经成为我梦里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