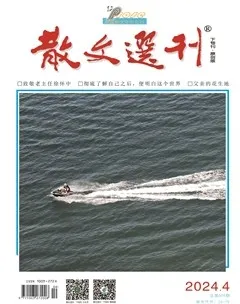黄瓜里的秘密
关如惠

腌黄瓜,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绵长细小的田埂绿意盎然,野草肆意疯长盖过田埂,走在上面,露珠沾湿了裤脚,冰凉冰凉的。稻田旁有一块菜地,那是阿公阿婆的菜园子,也是他们的乐园。只见几垄黄瓜郁郁葱葱,遮住了天空,竹架吃力地撑着,一条条黄瓜从藤蔓垂下,翠绿米黄,微胖修长,站成一支支休闲的队伍。阿婆走到黄瓜架底下,用枯枝般瘦削却有力的手摘下一根根黄瓜,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仿佛捧着一个个刚出生的婴儿。
中午时分,阿婆开始进行制作黄瓜皮的工序。她先将黄瓜放在滚开的一锅水里焯水,接着用漏勺捞起黄瓜放在篮子里,用筷子在黄瓜上扎出一个个小洞,然后将黄瓜置于大石头下,压出黄瓜内的水分。隔天再用粗盐和着黄瓜一起揉搓,腌渍入味,再将黄瓜放到大石头下压出水分。此后,将腌渍好的黄瓜摆在数个簸箕上,放在铺满芒基的广场上任由太阳暴晒,去掉水分,析出盐霜,放进瓦罐保存,需要时再取出食用。
每当腌黄瓜时,我看到阿婆用裂了一道道血口子的双手揉搓着粗盐和黄瓜,我的心底突然一阵痛楚。“想要收获,就要付出啊;要想生活好,就要去拼搏!”阿婆教导我说。小小的一条腌黄瓜,背后藏着阿公阿婆的多少血汗啊!
老屋的角落里常年放着一个大瓦罐,里面总有吃不完的腌黄瓜。可是,年幼的我常一边艳羡嘴馋着别家小孩那五颜六色的零食,一边皱着眉头咽下一口口的腌黄瓜,心里很不是滋味。每当这时,阿婆总是鼓励我说:“阿妹,黄瓜送粥,健康幸福啊!勤勤读书,将来就有出路!”
后来,我跟爸妈到湛江这个很大的城市里读书,离开了阿公阿婆。一晃半年过去。有一天,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头疼很厉害,心急火燎的爸妈带我去看医生,打针吃药,忙碌了近一周,病情才缓解,但整天晕晕沉沉,没胃口。妈妈担心地问我:“囡囡,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阿婆做的腌黄瓜和黄瓜蒸肉饼!”我难过地说。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门口出现了一罐腌黄瓜。它静卧在不起眼的纸盒子里,躲在门口不起眼的角落里。我迫不及待地解开罐口包裹着的层层塑料袋,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心爱之物——橘黄的腌黄瓜时,我的心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不禁泪流满面。不必怀疑,这罐腌黄瓜一定是远在老家的阿婆托人寄给我的。凝视着这份特殊的礼物,思绪不禁回到一年前的那次返乡。从那次以后,腌黄瓜成了我和阿婆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后来得了一种皮肤病,看了很多医生也看不好。医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进行膳食调理,方可慢慢治好。這种病发作时,全身瘙痒,昼夜难止,晚上尤其厉害。爸妈要上班,没时间照顾。爸爸说:“我叫阿公阿婆过来照顾你,好吗?他们劳累了一辈子,也该清闲享福了。”阿公阿婆就这样来到我家。
白天皮肤瘙痒尚可对付,但晚上就严重了,一旦发作起来,难以停止,吃不香,睡不着,要不停地抓挠,哭闹不止,导致遍体鳞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阿公阿婆和我爸妈分班倒轮流照看我,他们一人抱着我走来走去,不停地哄我睡,另一人抓住我的手防止抓挠。一番操作下来,天也亮了。经过数月的折腾,他们身心疲惫,愁眉不展,消瘦不少。阿公阿婆更厉害,有了黑眼圈,面部瘦削,步履不稳,像踩棉花一样。幸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照顾,我的病情稳定下来,慢慢好起来了。
我读小学了,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早晚由妈妈接送,阿公阿婆见无事可做,又闲不下来,觉得很无聊没用,便天天嚷着要回乡下,爸爸多次劝说无效。妈妈说:“你们回乡下了,如惠会伤心,再者她喜欢吃阿婆的腌黄瓜。”爸爸便心生一计,对他们说:“你们是种地能手,我们家楼下有很多空地,不如开垦来种点儿东西。”这下他们不吵着回乡下了,两眼放光,喜上眉梢。
说干就干。爸爸买来锄头、铁铲、铁耙、水桶、扁担等,他和阿公阿婆一起卖力地开垦荒地。经过艰苦努力,昔日野草萋萋的荒地被改造成了一块坡地。到阿公阿婆大显身手了。他们将坡地弄成一垄垄的,随不同季节种上黄瓜、豆角、空心菜、白菜、萝卜、番薯、芋头、玉米等作物,我们一年四季都不用买青菜。阿公阿婆将黄瓜摘下制作腌黄瓜,还将每天吃不完的青菜送给左邻右舍,惹得邻居们啧啧称赞。阿公阿婆一脸成就感,我也一脸自豪感。
再后来,我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阿公说:“老家的老房子要塌了,我要回去看看。”爸爸不好阻止,就答应送他们回去。
爸爸回到村里,请来师傅修缮老屋,更换朽掉的桁椽,翻新瓦面,加固泥墙,抹好墙缝。他还采购一些生活物资,交代村中兄弟密切留意阿公阿婆的情况,并叮嘱阿公阿婆他们要注意身体,不要干重活,这才放心地去上班。
六月的正午,太阳毒辣,我提着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乡村的水泥路蒸起层层热浪,一片蝉声聒噪,但不影响我想见阿公阿婆的心情。终于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四合小院,门前静悄悄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晒着几排腌黄瓜,在烈日下失去水分,黄瓜萎蔫而扭曲。
我笨拙地绕过这些腌黄瓜,轻手轻脚地走向里屋,生怕打扰到阿婆的午间清梦。刚钻进屋檐的阴影,却见阿婆正背对着我,伏着身子忙活,瘦弱的脊背弯成了一把弓。听到我的脚步声,阿婆连忙有些吃力地起身,两手在围裙上匆忙地抹着,准备腾出手来帮我提行李。
“阿婆,又腌黄瓜呢?”我有些嗔怪地说,“家里都已经不愁吃穿了,还整天腌这些黄瓜来吃,对身体多不好!”我叹了口气,打开背包,一件件拿出城里买的补品。这一盒是电视上推荐的氨基酸口服液,那一盒是外国进口的花旗参,明晃晃、金灿灿的包装,与这土气的老屋很不相称。阿婆没有说话,赶忙用擦得半干的手去接住,局促的样子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在暮色中,她麻利地收着剔透如黄玉的腌黄瓜,耳边,雌雄鹧鸪那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在山野上空久久回荡。
此时,一张方桌上摆着一大钵热腾腾的白粥。
“阿妹,快来吃一碗家乡的白粥和新鲜的腌黄瓜。”阿婆热情地招呼道,“我就说嘛,先苦后甜,阿妹有出息了!”
“对呀,我们关家的后代肯定厉害!怎能输给别人?”阿公骄傲地说。
“如惠,你能有今天,得感谢阿公阿婆的照顾和培养啊!要感恩所有人对你的帮助和支持啊!”妈妈动情地说。
还是原来的做法,还是童年的味道,我却有异样的感觉。沾上酱油,配上微烫的老火靓粥,和着眼泪,我埋头喝了起来。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