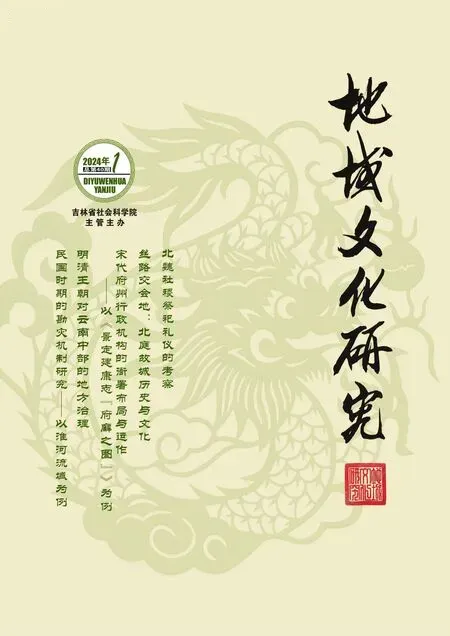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
——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
李希光
东晋至南朝,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略由直接统治转向间接统治①尹建东:《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而汉朝在云南所建立起的“华夏网络”秩序也在这一时期被打破、颠覆,故而自隋文帝起中原王朝就试图重塑云南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②古代能否实现对边疆的有效统治,与中央国力的强弱和该地区所处的下垫面环境有关。中央统治力越弱,所能供给于边疆的经济与社会资源越少;而下垫面环境越复杂,其治理的难度越高。汉时对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军事征服,其支撑在于强大国力所能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在下垫面环境方面,地理的阻隔、复杂山地生态环境成为东晋南朝有效统治南中地区的障碍。韩茂莉认为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多以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为基准,这条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参见韩茂莉:《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由于隋唐的介入及南诏的崛起,云南地区经历了一系列连锁的政治事件,而云南的政治地理结构也呈现一系列连续的变化过程,而这一变化尤以安史之乱前③自隋文帝经略云南起,由于中原王朝的政治介入,云南经历了一系列连锁的政治事件。为方便行文以及不割裂这些政治事件的关系,本文所指“安史之乱前”指隋文帝开石门关道起至天宝之战爆发前。最为激烈。
关于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地理空间进程的研究,许倬云首先指出中国历史的空间进程经过了向外扩张与向内充实两个阶段①许倬云:《试论网络》,载于《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31页。,而罗新与鲁西奇则从不同方面阐释了这种空间秩序在中国南方山地的演进过程②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鲁西奇:《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据此胡鸿又提出了“华夏网络”的概念③胡鸿指出:“华夏网络首先是地理意义上华夏国家所控制的郡、县、乡、里等聚落以及其间的交通线所连成的网络,进而还包括在此地理空间网络中流通的物资、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在帝国中央权力的统一调度下,可以在某一结点集中广大区域甚至整个网络的力量。此概念兼顾了帝国疆域内部的不臣之隙地,较直观地描绘了帝国政治体系的空间结构。”参见胡鸿《秦汉帝国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之后,胡鸿与裴艾琳则分别对六朝长江中游与唐宋之际西南边地的华夏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性的论证。④胡鸿:《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裴艾琳:《唐宋之际南方边地的华夏进程与族群融合》,《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由此可见,前辈学者对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地理空间进程的研究呈现由浅入深的过程。但整体来看,这些研究缺少以某一时段、某一区域为线索的梳理。
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安史之乱为时间节点,将唐对云南的经略作为考察对象,把这一时期内不同的政治事件进行串联与重建,厘清安史之乱前云南地区政治地理的空间演变实态,并尝试窥探中原王朝与地方民族政权“华夏网络”政治地理建构的一般规律。
一、隋至唐初中原王朝经略云南的空间展布
自秦以降,中原王朝就开通了从宜宾至昭通的五尺道,并将滇东作为经略云南的中心,此地受中原文化影响深,且路程短,所以隋唐时对云南的经略也从这里开始。《新唐书·南蛮传》载:“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⑤(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5页。此路线经宜宾、威宁、曲靖至昆明的石门道,这与秦开五尺道大致吻合。宜宾至昭通的直线距离仅150公里,但自地形而观之,石门关道所经区域属川南丘陵向乌蒙山区的过渡带,沿线多峡谷、窄谷,河流落差大,不易通航,可供选择的陆路交通也较少。在陆路、水陆交通皆不便的情况下,经略云南需消耗巨大的国力资源,而东晋南朝国力有限,难以突破地形障碍,对云南实行长久、直接统治的政治动力也长期缺乏。
胡鸿指出,自巴蜀盆地向南的扩张,必须越过高山才能获得其平原地带的资源。⑥胡鸿:《秦汉帝国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克服地形障碍只是手段,获得平原地带的经济资源才是目的。在隋开辟石门关道前梁睿上书隋文帝所言:
“南宁州,汉世牂牁之地,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伏惟大丞相匡赞圣朝,宁济区宇,绝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仓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⑦(唐)魏征等:《隋书》卷37《梁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1127-1128页。
梁睿经略云南,获得经济资源的计划,是以克服乌蒙山为前提。按地形,云南大体可分为山区与坝区两种地域系统。相比环境复杂的山区,坝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地域小,较易建立起秩序化、组织化的社会。所以石门道开辟后,隋朝在昭鲁坝区、草海坝区与滇池坝区分置恭州、协州、昆州①恭州在今昭通市昭阳区太平乡,协州在今威宁县观风海镇,昆州在今滇池附近。参见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隋的这一行动被视为中原王朝重新经略云南,重塑云南政治空间行政体系的开端。
隋亡后,唐继续经略云南。唐初,吸取隋朝多军事征讨、少政治设施的教训,为稳定滇东爨氏,“以其子(爨玩)弘达为昆州刺史”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5页。,并在唐武德四年(621)在滇东置南宁州总管府,共置南宁、恭、协、昆等九州③(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94页。,七年(624)改为都督府,又置西宁、豫等七州,共十六州,八年(625)南宁州都督府将治所移至味县。贞观八年(632)置戎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为朗州都督府,改属戎州,开元五年(716)朗州又复名南宁州,④参见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磨州县述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同时以南宁州为核心的十字网络交通格局形成⑤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册《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图》,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期间滇东、滇中所辖州县又数度调整。至开元至天宝年间,戎州都督府共辖三十六州,其中南宁州辖十四州。⑥据方国瑜考证麟德年间分姚州都督府后,南宁州都督府所领三十六州,就是戎州都督府的三十六,林超民沿用此说。但郭声波则据新出土的《大唐故爨府君墓志》考证出开元至天宝之际南宁州实辖十四州,统辖范围上南宁州与戎州在地缘上并不重合,郭氏考证详确,故依之。参见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4-265页;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磨州县述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贞观至永徽年间,唐又先后派梁建方、赵孝祖等进入滇西对当地诸蛮进行招抚,后在滇西地区置姚州都督府,形成以姚州、昆州、阳州的东、中、西三大中心。⑦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郭声波:《唐代青蛉周近地区羁縻州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整体来看,云南的政区数量、分布呈由少至多,由东向西、逐步扩张的特点。
以政区的空间结构论之,坝区往往会成为辐射周边的经济、交通中心,而中原王朝所控疆域多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产粮为基准。⑧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6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唐朝新置州县多集中于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的坝区内⑨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磨州县述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优良的水热条件使得这些坝区开发后较易形成重要的农业区。按《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⑩参见(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7《云南管内物产》,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1页。由此可知,至唐中期,滇东至滇西沿线已广种水稻、黍、稷、大麦、小麦。苍洱坝区更是有“人众殷实,多于蜀川”[11](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77页。“其与完富与蜀”[1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5页。的说法。
之后,唐再以这些坝区为支点,开辟连接山区及更偏远坝区的道路支线①据严耕望、方国瑜、郭声波等学者的考证,天宝战争前唐朝就已以南宁州、姚州等地为支点形成完善的交通网络。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册《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图》,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郭声波:《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唐代青蛉周近地区羁縻州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进而开发、控制边陲之地的盐矿、山林等资源。《新唐书·南蛮传》载:“未几叛,史万岁击之,至西洱河、滇池还。”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5页。隋代史万岁攻滇西诸蛮时就开辟了从滇东至滇西往来的道路,所经多为云南重要的产盐区,《新唐书·南蛮传》载:“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③(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69页。这些“群蛮”指附近的莫袛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其内属唐,并在此“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④(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5页。,之后唐为控制此地盐井,又将姚州都督府治迁至弄栋川⑤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因开采技术有限,西南本地民族盐的获得需靠交换得来。而唐通过对盐的垄断,实现对民族贸易的控制,并以此成为本地贸易经济的主导,这样的行为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变化。⑥参见卢华语等《唐代西南经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而滇池附近的安宁也因“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⑦(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7《云南管内物产》,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87页。成为本地重要的产盐区,加之地处滇东、滇西、滇南交通结点处,进而成为唐经略云南的交通中心。玄宗遂于天宝四年(745)派章仇兼琼筑安宁城,并打通联结滇西至中南半岛的步头路。
例如,在进行“相似三角形”教学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假设学校旗杆上的绳子断了,要让你们去采购,你们在只有一条米尺的情况下怎么计算旗杆的高度以确定绳子的长度呢?显然将旗杆放倒或者搭梯子测量都是不现实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旗杆和影子作为三角形的两条边,再利用三角形相似的性质求出旗杆的长度。这样,不仅能够使数学的实用性得到进一步体现,同时也能有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氛围更加轻松自由。
二、唐初向云南经略的制约因素
实际上,受地形与本地政治生态影响,唐在云南建立的由坝区至山区,再延伸至边缘坝区的空间网络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新唐书·地理志》载:“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⑧(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40页。“皆无城邑”的断语虽显夸张,但表明在唐人眼中在戎、姚二都督府间尚未形成具有唐制规模的城镇。除文献记载外,考古发掘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以没于天宝战争的姚州为例,因军防所需,姚州遗址坐落于蜿蜒山的山梁之上,整个城址仅有单道城墙,城区规模小,布局简单。遗址内出土了许多南诏时的瓦当,却鲜有唐时的瓦当及建筑构件,证明姚州应缺乏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官署建筑,⑨何金龙:《唐姚州都督府遗址考古调勘》,《大众考古》2016年第4期。这与文献中“皆无城邑”的记录相符。姚州已是唐经略云南一百年后级别较高的地方军事治所,至于时间更早、级别更低的州、县,其城址规模可想而知。
综上,唐时云南政区数量不断增加,但区域内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的行政建置,或可以辐射、统合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导致连接地方的支点薄弱。⑩参见胡鸿《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裴艾琳《唐宋之际南方边地的华夏进程与族群融合》,《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如姚州、南宁州等核心支点或干线出现补给困难或部族侵扰等问题,唐廷又未及时展开军事征讨,唐在云南形成的交通网络就可能出现局部或整体的瘫痪。这一点从姚州数度迁址、废置的情况就可窥探出大概。姚州都督府至少经历了麟德元年(664)、垂拱四年(688)、开元十七年(729)三次设置,以及永隆元年(680)、开元元年(713)、天宝九年(750)、天宝十二年(753)四次废置,除后两次系因天宝之战所废外,前两次皆系没于蛮乱。①杨爱民:《唐朝姚州都督府立废问题刍议》,《昆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而姚州都督府每次设、废又会间隔数年,其不稳定必然影响唐对云南地方的统治。
实际上,自武则天起,唐在云南的经略就显得力不从心。神功元年(697),张柬之在上书武则天时曾言:“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盖讥其贪珍奇之利,而为蛮夷所驱役也。汉获其利,(蜀)人且怨歌。今减耗国储,费调日引。朝廷无丝发利,而百姓蒙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20《张柬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321-4322页。尽管张柬之罢黜姚州都督府的提议被武则天否决,但从中可见,国家内部对是否维持云南边疆统治已出现意见分歧。与梁睿相似,张柬之也是从经济、赋役的角度阐述经略云南的缘由,但梁睿与张柬之态度却截然相反,这反映出国家无法将本地资源很好的转换为国家所需财富的现状,以及不得不面对巨大沉没成本时所产生的惯性心理与现实状况的拖累所带来的矛盾。阻止中原王朝扩张的因素,关键是地理变化带来的经济生态差异与本地的政治势力,③胡鸿:《秦汉帝国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而前者仅是因变量,后者政治势力才是影响唐廷无法稳定经略云南的自变量。
以洱海附近的松外诸蛮为例,史万岁在隋初平爨乱时就曾出现过“度西二(洱——笔者注)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诸夷大惊,遣使请降”④(唐)李延寿等:《北史》卷73《史万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524页。的局面。唐贞观年间松外蛮又屡次叛乱,影响了滇西至天竺道路的畅通,于是嶲州都督刘伯英认为“松外诸蛮,率暂附叛,请击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后唐军“杀获十余万,群蛮震骇,走保山谷”⑤(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22页。。常规道路多沿山前平原与河谷平地而开,为保证道路的畅通,唐只能选择驱赶蛮夷,以实现对交通道路间山前平原与河谷的控制。而被唐朝所驱赶的蛮夷,不得不“走保山谷”,以求避难。这里的“走保山谷”说明在干道以外的山险处,可能还存在诸多不为唐朝所控制的支线河谷或平原“隙地”。这些不为唐朝所控制的“隙地”,给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新唐书·南蛮传》载:“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⑥(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21页。滇西山地环境多呈垂直地带性,所以不同海拔的民族会呈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并由此在山腰与山谷间形成规模不等、大小不一的政治体,这也造就了云南“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民族格局,直接影响了其治理的难度⑦鲁西奇、董勤:《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
王明珂注意到,在西北封闭多山的河谷地区,易形成多个分散、独立的部落群体,这些无主的群体往往会因战败而集体归降,但不知何时又会集体倒戈、反叛,这种不稳定的时降时叛给汉朝招致了麻烦。⑧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4-246页。而在云南山地,唐朝也面临与汉同样的窘境。当部分部落被唐击溃后,其余诸夷多表现为“群蛮震骇”“诸夷大惊”,而后或望风而逃或向唐廷请降。这些破碎、独立、无君长的部落多散布在地形崎岖的山险地区,若欲降服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从上文所述的姚州都督府的置废就可看出这种破坏力何等巨大。
三、唐、诏互动下的云南政治地理
从贞观至开元年间,唐经略云南近百年,但面对这些独立、松散的部落仍束手无策,所以为达到解除蛮乱、稳定边疆、牵制吐蕃的目的,唐开始着重加强对苍洱地区六诏的扶持。唐在蒙舍诏、越析诏、施浪诏、浪穹诏、邆川诏分置巍峰州、越析州、舍利州、浪穹州、邆备州,诸诏王均被任命为刺史,并赋予其统领地方事务的权力。①(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3《六诏》,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5页。开元年间,“五诏微,南诏独疆”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70页。,唐转而全力扶持南诏。“开元初,盛逻皮死,子皮逻阁立。(开元)二十六年(738),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③(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7《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280页。从地形看,六诏所居的苍洱地区实际是由巍山坝区、弥渡坝区、洱海坝区、邓川坝区、洱源坝区、宾川坝区所组成的地理单元,各坝区间虽有山地相隔,但彼此相距不远,联系紧密。加之“人众殷实,多于蜀川”的经济基础,较云南其他地区,这里具备形成高级政治体、实现军事统一所需的地理条件。而在这些坝区中,又以洱海以南南诏所居的巍山坝区为大。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前南诏已兼并其北的蒙巂诏,以及东部弥渡坝区的白崖诏,统一了苍洱地区南部。后又在唐的帮助下,于开元二十五年(737)跨过无量山,平定了洱海山前平原的河蛮诸部,并向北进抵邓川坝区,最终统一了整个苍洱地区。
南诏渐强后,滇中也成为唐、爨氏、南诏三方势力所交汇的政治中心。上文已述,唐廷为夺滇中盐业,欲在安宁筑城,并修步头路;爨氏自南朝起便久居滇中、滇东,并形成了一定的统治基础。《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载:“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征、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仇相嫌,经营损害。即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①(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2《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93页。从史料可见,开步头路前,爨氏内部虽已矛盾四起,但依旧是此地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南诏则具备了东拓的地缘基础。
从自然区划看,处于滇中的安宁属滇中川西高原湖盆区,其北至川西大渡河、安宁河谷,南至今滇南热带雨林区。特殊的地质环境,致使这里成为滇盐的主产区。唐之前云南采盐地仅集中在安宁、比苏等地,整体呈点状分布。至唐时,采盐范围扩至滇中、滇南至滇西等地,安宁的盐业开采也由点逐步扩至成“群蛮食之”的辐射面。②参见李清清《唐代西南地区盐的产销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页。另外,从安宁出发可北至西川、南达中南半岛,西抵苍洱地区,是联结滇中、滇西、滇南的交通要冲。故而唐、南诏与爨氏的政治博弈也从这里开始。
实际上,在南诏统一六诏前,针对南诏,唐已提出“拟侵蛮落,兼拟取盐井”③参见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2《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9-690页。的战略目标,唐廷希望借南诏的势力来达到对诸蛮夷的制衡,并实现对滇盐的垄断。④参见卢华语等《唐代西南经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彼时的南诏尚未统一苍洱地区,实控范围也未触及核心产盐区,故而可助唐完成此任务。天宝四年,章仇兼琼筑安宁城、开步头路。而除控制盐业资源外,唐修筑步头路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打通云南与安南都护府间的南向通道,进而将其势力延伸至滇南及中南半岛,此举势必会削弱爨氏在本地的影响力,所以步头路的修筑引起了爨氏的恐慌与不满。另据方国瑜考证,安宁至安南都护府的步头路需穿过滇中南山地丘陵区间的红水河谷。⑤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9-80页。道路沿途多深谷、沟壑,地形起伏大,故红水河比降大,需至今河口县以下水流平缓处才可通航。面对溯流行舟的不便,只能选择在高山、峡谷间开辟陆路小道。可想而知,想修通此路,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造成诸爨及周边筑路民族“赋重役繁,政苛人弊”⑥《南诏德化碑》,载于《蛮书校注》附录2,第320页。的根源,久之,必然招致其反抗。《新唐书·南蛮传》载:“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闻章仇兼琼开步头路,筑安宁城,蛮震骚,共杀筑城使者。”
后“玄宗诏蒙归义讨之”⑦(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6页。,但此时南诏已呈“意望亦高”⑧(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7《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280页。之势。正如上文所述,南诏统一六诏后,其东、北境已毗邻产盐区,而南诏又借平定爨乱之机,其政治势力开始染指滇中地区。事后南诏虽暂时退出滇中,却自此逐步控制了此地的盐区,并对周边民族施加政治影响。《新唐书·南蛮传》载:“阿奼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书闻,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讨不置,阿奼诉归义,为兴师,营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虏其族,杀辅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稍离弱。”⑨(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6页。南诏在未向唐廷汇报的情况下,两次进驻爨地,并代替唐廷成为爨地内部矛盾新的调停人。同时趁“诸爨稍离弱”之机,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于永昌城。”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6页。南诏这次东民西迁的目的有三。一是彻底瓦解爨氏在滇中、东部的政治势力。如此多的移民应不是阁罗凤一次所为,而是数次迁徙的结果。②王文光对这次移民人数存疑,他认为二十万户如以每户5人计算,总人数应达100万,如此多的人从滇池地区迁至遥远的永昌地区,技术上存在难度,而“皆残于兵”反映出从滇东至滇中爨氏的激烈反抗。笔者赞同王氏的看法。南诏通过移民的方式巩固其统治,纵观南诏史,有人数记录的移民有三次。第一次为“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估算人数在20万-30万;第二次为“又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第三次为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其人数分别在“万户”“千余户”与“数万”,显然“徙户二十余万”的人数远超这三次,而这三次人口迁移还是在南诏鼎盛期完成的。故而综合来看,阁罗凤初期南诏国力尚不具备一次就迁移如此多人口的条件,笔者认为这次移民实为数次移民的结果。参见王文光等著《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上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77-178页;陆韧、马琦、唐国莉《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以永昌地区人口看,南诏将爨氏西迁的目的显然不是充实人口。二是掌控姚州至安宁一线的盐业资源。但与唐朝不同,南诏并未像唐一样垄断盐业,而是与民共享,笼络了周边部族,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盐销体系。③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三是避免与唐直接冲突。南诏的移民之策实际是南诏向东收缩的战略结果,这样可避免在东线与唐正面冲突,虽然此时的南诏日渐强盛,但同期唐正向吐蕃、契丹等四境民族用兵,兵威正盛。面对唐在政治、军事上的威慑多少存在一定的忌惮心理,这点从天宝战争爆发前,阁罗凤数次向唐谢罪便可探出端倪。而滇中大量人口的迁出势必会造成短时间内本地政治势力的真空,进而在唐、诏间形成一个“不通中国”④(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316页。的政治缓冲区,使得南诏将拓疆目标转至西向的永昌与寻传地区。
不过好景不长,因不满南诏东拓,唐随即发动了对南诏的进攻。《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天宝八载(749),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⑤(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7《云南管内物产》,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84页。又据《新唐书·南蛮传》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⑥(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70页。两条史料对此事件描述一致,但《新唐书》未载何履光攻南诏、取安宁的时间,而《蛮书》有载。但按《蛮书》所记,何履光攻南诏、取安宁的战争从“天宝八载”至“十载”,耗时近两年,再参考两次天宝战争的时间,此战役历时过长,记述可能有误。而按《新唐书》所记,何履光攻南诏应是一次性完成,作为第一次天宝战争的前哨战,《蛮书》所载的“天宝八载”的时间应无误。而天宝十年(751)时第一次天宝战争已打响,而何履光从安南攻南诏是为配合鲜于仲通的唐军主力。综上,笔者认为《蛮书》是将两个时间的事件放在一起记述,即天宝八年(749)与天宝十年(751),何履光增两次攻南诏并夺回安宁城。
何履光天宝八年(749)第一次攻南诏时,进军神速,并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史料未载此战南诏方的动向。实际上,南诏杀姚州都督张虔陀后,阁罗凤曾“遣使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得,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所有”⑦(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71页。,但鲜于仲通不应,阁罗凤被迫投吐蕃,但依然向唐表示“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71页。。前已言及,阁罗凤数次向唐求和,是基于双方实力及长期友好关系的考量。另外上文已述,南诏迁出滇中,正是避免与唐作战的表现,而何履光对南诏的胜利正是基于此背景。史籍未载南诏方动向的原因,可能在于此战南诏进攻意愿不强、投入兵力不大,且唐、诏未造成较大伤亡所致。从阁罗凤在“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后主动向唐提出“愿还所掳,得自新,且城姚州”,由此可推之,何履光夺回安宁也应是南诏惧战后战略让步的结果。
天宝十年(751)至十三年(754)间,唐、诏双方爆发了两次天宝战争,结果均以唐惨败告终。②学界已对天宝战争的详细过程做了系统、全面、富有见地的阐释,故本文不再赘述。参见赵鸿昌《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陆韧《试论天宝战争与开步头路》,《思想战线》1997年第5期。这次战争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的政治地理格局。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无暇南顾,南诏占据了原来唐在云南的属地,之后以此为依托,向四境扩张,阁罗凤晚期已形成“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黔、巫”③(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67页。的疆域格局。在此基础上,南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地缘观④方铁:《论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并建立了一套适应于这种空间结构与地缘观的政治组织形式⑤其具体的表现,例如在南诏王畿“内地”置六睑(后改为十睑),在“边地”置八节度(后改为六节度、两都督)。参见王文光、李宇舟《论南诏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版)》2015年第4期。。至此,南诏的政治格局形态趋于稳定,并延续至大理国。元时,云南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接受直接管理,而南诏所形成的政治地理格局也被后世所继承。
结 语
以往学界都习惯将隋唐对云南经略放在中原王朝为主导的叙事框架内进行阐释。但若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看,则可能产生出新的解读: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朝根植于中原农耕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在经略云南百年后始终无法在云南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唐“华夏网络”的铺设也始终处于草创阶段。而发轫于部落制政体、比唐更熟悉云南政治生态的南诏成为唐扶持的对象。在唐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并完成对苍洱地区的政治整合。此后,南诏在与唐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原有的统治,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在政治地理表现上为南诏东拓与唐西进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也最终导致步头路事件的爆发。
本文尝试跳出以中原王朝或民族政权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将唐、诏等政治势力放在云南的地域空间内,去审视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下,云南地区政治演进过程,及此过程对后世云南归于中央王朝的影响。而安史之乱后,南诏对云南的统治又将经历怎样的政治空间变化,则需留另文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