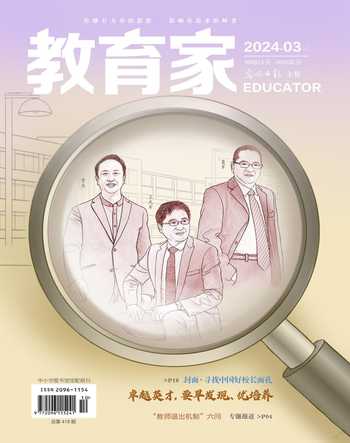病一次,方知读书须臾不可废离
王纬明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向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我,却在一次午休后,颠覆了对自我身体状况的认知“自信”。中午,我有在办公室躺椅上小憩的习惯。2022年冬至的中午,在解答完学生的问题后,我依旧延续了久已养成的午憩习惯。
一切似乎和往日没有区别。但是,以往小憩一刻钟的我,那天却怎么也醒不过来。蒙眬恍惚之中,我试着努力睁开眼睛,眼前却是晃动不止的天花板,想抓著躺椅扶手站起来,还没等站起就被无情地“甩”回原处。我猛地一惊,不祥的预感掠过:是心脏,还是脑袋出了问题?
在同事的搀扶下,我一步三晃地来到医院,心电图、脑CT等一通检查下来,竟显示一切正常,但停不下来的眩晕感还是让我忍不住追问医生,病因究竟是什么?医生的结论是身体疲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建议回家静养几天。
身体既已“报警”,那就好好调养将息吧。可没有任何预设的“休假”,我却无法静心消受。眩晕与康复之间的“空隙”究竟该如何填补呢?拿本书来看,想必会招致家人的一致反对,平时就因长时间低头看书,颈椎时时“报警”,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好。闭上眼睛,尽可能保持脑袋丝毫不动,将手机“捞”到手中,微睁一目,打开听书软件,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听什么呢?就听林清玄的《生命的酸甜苦辣》吧,比较契合此刻的心境。眩晕持续的几天里,我硬是把62集的《林清玄散文精选》整整听了两遍。
病一次,方知什么须臾不可废离。于嗜好阅读的我而言,这须臾不可废离的便是读书,只是平日不眩晕时没有感受到这种“自由”的珍贵。听书虽然少了翻书翻页的“麻烦”,似乎方便许多,但总感觉不如随时停顿与作者“默语”,随手批注与自己“共情”来得酣畅痛快。
眩晕之症切实唤醒了我对习焉不察的“从心所欲”自由读书的珍视,但这种感觉却并非始于这次突如其来的“发病”,而是久已潜伏在了日常的“病症”之中。
三十不立,四十有惑。静下闲思,我总是如此戏谑自己。翻过了三十岁的山,越过了四十岁的弯,本应是“撩动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的状态,可现实却是面黄胡须硬,焦虑的“火焰”时不时跳出来浅灼低烧。曾经的青年教师升格为中年教师,曾经被鼓励动员参加各种比赛变为被暗示不符合参赛年龄等各项要求,以往师生关系中无话不谈的惬意疏离为现在师生关系中的似近实远……这些变化一次次提醒我,自己恐怕是进入了“教师职业悬浮期”。
如有明显的感知,尚可在迹象初显时早早开始心理重建,但不易察觉的感知却狠狠地将我撞得踉踉跄跄,几乎不会“行走”。这种踉跄之感最直观的“提醒”是学生的眼神,以往课上学生的眼神有光彩、有灵性,四年前新教材刚开始实施后课上学生的眼神中却出现了迷茫和混沌。那眼神,赤裸裸地提醒着我,以往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的课堂正在被怀疑。
新课标标志着新的素养要求,新教材重构着新的学习方式。“新”的面前,所有教师都是“新”教师,不论年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彻底“病”了,因“新”而病,且是在没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假装不焦虑,是我这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中年教师最后的倔强。但心病还须心药医。既然是因“革新”导致的“心病”,那还需从此处觅“药”。于是,研读新课标,研习新教材,研讨新课堂,成了我过去四年教学生活的常态。啃读一本本专业理论书籍,研读一期期专业杂志,从理念更新到实践履行,从任务群架构到大情境创设,从单元设计到整本书阅读……我一次次走在医治“心病”的路途中。
低徊愧人师,不敢叹辛苦。眼明心又亮,无愧读书人。身病一次,心病一次,两样病症,一种提醒,使我更加坚信,在我的生命中读书这件事须臾不可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