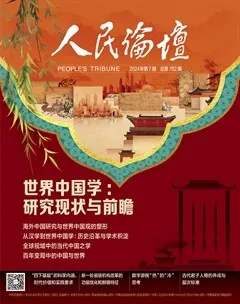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董欣洁
【关键词】中华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并独立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不仅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的纵向发展同步前行,而且通过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各种群体联系日益紧密的横向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考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就会看到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的自立之道,而且展现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对摆脱贫困、消除压迫的不懈追求,更加能够说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辩证统一和未来趋向。从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特别是19世纪中叶中国被卷入世界体系之后的西学东渐,到新时代蓬勃开展的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意味着人类历史关键节点的转换,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是人类文明事业的重要新进展。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的自立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正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的自立之道。
在众多重要元素之中,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把握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穷物之理即为格。中华文明讲求在穷物之理的过程中使自身与世界合为一体,实现自身与他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实现个体的内在精神自由,实现个体与世界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这个不断实践和升华的过程,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行之而成”“道通为一”,即“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这也成为中国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即使存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时候、即使“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也有无数学人接续努力,形成了“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①。
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国与世界开放互动的交往图景。其中,中华文明与古代印度佛教和16世纪以后欧洲(西方)文明的交流是人类社会两次大规模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文明互动,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翻译—会通—超胜”②的文明互鉴思想。在这两次大规模的跨文化互动之中,中国先秦的本土思想资源,即包括孔孟学说和老庄学说在内的诸子百家思想,是中国学人格义、吸收、会通、融合外来文明成果并创造新的文明成果的历史根基。事实上,以中华文明为基本义理,创造性吸收转化外来文明成果,产生新成果新话语新义理,立己达人,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连续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展现出来的基本形态之一。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不断彰显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不断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过程。
在文明互动过程中,为有助于翻译和会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出格义的方法。所谓格义,正如国学大师汤用彤指出的:“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③格义是晋代僧人竺法雅创立的一种阐述讲授佛教义理的方法,即运用为中土士人易于理解的儒道思想、名词和概念去比附解释佛经中的事项、教义和概念等内容,“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即以中国原有之观念比配于佛教观念,进行比较分析。④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也指出:“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陈寅恪还认为,格义之说“成为傅会中西之学说”,“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⑤
这种“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傅会中西”的格义方法,成为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接触后形成的一种先期的会通形态。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时人便以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佛经。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互鉴会通日益深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佛教理论,演化出包括“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在内的许多派別,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互动成为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文明互鉴的典范。这也说明,文明互鉴是人类社会实践成果的交流互鉴,其意义在于通过相互切磋、学习和比较,辨其同异,进而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
在明末(16世纪末)耶稣会士入华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用格义的方法来了解西学。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则于1631年更进一步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系统思路(即前述“翻译—会通—超胜”)。正如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指出,徐光启早期研习《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意图接续汉学之“勾股”,结识利玛窦之后,得知希腊亦有“几何”之学;他主张融通“汉学”和“希腊学”,创为明代中国之“新学”,实为时代先驱。⑥明代官员彭惟成在为1612年初刻的《泰西水法》撰写的“圣德来远序”中谈到:“今西洋儒彦觐我文明而来,……吾辈相与邂逅,缅惟畴昔,博物洽闻,吹藜天禄,固已知其所知者,并于西洋儒彦获知其所未知焉。吾未知西洋之所知,犹之乎西洋未知吾之所知也。”⑦其时中国学人在文明互鉴方面这样坦荡开放的胸襟见识,实令后人钦佩。
西学东渐中的中西互解
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欧文明能够开展较为平等的交流。不过,当时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入华,却无法达到佛教入华时交流互鉴的历史高度。何兆武、何高济早已指出:“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利玛窦自己儒冠儒服,尽量使自己中国化”,“尽量利用(或者说附会)中国传统的文化”(联合儒家反对佛道,又援引先儒反对后儒),但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规模和持久性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直到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三百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包括利玛窦在内的欧洲海外传教活动的物质动力,是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进行的海外扩张,而基于这个势力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不可能违背这一物质势力的利益或者超出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外的。⑧这个判断可谓一语中的。法国学者梅谦立认为,传教士南怀仁的“理学”变成了一种绝对真理来判断中国文化思想的得失,而这样的哲学对话很难有进步,因为它完全忽略考虑话语本身的必要条件,南怀仁介绍的具有普遍性的“理”,无法构成一种跨越文化的思想桥梁,相反拉开一种无法弥补的距离。⑨
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对欧洲或西方学人来说,实际上不利于他们深入把握与中国这样连续发展数千年的原生文明互鉴的历史良机。美国学者埃德温·J.范克利提出,18世纪欧洲学者越来越关注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纳入他们的世界历史观,这并不意味着18世纪的普遍史学家写出了成功的人类通史,大多数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遍史中包含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通常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而且很少与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⑩尽管如此,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亚历山大·斯塔特曼针对欧洲启蒙运动被视为现代时期的开端、以科学为标志和保证的进步理念经常被视为西方对启蒙运动加以继承的传统观点,指出当时欧洲的许多辩论都涉及对中国知识传统的专注、持续和变革性的参与,中国科学塑造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遗产即西方的进步理念。11
随着19世纪上半叶亚洲特别是中国与西欧北美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转折,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明显加速。“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所指称的那种盲目地把欧洲或西方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无视甚至否定其他地区文明价值的自我中心意识迅速膨胀。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现实威胁和“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以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话语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与学术理论的现象大量出现。有学者指出,西学东渐是“把中国文化传统启蒙到西方的现代化轨道上去”。12殖民列强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强势,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过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本土文化立场。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并不断超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当中的常态。
所谓西学东渐,实际上是中西互解。因此,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中学西渐的过程。1840年以后的中国,面对世界各国各种思潮的涌入,特别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先进分子明确提出:“必需以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为考验,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诡辩。”13对这个阶段文明互鉴思想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迈向现代进程的艰难探索和积极成果。本文试举几例分析这个历史阶段文明互鉴思想的新内容。
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职的黄遵宪(1848—1905),在1887年成书的《日本国志》中分析了其时涌入的西学。黄遵宪认为:“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尚同、兼爱,明鬼事天,即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人如己”;“其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因此,“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如果说这些分析还在格义的层面,但黄遵宪不仅看到现象的同异,还能够努力归纳内中的脉络,指出“盖一国而古今不同风犹如此,况东西殊域,其俗岂得无异?然其源流变迁大概从同,斯亦奇矣”。而且,黄遵宪进一步指出向西方学习新技术的必要性,“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夫弓矢不可敌大炮,桨橹不可敌轮舶,恶西法者亦当知之”。更重要的是,黄遵宪既能看到西方列强在科技上的长处,也能看到西方的对外暴力掠夺交往与中国的对外和平交往截然不同。他指出:“中国之论兵,谓如疾之用医药,药不可以常服,所谓不得已而用兵也。泰西之论兵,谓如人之有手足,无手足不可以为人,所谓兵不可一日不备也。余尝旷观欧洲近日之事,益叹古先哲王以穷兵黩武为戒,其用意至为深远。”特别是针对西人的“治外法权”之毒已经遍及亚细亚的现象,黄遵宪指出:“欧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约之始犹不敢遽施之我”,“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他鲜明地提出“夫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论小大,苟为自主,则践我之土即应守我之令”。14“践我之土即应守我之令”,这是对文明交流互鉴发生的平等、相互尊重前提的原则性主张。
被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赞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严复(1854—1921),于1896年对“文明”“草昧”概念的传承与新解值得关注。“文明”一词,在传统文化中颇有深意。其中,“天下文明”者,意指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与文明对应并表示在文明发展阶段之前的概念则是“草昧”,即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15这组范畴意指文明(状态、阶段)经由初始时期的草昧(状态、阶段)而来。《资治通鉴》中便有“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一言。到17世纪初,中文的“文明”一词已经具有作为实体的含义。前述的彭惟成1612年撰写的“今西洋儒彦觐我文明而来”,正可作为例证。根据完稿于1826年的《皇朝经世文编》中所载,清代直谏名臣孙嘉淦(1683—1753)在《南游记》中写道:“天地之化,阴阳而已。独阴不生,独阳不成。……文明发生,独此震旦之区而已。”16这也是文明作为一种实体含义的明显例证。严复借翻译《天演论》立言,一方面继续用文明和草昧的范畴来解释社会进步历程,另一方面也受到西学的文明/野蛮观念的影响,运用了“野蛮”一词。他指出:“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他仍然从草昧的传统含义来解释野蛮,即“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土番猺獠,名为野蛮”。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严复的核心思想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17
梁启超(1873—1929)在1896年分析如何界定文明与野蛮。他认为,“然则文明野番之界无定者也,以比较而成耳。今泰西诸国之自命为文明者,庸讵知数百年后,不见为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越完备公允,则社会越文明。他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性,多次强调中国作为文明之古国,在促进文明交流进而光大文明方面的作用。梁启超在1902年指出:“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質,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他写道:“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佛教之不灭,皆中国诸贤之功也。……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国人矣。”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中华文明的信念与时代洞见。18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1866—1925),重视探讨文明的交流与作用。他在1904年提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而且,孙中山先生用传统文化解释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19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0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重大的世界历史性事件。苏联历史学家耶·马·茹科夫指出,这表明亚洲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使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压迫的范围不断缩小;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主义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并在亚洲各国人民历史上写下新的光辉一章。21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新形态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其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永续发展。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华文明推动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新贡献。
在道德观方面,对待人与人交往、国与国交往,中华文明始终倡导以和为贵、亲仁善邻、互利互惠。中华文明“翻译—会通—超胜”的文明互鉴思想,在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的奋斗过程中不断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能动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这就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即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和社会生活结构的持续优化,科学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激发出最广大人民的创新活力。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的,而且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获得丰富时代内涵,焕发出强烈的现实感召力。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3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的雄厚发展动能和人类文明事业的光辉前景。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交往实践蓬勃开展,互联互通互利的一体化联系日益紧密。有数据表明,202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9753.4亿美元,已经超过了2022年欧盟与美国的货物贸易总值8677亿欧元,2020年起东盟连续3年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另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峰值2821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且,2022年中拉贸易总额达4857.9亿美元,中国继续保持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方兴未艾。“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已经成为西方某种惯性的意识形态想象。有学者归纳指出,“欧洲中心论”的批评者如萨米尔·阿明、贡德·弗兰克和爱德华·萨义德等人,都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围绕着理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独特”兴起而构建,因此根据其他民族和文明相对于西方所缺乏的东西来将其概念化,并将其转变为缺乏文化多样性和历史的无差别“他者”。22前述分析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西方从文化上压制其他文明的具体思路,但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束缚,还不能辩证地解释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为阐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具体条件。文明演化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使其成果不断再生产,如何使人本身存续并获得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生产中心,都是人类文明阶段性和多样性的展现,而它们又共同构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和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说明文明互鉴的意义,在于人类不同群体社会实践成果的相互启发、切磋与借鉴,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務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是人类文明事业的重要进展,承载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生动体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的“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将能够持续地“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3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潜能前所未有的深度释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BSS01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VLS0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13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55、519、40、41页。
②⑥⑦黎难秋编:《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徐光启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6、109页、133页。
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4—165页。
④释慧皎著,朱恒夫、王学钧、赵益注译:《高僧传》(上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03页。
⑤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3、185页。
⑧[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者序言”。
⑨12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西学东渐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0、45页。
⑩Edwin J. van Kley,“Europes ‘Discovery of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ume 76,Issue 2,April 1971,p. 384.
11Alexander Statman,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23, Introduction,pp. 1-2.
14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日本国志》(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日本国志》(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3、801、802、913页。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34页。
16魏源撰:《魏源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75页。
17徐雪英编:《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严复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1、103、97、395页。
18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258、264、265页。
19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7、195页。
21[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前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2—3页。
22R.J. Barry Jones,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p.464.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89页。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