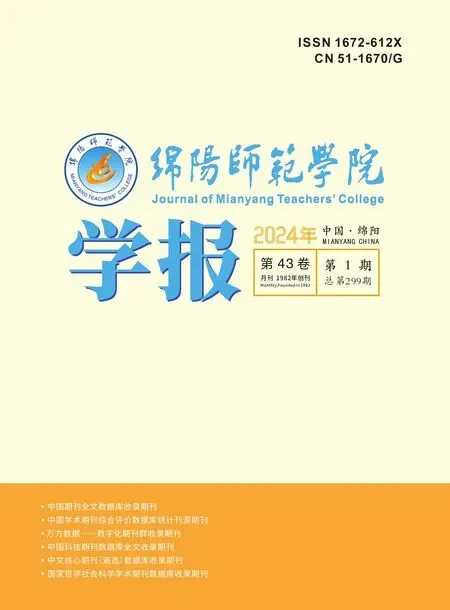论《拉奥孔》“诗画异质”中的美丑思想
张晓怡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莱辛的《拉奥孔》从时空范畴论述诗与画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的异质和联系时表述了他的美丑思想。莱辛反对温克尔曼将拉奥孔雕像的平静表情归结为古希腊人对于自然情感斯多噶式的压制。他认为,拉奥孔雕塑把极端的身体苦痛冲淡为一种轻微的情感,是因为表情扭曲的丑与古代艺术的最高法律——美互相冲突,所以,丑是造形艺术拒绝的题材。但是,由于诗所运用的语言符号具有先后承续的线性特征,丑的效果能够得到削减,因此得以进入诗的艺术殿堂。丑在诗中的表现和作用与在空间艺术中大相径庭,形态的丑陋引起的生理反感还能进一步深化为供人娱乐的喜剧性和滑稽性。莱辛从题材、媒介、审美接受的感官和心理功能、艺术理想四个方面来判定诗与画的区别。美和丑既是用来衡量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异同之处的审美标准,又总结了美与丑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表现特点,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具有内在关联性。这里拟从艺术作品的题材、艺术真实和审美接受心理等角度探析莱辛在《拉奥孔》中阐释“诗画异质”观点时体现出来的美丑思想。
一、形体:美丑的物质形式
对莱辛而言,美和丑都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有客观属性的物质形体和“一眼就可看遍”的特征。美和丑都来源于客观世界,是物质实体感性形式的显现。这种实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1]157。但是,美和丑无论是作为艺术题材还是作为摹仿手段,它们进入画(造形艺术)和诗(文学)的方式不一样,各自的作用也有所区别。
不同于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同时关注于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美,莱辛在《拉奥孔》中将美限定在物质层面,美的对象必须是具体可感的物体,物体的美具体包括形体的美、颜色的美和表情的美,表达物体美是空间艺术的绝对使命:
美这个概念本来是先从有形体的对象得来的,却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可以运用到许多不同的东西上去,可以运用到形状上去,也可以运用到行为和思想上去[2]1。
虽然美的普遍规律是诗与画都必须遵守的,但是它们在诗与画中的表现有各自的规定,尤其是在处理人物情感的表达时,区别非常明显。空间艺术杜绝直接摹绘不加节制的激情,如暴怒、哀伤、绝望。这些情绪体现在塑像的面孔上所造成的形态扭曲违背了人作为最高理想的物体美应有的线条美,而且还会破坏材料的完整性。在这些顷刻间表情发展到了顶点,作品的内在生命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张力,既泯灭了作品的含蓄美,也剥夺了审美接受者的想象——转化快感的一种审美能力。可见,绘画和雕塑如实呈现人物的极端情性,就是丑的。相对来说,诗塑造人物的目标是行动和思想,并不在于外貌情态,因此诗表现生理苦痛的艺术手段完全不受题材的限制。
“不可入画,但可入诗”正说明了“指号”对丑进行取舍的决定性作用。莱辛相信,“绘画最适合于用来描绘处于美的状态中的美的形体,尽管他有关于孕含性的顷刻的学说,但他并不想让这种使人的与比例与和谐的美让位于表现——让位于激烈的行动与情感,后者毕竟是诗的专长”[3]265-267。由于诗通过语言的时间性将对象的整一和物体的空间占有分解为先后承接的独立部分,美和丑的效果都会得到削弱,因此诗对丑的表现并不违背对美的追求。和“美有形体”一致的是,他对丑的关注也是着眼于感性的物质形式,丑的特点是“许多部分都不妥帖,而这些部分也要是一眼就可看遍的”[2]142。莱辛对丑的界定较之美更简单,也更片面,但是在他心目中,美和丑都存在于可感的客观物质之中。
丑这种客观事实不仅会形成生理性的拒斥反应,还直接关系到审美欣赏的心理效果和道德伦理的善恶判断。诗中的形体丑除了“看起来不顺眼,违反我们对秩序与和谐的爱好”[2]149,还必须同时满足“显得脆弱而有病态,妨碍心灵自由活动的表现,因而引起不利的评判”[2]143等条件。惟其如此,我们评价这种丑的人物时才会产生“怜悯”的情感,而诗人正是利用这类反面因素去强化某种混合的情感——令人既可笑又可怖的情感波动。怜悯、可怖性的丑在诗中引起的情感变化,是莱辛对亚里士多德“疏泄”概念的继承和创新。
物质形体是莱辛美丑思想的客观基础。他提升了物质在艺术中的地位,对物质的关注是他构建“诗画异质”论的基石,这与他从媒介的角度考查诗画界限的方法互为表里。美和丑都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造形艺术与时间艺术又因各自的长处和局限,对美和丑的表现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二、艺术真实:题材与价值的关系
在莱辛的思想中,“美”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客观物质的对象;二是指一切艺术作品的最高目的和价值。自然界的物体有美丑之分,而美才是一切艺术追求的最终目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要求艺术真实平衡美与真的内在冲突。美的题材自不必说,丑的题材和作品价值即“美”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应该如何解决,是艺术能力“化丑为美”如何可能的问题。莱辛认为艺术家的才能取决于摹刻对象的美的级别,而与表现技巧和构思方式无关,即使不和谐的物象是真实的,不属于美就没有资格进入艺术的殿堂,但是他也否认艺术家不能利用丑的题材制造出美的作品。
尚未摆脱新古典主义影响的莱辛鄙视泡生和庇越库斯一类专门描绘低级趣味的画家,但是他不否认二人的艺术才能是高超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实现了艺术供人娱乐的目的。在绘画和雕刻中,畸形、丑陋一类的题材即便成为了作品的表现对象,它们本身的丑这一属性也不会得到任何改变。莱辛是从绘画给人们带来的视觉感受出发论证的,他多次提到丑的事物在绘画中和在自然中一样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感,但他并未否认过艺术家的能力,他认为在丑的事物身上,艺术家的才能仍然可以得到体现[4]。在创作中,雕像在表现拉奥孔遇难的场景时,诗中穿着衣服的形象脱胎为裸体的形象,诗中放声哀号的情态被冲淡为雕刻的叹息,这些都是按照“最富有孕育性的顷刻”这种符合真实的美来塑造艺术真实的。在审美欣赏中,艺术的介入能让形体丑脱离实体和习俗,过滤为表象的形式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去发现其中的美,由丑的题材引起的忧愁、畏怖、怜悯一类不愉快的情感也能进一步转化为快感。在这里,莱辛从美的视角来规定绘画和雕塑处理美丑题材的原则,他将真实置于美的范畴来化解丑和理想的内在冲突。这是由物体的空间并列性决定的,若艺术如实摹仿丑的对象就会沦为平庸的作品。莱辛苛刻地认为这已丧失其艺术的身份,艺术无法调动审美接受主体的想象去进行二次创造,是比美的缺席更糟糕的情况。
美与真在诗中的配合,比在绘画中要复杂得多。诗使用的是语言这种人为符号,描述的动作和情节在语言的先后承续中得到完整再现,美和丑的效果都得到了减弱。因此,莱辛无惧丑的题材会戕害诗的艺术效果,他的辩护相当隐秘。对于美,诗则要小心翼翼地处理,要通过美的效果——化美为媚的动态描写去构思物体美的呈现方式,避开对比例、色彩、尺寸等数学关系的精准描写。诗歌语言对物体美各部分的胪列既是“言不尽意”的遗憾,又破坏了美的整体性和空间性。对于丑,听觉符号的分解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它的真。诗人利用“反衬色调”去关注人物身上的矛盾性格所蕴含的可笑性,丑便失其为丑,而成为真的化身。但是,这种艺术真实并不具备科学意义,其目标是要执行美的意志,丑在这里就被转化为艺术美的组成部分。莱辛的“失其为丑”,实质上还是反对艺术表现丑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在真与美关系的问题上,莱辛的主张是以美为主,真服从美[5]。诗在宣扬行动中对比人物的完美和不完美所彰显的真实个性,体现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对旧传统的破坏给人的思想带来的变化,而诗(戏剧)的生动形象能够扩大受众群体的范围,启迪新阶级塑造符合理想的民族人物,去实现社会变革和改造人心的时代任务。与其说莱辛“否认诗所写的行动和思想感情可以美,即内容意义可以美”[6]340,毋宁说莱辛默认美是包括诗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先验价值。诗宜于描写动态性,这种特点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就是它的美所在。只不过,比起莱辛公开表示“美是造形艺术的最高目的”,莱辛拥护“诗是美的”的态度比较低调罢了。
朱光潜认为莱辛评述艺术作品的题材属性和审美效果的“问题的关键仍然在内容意义和个性特征描绘的真实是否有助于产生美的效果;这也就是在艺术中内容应该占什么地位的问题”[6]342。莱辛主张题材决定作品价值的信念,描绘美的题材就会把艺术创作导向美的生产。当题材的丑挑战艺术真实的时候,诗与画如何协调丑与理想在艺术形式中的具体表现,莱辛则把权力交由美来定夺。绘画的真实隶属于美,丑要经过真实与表情的改造才能转化为美的形式;诗中的艺术真实来自对美和丑的间接反映,通过题材的真实性去执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莱辛的文艺观在本质上是追求美的,真是为美服务的外壳,在画中真与美并置,美的地位是显性的;在诗中真实是为了实现美的,美的地位是隐性的。
三、审美接受:从生理到心理的递进
莱辛认为,美和丑既体现为作品题材与艺术价值的呼应,也影响着听众或观众的心理效果,对接受心理的关注体现了他艺术哲学中人本主义的一面。莱辛认为,美的题材给审美主体带来的生理反应是快感,接受主体需要依靠想象去形成逼真的幻觉;丑的题材引起的是反感,具有可嫌恶的性质,丑所引起的所有不愉快反应是无可避免的,都出于我们的自然本性。尽管艺术的介入使丑往积极的方面发展,但是丑感永远也不能转化为快感。美和丑都是以实体和表象的形式参与我们审美经验的生成,遵循从身体到心理、从生理到审美的变化机制。
物体美在接受主体审美经验的构建中经历了从实体到表象的变化。在绘画和雕塑中我们是通过视觉官能来接收美的,但眼睛并非是唯一的接受官能,更重要的官能是想象:“凡是我们在艺术作品里发见为美的东西,并不是直接由眼睛,而是由想象力通过眼睛去发见其为美的。”[2]44想象不受符号、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允许我们的官能透过审美形式去唤起同实物一样的意象,而在每一次想象中实物如在目前,于是快感便随着这种“逼真的幻觉”而来。诗,亦如此。如果说文学的外部形式主要靠读者的耳朵和眼睛把握,那么内部形式的再现则需要人类的想象力参与。无须论证,想象力是人类特有的心理能力,想象也是审美反应过程的重要环节[7]。诗的画意不一定可以物化为实体性的图画,但是,诗人运用语言文字将其描述出来,诗歌意象的“生动性”即“逼真的幻觉”,能够调动我们的想象去参与作品意义的建构,就能够引发我们如观看物质性图画时的快感。可见,我们的审美生发机制建立在感官印象的基础上,再经由想象的加工深化为精神性的审美感受。另外,想象力也是检验艺术家创作才能的重要依据。莱辛指出,画家摹仿自然风景的艺术能力比摹仿自然风景的蓝本更高超,因为人为符号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创作的难度。
丑不区分实体和表象,都会在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中产生负面情感,“并不是由于假定那引起嫌恶的坏东西是实在的,而只是由于它的单纯的表象,因为那表象却是实在的”[2]148。莱辛只同意让诗收留它,因为声音符号可以化解丑所带来的不愉快效果,甚至还能催生混杂着可笑性和可怖性的情感去增强诗的艺术感染力。可笑性增加丑的滑稽性与戏剧性,可怖性则能够产生怜悯来净化人的情感,使身体上的激动得到平复。当丑和具体的形状联系在一起时,丑的痛感就会在它制造出来的喜剧性和怜悯中被克服,产生净化情感的吸引力和快感。但是莱辛不同意亚里士多德“丑经过艺术的摹仿,情况就变得有利”的观点,还坚决否认形体丑引起的痛感可以转化为快感,可见他对丑题材的深恶痛绝。
美和丑以实体和表象的形式参与了审美经验的生成,接受主体的审美历程完成了由感官到审美的递进。我们以快感来回应美的艺术题材,调动想象去产生“逼真的幻觉”来构建作品的完整意义。经过艺术的作用,丑带来的痛感进一步转化为喜剧性和怜悯,以此净化丑给人造成的不适。
四、结语
莱辛的美丑观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与他对诗画界限加以绝对化和汲汲于发挥文艺的功利性去参加阶级斗争的主张有关,也与丑在艺术中的审美价值有关。首先,莱辛只关注到了美和丑的物质形式。物体的美和丑只在感性形式上见出,他否认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的理性意义,也就间接地否认了精神性的美和丑的正面意义。其次,将作品的题材和价值混为一谈,只要描写了美的题材就是美的作品,美的创作必须体现在对物体美的表现上。这种机械化的态度质疑艺术家和接受者的主体精神,否认了审美价值的多元性,也反映出他人本主义精神不坚定的一面。最后,极度尊美贬丑。艺术真实要符合美的法则,绘画和雕塑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表达,而诗宜于描写动态的优越性特点在他看来就是美的,所以诗对于丑的题材有恃无恐。莱辛在论丑时,其目的是通过寻求诗与画之间的界限,对不同艺术门类的特征进行具体入微的论证,同时也对西方古代艺术的发展史作出自己的判断[8]。由此更可见出,在莱辛心中,丑的题材根本不具备和美一样的地位和作用。
莱辛的美丑思想零散地分布在他对“诗画异质”的辨析中,又与他从媒介的角度探究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本质区别保持方法上的一致。美和丑的内涵既指向自然物体的形式特征,也关涉艺术真实与作品价值的对等关系,还会对接受主体产生特殊的心理效果,涉及到艺术创作、艺术价值、审美接受等诸多方面。莱辛的美丑观具有完整严密的思辨色彩和现实性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体现出他客观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却是不彻底的。他奉古希腊艺术为美的圭臬而无视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把美和丑的内涵从社会现实中独立出来,抽象地总结它们在不同艺术种类中的表现和特点,极度排斥丑的价值,又体现了他的保守性。结合莱辛探讨“诗画异质”的比较来分析他的美丑思想,藉此掌握莱辛美学思想的现实成因和深层内涵,对于我们思考美和丑在艺术哲学中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