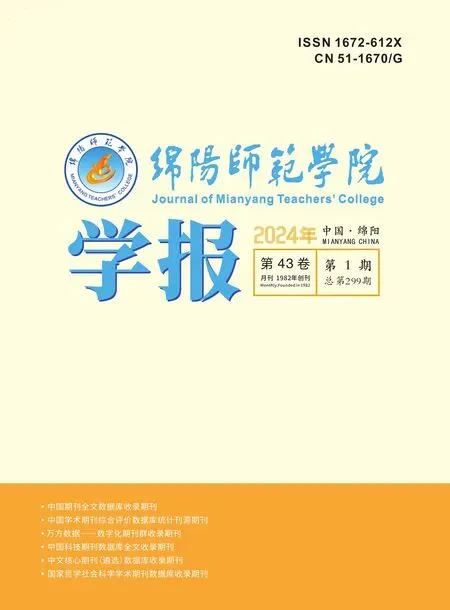从困顿的“人”到自由的“仙”:论民族舞剧《李白》中的李白形象
卢 莉,姚舒月
(1.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2.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一、引言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1]744(《南陵别儿童入京》),盛唐文化哺育下的李白,以昂扬奋发的乐观精神,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诗篇。其本人也多以“狂人”和“仙人”等各种形象,长期活跃于文艺作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民族舞剧《李白》在塑造李白狂狷、飘逸形象的同时,以艺术与历史相融合的形式塑造了一个更丰富多样的形象,展现了他逐渐从困顿的“人”转变为自由的“仙”的过程。
剧目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幕《月夜思》,以画卷的形式讲述了李白在岸边望月而思的情境,顺其自然地引入后面《仗剑梦》《金銮别》以及《九天阔》三幕主要剧情。其中前两幕以李白入永王幕系狱流放夜郎的故事为主线,插入供奉翰林遭赐金放还的经历,塑造了一个用世之心强烈却仕途坎坷、久遭困顿的“人”的形象,第三幕讲述了李白在流放途中和被赦后的感怀,塑造了一位逐渐放下,最终获得大道而解脱的“仙”的形象。尾声《鹏捉月》与序幕《月夜思》呼应,讲述了李白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后,最终在其《静夜思》的吟唱中独自踱步归去、捉月飞升。
从形象塑造来看,剧中的李白更接近“仙”,他的衣着永远素雅,多独自身着白衣素袍,脊背挺直,袖口宽大,举手投足颇有仙风道骨之感,同周围人的斑斓衣着迥然不同。尤其是序幕《月夜思》,开场就以画卷形式塑造了一副画中仙的形象。在茫茫白烟中,场景犹如画卷般缓缓打开,李白仿佛画中仙人,一头华发,身着白衣,披着长长的白袍,独自一人站在石岸之上,抬头仰望苍穹,时而抚摸胡须,时而举臂慨叹。明明站在岸边,但李白脚下的河岸却缓缓移动,打造出“舟不移岸移”的景象,意境飘渺,仿佛李白即将飞仙。后续的剧幕中,不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身在山野,李白也依然身着白衣素袍,有时候甚至散发赤足,仿佛已入无我之境,一副逍遥散仙的模样。
拨开外表的塑造,舞剧《李白》的深层意蕴在于以跌宕起伏的剧情深入到李白内心,着重展示了李白身为“人”的困境和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在剧中,李白不仅是“仙”,更是一位久在困顿中的“人”。
二、困顿的“人”:功业的渴望与幻灭
李白的困顿源自其对功业的渴望和对现实的幻灭。舞剧抓住了李白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对他所遭遇的外界束缚和内心苦痛予以了形象化的展现。
第一幕《仗剑梦》开门见山,演绎了李白政治生涯乃至人生经历中最难度过的危机——入永王幕系狱流放。这一幕由“老骥愤”“囹圄悲”“夜郎泪”三个片段组成,在生死存亡之间着力刻画了李白对政治功业的追求和失意。
李白入永王幕府,是为了实现其“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1]1225(《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时值安史之乱,中原四处沦陷,李白对此发出了“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1]113(《古风》其十九)的慨叹,深怀着对安史叛贼的无比愤恨以及对百姓的巨大同情。适逢永王李璘被玄宗分封至长江流域,玄宗下诏称“(永王)应须士马、甲丈、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2]6984,且“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同奏”[2]6984。由此,永王到江汉一带招兵买马、招揽贤士门客,并向在庐山隐居的李白三次发出招揽。李白虽已年老,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满腔的家国情怀并未因年华老去而消散。因此,尽管李白在《与贾少公书》中多次道出内心的惶恐不安和犹疑,称“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1]1234,且“勾当小事,但增悚惕”[1]1235,但他想以身许国的热切之心终究使他成为了永王的幕下。他以为当时的形势类似于东晋,需要他这样的贤士辅佐永王以收复中原,于是高歌:
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1]555-556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永王东巡歌》其八)[1]431
李白怀揣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奔赴永王幕下。舞剧对此情景予以了艺术化的展示:李白一头白发高束,身着白衣,在鼓点乐中,手拿卷轴及毛笔指点将士、挥斥方遒,动作大开大合、恍若舞剑。这里的李白虽然已是“老骥”,但也是意气风发的。
然而,李白的政治眼光是不精准的。在他满腔热情地劝勉永王收复失地、挽救中原之时,殊不知自己已然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肃宗和玄宗的父子之争,李亨和李璘的兄弟之斗,打破了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美好宏愿。永王兵败,李白被俘。他曾写下的《永王东巡歌》在有心人眼中已然成为他谋逆罪名的铁证,最终以“附逆作乱”的罪名锒铛入狱。热血沸腾的“老骥梦”破碎,李白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囹圄悲”。
舞剧以夸张的动作、具象化的道具以及高度凝练的人物设置,展示了外界对李白的束缚。李白树敌颇多,但剧中将所有的敌对人物凝练为一位对手,两人展开了一幕精彩的对峙。对手身着官袍、头戴官帽,趾高气扬地对李白步步紧逼,虽无言语,但气势锋芒毕露。随后两位侍从搬来凳子,请李白入座。李白步步退让,却也是退无可退,终究被迫坐下。这个“凳子”即是“罪名”的具象化表现,李白的坐下也意味着坐实了“附逆作乱”的罪名。本是寓劝于讽、字字饱含家国情怀的佳作,如今却被有心之人污蔑,成为了对他口诛笔伐的工具。李白在舞台上来回地奔赴,象征着为自己正名而努力。然而几根木棍组成一张密网,让李白困顿其中无处可逃。最终李白只能绝望地跪在地上,任由奸恶小人丢掉他的乌纱帽,一派凄凉。身陷囹圄、惨遭流放,李白遭遇了政治生涯中最惨烈的失败,身心都陷入了巨大的困顿之中。
曾经恃才傲物的李白,以为等来了他施展抱负的机遇,谁曾想却是有性命之忧的囹圄之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压抑着这位天才诗人,伴随着悲戚的笛声,李白负手跪地仰望苍天,几番跪起的动作,充分道出了李白内心的崩塌与建设。最终他捡起乌纱帽抱在怀中,表明了他对家国情怀的不放弃。此时舞剧以幕布背景的形式缓缓展示出《流放夜郎赠良宰》一诗。此诗原名《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1]567,是一首自传体长诗,亦是李白内心此刻最真实的写照。在诗中,李白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慨。他眼见家国“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的惨景,报国热情高涨,再加上永王的招揽,加入永王幕下,对此李白称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如今“扫荡六合清”,李白称自己“仍为负霜草”,希望“日月无偏照”,肃宗能体恤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减免他的罪责。诗的最后,李白表明自己虽然遭遇打击,但仍怀有一颗报国之心,希望“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使他“终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赤子之心不要落空。此诗字字真心,令人动容,却没能打动肃宗的心。历史上,李白仍然是等到大赦天下才得以脱罪。
若说第一幕《仗剑梦》是李白人生最低谷的刻画,那么第二幕《金銮别》则演绎了李白世俗成就最高的人生阶段。在这段时光里,李白应召入翰林,成为玄宗近臣,常随侍左右,写下《清平调》等千古绝唱,一时间风光无限。然而此时看似风光的李白,内心仍然是困顿的、不自由的。他的困顿源自率真性格和虚伪官场的冲突,舞剧对此有十分戏剧化的表现。
这一幕开始就上演了一场虚伪的官场图:群臣在欢快的音乐中笑容满面地打着招呼,但一转身个个脸上都带上了嫌恶表情,充分讽刺了官场的虚伪。天真率性的李白在这样荒诞的场面中挺着身姿进场,凭诗名得玄宗赏识,意气风发。这样的宠幸带给李白无限的骄矜,同时也招来了同僚的妒忌和僭毁。舞剧以斗酒的形式充分展现了这场冲突。李白身着白衣,头戴白色官帽,同周围灰色调为主的众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李白一人与众人斗酒,众人将李白狠狠灌醉,又高高举起,最后将他重重摔在另一宠臣脚下,本来讨好李白的群臣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可见官场的险恶和官员的趋炎附势。醉醺醺的李白似乎还没察觉到周围的危机,在醉酒中恍若至仙境,拿起长剑与众女同舞。有心陷害的小人拿长剑做文章,带领一众大臣在玄宗面前尽情诋毁李白。率真的李白斗不过这群虚与委蛇的同僚,最终无奈走向“翰林别”的结局,惨遭赐金放还。李白的政客梦,再一次破碎了。
对于官场的黑暗、同僚的诋毁,李白在诗中多有愤慨: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1]1113
以青蝇比喻势利的庸俗小人,以白雪比喻自己高尚的志向和品格。李白自认为是潇洒大度、脱略形迹的人,而那些小人却一再构陷他心胸狭隘、性情偏激。面对这些诽谤,诗人也生出了归隐之心。但纵观李白的一生,这样仕不如隐的想法不过是排解之语,政治功业是其一生难以割舍的追求。虽有还山归隐的意象,但更多时候李白还是唱着“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1]743(《别韦少府》),长期游走于各地,关心国家治乱。
其实,翰林供奉时期的李白,除了舞剧中所展示的因同僚陷害而饱受困顿,细读其诗,不难发现此时的李白还因其政客理想和词客现实的冲突而极度受困。李白的理想是成就功业大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藩书,并上《宣唐鸿猷》①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1]1460,记述了李白进谏兴亡之言的举动。然而,李白诗中却称“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1]709(《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他所进献的兴亡之言并未被采纳。玄宗虽甚爱李白的才华,瑶池宴会、玉辇出行都让李白随侍左右,让他奉诏作词。李白也写下了《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诗篇,被誉为“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3]106,但这与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1]1225(《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客理想相差甚远。他在长安写下了颇多评议时政的诗歌,但都未被采纳,最后还落了个“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头飞”[1]1132(《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的结局。理想不被理解以及无法实现的现实,亦成为李白困顿的来源。
总的来说,历史中的李白一生追求政治,也失意于政治。政治于他是毕生的追求,也是其痛苦的最终来源,他的政治生涯并不厚爱他。自青年至晚年,李白都热衷于仕途,渴望以身许国。然而回顾李白的一生,虽有诗名冠天下,但在仕途上却是反复受挫。青年时期的干谒、上书无门,壮年时期的赐金放还,晚年的永王兵败,无一不造成其内心的失意与痛苦,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实现其政治抱负。舞剧《李白》抛开以往“仙人”形象的惯例,别出心裁地抓住了这一特点,还原了历史上一个为功业理想所困、更真实的李白。
三、解脱的“谪仙”:超迈飘逸和陶然忘机
舞剧《李白》在塑造李白困顿的“人”的形象同时,还着重塑造了一个仙者形象。正如前文所言,将李白塑造为仙者不是奇事。例如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杂剧,以经典的“御手调羹”“醉草答藩书”“醉写乐府词”“醉后捉月”等情节,着力突出李白在诗才和性情上的非凡,塑造了“诗仙”“酒仙”的形象;再如《换夫妻》第七回《请乩语搬娶前妻》中术士扶乩,李白以“蓬莱散吏”的形象出场;又如《于少保萃忠传》第二十四传《于公荐贤置州县徐珵改讳治张湫》中,李白亦是作为神仙被小吏捧箕召唤而出。可见,以往小说、剧目中的李白往往被着重突出他超凡脱俗的一面:他蔑视权贵、不在乎名利,以金龟换酒、与风月同眠,甚至已然成仙,强调了他与芸芸众生的不同。舞剧对于李白仙者形象的塑造,则更关注他的内心,通过肢体语言等形式演绎出他内心从困顿到解脱的过程,最终羽化登仙,完成对自由的向往,达到“仙者”境界。
(一)大醉后的消解
舞剧中,李白内心的困顿是由醉酒来消解的,《仗剑梦》《金銮别》两幕均以李白醉酒落幕。《仗剑梦》中,李白梦想破裂、身陷囹圄且惨遭流放,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伤害。因此,在此幕最后,剧目特意安排了一段李白赤足拿起酒壶的独舞,以表现他对内心困顿的抵抗和解脱:
夜郎之路难行,身心受困的李白走得步履蹒跚,极其失意。他猛然想起包袱中的酒,用力地拨开层层包裹,取出酒壶痛饮。痛饮之后,是醉酒的狂欢。李白面带笑容,赤足舞蹈,动作大开大合,痛快至极。最后,李白紧紧抱着酒壶,梦回金銮殿前的往事,以醉梦消解政客理想破裂的困顿。在这里,酒是李白的慰藉,大醉是对困顿的消释。
另外,《金銮别》一幕中李白因同僚陷害而被迫辞别的时候,也上演了一场李白醉酒后的独舞。与之前不同的是,李白手中拿的是剑。“剑”对于李白而言是特殊的。他曾多次以“剑”入诗,如“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1]284(《塞下曲六首》其一),“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1]721(《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可见剑是其建功立业之志的寄托。然而此时的李白,却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1]189(《行路难》其一)。官场的勾心斗角、词客和政客的冲突,让他的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这样的困顿是如此的压抑和沉重,剧目仍然以醉酒的形式来完成李白内心情感的宣泄。在剧中,李白赤足持剑,尽情挥舞,背景中也加入了《将进酒》的朗诵,诗、乐、舞合一,表现了李白怀才不遇之情的消解,浑然一副高饮大醉的酒仙形象。正如李白诗中所叙:
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贤圣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1]180
金钱不足贵、功名不足惜,在时间的长河中,生命的价值都将消解,不如追求面前的美酒,以此获得心灵的自在与自由。虽然有满腔的报国热情,但现实的困境让李白深受束缚,对此李白选择以傲岸的身姿挥别令他困顿的官场。舞剧中的李白肢体语言极富感染力,尤其是最后的笑和离别将李白复杂的情感转变和豁达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李白肆意舞剑后,摊开双手仰天大笑,又由笑转哭,最后利落地转身,傲然地挺着腰,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个黑暗的官场。李白醉了,也清醒了。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所以他离开了,他也自由了。
可见,剧目对于李白困顿的消解,主要以“醉酒”来完成。这既符合李白嗜酒的史实,也符合仙者形象的塑造。这种“醉酒”不是烂醉如泥,其本质也不是逃避现实。这种“醉酒”,是潇洒痛饮,是欣然大醉,是对黑暗现实的轻蔑,也是李白对内心的守护。因为李白的困顿表面上源自其功业追求的失败,而本质则在于他傲然天真的个性无法同现实的政治环境相恰合。如果李白真的只渴望功业,那么面对官场的虚伪和黑暗、词客现实和政客理想的冲突,凭借他非凡的才情,他只需低头迁就,功名就唾手可得。可李白与常人不同,他是人,也是傲然兀立的“仙”,他坚守其内心的理想和美好,不愿做为功名低头的庸碌凡人。当现实与内心的冲突无法和解时,李白只得借助醉酒来实现内心的自由。他的醉是打破了一切现实束缚的醉,不论是时空还是金钱都不再成为他的枷锁,在醉态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正如最后一幕《九天阔》中,李白上演了一段《月下独酌》的醉舞,在酒醉中获得了极致的精神体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其一)[1]1063
同渔人、樵夫分别后,李白独自坐在山间月下,举杯遥敬高处的月亮。在酒的催发下,李白从舞台一角的石桌前逐步移至舞台中央,反复做出敬酒的动作,随之翩然起舞,以群舞组成的月亮和影子也跟随李白做出相同的动作,形象地演绎着诗境。最后李白又回到舞台边缘的石桌前,深情地凝望着月亮,再次对着月亮拱手遥拜。
在醉酒中,李白摆脱了世俗的一切,抛却了对功名的追求、辞别了相交的好友,回到山间明月下,独自观照自我。他频频举杯,是在邀月,也是在问心。功名追求和内心自由孰轻孰重?千金厚禄也好,万古垂青也罢,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通过醉酒,李白排除了外物的干扰,在花丛下享受着个人的体验,当个体的精神放大到极致,外界的一切都随内心而动,因此“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亮和影子都随“我”而动。最终,李白达到了自由的境界——“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所谓“无情”,要追溯到《庄子·德充符》中所讨论的“有情”与“无情”之争: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4]221
也就是说“无情”并非指没有感情,而是指不因为喜好和厌恶来伤害身心,要顺其自然,不给生命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李白这里所说的“无情游”也就是指回归自然本性,不必强求,也不必客套,率性而为。即李白真诚地表示,希望自己和影子、月亮的交往是永远的“无情游”,聚散随心,并期许下一次能和它们在天上的云汉中相见。与无情之物结无情之游,却是最有情之语。此情此景,李白当称为“得道之仙”。
总之,舞剧反复以“大醉”的行为来表现李白对内心困顿的消解和对自由的追求。同时,舞剧也看到了山水以及明月对李白的重要意义,演绎了他在山水、明月中抛却一切烦恼,终获自在的意趣。
(二)山水中的自在
从李白的形迹和所留存的诗歌来看,他是喜爱山水自然的。其足迹遍布名山大川,亦曾多次入山修道,追求无碍自在。山水对于李白,就是其精神的家园,他总是能从中获得排解。正如其诗中所写:“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1]1070(《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在名山的游览中,身心都远离了尘俗,达到了逍遥自在的境界。舞剧第三幕《九天阔》所刻画的李白,正是一位在山水中陶然忘机的仙者形象。
此幕的背景幕布换成了水墨山水图以营造李白身入名山的情境。伴随着民歌风调的音乐,群舞身着白衣,头戴蒲扇配饰,长袖飘飘,莲步轻移,缓缓入场。她们跳起了白纻舞,仿佛水中清波,又如山间云雾,极其灵动。渐渐地,渔人、樵夫以及二三野客逐渐出现在场景中,他们或下棋,或谈乐。正如李白《与贾少公书》中所写“混游渔商,隐不绝俗”[1]1234,远离官场是非的李白,不是完全的隔绝尘俗,而是深入民间的远游。因此,舞剧中的李白自然地加入到这些山野之客中间,同他们喝酒谈笑、畅聊古今。伴随着交游的深入,舞剧还安排了一出踏歌舞,即渔人、樵夫在岸边跳起了欢快的踏歌之舞。手臂以撩、甩、晃等动作为主,腿部以踏步、跨腿和踏瞭腿为主,身姿自在随性,充分体现了极具民间色彩的“达欢”意识。剧中李白也逐步加入到群舞的“踏歌”之中,随渔樵共同起舞,展现了他徜徉其间的欢乐与自在。
可以说,在官场中深受迫害的李白,终于在山野中找到了真情实感的朋友。他在渔人、商人等野客中收获了纯洁的友谊,从而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满足。
另外,第三幕《九天阔》还以《孤云闲》一节展示了李白在山水中忘怀一切功业追求,陶然于山水之乐的自在之境。这一小节中,没有复杂的剧情和多重的人物关系,主要展现了李白放下一切后的豁达。李白面带笑容,身着白衣,赤足舞蹈,姿态潇洒又颇有力道,再现了他经历了重重困顿,在酒、友、山水中悟得大道,以昂扬的精神去拥抱人生的心路历程。这样的李白不仅是陶然忘机的闲散客,更是看破执念的逍遥子,是得道的“仙”,其内心再度丰盈,充满生机。
(三)以鹏捉月的自由
关于李白的死亡,历来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醉死,据《旧唐书》载,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5]5054;二是病逝,据王琦《李太白年谱》,李白在永王事件后,仍然怀揣着报国之心,听闻李光弼带兵保卫吴越,他亦想杀敌请缨,曾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抒发其请缨杀敌、建功立业的志气,可惜最终因病被迫放弃,最后于宝应元年病死于当涂,时年六十二岁;三是溺亡,此种说法多见于民间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说法便是“水中捉月”而亡。如《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追月而死”②[1]1612,称李白身着宫锦袍,姿态傲然,最后醉酒捉月而亡,突出了他的傲岸不羁。此外,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还有“(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6]193的说法。此说法中的李白更添道家色彩,不再是身着宫锦袍,而是一位好黄老之术、身骑青牛的道士形象。最终捉月而亡的结局更增添了道教色彩,突显了李白的仙人之姿。
民族舞剧《李白》在以往“捉月而亡”的基础上,给李白安排了一个更加艺术化和理想化的结局——李白在自然山水中放下了一切世俗的追求,最终反复吟咏着那首最为简朴的《静夜思》,犹如鲲鹏一般,奔赴明月。相比历史上的病死当涂和颇富传奇色彩的“捉月而亡”,舞剧的安排显然更加浪漫。李白的结局不是死亡,而是化身理想中的鲲鹏,奔赴月亮,与明月永存。
值得注意的是,舞剧在这个结局中选用了两个关键的元素:鲲鹏和明月。
李白对于鲲鹏的吟咏和寄托是深沉的。他曾赋《大鹏赋》以大鹏自况,想象自己如同大鹏“块视三山,杯观五湖”[1]5,“跨蹑地络,周旋天纲”[1]10,充满了斗志和生命力,并且最终“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1]10,摆脱了现实羁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另外,李白还有《上李邕》《临路歌》两首诗歌,均以大鹏为主体: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揺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1]511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1]452
两首诗歌中的大鹏同《大鹏赋》中的大鹏一样,均脱胎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具有至大至刚的特点,是自由、理想的象征,只是不同诗篇中的大鹏遭遇各有所异,也象征了诗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不同境遇。舞剧将李白物化为大鹏,既符合李白的精神寄托,也极具浪漫色彩。
同样,李白对于月亮的呼唤和归宿感也是极强的。他曾在诗作中多次吟咏月亮。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识月;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邀月;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寄月;有“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的望月……毋庸置疑,李白每次和月亮的互动,都是一种“人月相得”的精神体验,其真正的旨趣在于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尤其是其千古名篇《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346。
明月皎皎于床前,诗人以为此等天上的清辉是地上的寒霜,短短一句沟通了天地;而后诗人在举头和低头之间,达到了人月相得的精神境界:这轮亘古不变的月亮勾起了诗人对儿时月和故乡月的记忆,时空的界限就此超越,物与我也就此相连。
纵然李白一生写过无数佳篇,但大道至简,他最终还是最得意于这首最淳朴、最自然的小诗。舞剧中,李白反复吟咏此诗,以鲲鹏之姿回到月亮,也就象征着他获得了真正的解脱和自由,回到了他最干净、明亮的精神家园。回顾李白的一生,纵然汲汲于“使寰区大定”的政治理想,但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才是他生命的本色。舞剧这种极具艺术化的结局,圆了李白内心最根本的梦想,也是对他内心更真实的还原和表达。
四、结语
李白虽离我们相距千年,但关于他的书写却从未停止。在流传中,李白被不断演绎,或神化,或仙化,如何认识李白,如何贴近李白,如何演绎李白,成为了重要话题。舞剧《李白》对于李白的塑造,是对诗、乐、舞三种艺术形式的贯通,是历史与艺术的融合。
剧目以李白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却打乱了时间的顺序,以现实和梦境的形式串联起李白历经永王事件惨遭流放、供奉翰林又遭赐金放还以及纵情山水终得大道的人生经历。事实上,李白参与永王事件已是人生的暮年。他于至德二载(757)加入永王幕下,同年就惨遭流放,于乾元二年(759)获赦,此时李白已经五十九岁[7]104,距离他人生的尽头只有三年了。舞剧以此事件为开篇,是对李白人生理想的深刻认识。因为,政治抱负是李白的人生之重,前半生他不断干谒渴望仕宦,后半生在经历了赐金放还、永王事件等政治失意后仍渴望随军杀敌建功立业,只不过囿于病躯才作罢。舞剧以永王事件为开场,梦回金銮为第二幕,抓住了李白仕途中的典型事件,展示了他对于功业的渴望和政治上的失意,塑造了一位本是天之骄子却在政治追求中屡受困顿的人的形象。另外,由《仗剑梦》《金銮别》再到《九天阔》的顺序,也展现了李白内心的转变:从因政治理想而饱受困顿到从山水、诗酒中获得出离世外的解脱和自由,完成了从“人”到“仙”的转换。这样不仅突出了李白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更有力地表现了他内心的豁达乐观和自由精神,并且后者才是李白生命的本色。正是因为李白的豁达和对自由的追求,才使得他能从众多仕途失意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化中唯一的“诗仙”。
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便是阅读他的作品。舞剧中随处可见对李白诗词的化用,不仅使得舞剧的表演更贴近李白的内心,也使得整个剧目更富有艺术性和文学性。例如在《仗剑梦》一幕中展示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此诗是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篇幅颇长,真实地道出了其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自身前途的担忧,抒发了其政治感慨,情感悲愤。结合舞者跪地仰天等舞蹈动作和背景中的悲壮音乐,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李白此时复杂又激荡的内心。又如《金銮别》最后一节时,舞剧以帷幔的形式缓缓展示了李白《将进酒》一诗的书法作品,字字潇洒又遒劲,增添了舞台的美感。接着,在背景音乐《将进酒》的吟咏中,舞者以充满力量和气势的动作传递出文字中的情感和意境,其赤足舞剑、仰天大笑等动作刚好与吟咏声中的怒音、停顿和起伏相配合,道出了李白此时的悲愤和豪纵,诗、乐、舞就此贯通。
总之,民族舞剧《李白》对李白形象的塑造是一场历史与艺术的融合,它不是李白生平的再现,而是对李白内心的表达。从“人”到“仙”的转变,道出了李白对政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注释:
① 《新唐书·文艺传》:“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又王应麟《困学记闻》:“李白上《宣唐洪猷》,亦记本传召见金銮殿一篇者也,今集中阙,疑对策之类,言王霸事。”
② 据松浦友久《关于李白“捉月”传说——兼及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现今流行有关捉月著述,大都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为最早。但清王琦《李太白年谱》(王注本,卷三十五)中宝应元年(762)条中,只记有:‘《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由于只照引未被确认的原典,至少在现行的《唐摭言》诸本中,不见这一记述。或许,乾隆年间,王琦所用的《唐摭言》原文中可能有这一条,因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从王注本再转引此条时也应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