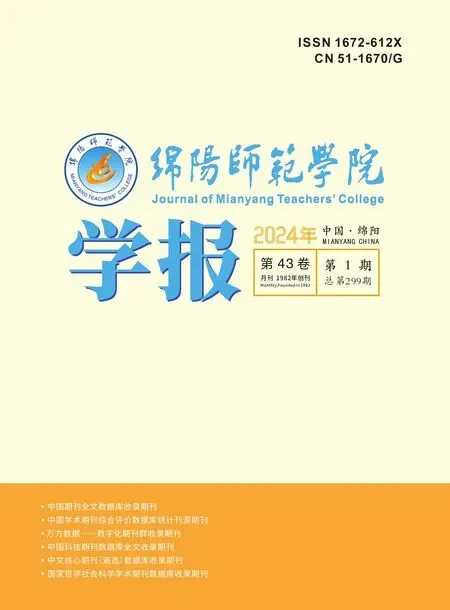文字与图像关系的“再穿越”
——以《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为中心
樊 祥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影像技术的蓬勃发展,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萌生的以图像为核心的生产与消费逻辑愈渐强盛,图像的功能适用域得到极大拓宽,成为普泛化的社会存在,美国学者米歇尔据此将之名为“图像转向”。图像转向的文化症候及其诱触的连锁反应,掀起了当前学界关于图像问题的研究热潮,语言与图像的关系①便是其重要的问题域。赵炎秋的新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以下简称“赵著”),即是一部相对系统全面勘探、解析和研究语图关系的力作。这本著作既可以说是他对先前“形象诗学”研究的一次跨媒介“穿越”,也可以说是对业已经过大量阐释的语图关系研究的“再穿越”,因而提出不少极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洞见。鉴于此,笔者拟从生发缘由、理论新质、方法论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以期阐明其对当下语图关系研究的学理贡献。
一、偶然还是必然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是个古老的话题,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新媒体技术的普及,更是逐渐被推向理论舞台的中心。因为图像对语言的不断侵入、僭越和挤压,造成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减和逼仄,由是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语图/图文”之争。赵著的生发背景即源于此。虽然他在后记中明确声明,研究语图关系主要缘起于2010年和2011年的两次会议,但笔者认为,这两次会议仅是触媒,因为其在2008 年发表的《在理解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便已经涉及语图关系的问题,而且还被用于同年7 月在青海西宁举办的“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由此可见,赵炎秋其实早已开始关注语言与图像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赵炎秋以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世界图像时代”的命题为切入点,客观剖释了该命题蕴含的三个理论层次,从而既廓清人们通常片面援引其佐证“读图时代”的认知舛误,同时也阐明语图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对“关于世界的图像”和“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有意识界划,启发我们要对当前图像占主因的文化症候作多层次的观照。相较于语言,图像表征世界具有直接性、形象性的优势,所以它的疯狂增殖和过度丰裕的确可以说是“读图时代”,但这仅是呈现意义上的“关于世界的图像”,而非海德格尔所意指的“世界图像时代”,即“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被把握”不仅表明世界是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还标示世界图像化的结果。当然,这还不是指以图像的方式把握世界。以图像的方式把握世界,除了指涉世界图像化的结果外,它还包括整个图像化的运作过程。应该说,这才是“世界图像时代”预言的真正要义。然而,这是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世界的图像化,抑或说以图像的方式把握世界,最终还需要经过语言/心灵/思维的再转换,世界敞开的意义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虽然可以将世界以图像的方式表现出来,却很难完全将它把握为图像,更无法主要用图像的方式来把握它。要把握世界,主要还得借助语言的方式。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类思维的主要载体。……图像的作用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大,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对立其实也没有人们所想象得那样严重。……而既然这样,在图像狂欢的年代,我们就仍有理由相信,语言以及作为语言的艺术的文学,是不会衰亡的。”[1]
概括来说,这段论述可以简要归纳三点信息:第一,语言与图像均是表征世界的方式,不过由于语言与思想的直接对应性,所以它的表意能力更突出;第二,语言与图像虽说存在对立,但绝非完全的二元对立,它们的对立只是表征世界的分殊,而在探掘世界意义方面则需要二者相互配合;第三,图像的“井喷”式涌现尽管造成语言/文字/文学的边缘化危机,可依凭特有的表意优势,它们的合法性仍无可置疑,只是原有的显赫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跌落。显然,这是对此前争论得沸沸扬扬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表态。进一步来说,赵炎秋的这些真知灼见,即使还比较笼统,未能深入展开,但也已经超脱片面看待语图关系的情绪化认知,具有继续深拓和挖潜的可能性。他在两次会议中关于语图关系的意外之“思”,与其说是其声称的转向缘起,毋宁说是将早已揭橥的这种潜隐的可能性快速变现的助推器。换句话说,他对语图关系的关注,并非一次突发奇想的偶然之“思”,而是实已含蕴必然性成分在内的积极主动之“思”。
如果联系他之前的“形象诗学”研究,那么这种由语言/文学/形象到图像的理论位移,便可得到自洽的说明和佐证。《形象诗学》是赵炎秋根据其博士论文不断思考和打磨成的一部关于“文学形象”研究的扛鼎之作。在这本著作中,他从作品的角度出发,钩沉文学本质研究的四条路径(形象论、情感论、语言论和形式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辨与整合,将文学的本质界定为文学形象。于是,围绕文学形象,他又从它的内涵、构成、评价、意义、创造、接受等方面作了全景式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著主要探讨的是文学形象,但也零星涉及有关图像的论述,只不过是作为前者的参照或注解,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图景。如他对文学语言如何过渡为文学形象的解释:“语言是抽象的,它只是一些干巴巴的符号,没有感官直接性。因此,它不能像绘画中的线条与色彩、雕塑中的石头与黏土,甚至音乐中的音响与节奏那样,依靠自己本身的物质性来建构文学形象,而只能依靠符号所表现的意义。”[2]214-215也就是说,文学形象生成机制的内在奥秘就在语言的“构象性”,但由于语言不像绘画/图像那样可以凭借物质材料直接构象,所以只能依赖语言符号具有的表意特性。虽然这仅是对语图构象差异的宏观勾勒,但透过此可知其实乃之后相关研究的理论滥觞。
或许正是由于赵炎秋孜孜于对文学本质/文学形象问题的不懈探索,所以当异军突起的图像理论大肆蚕食文学的版图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自然也就合理顺延为新的问题域。换言之,他并不只是因语言/文学遭遇危机所激起的使命意识,而是对文学及其基础理论的熟稔,使其切实察觉语言与图像之间绝非简单的对立或同质关系。因此,他由语言/文学向图像研究领域的跨媒介“穿越”,其实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合力促成的结果。
二、语图关系研究的“再穿越”
如果说赵炎秋在《形象诗学》《理解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中的相关思考,只是对语图关系所作的初步识断,那么《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则无疑是全面地绽出。因为在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不断“交涉”过程中,他逐渐强化和开掘了对语图关系的原有认知,从而实现了理论阐释的跃进和“再穿越”。既是如此,这便意味着其研究具备新的理论质素。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重勘文字与图像的辩证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文本“之间”“之内”两个层面。就前者来说,它是对文字与图像两种文本之间关系的总体认识。赵炎秋并不否认文字与图像存在对立,但却反对将之无限放大,以至于导向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极端情形,因为这既非理性甄别后的价值判断,亦非艺术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对立毕竟只是文字与图像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其还有另一种相互联系的内生形式。因此,他将这两种形式辩证地概括为“异质性”和“互渗性”,并就二者的表现分别作了详细阐说。“异质性”指的是文字与图像存在和反映世界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呈现形式与思想关系的差异。简言之,“图像以具象的形式存在,它对世界的反映是直接的、直观的,而文字则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它对世界的反映是间接的、抽象的。……就图像而言,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一致的;而就文字而言,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不一致的。……图像与思想的关系是间接的、分离的;而文字与思想的关系是直接的、同一的”[3]90-93。至于“互渗性”,则是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相互支撑性、相互渗透性和相互转化性。可见,异质性和互渗性的理论归纳,实已恰切道出了文字与图像辩证关系的真谛。
就后者来说,它又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是指文字与图像共处同一文本之内的主次关系;广义层面是指文字与图像所建构的内部虚构世界的异同关系。赵炎秋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指认和识辨文字与图像表征世界的符指差异,即文字用所指、图像用能指,客观而雄辩地阐明了二者同居一文本的主次问题。在他看来,文字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同构性关系虽然生成实指效果,但这并不代表其在同一文本中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种实指效果主要是就符号内部(能指→所指)而言,可事实上它与世界的联系是由所指完成的。相反,图像的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非同构性关系虽然导向虚指效果,但这也并不代表它在同一文本中必然处于次要地位,因为这种虚指效果主要是就符号(能指)与其所表征的世界而言,符号的所指与之无关,也即它与世界的联系是由能指完成的。概而言之,在同一文本内,主次之位的划定需要根据把握对象而定,若把握思想,那么文字占主导地位;反之,若把握表象,那么图像则占主导地位。其实,“这完全是由观察的角度决定的”[3]114,因此文字与图像的主次问题遂得到辩证地解决。当然,更令人惊叹的是,赵炎秋对文字与图像辩证关系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探讨了可能世界理论视域下的艺术虚构世界。他认为,文字与图像艺术虚构世界都是纯精神性和想象性的可能世界,但由于二者自身的差异,所以导致建构的虚构世界在表现范围、真实性标准、世界形态与类型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同。
由是观之,赵炎秋对语言/文字与图像关系的辩证图绘,不啻是一次新的理论“穿越”。因为自文字与图像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以来,人们通常对之持存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基于社会图像化的客观现实,极力鼓吹和肯定图像对文字的优越性;一种是面对图像的挤压和僭越,奋起捍卫文字的坚固领地;一种是综合看取二者的关系,即承认它们各自的优势,文字与图像可以相互增补。显然,第三种看法更值得重视,因为它以辩证的视域摒弃了那种简单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但笔者认为,这种辩证的看法还不彻底,具体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假如这种辩证的视域是从整体层面(文本“之间”)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宏观指认,那么我们实际并不清楚它们同居一文本的情况;另一方面,假如这种辩证的视域是就文字与图像结合的作品(文本“之内”)而言,那么我们也很难确当地厘清它们在文本内部的辩证关系,同时还可能因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联系,作出文字优于图像的主次判断。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职是之故,赵炎秋从文本内外两个层面对文字与图像与“异质性”与“互渗性”与“实指”与“虚指”关系、艺术虚构世界的辩证阐发,无疑切中时弊,不仅深化了语图关系的研究,而且也体现了他极富创造性的理论开拓意识。
其二,重释文字与图像思想的生成机制。这主要表现在鞭辟入里的符号学分析,从学理层面澄清并消除“图文之争”的理论龃龉。承上所述,赵炎秋通过解析文字与图像表征世界的符指差异,已经对二者关系予以辩证的理论定位。也就是说,图像与文字作为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各有优长,毋须将之置于非此即彼的位置,以致漠视它们的内生联系而过激地作出“文学终结论”的单维判断。应该说,这还只是总体的勾描,并未具体解释它们的符指差异“何以”能够解消图文对峙的惯常认知。因此,他围绕文学形象、图像表象及其同思想建构的相互关系,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推衍,从而使“何以”解消的问题得以昭然若揭。就文学方面看,他认为文学形象内部构架的四个层次(语言、语象、具象、思想)可以划为两个符号层级,一是语言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层,二是具象与思想作为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形象层。文学形象即源自语言的构象功能,但由于语言的符指具有任意性和人为性,所以它在构象的过程中,其意义的独立性并没有完全消散,而是依然在发挥作用,由此它既可以表现能为感官把握的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也可以表现无法用感官把握的深藏于内心的隐秘思想。然而,正因文字表达思想的直接性和清晰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内涵思想的丰富性。就图像方面看,情况则与之相反。由于图像是用能指/表象/画面表现世界,它们的建构材料(如线条、色彩、光线、体积等)并不像语言/文字那样本身具有意义,所以图像思想只能通过图像的表象来反映。如此一来,图像表象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也就决定其往往只能表现视觉可以把握的客观事物的外显形态。同时,图像思想隐匿于图像表象的客观现实,也决定其表达思想的简单性、间接性、模糊性和开放性,但相对来说也更为丰富。
不难发现,文字与图像建构思想的基本路径大体相似,即都需要通过“象”的中介,可由于形塑“象”的物质材料不同,所以导致它们的表意机制也存在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仅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是文学形象,还是图像表象,它们的表意方式均存在优势和不足。这表明,语言/文字与图像作为两种表征世界的方式,二者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反观彼时崛起的“图文之争”,包括继而由之引发的“文学图像化”“文学终结论”等话题,其实质都在于语言/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表意“特权”的争夺。实事求是地说,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立场围绕语言/文字与图像问题展开的理论交锋,的确多角度地展示了这两种符号的运作特点及表意优势,深化了我们对语图关系的认知。不过,从符号学的角度辩证且深入地解析语言/文字与图像符号表意机制的异同,其时并不多见。从此意义上来说,赵炎秋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为重新介入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学理依据。
其三,重审“言象意”的层级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以“象”“意”关系为基准,系统地区划了人类的四种表征方式和两种“象”类型。简单来说,赵炎秋认为,由于语言的符指与思想的天然关联性,所以它既能够直接表达思想,也能够专门构建形象,于是文字类作品便存在“文字—意义”“文字—形象”两种表征系统,前者如哲学著作,后者如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前者就不符合“言象意”的结构模式,后者则明显契合。就图像而言,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它缺少“言象意”结构中的“言”。不过,从宽泛的层面来说,其建构材料也可以看作某种类似于“言”的成分,故而对其亦可作“言象意”的结构分析。由于图像是用能指表征世界,它的具象性决定其能够直接构建表象,但图像也需要表达思想,因此它也存在“材料—表象”“材料—表象—意义”两种表征系统。后者显然符合“言象意”的结构模式。进而言之,如果只关注文学与图像作品中的三种表征系统(排除“文字—意义”型),那么即可管窥“象”基本都处于枢纽的位置,但其功能指向却不同,由是遂构成审美之“象”和表意之“象”两种类型。不言而喻,“审美”和“表意”的限定差异,意指前者着重于构“象”,后者聚焦于达“意”。前者的“象”自成独立体系,“意”并非艺术家关切的重心;后者的“象”缺乏完满性和自足性,仅是达“意”的手段与途径。虽然这两种“象”类型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并不代表它们彼此绝缘,因为它们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所以其边界较模糊,存在一定的过渡性,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是纯审美或纯表意之“象”。
毋庸置疑,赵炎秋对“言象意”内部结构进行的这种层级划分,是相当有见地的。这不仅是由于他深入文字与图像的内部,将它们各自的特点、运作机制及其盘错的复杂关系外显化,而且他还通过这种外显化,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偏救弊。典型的案例就是他对魏人王弼“言象意”观念的反思。他认为,王弼以《周易》为批评对象所建构的是狭义的“言象意”结构,也即那种不含审美之“象”而仅适用表意之“象”的文字与图像类作品。这就警示我们,如若不加辨别地把这种狭义的“言象意”结构模式的批评实践普遍化,而忽视其它类型,如审美之“象”,那么导致的结果便是理论批评的错位。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就是它的实践批评,尤其是将之用来重新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结出不少的硕果。然而需谨慎的是,这种试图以文字与图像的“言象意”关系重释具体文本的理论冲动,需要认真考辨批评对象能否与之正向对接的问题,或者说应该对接“言象意”结构中的哪个层级,以避免笼统、宽泛的运用。正是在这个层面,我们说他对“言象意”结构的层级划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破立结合”的辩证思维
任何一种研究都需要方法论的支持。通常而言,研究方法是确保研究课题能够取得理想研究效果的工具与手段,也是主体思想、观念和意志的外在投射。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指出:“所谓方法就逻辑程序的体系,……学者对于自己设立的命题,正因为在逻辑上得到了证明,才主张它是真理。而支持这种论证的整个结构就是方法。……方法不过是手段,所谓手段是由行使主体的意志如何而决定其死活的中介物。”[4]19-21因此,在阐明赵炎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理论新质后,有必要迂回就贯穿整个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理论透视,因为它既可以展现这些理论新见的具体生发过程,也可以洞悉其背后的思想推手。笔者认为,这一推手就是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正是赵炎秋“穿越”文字与图像之间种种迷雾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当然,推动和牵引这条方法主线不断演进的则是他同古今中外众多“他者”所展开的“对话”,以及由此采用的破立结合的论述方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横贯其间的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说,不论事物内部还是事物之间,它们都并非独立、静止地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呈螺旋式地发展,因为矛盾的可转化性切断了任何非自然力量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所施加的阻碍。显而易见,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矛头直指各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它所追求的是“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虽说对事物进行绝对肯定或否定的二元论判断,某种程度上也能获得“片面的深刻”,但毕竟容易导向视域的盲区,无法形成全面整体的认知。“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正是对此种认知盲视的纠偏。可以说,赵炎秋秉持与践行的也正是这种思维方法,最显明的征象就是他对文字与图像的“异质性”与“互渗性”、“实指”与“虚指”、“审美之象”与“表意之象”等关系的辩证识断。但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辩证识断是如何被结构和充盈起来的,也即通过何种方式逐步进抵语图关系的这一内核,于是问题遂转向具体论证的层面。
综观他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推进这种辩证认识不断生发的关键就是强烈的“对话”意识,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破立结合的论述方法。因为在同“他者”关于语图关系研究的对话过程中,认知视域的分歧反向激活和唤醒了其内心潜隐的理论冲动,从而使他在这方富饶的沃土中得以继续腾挪施展,所以围绕“他者”的观点进行“破”“立”正反两方面的阐释,自然也就成为合理的研究路径。总的来说,在《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中,赵炎秋与古今中外的“他者”展开的对话主要有三次:对莱辛的诗画差异说、赵宪章教授的语图关系论、王弼的“言象意”观的理论反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与赵宪章的对话,因为这次对话不仅直接促动他开始着力聚焦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而且由此还牵出一次同索绪尔展开的关于语言与文字是否分属同一系统的更深层次对话。毋庸讳言,这几次对话既是思想的交流,也是理论的博弈,它们的基本逻辑大体相同,即都是先分析莱辛等人观点的恰切与偏颇之处,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进而实现辩证的超越。
首先是与莱辛的对话。谈论语言与图像、诗歌与绘画、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关系,莱辛往往是绕不开的理论家,这主要归因于他在那本享誉盛名的著作《拉奥孔》中最早对这两种艺术的差异作了相对系统的考察。所以,在“读图时代”的语境下重探语图关系,莱辛的诗画差异观自然成为高频率被征引的对象。这不光是由于“经典”光环的影响,更是由于他的理论阐释的确触及诗画的某些重要区别。但任何理论都不会绝对无懈可击,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疏漏,只不过经常被主要优长所掩盖。莱辛自然也不例外。与绝大多数学者征引莱辛的理论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不同,赵炎秋凭借深厚的古典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对莱辛的诗画差异理论进行了辩证地剖析。一方面,他从媒介、题材、观众接受、艺术理想四个角度概述了该理论的具体内容,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又从范围、时代、探讨诗画界限的出发点三个方面指出了其理论局限(“破”),尤其是第三个方面。因为通过辨析莱辛诗画差异观的根源,他抛出了自己的观点(“立”)。如其所言,“莱辛不从诗画媒介本身去探讨诗画之间的差异,而从它们蓦仿自然的角度去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抓到差异的本质”[3]67-68。因此,诗画关系的诸种差异就被锚定在特定的媒介维度,而这种原生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点:前者的媒介具有人为性,它是用所指表现世界;后者的媒介具有自然性,它是用能指表现世界。所以,经过这样一种跨时空的潜对话,他基本确立了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核心基质。
其次是与赵宪章的对话。赵宪章是我国研究语图关系问题的著名学者,在该领域成果丰富、成就巨大。2012 年,他在《文学评论》第2 期发表的《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一文,对语图关系作了极具理论思辨色彩的符号学阐释,特别是对语言实指和图像虚指功能,以及语言“隐喻”修辞属性所导致的图像化、虚指化的语象变体的分析,更是独出机杼和摄人心魄。然而,他通过拔升和倡扬语言实指功能而强调其在同一文本内的主导之位,其实并不完全符合艺术史的发展实际,亦即未能辩证看待语言与图像主次之位的动态关系。对此,赵炎秋提出不同的见解,并撰文与之商榷,这就是发表于2012 年《文学评论》第6 期的《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赵著第二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他围绕赵宪章文章中的几个核心论点,逐一辨析,在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思想的角度看,语言是实指的,图像是虚指的;从表象的角度,图像是实指的,语言是虚指的”,“语言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只是一个或然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是以思想作为判断的依据还是以表象作为判断的依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图文自身的要素及其运作方向,以及其外部条件”[3]125。但也有学者对他的观点表示质疑。如赵敬鹏就指出,赵炎秋的文章“名曰探寻‘文字与图像’,实则通篇谈论‘语言与图像’,全文混淆使用‘语言’和‘文字’之处比比皆是。既然语言和文字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那研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显然不等于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而文字符号的实指或虚指,也就成了另外一个问题”[5]。言下之意,赵炎秋从“文字与图像”的角度再探语图关系并不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因为文字与语言分属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所以它们既不对等,也不能简单置换。于是,问题便聚焦于语言与文字是否如索绪尔所论证的那样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由此,赵炎秋遂又同索绪尔展开了对话,这就是他2015 年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 期的《语言与文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之四——重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赵著第三章第一节的主要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索绪尔主张语言与文字分属不同符号系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文字只是表现语言的载体、语言可以独立存在、语言先于文字产生。这三点虽然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内比较自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并不完备。因为语言与文字并非只是简单的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而且脱离文字的语言很难发展成一种相对成熟、精细的语言,此外文字也有可能先于语言而存在。循此可见,在对赵宪章和索绪尔观点的反思过程中,赵炎秋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和深化了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辩证认知。
最后是与王弼的对话。随着对文字与图像关系及其各自特点的深入把握,赵炎秋开始将思考的重心落实到文字与图像作品中的“言象意”关系。王弼的“言象意”观即是其考察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突破口,因为王弼是我国较早且系统阐释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理论家,所以对他的观点进行再语境化的解读,有助于快速厘清和定位“言象意”结构的内部关系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通常而言,王弼“言象意”观的基本要义就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应该说这是古人对言、象、意关系最具逻辑性的概括,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赵炎秋在总体肯定王弼“言象意”观的同时,却也认为其存有一定的局限,并不具备普适性,尤其是不能与当前文字与图像作品中的“言象意”结构相提并论。因为文艺作品的门类广泛,有的专注表“象”,有的专注表“意”,并且不论是表“象”还是表“意”,它们都无法在达到各自的目标之后忘“言”、忘“象”。换言之,“言象意”结构的内部关系其实是多元的,并非仅有王弼那种窄狭的递进式类型。而其之所以窄狭,原因就在于批评对象《周易》具有特殊性,也即是一部专门以卜筮为目的的文字类作品。因此,通过对王弼“言象意”观的辩证解读,赵炎秋不只重新区划了“言象意”结构的边界与类型,而且还围绕该结构进一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人类四种表征方式和两种“象”类型,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理论空间。
综合来看,赵炎秋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特色有两点:一是总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这就规避了研究视域的单一,以至于能够对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进行均衡化、整体化的观照。二是基于同“他者”的对话,采用破立结合的论述方法。这就具体展示了其研究的内在肌理,以至于能够对主要观点的生发路径进行立体化的透视。两相结合,在这正—反—合的论证结构中,文字与图像的复杂关系遂得到和盘托出。
四、结语
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因此它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学术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特别是在该问题业已经过大量阐释,并随着各种新兴话题如万花筒般不断涌现,而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热潮实已渐趋消退的情况下,若想再发掘新的学术生长点绝非易事。赵炎秋自其风头正劲之时介入,经过长期的持续跟进,独辟蹊径地在“他者”话语的镜鉴下成功实现突围,析出不少理论新质,由是完成对自我和他者的双重“穿越”。不过客观地说,其有些观点还可继续斟酌,如从文字与图像占比高低的角度区辨语言文化和视觉文化作品。毋庸置疑,这种划分固然可以相对便利地解决图文结合文本的归属问题,可这个比例的尺度却无法精确地度量,尤其是文字与图像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如何正确判定它的归属便是棘手的问题。即使如其所说,随着文字与图像比重的不断升降,语言文化和视觉文化作品可以相互转换,但并没有对这种转换的机制作出说明,所以,这种依据文字与图像占比高低所进行的区辨更多是基于常识经验的判断。然而,瑕不掩瑜,赵炎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突出中国元素、中国视角和中国经验,对文字与图像关系作出的相关思考及论断,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内语图关系研究迈向新的阶段,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学者对该问题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注释:
① 在赵炎秋教授的《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中,“语言与图像”的对举被置换为“文字与图像”,这种置换暗含两种不同的语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