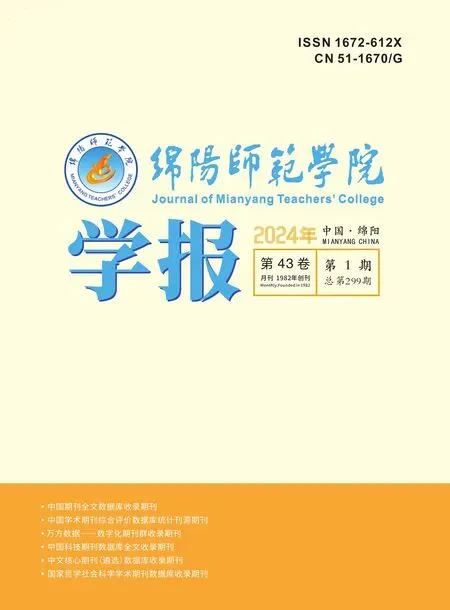情感、理性与选择
——叶芝《骸骨之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
何 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引言
《骸骨之梦》是叶芝(W.B.Yeats)1919 年在夸拉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政治戏剧。这部戏剧将1916 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放置在渺远的历史长河中来进行审度。作品描述了一个男青年从子夜到黎明的人生经历。男青年参加了复活节起义,失败之后离开都柏林邮政总局,化装成阿兰的渔夫,准备连夜从爱尔兰西部的克莱尔郡乘船逃亡到海外去。在这僻远的山间,男青年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女青年。他们给男青年讲了一个故事,追溯了英国人来到爱尔兰的历史。德沃吉拉是米斯国王的女儿,博瑞福里的国王奥洛克的妻子。她跟伦斯特国王迪尔米德一见钟情,两人为此不惜相约私奔。这个事件发生在1151 年,奥洛克和他的朋友们为了夺回德沃吉拉,带着军队攻打伦斯特。在其后的战斗中,迪尔米德的军队被奥洛克及其联军打败。流亡到英格兰之后,迪尔米德恳求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帮助他打败奥洛克,并且愿意割让伦斯特部分土地作为出兵的报酬。迪尔米德借到了一支军队,由斯特朗博带领,这是英格兰人第一次大规模入侵爱尔兰。英国人来到爱尔兰之后,到处烧杀抢掠,犯下了很多残暴的罪行。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为此悔恨不已,他们死后灵魂一直在爱尔兰大地上飘荡。他们仍然相依相携、不离不弃,但是只要肉体触碰和嘴唇相吻,就会产生火灼般的痛苦。这时男青年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700 年过去了,他们内心的悔恨仍然没有消减,只有得到爱尔兰人的原谅,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结束灵魂的漂泊。然而这个有着坚定民族主义信念的男青年给出的回答是绝不会原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急速旋转的舞蹈中,这对恋人宣泄着心碎的绝望。此时黎明已经到来,两个灵魂在熹微的晨光中消失,而男青年还要继续他逃亡的旅程。
这部戏剧发表之后,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纳善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爱尔兰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这部戏剧“让变成鬼魂的一对恋人回归他们可怕的命运,让年轻的革命者保持坚定。尽管充满了残酷的痛苦,男青年还是对这对恋人700 年来残酷的痛苦做出了让他们深感一切都是徒劳的回答”[1]210-211。克拉克认为戏剧中的人物不是作为个体出现的,而是“爱尔兰历史和现代文明史趋向的象征性体现”。叶芝将男青年拒绝的行动放置在主观思想结束和客观文化重新开始的黎明,这是“对爱尔兰犯下罪行的幽灵的诱惑的拒绝,这种罪行在毁灭国家方面比英国军队更可怕。因为主观和内部的危险被认为比客观的危险更大”[2]55。文德勒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这部戏剧表现的是“心灵拒绝接受自己过去的某种行为的形象。在这种行为被承认、审度和原谅之前,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心灵中无法创造性地使用……男青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屈从于人类同情的爱尔兰历史的一部分,……他烦躁地从难以捉摸的夜晚的需求转向白天更粗糙的现实,乐师的最后一首歌体现了他对经验的拒绝”[3]192。布鲁姆认为戏剧中男青年的拒绝是“幻觉上的失败,当这对恋人在他面前跳舞时,他们为男青年提供了摆脱狂热和仇恨的绝佳机会,尽管他几乎屈服了,但最终还是以一种丑陋的固执告终,诅咒诱惑。原谅就是抛弃悔恨,因为仇恨也是某种反向的悔恨,是男青年自己‘对自我的黑暗偶像崇拜’。叶芝看到仇恨使茅德·冈和其他女性变得面目全非。在他更富有远见和救赎情绪中,将这种仇恨理解为爱尔兰的一种枯萎症。该剧的最后一首歌清楚地表明,这种枯萎症正在削弱我们的想象力”[4]308。尤尔说:“这个古老的故事与现在逃亡和灾难的时刻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后者正是从前者生发出来的。这对恋人生活在他们自己制造的废墟当中;他们向参与革命和逃亡的旅行者表达了绝望的诉求,他们是旅行者的父辈……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转圜的空间。士兵本人被困在这个逻辑严密的圈套里:他是他们违法行为的后果之一,因此不能原谅他所反抗和诅咒的罪恶的制造者。”[5]95-96
以上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骸骨之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这个戏剧中,“灵魂梦回”这一情节看上去荒诞而离奇,作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建构这一戏剧呢?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个人情感悲剧,同时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悲剧。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为了私人性的情感,出于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最终做出了引狼入室的非理性选择。他们身上理性意志的萌生,让其灵魂一直得不到安宁,为罪恶的行径忏悔了700 多年。在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中,参与了复活节起义的男青年最终做出了绝不原谅他们的罪恶的伦理选择。通过描写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灵魂梦回”和男青年的坚定选择,叶芝为爱尔兰民众和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伦理警示和道德榜样的实例,推动人们去思考个人、民族、国家等更深入的政治伦理问题。
二、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卖国行为的驱动意志
英俊潇洒的伦斯特国王迪尔米德和美丽温柔的博瑞福里王后德沃吉拉一见钟情。“她选择了这男人,她也被这男人所选择。”[6]282他们的情感主要是出于肉体欲望的驱使,动力来源于他们的自然意志。“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libido)的外在表现形式。”[7]42“自然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7]42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每个人都是斯芬克斯式的人物,身上都有着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的来源主要是人的大脑,它赋予我们评价事物的善恶标准和理性意识。兽性因子则来源于我们的身体,它是与本能和欲望密切相关的,“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7]42。自然意志时时刻刻都想要摆脱理性的控制。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受到对方美色的诱惑,从而相互吸引并投入对方的怀抱,这是动物属性的本能起作用的结果。
为了与德沃吉拉长相厮守,迪尔米德的自然意志很快转化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的直觉的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人的活动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的约束。自由意志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人的不同的欲望,如性欲、食欲、求知欲等。”[7]282表面上自由意志跟自然意志有交叉,但是“自然意志是最原始的接近兽性部分的意志,如性本能”,而“自由意志是接近理性意志的部分,如对某种目的或要求的有意识追求”[7]42。由于德沃吉拉已经嫁给了博瑞福里的国王奥洛克,迪尔米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由意志推动他将德沃吉拉掳走,实际上两人是为了情欲而私奔。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当时的婚姻伦理,而且还是对博瑞福里国王奥洛克的极大侮辱。因此迪尔米德被奥洛克及其联军打败可以说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在被奥洛克打败后,迪尔米德将诺曼人和英国军队带到爱尔兰,这是他非理性意志驱动的结果。非理性意志是“一种希望摆脱道德约束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往往受情感的驱动。非理性意志是受情感驱动的非道德力量,不受理性意志的控制,是理性意志的反向意志”[7]49,所以非理性意志往往是“以不合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认知和判断”[7]251。迪尔米德被打败之后逃窜到英格兰,为了情欲和仇恨,他愿意将伦斯特的土地割让给英格兰人,只要他们能帮助他打败奥洛克。为了个人情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私人性的个人恩怨演变成了公共性的政治上的背叛,这说明迪尔米德在激情狂怒之下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将国家的内部事务国际化之后,诺曼人和英国军队来到爱尔兰,开始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血腥统治。正如德沃吉拉所说的那样,他们这些卖国者“没有思想只有爱情”[6]281,激情淹没了理智,盲目的爱情让他们做出了悔恨终生的错误选择。
由此可见,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生前所过的基本上是动物性的生活。在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等没有多少伦理道德意味的兽性因子的支配之下,他们做出了追求情欲、相约私奔、盲目战斗、引狼入室等错误的人生选择。
三、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忏悔和自我审判
英国人来到爱尔兰岛之后,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屠杀,肆意掠夺人们的财物,将这块土地变成了遵循丛林法则的人间炼狱。过去700 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到了1916 年还是这样。在一对年轻人叙述他们过去的情感经历的间隙,男青年用语言描述了英国统治者当前的罪行。很多人遭到殖民军队的屠杀,“这田野在吸饱了像我这样的人的鲜血后都变红了”[6]279。很多宁静的家园被焚毁和破坏,“在克莱尔、凯里和广大的康诺特地区/还有一处因为/其圣洁和建筑的美而闻名于世的房子/不被敌人糟践的吗?”[6]280爱尔兰西部很多著名的庄园和建筑都未能幸免,“在晨曦中/我已经能够看到阿兰岛/克勒马拉山和戈尔韦,看到那些/被敌人掀翻的房顶和推倒的山墙/以及从古老的房间里拆下来的镶板”[6]283。很多古老的市镇在英国人的蹂躏之下毁于一旦,“那市镇变成了废墟/……,在那些山墙和雉堞间,这个市镇跟任何一个/古老的令人羡慕的意大利市镇没什么区别”[6]283。英国殖民者甚至将很多大树都砍掉,将山上的植物一把火烧光,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反抗战士们无处躲藏。作品中特意提到的这些地名说明整个爱尔兰都处于殖民者的粗暴践踏和血腥统治当中。
这部作品的题材受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德沃吉拉》的影响,但是叶芝对这一题材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以表现卖国者理性意识的回归。理性意识属于人性因子,来源于人的头部,其主要由理性意志所驱动。“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接近道德意志的部分,如判断和选择的善恶标准及道德规范。”[7]42理性意志“以善恶为标准约束和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志弃恶从善”[7]253。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写到,英国人来到爱尔兰之后,年轻人都无法原谅德沃吉拉,认为她和迪尔米德背叛了祖国和民众,给爱尔兰人带来了灾难和奴役。叶芝对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两人的痛苦作了艺术性的夸张。过去两人曾经枕靠着对方的手臂,生活在彼此温暖的怀抱当中,享受着他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但是英国人来到爱尔兰岛后所犯下的罪行,让他们一直处于自责的痛苦和悔恨当中。他们的灵魂遭受的是与生前完全相反的诅咒和惩罚:他们之间那深沉的爱恋依然存在,仍然肩并肩地漫游,相互深情地凝视,但是却不能再亲吻和拥抱,肉体的接触会让他们产生火灼般的剧痛。“尽管他们可以用眼色传递情意,但是他们的嘴唇却吻不到一起。”[6]281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意识到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在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去损害国家利益,导致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极端错误的。为此两人死后的灵魂一直在爱尔兰大地上飘荡,罪行的记忆让他们对肉体欲望保持着条件反射般的厌恶,700 多年来内心都无法平静。灵魂的飘荡实际上是卖国者对自我行为的批判和所作之恶的自我谴责过程,必须要得到爱尔兰人的原谅,才能结束他们灵魂的漂泊。
这部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构思深受日本能剧的影响。叶芝说:“这部作品的观念来自于世界范围内都相信的死者梦回的信仰,在某一个时间段,通过生活中比较个人性的思想和行为展现出来。”[8]692一个人内心当中有强烈的情绪,死后将无法得到安宁。他的灵魂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事件发生的地方,自我管束、自怨自艾、自我抚慰,一直到这种情绪慢慢平息。在叶芝的《幻象》中就专门讨论了灵魂的净化和转化的过程。叶芝的《窗玻璃上的字》和《炼狱》等戏剧也采用了这种灵魂梦回的形式。从人物关系和艺术氛围上来看,看到这部戏剧的观众马上就会联想起荷马史诗中的帕里斯、海伦、墨涅拉俄斯,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保罗、弗兰采斯卡、简乔托等人物,但是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是受到以观阿弥和世阿弥为代表的日本能剧作家叙述模式的影响。通过庞德和费诺罗萨,叶芝接受了日本能剧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日本能剧中的梦幻能主要写鬼魂和亡灵,表现的是爱情等幽怨的人类情感。在叶芝的所有戏剧当中,《骸骨之梦》的服装、动作、诗歌、音乐等是最富于日本传统能剧风味的。在这个类似于能剧《锦木》的作品中,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是主角,代表的是远去的历史。逃亡的战士是配角,表现了现在的生活和苦难,并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戏剧将时间设置在子夜到黎明,而且在合唱歌式的副歌中四次写到公鸡的啼鸣:“伸长了脖子,拍打着翅膀/红色的公鸡,正在啼鸣。”[6]279-280、285在爱尔兰的传说中,昼夜交替的时刻经常会出现超自然现象或者是幻象。这就为剧情的出现提供了可信的心理基础。公鸡的啼鸣则增加了戏剧紧张的氛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叶芝赋予了“灵魂梦回”这一情节模式以深刻的政治内容,这是他继承东西传统基础上结合爱尔兰实际生活创新的结果。
四、男青年拒绝宽恕卖国者的伦理情怀
男青年听完陌生人和女青年的故事,才知道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爱尔兰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对恋人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鬼魂。在路途中,陌生人和女青年还提到了多诺·奥布莱恩(Donough O’Brien)的墓地。多诺为了自己的私利,将苏格兰人引到了索蒙德(Thomond)并占领了这块土地。兵败之后多诺从阿森莱战场逃了出来,1317 年死在科科蒙罗的修道院。这可以被看成是这对恋人对男青年的初步试探,但是男青年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认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只会让爱尔兰变得更加贫弱。
面对陌生人和女青年希望得到他原谅的请求,男青年必须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7]267。男青年的伦理选择涉及到他以怎样的身份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7]264。从青年男人这个身份来看,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那令人叹惋的爱情故事,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激情,那犯错之后700 多年还在持续的忏悔,都让男青年深受感动。这说明他们的故事挑动了男青年的自然情感和自由情感,让他曾想站在这对年轻人一边,所以他说“我差点屈服并原谅这一切了”[6]284。
但是从其爱尔兰人和被压迫者的身份来说,英国人数百年来的罪恶行径,男青年最近一段时间耳濡目染的英国人的暴行,让他心中充满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憎恨。男青年表示,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绝不会饶恕这对恋人带给这片土地的深重苦难。“噢,绝不,绝不/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这样的人绝不应该被原谅。”[6]283-284这坚定的话语被男青年重复强调了三次,他的这一伦理选择是集体理性意志对个人伦理情感引导、调整和修正的结果,同时也是现实遭遇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投射,因为很多抗英志士的遇难都是叛徒出卖的结果。这一选择让这对恋人的努力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让他们感到异常失望,其灵魂将在爱尔兰大地上继续飘荡。这部作品的最后写到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鬼魂在令人心碎地舞蹈,以表达其深深的忏悔和痛苦之情。通过舞蹈,叶芝使人物抽象的内心情感得到了表征性的传达,因为“代替本性中混乱的激情的是舞蹈,一系列的姿势和动作,其代表的可能是一场战斗,或者一场婚姻,或者一个鬼魂在佛教炼狱中的痛苦”[5]93,而此时天已经亮了,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悔恨还要继续,男青年的逃亡也还要继续。
这部作品中面具的使用既遵循了能剧的创作原则,又带着反讽的意味。青年战士没有戴任何面具,穿着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阿兰渔民的服饰,但德沃吉拉和迪尔米德戴的是英雄的面具,而且穿的是古代的服饰。作品中的两个主角都带了面具,表示他们是鬼魂,对自己过去的行为羞于见人,而且还指代抽象的一切卖国者。逃亡的士兵没有戴面具,表示他是活人,对自己的抗争行为是很骄傲的。面具和服饰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严肃的氛围中也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要理解男青年所做的伦理选择,我们必须回到1916 年复活节起义这一伦理现场。1916 年4 月24 日,也就是复活节的第二天,革命者皮尔斯、康诺利等人带领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国民军在都柏林发动武装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700 多年来的统治。起义部队占领了都柏林部分市区,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随后起义队伍遭到了英国政府和军队的残酷镇压,很多参加起义的爱尔兰民众惨遭杀害,16 个起义领导人包括茅德·冈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被以叛国罪处死。
这次起义尽管由于参加人数过少和准备不足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其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还是震惊了爱尔兰和西方世界。叶芝曾用《1916 年复活节》来缅怀参加这次起义的领袖和战士们。在诗歌中,叶芝写到了这些起义领导人日常的生活和思想。他们都是有着喜怒哀乐的凡俗之辈,但是经过枪炮声和硝烟味的洗礼,粗鄙之徒突然间变得崇高了。“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诞生了。”[9]180叶芝认为这些革命者已经成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传统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鲜血和壮举创造了崇高的美感,营造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氛围,将会影响一代代爱尔兰人们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五、结语
通过写男青年象征性的旅程,《骸骨之梦》表现了爱尔兰700 多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旅程中,一个抗英战士为了摆脱英国统治者的迫害,穿上法兰绒男裤和牛皮靴子,乔装成阿兰的渔夫从都柏林邮政总局出走,准备连夜经由西海岸的港口逃亡到海外去。他满怀恐惧、仓皇逃亡,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逃命,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但陌生人和女青年的故事让他理解了历史和现实、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关系,让他对英国统治者的暴行充满着憎恨,最后男青年做出了决不原谅这对年轻人的伦理选择。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实际上也体现了爱尔兰人的集体理性意志。
在这个戏剧中,叶芝塑造迪尔米德、德沃吉拉和男青年等人物形象,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诲大众。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或自然意志的交锋和转换,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怎样抑制自然意志和引导自由意志,让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7]42。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兽性因子泛滥,其思想和行为对爱尔兰民众、广大观众和读者起到的是伦理警示作用。男青年对英国统治者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永远不原谅这对出卖国家利益的恋人。他通过所走过的旅程完成了自我教诲和自我成长,是作家树立的一个道德榜样。因此对于用心去经历了这段旅程的观众来说,这部戏剧反思了爱尔兰多次起义却都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少爱尔兰人像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一样只重视自己的私利,不顾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同时揭示了爱尔兰民众一次次参加起义、不怕牺牲的心理因素,歌颂了皮尔斯和康诺利等在起义中牺牲的领导人和广大民众。
为了表现爱尔兰人内心的觉醒以及他们的革命斗志,《骸骨之梦》将历史、现实、情感、理智等融合在一起,具有很多政治戏剧都无法达到的审美意境和艺术技巧。叶芝曾对格雷戈里夫人说:“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来我写得最好的作品”,“唯一担心的就是政治色彩太浓了”[10]88。为了淡化政治色彩并增加美学意蕴,《骸骨之梦》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来写1916 年复活节起义的,通过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两人的悔恨和逃亡者的憎恶情绪体现了作家对英国和爱尔兰关系的看法。叶芝将卖国者的悔恨和人们对他们的憎恶的时间夸张性地拉长到700 多年,既增加了情感的强度,同时也体现了爱尔兰民众的集体理性意志和最高的内心真实。这部戏剧将程式化的舞台动作、渲染气氛的合唱歌曲、富于象征色彩的人物面具、人物内心外化的舞蹈等很多艺术因素结合起来,体现了叶芝融合东西戏剧的积极努力和尝试。凯伍说“这部戏剧是欧洲戏剧发展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11]325。仔细思量,笔者认为叶芝的《骸骨之梦》无疑当得起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