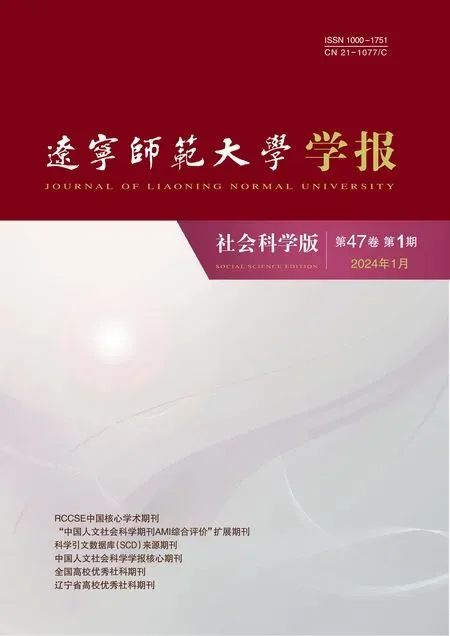论东西长篇小说的“重复”叙事
张学昕, 李昕泽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东西作为晚生代作家,前二十年先后创作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长篇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而间隔十年后问世的《回响》,更蕴藉着这一特定时间段作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彰显着东西为“时代记录档案”的决心。细读东西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重复在其小说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些重复现象既表现在一部小说内部的意象、细节的重复上,又表现为多部小说主题、模式的重复。通常而言,重复的生成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无意识的写作产物,另一种则由作家精心构思而成。对于东西的创作而言,重复是他精心选择的叙事策略,更是根植于心中的创作本能。纵观当前的研究状况,对于东西小说重复叙事的研究较多停留在表层现象,呈现零碎、表层的特点。对于东西的重复叙述通常以命运轮回、大量的巧合等细部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并未系统完整地论述东西重复叙事的具体呈现、运行方式以及意义。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指出文学作品充盈的阐释空间来自众多重复现象的组合,诸多意义的迸发具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重复”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思考方式,是意义建构的基石[1]13-16。本文将借鉴米勒的重复理论,通过对东西小说的文本细读,从荒诞剧的上演这一角度剖析东西小说重复的艺术生成,以狂欢错位的时代百态与徒劳无力的个人境遇两个角度展示东西重复叙事艺术的价值。
一
米勒曾在《小说与重复》中将小说出现的重复现象大体分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上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1]7就此而言,在东西的小说中,身体是最直接的重复意象,不断传递着人的生存境遇与痛苦体验。然而这种身体写作,不是附着粗俗的生殖器官与生理体验的直白描写下半身的写作,而是将身体置身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与意识约束中,“它为人们展示了历史与身体的纠缠,在身体的成长过程中,历史推动着身体、性的行动,而身体与性的异动也反映出了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变迁”[2]。如果说欲望的张扬是个体极致的舒展,而欲望的萎缩则是极致的压缩。然而在欲望中存在着一个强力的主宰,为权力机制所操控,因而身体成为权力机制运行下相应道德与权威的附属物。《后悔录》中曾长风与曾广贤则是纵欲与禁欲的一组呈现。这对父子的一生都被欲望所拖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禁欲的社会风气下,人们自动阻拒“性”的存在。而曾广贤的不幸是以与父亲、邻居们观看两只狗的性交为起点,长期被迫禁欲的父亲受此刺激,渴望与视禁欲为圭臬的母亲亲近,但却被拒绝。由此与邻居赵山河偷情,然而此事被“我”无意透露出去。至此,家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父亲遭受批判毒打。父亲的境遇使得“我”由对性的好奇转为恐惧,由此陷入了“我”与性纠缠不清的困境。“我”因为对性的恐惧,造成母亲、小池、赵敬东等人的悲剧,同时自己的人生也步入逼仄。可以说,“曾广贤的性禁闭,由被动走向了自觉,由恐惧、厌恶走向了顺从,最终抵达禁欲的极端——欲望的被阉割,这是无法被修复的永久性的身心创伤”[3]。应该说,这种损毁直接表现在生育能力的丧失、新生命的断裂。《耳光响亮》中从渴望当英雄到利益至上的金大印、生育三个孩子但改嫁后却无法生育的何碧雪、历经三次流产最终丧失生育能力的牛红梅,甚至是在无父无母管教下独自成长的牛翠柏都是被阉割的,牛红梅与金大印两个都丧失生育能力的人结合在一起,注定无法孕育新生命,东西将两人的命运用一纸协议扭结在一起,暗指错位混乱的一代注定无结果、无希望的既定事实。
东西对于身体体验的极致呈现,显示出身体可触的真实质地。对于心灵的瞬时捕捉加以延宕,则印证着东西在心灵探索、逼近人性上的漫漫征途。东西关注个体身体切实的体验,他曾谈及自己的创作理念是力图记录情感档案,这也是小说中大量展现人们残缺心理的直接原因。“人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真要写出点好东西,就得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4]——实质上,从东西这番自我剖白中,我们也感受到其探索心灵的炽热坚决。
《回响》是一次充满大量心理意象的文本实践,小说中涉及人物的诸多情感症候。当受害者夏冰清的尸体摆在父母面前时,两人竟无法辨认女儿的尸体,面对警方的调查,两人也是含糊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明显是心理远视症的体现,“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他们再次证明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5]7。这样的细节书写中,透露着东西对于现代人情感交流的一种隐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即使血亲也无法消融。女警冉咚咚陷入大坑案与丈夫情感的双重侦探中,竟产生了幻觉,幻想出郑志多——这位曾与自己有刻骨铭心情感纠纷的初恋男子。可见人们在诸多压力之下,为自动逃离现实而不断衍生幻想。吴文超获得大笔金钱时,产生了赚钱太快的罪恶感,这便是所谓的“道德恐怖症”。杀害夏冰清的凶手易春阳患有“被爱幻想症”,他热爱诗歌,却因相貌丑陋、家境贫寒在上学期间遭受嘲笑,由此在极度扭曲自卑下,竟将暗恋的谢如玉与相处有好感的吴浅草结合,幻想出谢浅草这一女性,来满足自己才华被肯定、被人爱慕的心理需求。这种症状的根源是个体满目疮痍的心理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疚爱”是东西对于心灵探索最为显著的成果,捕捉到了现代人心灵的残影。这种心理的产生是内疚的转移,更深的内疚转化为一种爱,这在《回响》中比比皆是。“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为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5]346这种内疚是隐埋在心底良知的苏醒,内疚促使行动的产生,爱的加持则会维系关系的稳定。这也是东西透过纷乱的生活表象后挖掘内心最深层的秘密。
残损的身心意象,尽管不尽相同,但是都指向着孤独的痛苦体验。东西在其绵密细致的日常经验书写中,展现了不同的孤独感受,并将这种瞬间感受延宕、拓宽。东西正是在这种感性层面上的“孤独感”,演绎出孤独对于人类全体的哲学意义,并凭此考量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孤独是个体必经的人生体验,但是当成长与孤独联系起来时,孤独似乎显得更加残忍无情,令人刻骨铭心。成长的回忆犹如海妖的歌声吸引着当代作家,作家自身的回忆也在文本中焕然一新,这种创作更像是一场告别仪式,是作家调动全副身心,完成一代人共同经验的缅怀,并挥手作别。《耳光响亮》中的牛家三姐弟的成长便是孤独的具体呈现。在父亲失踪、母亲改嫁的境遇下,哥哥牛青松的成长充满着血腥、暴力。他与不良青年厮混在一起,械斗盗窃,间接成了姐姐被强暴的施害者。他捡来名贵手表为姐姐庆祝却被冤枉成小偷因而坐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割断自己的小手指,由此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规训。牛青松在这种失序的真空下成长,在发现父亲的日记的密码与自己的生日吻合后,认为自己是父亲最疼爱的儿子,由此重新寻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踏上寻父的路程。同样,牛翠柏也是孤独的具象,这份成长伴随的孤独意味着残忍的蜕变,从一开始对于继父金大印的万分抵触,到最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姐姐,承认金大印的身份。这种蜕变呈示出传统父子人伦的价值信条退隐,金钱利益至上的处事准则登场的变化。孤独是人生必经的阵痛,并非随着年岁的增长得以减轻,相反成为每个人命运的谶语。在东西小说的孤独人物谱系中,《后悔录》中的曾广贤可以说是最孤独的人。在曾广贤富有诚意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他备受压抑的孤独。他的“诚实”言语导致父亲被批斗、母亲自杀、妹妹失踪、好友自杀,“诚实”充当了这部小说的叙述核心与行为动力。因而,每当他说错话,就会打自己的耳光用来惩戒。在监狱中,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要思虑再三。没有人肯听他讲话,由此他才会十分珍重与女服务员的相处。被倾听是一种肯定,是主体累积情绪的一种释放。
可以说,曾广贤孤独的一生,一方面是与外部世界的脱轨,另一方面便是“一句话”的悲剧。由是观之,东西在逼仄的空间内进行超出身体的极限叙事,以此来展现个体所承受的极致痛苦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将“孤独”视为东西小说的母题,而东西在触及孤独面目时,并不仅仅止于简单的呈示甚至于展览,而是予以如何克服的思辨。在他的笔下,孤独的人物正是以人们互相团结的稀有品质穿过命运的窄门,而掠过窄门倾泻的光则是人性最闪烁的部分。《篡改的命》中汪长尺孤身一人在城市,为送出去的儿子今后拥有更好的生活,不惜答应大志养父让其跳河自杀的请求。汪长尺进行死亡前的告别时,探望前妻小文,此时小文已经儿女双全,曾经的恩怨全然化解。汪长尺死后,小文与丈夫按照他留下的遗嘱,将其身体与那把见证其梦想破裂的椅子送回故乡,汪长尺同时也给予自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孩子留下了一笔钱。这些卑微的底层人物,为了在城市扎根奋力生活,在他们之间流淌着区别于冷漠、自私的温情,正是这些许的温情,使得东西在直面现实的苦难时流下了共感的泪水。
东西执着地记录个体在社会发展与个人抉择之间的肉身痛苦与灵魂撕裂,透过作为载体的肉身,更是流淌出对于个体生存关怀的细腻与妥帖。东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守常定律:以超常态或是残缺的身体作为痛苦经验的载体,来呈现人们生存的困境。正是在这荒诞的底色下,个体沉浸在失语的孤独中。由此,东西对于现实、经验与境遇传达出更加清晰的认知与反思。
二
东西将人物置身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以重复修辞赋予其无可奈何的命运感,犹如一幕幕荒诞剧,使得叙事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戏剧性作为小说叙述的向度之一,与戏剧本身存在着融合与重叠。“戏剧性”一词最早出现在黑格尔《美学》中:“真正的戏剧性在于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事话。正是在这种话中抒情诗和史诗的两种不同因素可以渗透到戏剧里面而达到真正的和解。”[6]在这里,东西所运用的重复修辞贯穿于人物命运中,早已经不再拘囿于文本,在读者脑海中生成一场场荒诞剧。这种生成效果依托于强烈的戏剧性,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人物身上纷至沓来的冲突与巧合,命运由此被裹挟至逼仄角落。
结构意识是作家如何处理经验与创作的切入点,更是决定观察世界、感知生存体验的选择角度。可以说,“戏剧性”的摄入应上升至文本美学进行考量。巧合的植入是东西小说结构搭建的最直观的体现。“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7]于东西而言,巧合的应用是其叙述逻辑、人物自身性格逻辑交织而成的产物。巧合的复杂多变一方面需要感性的驰骋,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的缰绳。巧合的作用不仅是服务于延宕情节,更是叙事动力的显现。东西对巧合应用的最为突出的是《后悔录》,“后悔”的心理贯穿着曾广贤的一生。摆在曾广贤面前的无数选择,只要他中断一个令他后悔的事情,便可以重新开始一种平淡的生活,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做。这不禁令人思考,一个人的后悔竟可以累积成这种地步,将人裹挟至逼仄的角落不能逃离。如果将其放置于现实生活中,显然与常态相背离。“而东西所提供给我们的,恰好是一种对应物,一种‘反转思维’的叙事——不是检点个人在历史中的罪错与妄念,而是记述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错过,或是历史对于个人的玩弄,并由此生成了一种类似‘命运’的东西,一种荒诞而戏剧性的逻辑。”[8]同时,这种戏剧逻辑区别于日常生活逻辑,是日常逻辑与寓言逻辑的巧妙捏合——在文本中体现为戏剧逻辑,映照在人物身上的性格逻辑,隐藏在作者背后的叙述逻辑。曾广贤的极致后悔是如此的荒诞,但是东西把握住了曾广贤人物的性格逻辑——后悔。正如小说中“一个人做了太多后悔的事,就再也不想后悔了!”[9],这是曾广贤最根本的性格逻辑。正是持有这样的逻辑,他才会陷入一种循环的后悔中。
无疑,巧合的叠加,需要作者的叙述逻辑所掌控,在这种叙述逻辑中抽取一部分便是人物性格逻辑的形成。这种关系并非一个不容僭越的定律,当人物的性格逻辑战胜了作者的叙述逻辑时,叙述逻辑便会服膺于人物的发声。这种高度重合的逻辑所推进的、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巧合,由此将抵达一种极端化的状态。在东西的笔下,在某种角度可以说,极端叙述是重复叙事最为直观的显现。汪长尺一家三代的改命,都被东西收录成为一部极端的命运之书。张晓琴将《篡改的命》视为“一部极端的命运之书”,认为在叙述的极端笔触之下彰显着“存在的荒诞、人性的善恶角力,以及命运之神的残忍和人的无力”[10]。逃离乡村的苦痛、改变自己的出身成为城里人,是三代人共有的希望。东西从现实生活表象出发,以自己的艺术逻辑进行高度的涵盖与提纯,最终形成汪长尺不断被“篡改”、屡次改命未果的一生。日常的逻辑显然无法解释,由此戏剧逻辑与性格逻辑合力编织成了命运逻辑,以此昭彰了存在的荒诞。可以说,汪长尺便是命运逻辑派生的产物,这也与东西一直坚持的“跟着人物走”的写法相契合,“这个人开始他有尊严,甚至还有傲骨,但慢慢地尊严和傲骨都被削掉了,是现实把它们削掉的。为了让他‘最后一送’合情合理,我冒着巧合的危险,把千千万万个‘屌丝’遇到的困难都加在了他身上。”[11]
在《耳光响亮》与《回响》中,小说的戏剧性则凭借“寻找”这一周而复始的动作加以完成。父亲不仅是血缘关系上的称谓,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更是信仰、秩序与归属的所指。东西凭借人物反复寻找“父亲”的行为来呈现秩序猝然断裂下个体成长的剧痛,思考“秩序”的重构。《耳光响亮》正是践行了对这一“寻找”主题的落实。小说的开头便交代了父亲的失踪。在此处东西设置了一个巧妙的重合,父亲失踪的日子也是领袖去世的日子,由此形成了精神与血缘意义上的双重“父亲”失踪。这如同“达摩克斯之剑”一般悬于牛家三姐弟的身上,扭转、牵制其成长的轨迹。而当得知父亲并未去世、生活在越南的消息时,一切信念崩塌,“只要他还活着,就说明我们全错了,何碧雪错了,金大印错了,牛青松白死了,我们白活了。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为他流过的眼泪,全部变得没有意义了!”[12]这句话无疑是对“寻找”的意义消解的最为贴切的阐释。寻父设置的出发点无论是寻找血缘关系的所指,还是精神信仰的能指,都呈现出如此的特征:寻找父亲的初衷与自身渴望寻找的结果全然不符,这种反差也体现出东西对传统伦理秩序已经被现代社会运行准则所颠覆有着清晰的认知。由此寻找的结果注定落空,这也是对由寻找而彻底改变的命运的意图一种消解。其中隐含着东西复杂的情愫:一方面是对于传统伦理式微的缅怀,另一方面则是对狂欢驳杂的时代下必然结果的接受。在最新长篇《回响》中,东西选择将强烈的“戏剧性”稀释、下沉。较之之前创作中“寻找”的重复动作,增加了追寻的难度。冉咚咚最先问询的是与死者有着畸形婚外恋的徐山川,由此展开了人际关系的排查。嫌疑人如同藤蔓相互衔接,形成一个闭合的推演逻辑链条。其中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杀人动机,杀人的行动彻底落实在易春阳身上时,他也因为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而在法律上无法获得相应的惩罚。这种审判结果消解了冉咚咚与同事所做的意义。而就冉咚咚自己的婚姻而言,丈夫慕达夫的越界行为如何定义?这是自己面临裁定的问题,肉体之触与精神互通,何者是裁定的准则?冉咚咚对婚姻的审视实质上是在重审、重塑自己的过程。正如丈夫对她所说:“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比天空广阔。”[5]345如同文本中滋生的悬念等待人们去拆解,“空缺”揭示了某种存在的本相,无论是萦绕人物与读者的真相的猝然断裂,还是结局的含混“私了”,在漫长的拆解过程中,东西将人们的战栗与焦灼无限放大,完整感与安全感极致缩小。在周而复始又疲惫不堪的境遇中,人们究竟是任由堕落还是依然寻找?面对存在的命题,东西毅然选择了后者。
人物自身巧合的叠加,无时无刻不传递着一幕幕荒诞剧的美学奥义。这种荒诞感最为强力的冲击是,在人物命运的荒诞表象下,自身并未意识到、感知到命运对其“捉弄”与“薄待”。正如东西对于荒诞的理解:“现在不是小说荒诞,而是现实太荒诞了,荒诞到我的写作都像在抄袭现实,荒诞到我们的写作反而不真实,怎么办?我开始收了,不那么荒诞了,反而往实里走了。”[13]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判断:东西依托重复修辞所生成的戏剧性来处理现实与经验的关系,使文本既葆有现实的痕迹,又布满超拔现实的纹理。在荒诞与非荒诞之间,东西捕捉到了“真实”。东西以荒诞作为其重复修辞的美学标杆,以强烈的戏剧性、对称的对照性赋予人物鲜活的质地与高度概括的塑造。
三
东西小说中的重复叙事,并非简单机械的复制,而是其对历史、个体与存在探寻独具匠心的积淀,这正如赵毅衡所言:“意义的形成本身,是靠重复奠定的。”[14]探寻东西重复叙事的意义,便是探寻东西如何透过日常生活经验提炼时代的奥义,如何建构人类的生存寓言。
重复叙事的根源,是东西在其长达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深深根植的“重复意识”。这种重复意识具体而言就是对于直面现实的执拗追求。三十年,四部长篇,相较于其他当代作家,东西可以称得上低产。面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东西并没有选择紧迫跟进,而是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叙事耐心完成对现实的整饬与超拔,以四部长篇绵延出发展时期的巨变。这四部长篇具有双重的重复艺术。于单一文本内部,东西都选择了与主体各自契合的重复切口进行探寻;同时四部小说之间形成勾连,形成时间意义上的绵延性,共同汇成为狂欢放纵的浮世绘。《耳光响亮》聚焦于后革命时代情境之中牛家三姐弟的残酷成长历程。在血缘意义上的父亲与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双重缺席下,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小说的结尾,金大印为了利益不惜破坏祖坟甚至迎娶继女牛红梅这一系列有悖纲常的举动,显示着“父亲”缺席的无力。东西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牛家三姐弟的成长轨迹的刻画,精准地把握住后革命时代社会中精神复杂而又逼仄的现实。如果说,东西在《耳光响亮》中以革命时代少年在后革命时代所历经的碰壁、践踏作为创作的现实起点,那么,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则可以看作是《耳光响亮》的反向“赓续”,历史与人性的耳光穿过世俗的旷野击打着人们。《后悔录》则将年轮前置,以革命时代为起点,借着资本家的孙子曾广贤饶有诚意的孤独絮语,展现因为说实话而导致的人生不幸。东西捕捉到“情欲”来连缀革命时代人性的折堕。欲望服膺于革命,为启蒙所规训。“在政权的引导下,通过理论宣传、制度建立,使禁欲主义成了一种伦理的以致政治的规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15]东西不仅深刻地展示了特殊时代下人们刻有训诫标记的情欲追求以及当时的集体观念,更是挖掘了隐藏在情感认知最隐秘的“后悔”这一人性心理构造,抵达了社会与心理的双重真实。欲望沦为政治观念的训诫工具,不断的“后悔”导致个体命运与时代双重错位的上演,由此形成了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欲望的解构与建构。由此可见,东西在纷繁下沉的历史长河中,凭借《后悔录》打捞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欲望”的沉渣。
《篡改的命》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之间巨大的鸿沟下,一家三代人不断被“篡改”与企图篡改自己命运的过程,展示了在巨变时代下国人所经历的价值颠覆。“有一个现成的题材,推理的,但我犹豫了很久没有下笔,原因是我想写一部更现实的、更有力量的。首先想到了‘拼爹’,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现象,也是天天面对的现实,我注意它很久了。读书,看病,找工作,处处都在拼。”[11]86这是东西对于具体情境不断观察的累积。如果说前三部是对于时代巨变与个体挣扎的直观揭露,那么在《回响》中东西则将探索的视野下沉,聚焦于现代人的情感症候。在一起大坑案中,女警冉咚咚在破案过程中,发现丈夫曾有过两次开房记录,至此她陷入案情勘破与情感探寻的缠绕之中,由此便勾连出每个人内心的隐晦与幽深。反复探寻的脚步展现出每一个人的心理暗流,昭示了心有隐疾、尊严失落、人性幽深的百态。东西将案情与情感进行缠绕,深挖人性最为幽深的地方,毫无保留地揭示出当代人的情感症候。将这四部小说串联对比,不难发现东西凭耐下性子、潜心捕捉时代种种,以自己对于时代变化的理解构成了从“后革命”时代至现代高速飞跃的社会序列,描绘出长达四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宏图巨制。
可以发现,东西直攻现实的文本都呈现着及物性的特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及物性指的是,东西在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特征的时候抓住了它们的最大现实,或者说具体的历史性现实。”[16]这种及物的质地显示着东西直攻历史与时代的创作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时代与历史分文不差的描摹,而是在捕捉到最大现实的基础上将其抽象为共性经验,由此产生更广阔的意蕴空间,抵达人类精神的真实境况。东西用生机勃勃、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语言搭建起历史、现实的殿宇,“紧贴人物”的写法,揭示了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矛盾与龃龉,个人成长、生存所承受的逼仄窒息与放浪迷失。事实上,东西透过现实的表象,对经验进行审美化的处理,以此完成对于现实的超拔,从而触摸到时代美学的奥义。
“寓言性”是东西小说洋溢的文本特质,更是理解其小说的关键切口。正是执着于这种写法,东西谨慎地甄别、筛选现实,做到取材与题旨严丝合缝进而衍生更为深层的寓意。文本寓言性的生成依托于作家驾驭现实的能力,经过其超脱的想象力与严谨的叙述逻辑将这些素材整饬、重组。重复循环既是自然运转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同现实的本质所契合,东西以此为辐射点来表达对于人生的认知与思考。这是“先锋小说留给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遗产,即是哲学寓意的熟练生成,以及叙事形式的自觉彰显”[8]。显然在东西创作中完成了“遗产”的接力。“文本也产生了超越读者阅读心理的‘先验结构’。这个‘先验结构’之外的意蕴,就是文本寓言性的生成。”[17]在考量东西文本中的寓言性生成、探究个体的存在意义时,不难发现其中已然涵盖出统摄个人存在的底色——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周而复始的性质。正是基于这种底色,个体的一切活动也附着周而复始、庸俗无望的性质。这正如刘震云所言:“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18]
《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小说创作的重要节点,可以说涵盖了其今后创作的基本元素。那么小说是如何跳脱出故事的表象层面转而步入寓言特质的深层呢?东西的创作给予了一个可行的范例:“一个作家对‘事实’的‘看法’,不仅基本地确定了叙述的方向,而且决定着作家如何超越经验的局限,一旦作家找到有关世界和事物新的语言和结构,这个文本就可能由故事层面大踏步地真正进入寓言的层面,这时,小说的文本结构便呈现出一个新的空间维度。”[17]失语与沉默的悲剧更加隐蔽与残酷,更加广泛与幽深,这是文本跨时空的存在价值。《没有语言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开放的阐释系统,伴随着看法的变更而不断引申出多重寓言性。
东西笔下的人物陷入困境——挣脱困境——陷入新的困境的生存轨迹,构成了当代底层人物的“西西弗斯”神话。如果说在《耳光响亮》中耳光一次次地响起是现实给人物设置的困境与障碍,那么随之而来的笑声则是对行为的消解。牛红梅作为小说中欲望与美丽的化身,三次流产贯穿于其从憧憬爱情的明媚少女到歇斯底里的妇人的遽变。在牛红梅的几次笑声中东西揭露了其窘境,最为离奇竟是在看小品《吃鸡》时,发出连续的大笑声,孩子流产了。“她仿佛凭借本能模模糊糊意识到了生活的荒诞无稽,然而这种倏忽而至的领悟还达不到‘语言’的层次,于是只能托身于只有音响而无所指的笑声之中。”[19]流产成为惯常,也意味着牛红梅已经接受了生命的流逝,更多呈现出一种平静的沉默,绝望与顺从是人物面对生存困境的姿态。于东西而言,生活的诗性早已高高悬置,日常对于存在完成了拆解与指认。东西的重复叙事建构了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每个人依旧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神圣崇高被日常的琐碎所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庸俗、苍白与无望。
不同于先锋作家在追求文本寓言性的过程中,选择有意淡化时间与地点,将人物简化为特定功能的叙事符号,显然东西更侧重将寓言化置身于日常生活中,质言之,是抓住日常经验最为突出的特征,并赋予寓言性的特质。东西凭借着先锋余绪,对冗杂日常高度提纯,对于存在现实深度勘探,涵盖出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寓言——意义的消解与动作的消耗。应该说这是生活一个真实的侧影。
如果说,重复书写揭露了生活的本质,那么东西在生活无法“篡改”的本质中抽取提炼,使之上升至命运逻辑的排演中。毋庸置疑,命运是东西小说中形而上意义的“生存寓言”。《后悔录》中曾广贤充满后悔的一生,就是由无数后悔链条编织的枷锁而将其束缚的。《篡改的命》中,东西通过汪长尺一家三代的改命来揭示命运逻辑的粗暴与虚妄。行为与境遇的发生正是在下一次的“重现”中令人警觉,又在反复的上演中消解意义,成为机械的轮回,人们无法逃离也无法改变。
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东西勾勒了人类在沉寂庸常的生活中难以摆脱重复的轮回,最后只能陷入“失语”境地的生存寓言。其后的文本实践不断拓深寓言的阐释空间,由此生成重复的美学意蕴。东西的重复叙事存在两种姿态:一是受“寻找”所驱使的人们,在沉寂的生活中不断消解自身存在的意义;二是面对命运代际的轮回,父子为挣脱命运的渊薮,奋力前行。在这样具有差异的重复设置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困顿,也体会到生命的坚韧与抗争的炽热,进而肯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东西在构建生存镜像的过程中,通过循序渐进且富有差异的重复叙事,在人物看似平缓却布满暗涌的生命长河中,放射出芸芸众生的人性烛照。
当梳理东西长篇小说时,我们会发现重复不仅体现在小说细部中,更是根植在东西创作的意识中,成为一种本能,彰显出独有叙事秉性。重复对于一部文本以及多部文本之间而言,是东西对人类痛苦经验的呈现,是对线性逻辑的消解,更是对孤独处境的关怀。重复对于东西而言,是直面现实、捕捉社会历史与个体成长的执拗,亦是对存在的探寻。以上是东西重复叙事所生成的文本美学与书写意义。毋庸置疑的是,东西保持着极度灵敏的感知,将现代人的生活境遇、社会巨变、命运波折等这些沉重而又可触的状态,以一种高度凝练而又戏谑的口吻来间离生活,至此沉重与轻松置换,氤氲文本的是“无法承受之轻”的空虚与失落。同时,东西与存在周旋的过程中,始终坚守一种深沉的道德意识与叙事伦理,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捍卫尊严。东西触摸经验、真实的内核,凝视人性的褶皱时,如何在重复中雕琢差异,又如何在差异中整饬重复?这是东西在其漫漫创作之路上,所求索的“永恒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