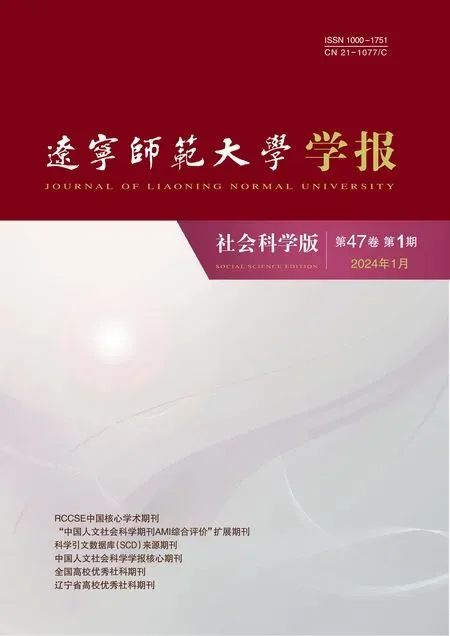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中的马尔主义及其当代评价
姜 宏
(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Н.Я.Марр, 1864—1934)是俄罗斯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极为独特的人物,他本人及其学说既享受过最热烈的推崇,又遭到过最彻底的否定。时过境迁,目前学界对待马尔及其学说或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或是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主义原则)要求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此,我们至少不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马尔首先是一位才华出众、著书立说的学者。此外,语言新学说(новое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作为马尔的代表性成果,对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民族考古学和理论语言学研究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应该说,这值得我们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国内学界以往对马尔及其学说的研究主要限于语言学框架之内,且多是对其学说形成背景进行分析,缺乏对该学说本身的深刻评价[1]。然而,马尔学说在讨论语言问题时着力发掘语言本质及其普遍性特征,流露出浓厚的语言哲学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语言学理论,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语言哲学。将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置于俄罗斯语言哲学史的维度之下重新考量,需要基于马尔所处的时代语境,对该学说兴起与衰落的缘由、理论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辩证的梳理和评价。
二、语言新学说的缘起与终结
“语言新学说”,也称“语言考古学说”(пале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языка),是由马尔提出的关于语言历史和语言阶级性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马尔已经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研究的知名专家、高加索考古学的建构者,在高加索和欧洲语言历史考古领域深耕多年。可以说,他的语言研究是在语言文化历史视域下进行的,带有鲜明的民族载体特征。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马尔之所以始终关注语言问题并提出语言新学说,与他在成长期间的语言学习经历不无关联,更与他的高加索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雅弗语(яфе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1)“雅弗语”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它被阐释成一个语系,包括高加索的语言,如格鲁吉亚语、卡特维尔语、孤立语和一些罕见的古老语言。后来它被解释为世界各地语言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相关的一个阶段。一开始马尔将雅弗语成分的普遍性解释为各民族的迁移,后来又认为它是一个原始现象。研究密不可分。
马尔自幼成长在一个父亲讲法语和英语、母亲讲格鲁吉亚语的家庭。中学期间,他便掌握了多种语言:俄语、德语、法语、英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等,而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时,他又学会了高加索和近东地区的所有语言。马尔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学的缘故。在重建高加索和欧洲语言史的考古语言学工作中,他注意到语言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马尔早期语言学文章中频繁出现“雅弗语”这一术语,以解释高加索语言和闪族语(семи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之间的古老亲属关系。众所周知,闪族语和含族语(хамитские языки)(2)闪族语又称闪米特语,含族语又称含米特语。的名称源于《圣经·创世纪》人物挪亚的两个儿子——“闪”(Сим)和“含”(Хам)两兄弟。而挪亚还有一个儿子,叫作“雅弗”(Яфет),于是马尔用“雅弗”来命名闪族语系的高加索亲属语言[2]182。后来,他将传统语言学尚未明确亲缘关系的语言称作雅弗语,而那些已经被归入某一语系的语言则被看作是两个原始语杂交的结果,即公认语系语言和雅弗语言的杂交[3]。马尔对雅弗语的考古学研究,人称“雅弗语理论”(яф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也称“雅弗学”(яфетидология)。雅弗学是马尔语言新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历史上被冠以“马尔主义”(Марризм)的名称。
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和苏联社会的整体思潮这两方面因素出发,我们不难理解马尔语言新学说备受推崇的缘由。一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比较语言学显露出理论局限性。青年语法学派仍在着力发现和论证语音规律,而对语言的普遍性问题——语言本质、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世界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兴味索然。相反,并未接受过语言学专业教育、对历史比较方法知之甚少的马尔尤为看重语言普遍性特征的研究价值,其语言新学说试图解决的正是这类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初苏联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种形势下,马尔决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到语言学中,由此推出了“语言新学说”。该学说否定了19世纪的整个比较语言学,其理由如下:(1)不曾存在印欧语系,也不曾存在统一的斯拉夫原始语言。但是,存在着所谓的雅弗语系。世界大洪水之后,挪亚在高加索建立了根据地,而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展的。(2)无产阶级语言学无法接受由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家们提出的世界语言分类。这种分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它人为地拔高了带有屈折词法结构的印欧语言。(3)印欧语言学并未对语言起源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4)印欧语言学采用的是形式主义方法,其注意力集中在语音和词法上,而把词汇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完全忽略了语义学的内容[4]。在此基础上,马尔指出了采用类型学和社会学方法对语言事实研究的重要性。在当时看来,该学说极富理论特色,它的提出被认为是恰逢其时、十分迫切的。在马尔主义最为盛行的时期,马尔及其追随者们几乎占据了高校和学术机构的所有领导职位,他们要求语言学授课和研究必须依据马尔的学说和原则展开,而早于马尔的以及国外的语言学研究被全面禁止。
马尔主义在苏联的盛行直至1950年才结束。1950年5月9日,《真理报》组织了一场语言学大讨论:在几周内,苏联主要报纸都有机会登载赞成或反对马尔主义的言论。斯大林于6月20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终结了这场讨论,也标志着马尔主义的破灭。该文指出:马尔将狂妄的、傲慢的、自大的、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入了语言学,从而彻底地、轻率地否定了马尔之前的语言学中的所有内容[5]。此后,马尔及其学说遭受了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批判,它被认为是伪科学的、庸俗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被称作苏联语言学中的庸俗化唯物主义(Вульгарно-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流派[6]。
三、语言新学说的主要观点与思想内涵
我们认为,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就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饱受争议却也别具一格的阐释。
(一)语言本质观
马尔从庸俗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直线型的、简单粗略的解读,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雅弗语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阶级性学说(учение о классовости языка)。在他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由集体劳动驱动的、以生产和生产关系为前提条件的物质文化,而其他所有非物质现象都属于上层建筑。因此,语言与艺术和科学一样,是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财富。由于任何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具有阶级性,故语言也是有阶级性的。马尔说:“不存在民族的和全民的语言,但存在阶级语言。相比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之内不同阶级的语言来说,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阶级的语言呈现出更多类型学上的亲属关系。”[2]197在确立语言阶级性的时候,马尔所采用的理据是阶级关系在语言中的明显反映。阶级性语言的结构不仅能反映社会结构,还能反映政治体制,因为不同阶层的代表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他断言,相比较古代标准格鲁吉亚和民间格鲁吉亚语以及古代标准亚美尼亚语和民间亚美尼亚语而言,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间语言更为相似[2]127-135。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阶层或语体,不同语言的同一个阶层或语体更为接近。
马尔将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直接运用到了对语言的定义上,强调语言与物质文化的紧密联系:“所有语言都是人类集体的创作,它不仅仅是人类思维的反映,还是人类社会体制和经济在语言技术和结构以及语义上的反映。因此,语言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整个组成是一个映射,更具体地说,是沉积……语言现象与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历史之间是一种有机的联系。”[7]79按照马尔的观点,现实、思维和语言在其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因此,研究语言材料时需要考虑语言的所指材料。他说:“史前物质文化古迹本身的命运不会与史前相应国家的语言命运相左。”[8]
(二)语言起源观
在人类社会中,语言以思维为基础,并不断建构和完善,这在马尔那里获得了“语言起源过程”(глоттогон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的名称。马尔的语言起源统一论(теория единства глоттого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所有语言的起源是统一的,所有语言起源于四个原始成分。尽管各民族语言的出现是相互独立的,但因为文化是统一的,而文化发展经历了相同的阶段,所以文化中的所有过程是相同的。在社会发展中随处可见一些相似的规律,那就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者制度替换另一种形态或制度(原始体制、奴隶体制、封建体制等),因此,在语言发展中也应该随处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律性交替。换句话说,语言起源过程是统一的。马尔认为,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是雅弗人(Яфетиды),他们是车轮的发明家和火焰的征服者。雅弗人在劳动过程中发明了语言,语言确立了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通过与雅弗人的联姻向其他民族传播[2]127-135。
马尔用声音来对世界语言的多样性进行描写。最初的言语都起源于四个原始元素,也就是最初的四个劳动号子,它们是:САЛ(sal),БЕР(ber), ЙОН(yon), РОШ(ros)。这些成分的不同组合代表着语言起源的古老阶段:从扩散音系统到音素水平(或音位层次)及其相应的义素语义形式的发展。这四个语言成分是所有民族共有的,它们属于每一种语言,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任意长度的任何文本,最终都仅仅是这四个自身没有任何意义、以一定线性序列组合的初始元素的语音转换的结果,这决定着语言起源过程的统一[7]59-60。
我们采用А.В. Десницкая的话来总结马尔的语言起源论:“马尔认为,有声语言是作为劳动祭祀行为中的生产手段出现的。有声语言的最初成分是含混不清的喊叫声。在有关思维最初发展阶段的唯心主义观念的基础上,马尔把有声语言的出现归入到宇宙思维替换图腾思维的阶段。”[9]
(三)语言发展观
马尔对语言发展观的阐释较为晦涩和复杂,我们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语言发展规律说,即人类语言的总体趋势是从多语到统一语;其二为语言发展方式说,即杂交是语言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三为语言发展动力说,即语言状态的变化是社会形态改变的结果。简而言之,世界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通过杂交的方式从多语现象到统一语言的过程,而语言发展的动力是由生产新形态所引发的社会性转折。
就语言的发展规律来说,马尔认为,世界上所有语言具有同一个起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都具有同一个原始语。语言不是起源于同一个原始语言的多语发展和变化,而是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单向发展——从多元到统一。至于语言发展的方式,马尔把语言杂交看作造成亲近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个别语言尤其是印欧语言的形成过程中,语言杂交起着重要作用。他说:“并不曾有任何语系的存在,也不曾有亲属语言的分裂,语言只会进行杂交,通过这种杂交方式,在通向统一世界语言的道路上,语言的数量会减少。”在马尔看来,在未来应该会出现一种统一的世界语言,他甚至提出了关于创造统一的全人类未来语言的思想。马尔的语言发展动力说,也即“语言阶段论”(учение о стадиальности языка)指出,语言结构会随着社会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语言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形态或制度变化的结果。由于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初始到当代——反映着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在语言发展中同样可以表现类似的变化[2]127-135。他指出:“所谓的语系……乃是符合不同经济和社会类型的不同系统,在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一种语言系统也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系统。”[2]107如此一来,社会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应该伴随着语言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而且语言状态的这种转变伴随着语言的一种结构的彻底破坏和另一种新的、本质上不同的、但保留许多旧系统成分的语言系统的出现。换而言之,思维结构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一致,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需要革命性的飞跃,社会历史中各个阶级进行革命的同时,不同阶级所说的语言也经历着革命性的飞跃,因此,语言的发展是革命性的飞跃,在革命性飞跃之后语言变得面目全非。
(四)语言与思维关系观
语言产生和发展问题使得马尔不得不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问题加以思考。我们认为,马尔的语言与思维关系观可总结为以下两点:一是语言与思维紧密相关,语言是思维的体现手段,可以反映思维水平;二是思维水平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语言体现着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思维特点。
就第一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说,马尔的出发点是:语言是与个人社会活动相关的思维的直接结果。任何新的思想或者思维活动都必须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才能传达,思维中所有的新事物几乎立刻都会体现在语言中,语言是思维形式的表达者,思维内容的形式可以直接在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中找到表达[10]。以上出发点在马尔看来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他坚持认为,研究语言必须紧密联系思维过程,“有声语言不仅不是始于声音,也不是始于词语,而是开始于一定的意识结构”[2]368;而就第二点(思维与社会的关系),马尔提出,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一个阶段性概念,即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是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而思维直接决定着语言及其语法结构[11]。这就是马尔有关语言与思维观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因素对思维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社会进化伴随着思维进化,由此可以建立语言发展和思维发展之间的决定性关系。而思维进化不是稳定的,它作为人类社会的创造物是随着生产活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在语言结构中得到反映[12]。也就是说,语言能够作为反映思维水平的或多或少的先进形式,而思维水平直接取决于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可以发现,马尔的语言学试图建立一种以社会类型学为基础的语言和思维的类型学。简而言之,马尔将语言归属于上层建筑,这使得他将语言形式结构的一定类型与思维的一定类型联系起来,而通过思维再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水平的一定类型统一起来。这也是马尔提出阶段性理论的重要理据:语言自其出现的那一刻起就经历了一系列与社会发展阶段相符的阶段[13]。
如果将马尔以上思想进行融合和整合,那么我们可以采用С.Д. Кацнельсон的话语对其进行概括:(1)语言不是自主的、独立于社会的存在物,而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要产物,这一产物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交际需求而增长;(2)语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要求对语言及其基本结构成分,也即语法结构和词汇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研究;(3)语言历史不是偶然和多向变化的混沌流,而是从最低形式上升到最高形式的有规律的过程,该过程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渐变过程为条件的;(4)语言结构(或系统)的形成规律对所有语言来说是统一的;(5)语言的语义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本质上的阶段性变化,这使得语言形式反映思维形式的阶段性变化成为可能;(6)语言发展中早期阶段的特点是混合性或扩散性以及多义性;(7)在语法结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句法学的历史[14]。我们认为,Кацнельсон的总结,就全面性、条理性和公正性来说,是对马尔语言学基本观点比较妥切的表述。
四、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的历史解释与当代评价
如果说1950年之前马尔及其学说堪比苏联语言学宗教,是一种信仰,那么在1950年之后,马尔学说则经历了毁灭性的批判。直到20世纪末,马尔的著述逐渐得以恢复,尤其是他有关语义学和文化学的著作,甚至出现了一个叫“新马尔主义”(неомарризм)的概念。不得不承认,这是科学范式转换的结果,它是在结构主义“严格系统”向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柔和系统”的转折中产生的,因为在后者中任何非理性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此,我们不准备对马尔及其学说进行深刻的社会政治性评价,主要就以下几点做出说明:其一,就前文所述,马尔的语言新学说主要涉及语言本质、语言起源、语言发展,以及语言、思维、社会之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语言哲学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因此,马尔的语言新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纯语言学理论,不如说是典型的语言哲学观念;其二,马尔学说,不管其成果和结果如何,马尔其本人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马尔是第一批建议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注重思想政治方向的语言学家。对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满,寻求新的方法论(马克思哲学原则)以及早年形成的对语言起源和进化问题的科学兴趣,所有这些因素加强了马尔对其研究道路的深刻信仰;其三,我们很难把马尔的语言哲学观点归为某个具体的方法论流派,因为在他的观点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纯粹的科学基础,还有意识形态,甚至还包括纯人类学的因素。用В.А. Звегинцев的话说,不能忽视马尔本身的多面形象,其科学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越来越明显的异常特征”,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尽力不去指出,或者尽量绕开[15]。不得不承认,马尔的部分观点在语言学的某些领域至今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例如,马尔将社会学因素纳入语言学研究、对语义学研究的重视,以及历来凸显的功能主义思想等对俄罗斯社会语言学、语义学以及功能语法学等流派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尔主义因受到彻底的批判而退出学术舞台,但以今日之眼光来回看马尔及其学说,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一些十分重要的事实。首先,要理解马尔时期的语言新学说只有置身于他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应该承认,马尔所有的活动都出于要在自己的领域内为生活和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服务的热切愿望。他与印欧学派之间的斗争在当今的语文学家看来是不理智的,但事实上这是受到当时主流思潮的影响,那就是苏联理论语言学应该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而不能成为其他社会体制下的外国理论的影子。在这条道路上他似乎犯下了不少错误。但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某些错误也许恰恰代表着一种创造天性。可以想象,以考古学方法为依据、综合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进行语言研究,马尔的学说自然是不合规范的,破坏了当时语言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公认观念。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体现了他敢于使用不同寻常的论证方法和全新理论途径的精神。而用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理念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跨学科观念。Ю.М. Шилков指出,如果用现代计算机的术语,那么马尔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方法论的“驱动程序”效果,也就是认识上的震动[4];其次,当时马尔身边集聚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杰出学者,包括И.Г. Франк-Каменецкий、О.М. Фрайденберг、С.Д. Кацнельсон和И.И. Мещанинов等。无论是马尔本人,还是其学说吸引了这批优秀的语言学家,不能否认的是,他们都有着自己深刻的思想,不会轻易受人摆布。
众所周知,Е. Д. Поливанов是马尔最为激烈的反对者,他第一个公开召集关于雅弗学理论的讨论,并论证该理论的不合理性和无根据性。然而,与此同时,他对马尔的某些著述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就以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对马尔的一句评语作为本文的结尾:“除了雅弗理论,还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马尔是一位伟大的学者。”[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