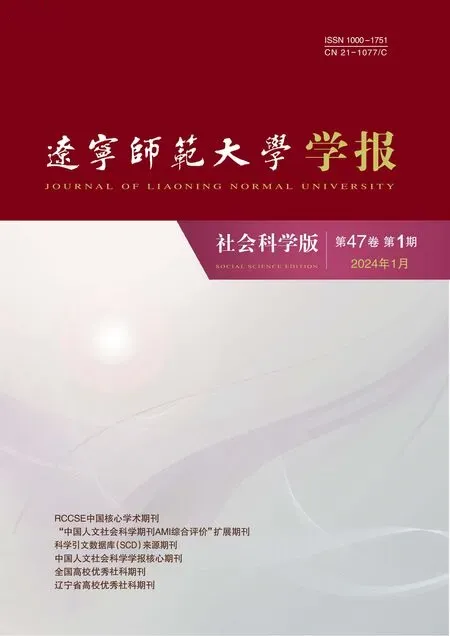文苑近侍:清入关前大学士的职能角色与权力演变
刘 洋
(1.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2.故宫博物院 博士后工作站,北京 100009)
清代内阁大学士领袖班联、表率百僚,是文官体系中唯一的正一品实职官缺,正如《清史稿》所言“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述主要反映了清中期已降内阁定制后的情况,而清初大学士的地位与形象则远非如此。然而有学人却忽视了内阁制度确立前后存在的这种差异性,以至误认为清初大学士一经甫设即位列宰辅,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阁臣“赫然为真宰相”的形象更是加重了上述误解。事实上清代内阁并非入关后直接模仿明制,而是在关外时期文馆、内三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至康雍年间逐步完善定制。在此过程中,大学士的政治地位与实际职权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试通过对清代内阁的溯源(1)此前张晋藩、郭成康在《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对清初文馆与内三院的发展演变、职能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总体论述;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张一驰《内阁制度与清前期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则通过对满文档案资料较为深入的解读,进一步丰富、细化了上述研究。此外,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郭松义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制度史研究著作对此内容亦有述及。,重点探究清入关前大学士及其前身文馆诸臣的主要职能与权力运作方式的变迁情况,进而宏观审视其政治角色如何兼具儒臣与近侍的二元特征,以此深化对清代中枢体制发展轨迹的认识。
一、“文字”职掌与天聪初年文馆的创立
清代内阁最早可追溯至入关前设置的文馆。努尔哈赤起兵后,在崇尚武力四处征伐的同时,身边也逐渐汇集了额尔得尼、达海、库尔缠等一批兼通各族语言的饱学之士,渐有获赐“巴克什”之名号者。他们常年侍从征战,受命撰写公文,翻译汉文典籍,出使联络各部,在建州女真崛起、立国过程中贡献尤多。特别是额尔德尼,每次汗用兵之时,皆在旁随侍,多次建议从各部落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入手给予招抚。又奉命根据蒙古文结合本族语言创制了女真文字,进而被后世君主誉为“一代杰出之人”。又如精通满汉文字的达海,日伴汗之左右,凡后金发与明廷、蒙古、朝鲜的国书及晓谕汉族士绅的政令皆由其撰拟、宣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统治者对于汉族士大夫与儒家文明存有较为严重的民族偏见,未能充分认识到文治对于国家兴起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国中儒臣大都为满人,且数量较少,未形成明确的组织机构;其二,儒臣侍从角色十分显著,尚没有固定、明确的官方职掌。其虽以语言文字见长,但功名、待遇仍需通过疆场之战功搏取,“文字”相关工作仍停留在临时运用层面[2]83。
皇太极继位为汗后,日益重视文臣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正式确立了儒臣分工、共值书房的制度。
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初太祖制国书,因心肇造,备列轨范。上躬秉圣明之资,复乐观古来典籍,故分命满汉儒臣翻译记注,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焉[3]。
按上文所记,汗明确将儒臣分为两班,一班由达海负责,包括刚林、苏开、顾尔乌浑、托布戚四人,专司翻译汉文经史典籍;另一班以库尔缠为首,辖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职掌记注本国政事。与以往相比,儒臣不仅在数量方面明显增加,而且首次被明确赋予了以“文字”为中心的两方面职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随事需要临时受命的工作性质。总之,儒臣分班入值、各有专司原则的确立,使之呈现出日渐正规化、组织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其办事值所也渐有了“书房”(文馆)之名号[2]86。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在文馆举行盛大仪式厚赐归宁的公主及土谢图奥巴额驸后,来到了巴克什库尔缠的值房,并与之交流。“问所修何书,对曰:‘记注上所行事。’上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观。’”[4]110后又来到达海之值房,阅览了其所翻译的《武经》一书,并借箪醪劳师的故事斥责了额驸顾三台不能上下同心,以至用绳子将战死的士兵拽归[4]110。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库尔缠获罪身死,皇太极以其撰修“文意不合”下令文馆诸臣增修努尔哈赤在位期间的用兵行政事宜[5]42。鉴于汉文史书虚词甚多,其又命儒臣于宋、辽、金、元四史内择选有关国家治乱兴衰之篇给予翻译宣讲,而对详载施展法术等交战细节的野史则概行禁止,以免国人信以为真、混淆视听[5]167。除上述日常职掌外,天聪年间达海还奉命修订了努尔哈赤时期额尔德尼等人创制的“老满文”,形成了所谓“新满文”。与原来相比,此番文字增补了十二字头,并酌加圈点,同时适当添加了外字。不仅有效解决了一些人物、地名等专有名词书写时的混乱,而且对汉文典籍的翻译亦大有裨益,对满族文明的发展与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天聪中后期文馆儒臣职能的政务化
天聪中后期,伴随汗权的集中与君主权威的奠定,原本作为儒臣办事场所的文馆亦逐渐演变为汗的近侍机构[6]。在此过程中,入值文馆的儒臣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人员数量进一步增加,且来源多样化。既有先前的满洲儒士,又有后来自行归附或被俘投降的汉族官生,另外后金国自行开科录取的部分士子也被纳入其中[6]。这彻底改变了以往儒臣中尽为女真的人员格局。二是汉族官生知识渊博、整体素质较高,多人有从政履历。其陆续加入不仅为文馆增添了新的力量,而且逐渐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尤其是范文程等人受到了汗的格外倚重。三是儒臣群体特征更加突显,其政治角色愈发以文馆的整体职能角度呈现。在此基础上,作为亲信侍从的文馆诸臣除官方规定的文字方面职掌外,其日常实际职司明显呈现出政务化的趋向。郭成康先生曾对此进行了分类探讨[2]92-94,本文则进一步细加分析如下。
第一,代传谕令,充当大汗与诸贝勒大臣交流的媒介。由近侍儒臣传谕宣旨,在天命时期就已非常普遍,至天聪年间得到了继续发展,特别是在传宣汗谕过程中,他们经常又会将诸贝勒大臣的陈请回奏予汗,实际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如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窦土门福晋来降,按照后金的习俗则应改嫁。大贝勒代善遂领衔奏请由汗收入后宫,而皇太极则派希福等人宣谕由家室不和之贝勒娶之。代善等坚持原意,转令希福代奏大汗,所谓“福金委身顺运,异地来归,其作合实由于天。上若不纳,得毋拂天意耶?”[7]后在文馆诸臣的劝说下,皇太极终将其纳入宫中,后居五宫主位之一。
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后金政权通过多年四处征伐国势日盛,诸贝勒遂请希福、刚林等近臣代奏大汗早建尊号即皇帝位,然而皇太极却多次以时机未到予以推辞。在这种情况下,分管礼部事务的贝勒萨哈廉即号召诸贝勒对天盟誓效忠,以消除汗之顾虑,所谓“汗不受尊号,其咎皆在我等诸贝勒。诸贝勒不能自修其身,为汗克尽忠信、展布嘉猷、勤修治道,涂请汗受此大号,汗不肯轻受耳”[5]221。随即诸贝勒采纳其议,依次盟誓以表对汗之忠贞不贰,并再请文馆诸臣将此情形转奏,进而得到了首肯。在此基础上,汗又命希福等人以“诸贝勒请定尊号,地方尚未统一,未知天意,不能受尊号”[5]222为由试探宁完我、范文程等文馆汉臣意见。在取得众汉官一致拥戴后,皇太极遂于同年四月登基称帝,按照中原王朝五德终始说“以水灭火”之意定国号为清,与明朝正式分庭抗礼。
第二,奉命会商机务,为大汗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较之专事征伐的武将,文馆儒臣群体大都熟悉中原典章制度,通晓古今兴衰之理,整体素质较高,且与汗关系近密,充分了解彼之意图,进而扮演了汗的心腹智囊角色。如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对国中不断滋生的应大举伐明,速成伟业的虚骄之气严加指斥,所谓“不过欲速出师以劳师旅,攻克城池,冀得财货,以偿一己之勤劳,而军国之艰难竟置之膜外也”[5]149。同时下令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文馆儒臣谋议伐明过程中可能要面对的一系列新情况。
今我常所思者,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兴师,明主若弃北京而遁,其追之乎,或不追而攻北京,或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而即许之乎?抑拒之乎?若彼被围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民应作何安辑?我国诸贝勒乃至姑娘们、格格们皆以贪财为心,应作何禁止?[5]149
总体而言,汗萦绕于心之问题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与明廷作战过程中战和策略如何运用得当;二是攻入中原后如何安定民心,进而站稳脚跟。正是凭借儒臣们长期的谋划和辅佐,皇太极以后金国自身实力为基础,完善构建了“伐明如伐大树”的战略理论。其在位期间五次派兵入口,对明都北京围而不打,纵兵抢掠畿辅、山东、河南等地,不断蚕食明朝的有生力量,有效壮大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为日后成为中原之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又如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伙同哈达公主莽古济阴谋叛乱一案的处置问题,皇太极以诸贝勒大臣所议不妥为由遂命满汉儒臣再议。会议结果认为,上述人等危害社稷、罪无可赦,其自身及家族近支成员皆应处死。此外,儒臣们以“都不可大于国”之古训明确反对将莽古尔泰、德格类所属之旗下人丁、财物均分各旗。正所谓“都者贝勒也,国者汗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汗与贝勒皆抛等分之,则汗、贝勒无别也。二贝勒人口,汗宜尽取之,欲赐何人,惟汗命之”[5]214。此外,他们亦不赞成对首告者冷僧吉无功无过的处置意见,“若以冷僧吉为无功,则日后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日后计,则冷僧吉宜叙其功”[5]213。此议有力维护了皇太极的君主权威与自身利益,特别是通过将莽古尔泰原有的正蓝旗附入两黄旗,有力壮大了汗的综合实力,遂圣心甚悦得旨允行。
第三,经常奉命临时差遣,且大都事属机要。如天聪五年,大凌河城内粮草耗尽,明将祖大寿已决心归降,皇太极急令库尔缠、龙什二人至军前问候,并咨商后续攻取锦州之计[8]142。天聪七年,范文程、刚林奉命安插新来归降的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军将领,并传达汗之谕令,所谓“统领旧部驻扎东京,号令、鼓吹、仪从俱仍其旧,惟用刑、出兵二事当来奏闻,所属人民俱住盖州、鞍山,如或不愿令住东京邻近地方”[9]。安置完毕后,其又引领孔、耿等归附众将官至盛京觐见。
第四,代收诸臣章奏,转呈大汗批示。文馆职司章疏是天聪中后期儒臣职能政务化的重要标志,并开启了日后其角色逐渐向辅臣转变的先声。天聪七年皇太极一时疏忽,致使有往年五本章奏遗漏未阅,长时间未给出明确意见,文馆大臣马国柱、李栖凤遂催促汗宜尽快批阅。所谓“臣等蒙谕收掌本章,今有积下旧年本五个,臣等固知汗有事不得闲看,但这个上本的人,在外边怎么知道,待命日久不见分付,彼不说书房人藏着不奏,必说汗勤始怠终”[10]。又如天聪九年在文馆当值的龙什、刚林等人审阅臣工本章时,见觉罗索尔果多之孙所奏文辞不佳,遂擅自代为改写以递进,以致遭到了严厉处置,亦可说明上述职掌[11]。值得说明的是,后金时期官稀政简,六部、八旗主要政务信息仍大都通过朝会面奏方式裁定,文书运转体系尚未形成。同时,文馆儒臣对递进的章奏也只有接收与转呈的权力,并未掌握如同明朝阁臣所享有的票拟等处理权。
此外,文馆诸臣尤其是汉族官生又常上书言事,进而成为其参政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天聪朝臣工奏议》汇辑的奏疏中,绝大多数上奏者均有着文馆任职经历。其奏疏大体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建议仿行明朝官制,分步进行国家政权建设[12]。如天聪五年,宁完我针对后金政治制度改革在设立六部后陷入停顿的问题再次上疏急呼,所谓“臣等公疏请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等事,疏经数上,而止立六部,余事尽留中不下”[8]147。特别是对文馆(书房)之名长久未改,更是直言强谏,“我国笔帖赫包之称,于汉言为书房,朝廷之上岂有书房之理?官生杂处,名器未定,更易布置止一矢口之劳,皇上何惮而不为也?”[8]148总体而言,皇太极对改革后金政治制度持积极态度,并根据本国的政情循序渐进给予推行。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采纳上述建议将“笔帖赫包”改为“笔帖赫衙门”,标志着文馆已正式成为国家机构。皇太极称帝前后,又进一步改文馆为内三院,置大学士、学士等官,厘定了品级等第制度,汉臣关于国家制度改革的一系列主张基本得到落实。
如发现国家新政举措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事先未曾预料到的弊端,文馆儒臣亦常上书请求纠正。如天聪九年,针对皇太极发布的“满、汉、蒙古诸臣,凡见有知识堪用者,即行荐举”[5]145的求贤令,范文程认为其将使官员争相结党以致滥举非人,遂参考连坐法,提出了“当少惩其妄举匪人者,至于所举者果善,后有成效者,则其举主亦当给与记录”[5]151的应对举措,并获得采纳。
二是提出诸多伐明方略,以供参考。与改革政治制度等建议态度迥异,皇太极对一些汉族官生纸上谈兵,动辄畅言奇谋建议,特别是水陆两面并进、急取中原等一系列速成大业的主张十分反感,甚至大加指斥。所谓“动辄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国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关素号险固未易攻取。此岂非欲航海者咸没于水,欲攻险者致损其兵乎”[13]213。可见,皇太极在与明朝作战过程中虽多有胜绩,但其仍清楚两国之间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如若一味冒进用兵,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而且将会使多年蓄积起来的有限兵力大有折损。进而其明言到:“此等疏奏何益之有,朕为一国之主与诸贝勒共图军事,岂有不相其机宜之理,此自不待尔等陈说。”[13]213也就是说,虽然文馆儒臣职能呈现出政务化的特征,但用兵等军机事务则仍主要由汗与旗主贝勒商议定夺,汉族官生如无特命顾问,则无须自行陈请。
三、崇德年间内三院建置与大学士职能特征
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在称帝前夕正式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进一步明确了各院的详细职掌,具体内容如下。
国史院:该院职掌记注汗之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汗起居、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祭天祝文,升殿宣读之表文,祭祀宗庙之祭文;编修历代祖宗史书,墓碑铭文,一切机密文移,官员升降文册及诸臣章奏,汇纂史书;撰拟追封诸贝勒册文,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录记载之;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凡外国、邻邦往来文书,俱编为史册。
秘书院:该院职掌撰拟与外国往来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及辩冤词状、汗之敕谕、文武官员敕书;遣祭孔夫子庙,撰拟亡者祭文。
弘文院:该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为汗进讲,侍讲太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14]683。
内三院各有分工,或职司记注政令、纂修史书,或负责草拟日常文书及祭文,或侍讲汗及诸王,较之以往文馆的相关文字职掌呈现出更加正规化、专业化的特征。例如太祖武皇帝实录纂修告成之时,就由职司此事的内国史院官员复命,所谓“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15]。又如皇太极称帝后首次遣官祭拜先师孔子,则由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受命完成。
当年五月,皇太极又对内三院的官制进行了正式厘定。首先,长官称谓方面,罢各院长官承政之称,仿行明制设大学士。其为有清一代设置大学士之始,此后则相沿未改,至入关后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则一直为内阁的长官。其次,人员编制方面,初置国史、弘文二院各大学士一人、学士两人,秘书院大学士两人、学士一人[14]700。再次,品级等第方面,希福、范文程、鲍承先三位大学士均为甲喇章京品级,只有刚林系举人初次授官,所以低于前面三人为牛录章京品级。虽是如此,但为体现对天子近臣之尊崇,大学士各官均可越等按梅勒章京品级享有顶戴服饰与随从人役[14]700。按当时典制规定,梅勒章京品级准用银顶镀金嵌水晶,方带板镀金錾银腰带;出行执事为小旗六人、红帽夜捕手二人[14]706。值得说明的是,当时清廷制度属草创阶段,官员等级尚以世职标第,特别是内院大学士品级不仅因人而异,名实之间也有着明显差别,与后世阁臣之品级迥然不同。
伴随内三院作为官署的正式建置,大学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显著提高。除沿袭文馆诸臣的一些政务职能外,又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其一,随着清廷汉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各项仪制活动日渐增多,内三院大学士广泛参与其中,进而成为入关后阁臣的重要职掌。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学士罗硕、胡球等人将刚成熟的新鲜樱桃荐于太庙享用,并规定日后“凡新进果品、五谷,先荐太庙,然后进御,著为令”[16]。当年八月,皇太极始令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先师孔子,并仿行古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配享[14]742。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等又受命远赴科尔沁蒙古册封外藩和硕公主及亲郡王妻室[17]。此外,皇帝外出征伐或胜利归来,册立后妃等一系列典礼亦大都由内三院会同礼部预先制定仪节,大学士宣读正式敕谕表文。
其二,大学士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并在国家用人、行政及明清鼎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大学士范文程受命与吏部共议户部承政及启心郎之人选[18]559。在此基础上,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大学士鉴于“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满洲蒙古汉人承政,每衙门各三四员,其余皆为参政,官止二等”[18]559的不合理情形,对官制提出了改革建议,并得到了皇帝的积极采纳。一方面,改变各部院同时设置多员承政的局面,只设一名承政,例为满洲人充任,蒙古、汉人则改任左右参政。另一方面,增置部院官制等级为五等,在原有承政、参政的基础上添设理事官、副理事官、主事等官员,直接奠定了入关后部院官制普设堂官、司官的基本格局。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农民军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大举北上,明廷倾覆就在眼前,范文程有鉴于此,遂上书清廷速发兵南下谋取中原。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用兵不同以往,务必要申明纪律,力争做到秋毫无犯,使归附者知晓我方进取中原之意,并获得了睿亲王多尔衮的积极采纳。行军途中,面对明将吴三桂与大顺政权反目成仇,乞师助剿的千载难逢之良机,在范文程等人的精心谋划下 ,清军率先打出了“为尔君父复仇”的旗号,不仅相继赢得了汉族官僚士绅的支持与归降,而且迅速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大顺军,成功入主中原,进而完成了太祖、太宗多年之夙愿。
其三,身处中枢的内院大学士与皇帝关系近密,在朝局中已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协调能力。如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帝令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等率军围困锦州,以图一举攻取此辽西重镇。然而双方相持既久,清军多有损耗,身为主帅的多尔衮未经请旨则命全军后退三十里修整,同时允许将士轮流回家探亲。身在盛京的皇太极闻知后,认为此举将使敌人得以喘息以致前功尽弃,遂勃然大怒,严令上述王、大臣等回京戴罪,并由郑亲王济尔哈朗赴军前指挥。多尔衮等虽反复请罪受罚,但帝仍余怒未息。既不准入宫面见,又不许其入署办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子近臣的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等遂领衔请命建言。
前锦州撤回诸王、贝勒及诸大臣,违命离城远驻,任意田猎、怠玩从事,上怒之诚是。但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又未获入觐天颜。臣等思伊等回家日久,复近更番之期,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少霁天威,仍令入署办事[19]。
其虽肯定了皇帝对诸王、大臣的责罚,但亦明确指出,此次涉事人员较多且位高权重,如若长期不做结案,将使朝政陷入僵局,对国家日常政务与用兵征伐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最终皇太极从谏如流、适可而止,避免了君臣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经此一事诸王、大臣唯君命是从,皇帝权威更加巩固,为随后清军在松锦决战中上下一心、大获全胜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崇德年间内院大学士的政治角色仍是一介儒臣,而非中枢宰辅,与天聪时期的文馆诸臣没有本质区别。
一方面,内三院的官方职掌依然局限在文馆时期以文字为职能中心的定位,大学士对政事的参与完全有赖于君主在实际理政中的特殊任用,而并非典制明确赋予,其与天聪年间的文馆儒臣并无二致。事实上,当时清廷重大军政要务均由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日常行政事务亦有管部王贝勒等面奏皇帝裁决。大学士如无特旨,既无资格参加议政,又不能干涉六部政务。其对政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依仗皇帝倚重下的有限顾问与咨询。遑论汉唐宋元秉均国政的宰相,即与明中后期主掌票拟的阁臣相比亦差距甚远。
另一方面,内院大学士在品级上不仅低于国中旧有的固山额真等管旗大臣,而且亦逊于陆续仿行汉制设置的部院长官。特别是崇德元年都察院衙门一经甫设,其承政就高居昂邦章京品级,而当时内院大学士中如范文程、希福等在文馆侍从多年,资深望重者实际才为二等甲喇章京品级,明显低于前者[14]710。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再次明确内三院品级时亦记述到,“盛京原定六部为一品,内三院为二品”[20]。此外,清初八旗隶属关系森严,作为旗下属人的大学士对本旗旗主亦存在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如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发生的豫亲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的恶性事件,也仅是被罚银一千两、削夺所属十五牛录了事[21]。像范文程这样的亲信重臣尚且遭此奇耻大辱,入关前内院大学士之地位可见一斑,这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古之宰相判若有别。
四、结 语
清朝入关前大学士兼具儒臣与近侍的双重政治角色,而上述二元特征的形成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亲信“巴克什”群体身上就已逐步显现,至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仿明制设大学士后一直得以延续。作为朝堂上的儒臣,该群体文化素养较高,通晓多族语言,受命创立本族文字、翻译经史典籍、记注国家政事等一系列与文字职掌相关的事宜。作为君主之侍从,他们地居近密,除职司撰写日常公文外,又延展至传谕宣旨、顾问机宜、外出差遣等诸多政务。值得注意的是,儒臣身份是入关前大学士的基本角色与官方定位,无论是文馆还是内三院的法定职掌均系与“文字”有关的事务方面,而绝非国家政务。
然而天聪中后期,文馆儒臣凭借着与汗特殊的亲近关系,政务职能属性愈发显现。特别是崇德年间,内院大学士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还是在用人行政中的话语权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至顺康年间,伴随清廷别设翰林院专司文章事宜,号为“政府”的内阁则成为国家行政中枢。阁臣通过票拟章奏和御门听政后与皇帝面商机要的机会,稳定实现了对中枢决策的有效参与,其职能角色亦实现了由儒臣向辅臣的最终转变。与此同时,大学士的品级与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位居六部尚书之前为文班之首,俨然古之领袖群僚的宰相,原本的近侍色彩亦逐渐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