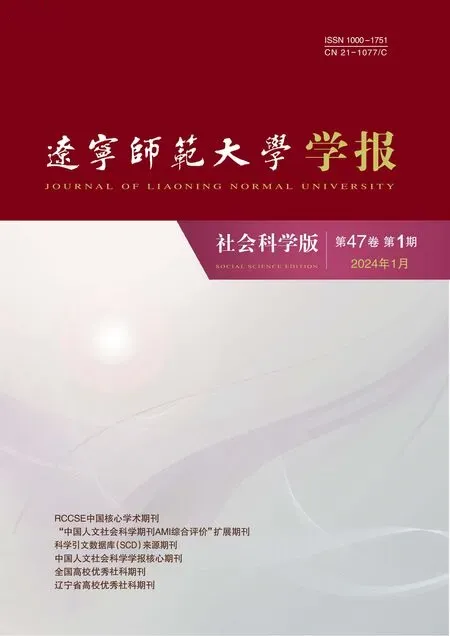凝视与想象:《回响》的回响
——东西小说《回响》和电视剧《回响》读札
石竹青, 任子钰
(辽宁师范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根据作家东西的长篇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短剧《回响》,自播出便引起广泛讨论,视频弹幕中反复弹出的“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这应该算是观众对于作品的直接回馈。随着媒介传播的手段更新迭代,人们由最初被文字浸润,逐步进入电视剧、电影所主宰的光影世界,再到如今以短视频、新媒体等媒介交融为标识的网络时代,人们被碎片化的体验方式裹挟,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与审美标准也产生了转变,这也促使传播手段、艺术创作机制不断革新。《回响》是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中一部还原度极高的作品。小说探讨了关于爱情与婚姻,现实与想象的话题,以悬疑的视角展开叙事,以叩问心灵的声音激发观众对于人性的审视及其对情感世界的全新思考。故事由妙龄女子夏冰清遭遇谋杀展开,女刑警冉咚咚着手调查,发现夏冰清身边之人皆以爱为名,实则别有用心。东西通过剧情的步步推进与反转,展现了人与自我的深层互动,给予观众基于现实的想象——爱以何种方式呈现?恨以何种方式消解?这些凝视与追问,使读者与观众在人物不断深入的自我认识与心理蜕变的过程中得以瞥见生活的真相。可以说,从叙事性文本到荧屏镜像,这两种艺术形式或文本形成一种审美互动和互文,让我们在对照性的阅读中获得新的理解,使得我们对文学叙事文本和影视文本各自的魅力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两者转化中生成的新元素有了更深入的体会。
一
叙事策略的选择不仅是文学写作的密钥,也是影视作品建构视觉故事王国的关键。“故事中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即‘叙’和‘事’;可能侧重有所不同,有的偏重于‘事’,有的偏重于‘叙’,但都是‘叙事’……讲述必定从不同的需要和观察角度进行了某种处理。处理的过程是一个逻辑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1]现在,《回响》将叙事披上了悬疑的外衣,尝试探讨婚姻与人性的本质,将荷尔蒙的冲动、生活“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呈现给观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从文字到镜头,悬疑外壳下叙事策略的转变,将长篇小说《回响》的“文学性”,继续沿着审美的路径,转换、传达和渗透进影视文本的肌理。也许,我们会惊叹电视剧《回响》对小说原著的“忠诚度”如此之高,由此看到小说家东西和作为编剧的东西,在这两种艺术样式之间做出怎样的“重构”。那么,我们再次回到东西创作的原著小说,其对传统侦探悬疑小说创作的背离,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特点与独特的艺术风格。显然,东西并没有囿于一般侦探小说同质化或模式的套路去创作,而是在具体地呈现侦破案件的同时,加入了对于人性的“侦破”。将故事融入冉咚咚与其丈夫慕达夫的感情纠葛,因而作品没有完全陷入罪案推理的模式之中,而是借由悬疑的外壳,展开故事思想维度的深度探索以及人物情感与心理的双重追查。小说的叙事结构是更具张力的,案件与情感的线索推进相对独立展开,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情感,最终章进行双线合并。文本与画面的表达层次是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则需要克服二者在媒介形式上存在的必然差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媒介具备非直观的特点,其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天然便具有细腻与灵活的表达空间,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文本带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意识到二者形式上的绝对差异,也并非意味着改编要完全丢弃或改写某些要点,结构及细节的调整是必要的。由于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娱乐特性,电视剧的改编对戏剧性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东西对结构进行了双线并行、交叉叙事的改编,这也是整个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少有的变动。剧集叙事尤为巧妙之处在于罗生门式的结构复现。故事从夏冰清惨遭杀害的案件讲起,随着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这些嫌疑人接连浮出水面,罗生门式的结构徐徐展开。通过套层式的叙述手法,让不同的人物讲述他们眼中不同的夏冰清,呈现其爱恨纠葛,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案件的走向愈发扑朔迷离,人物间的关系也陷入微妙的境况,人人自危之时,将无人吐露真情。每个人都为了自我利益的保全甘愿欺骗与背叛,而真相迷失在每个人的自我辩护中,女刑警冉咚咚只得在人物与人物的补充叙述中寻找蛛丝马迹,侦破人性的真相。
在一定程度上讲,叙事的开端往往并非由故事的起点所决定,而往往却是“叙述”的起点,而叙述的视点,既是叙事性文本的切入口,也是影视“入镜”的逻辑起点,因此,这种“视角的政治学”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影视作品的开端,对照文学文本的创作存在不同的呈现价值,选择怎样的事件进行影视化的表达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原作在故事开端进行了如下的描写:“冉咚咚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西江大坑段,看见她漂在离岸边两米远的水面,像做俯卧撑做累了再也起不来似的。”[2]1在这里,不同于文学文本,电视剧的开篇视角选择直击案发现场,将我们迅速带到大坑案之中,这是视觉艺术的优势。进一步说,影视作品中对于故事开端的呈现,进行了符合视觉逻辑的丰富与细化。叙事由一起人质劫持案展开,以冉咚咚果断处置凶犯从容解救儿童结束。这一开端事件的设计利用突发事件的促动作用将冉咚咚的人物形象在故事伊始便在观众心中定格,她雷厉风行、勇敢果断,是个干练且有着丰富经验的女刑警。与此同时,由针对此案的后续反响切入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日常情感生活,通过简短的对话,表达了慕达夫对于冉咚咚处置罪犯方式的不赞同。在开端几分钟就交代了二人的性格、相处之道与夫妻关系,也暗含着冉咚咚夫妻间存在着潜在且不可忽视的分歧,为后续二人婚姻危机的情节推进做了扎实的铺垫。紧接着,才是夏冰清的尸体被发现,冉咚咚成为案件负责人,剧中的主要事件“大坑案”由此正式进入观众视角。在此次改编过程中,除了叙事结构的调整,东西保留了所有核心内容。剧中人物的台词和动作,场景的设定以及剧情的起承转合,几乎复刻了原著的创作思路。我们可以说,改编的目的并非与原著一较高下,而是基于原著,找到契合时代的叙述角度,透过当下的思想风尚,以精致的视听风格予以呈现,使作品拥有独立于小说之外的艺术价值。东西对于原著的高度还原,使电视剧免去了文本内容上的脱离与质变,同时其基于媒介形式差异的合理化处理避免了如今“魔改”的问题,保持了审美的流行性,也延续了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
二
人物的塑造之于文学与影视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进一步说,基于影视创作的特性,改编不得不舍弃部分人物心理层面的细节描写,那么人物形象要立得住,性格特点要具备差异化便显得尤为关键。由于历史的处境是不尽相同的,个体所面对的选择自然有别他者。“每个人都需要外在‘他者’对自身的确认与充实来填补自我本质的内在缺失。‘自我’受‘他者’的影响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建构与转变。”[3]可以确认的是,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一份社会基于其身份形成的凝视的目光,在社会与他者的凝视下,人物竭力塑造着自我的价值,建构着自我身份的深刻认知。夏冰清是故事中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亲情的限制与衍生的隐性压力使她陷入自我的迷失,她无力抗争父母一步一步操纵她的人生轨迹,从而选择了逃避,用谎言维系与父母的关系,继续留在这个城市与徐山川建立了道德约束之外的爱情关系,过着迷失自我的无措生活,而在承认自己第三者的身份后,父母以怎样的眼光凝视着夏冰清,都有意地让她成为她。徐山川的形象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庸俗化成功男性的代表,将过错放置于女性身上而为自己辩白是他的惯用伎俩。论人性冷漠本质的呈现,则要着重强调徐山川这个人物的设置,由于他长期享受着事业成功带来的既得利益,其建立与他者关系的方式是通过以物质或权利引诱并支配女性,摒弃道德而实现自我的占有。性格的局限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徐山川的自私多情与不忠直接摧毁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也间接导致了夏冰清惨死悲剧的发生。慕达夫则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而克制物质与情欲诱惑的文人形象。他在精神出轨的边缘反复游离,内心深处充满不安与愧疚。冉咚咚则像是他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时而映照着他的幸福,时而裹挟着他的灵魂,在不断反思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他选择回归冉咚咚的世界,尝试与她寻回爱情与婚姻的真谛。东西对每个微小个体进行剖析,抽丝剥茧一般,通过人物的情感关系反映当下社会的婚姻现状与情感观念,对于人性的深层洞察,使其作品成为现实生活的侧写,并触探社会现实。冉咚咚执拗地寻找婚姻真相最终回归家庭,夏冰清因爱而生终又因爱而毁,沈小迎的爱情观与善恶观的转变使她选择交出关键证据……女性角色的行为与动因引发观众的审视。综观当下的话语表达,如何塑造女性,使之更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文艺作品实则需要更多因执着和追求功成名就的,因努力向上而如愿以偿的女性形象,而爱与恨的辗转迷失也许只能塑造极小部分的她们。
“创伤”(trauma)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中“损伤”,其原来的意思为“伤”。既可指由某种直接的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也可指由某种强烈的情绪伤害所造成的心理损伤。通常,人们将这种外部力量称之为“生活事件”。现代研究认为,所有的心理疾病都与这些生活事件有关[4]。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文学与影视艺术基于人物心灵的追问与思考常常是通过诉己之情而瞥见群体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关乎心理的主题总能够上升到人性的孤独与残缺。心理的幻视往往反映出人性深处的复杂现实,而人物基于原生家庭所携带的成长基因于人物而言如影随形。可以说,故事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皆存在心理的创伤,他们选择将现实的丑恶洗刷,任由自由的灵魂飞远。冉咚咚的人设在文学作品中不算多见,不可否认她是一名业务能力极强的女刑警,而当那份执念被她带入工作以外的生活,也就是说职业塑造的惯性思维方式冲破了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其迷失在虚无的想象中。分不清现实与罪案,焦虑与压力便爬上她的脊背,压得她透不过气,甚至患上抑郁,性格上的分裂与情感上的洁癖将她步步紧逼,滑向生活的边缘。而究其心理脉络,儿时偶然发现父亲与隔壁阿姨约会的事情使冉咚咚的内心衍生了不可言说的背叛感与抛弃感,这种延迟创伤的修复是漫长的,像一颗受了潮的定时炸弹,时刻等待被唤醒的契机,这也是她拥有情感洁癖的内在动因。夏冰清的人生悲剧同样要追溯到隐匿其背后的家庭因素,她的原生家庭是不存在亲情的,而父母极强的控制欲却成了压垮她的稻草。从改高考志愿,到被逼嫁给李晓伟为父亲造成的车祸减轻负担,每一步都充斥着父母的自私与独断,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人生始终在为他们的无能买单。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创伤性事件并非指重大性事件,而在于其非日常性及突发性,这对于人物生活的潜在影响是不容小视的,也不断重塑着夏冰清的人物性格及日后的价值选择。东西对于当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独到的剖析,并寻得了与观众对话的现实语境,以心理学的视角洞悉人物性格的养成与命运的走向,引发了观众深刻的思考。
三
说到底,文学属于个性的创作与思考,是作者眼中的另一个世界;电视剧作为媒介传播的手段,则是一种大众艺术。因此,文学改编常常面临影视作品消解原著文化立意与主题构想的难题。东西此次亲自操刀参与影视化改编,完成了一次针对人性与道德的大胆质询。市场经济冲击裹挟下的文艺创作的碎片化与同质化表征,人文精神与道德观念所面临的亟待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回归,双向影响并推动文学作品与影像作品的思想价值不能单纯停留于文本的语言或形式,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与创作,皆需依靠对于时代的敏锐洞察,对于现实的充分理解,包括对于人性弱点的精准剖析。爱情始终是文学与艺术永恒的议题。《回响》在探讨爱情与婚姻时,规避了一种习惯性套路,缩减了人物相爱的一般过程,强调人性由于本质的差异而体现的,存在于相爱之后,褪去了盲目与热情的裹挟所浮现的谎言与救赎、约束与迷惘。影视化的作品以几段插叙镜头,回溯了慕达夫与冉咚咚相识相爱的过程,着重把镜头对准二人婚后琐碎无常的生活,慕达夫的内心摇曳使冉咚咚踏上了破解谎言的追问与查证之旅。影视短剧《回响》极大程度还原并保留了人物极具“心理学家”风格的对话。冉咚咚与慕达夫之间的情感碰撞与拉扯,大部分是基于人物心理层面而触发的,并非常见小说中的触发条件,如某一激励事件。二人的交谈因此常以针尖对麦芒的态势展开,“爱就像真理一样永恒”。“爱可以永恒,但爱情不能。所有的爱情最后都会变成爱,两个字先走掉一个,仿佛夫妻总得有一个先死。”[2]264冉咚咚时常因心有不甘而挑起话题,慕达夫则由于心怀鬼胎步步迂回,“如果你非得在结婚之后找初恋的感觉,那就像在唐朝找手机,在月球上找植物”[2]264。东西基于人物的心理变化设计的一系列精彩的对白,在剧中也得以复现。诚然,从道德的维度出发,《回响》中的多角关系,实际上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约束,情感本身所讲求的责任与克制在其中变得模糊不清。东西并没有试图在创作中为读者和观众打造一个爱情的“乌托邦”,或者说“婚姻的神话”,反而以冷静的态度,通过勘察凶杀案的独特视角作为切入口,呈现了爱情的“灰色地带”与人性的伪善。从各执一词的责任推脱,从不同人物间的爱恨纠葛,解构背后道德形象的丧失与重建,探寻穿透人性本质的罪与罚、爱与救赎。剧集的结尾,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冉咚咚再次选择了慕达夫,慕达夫精神出轨的既定事实被原谅,二人窒息的婚姻关系出现了再次延续的可能,这些都成了观众聚焦与争议的话题。中国传统婚姻与价值观更多承载着道德约束与现实推力,尊重、妥协、道义、责任,使爱情与人生成为永恒的议题,同时也是永恒的谜题。作家东西在《回响》最终章试图将上述种种以“内疚”之情作以概括和表现,“她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2]112。而是否选择带着杂质继续一段感情,每个人则拥有不同的抉择。
“历史、人性和现实,这些附着于经验和记忆中的重要元素,对于东西来说,不仅仅是推陈出新的时间流变,同时也是亘古如新的返本归元。唯此,想象力、虚构力和时间之于经验的重构,才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反思人性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东西貌似游走于历史与虚构的边缘,实际上,他的叙述,在过滤掉历史的烟尘之后,已经使人性的真相更加清晰和逼真。”[5]让我们回到凶杀案的侦破过程,夏冰清的死因查实为徐山川试图与她分手未果便委托司机帮忙处理她这个麻烦,没想到司机又委与他人,在这样戏剧化的层层嵌套中,夏冰清竟意外死于一位精神病人之手。正如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凶案的真相令人唏嘘不已,现实的荒诞与人物的命运交织,谱写着生命的旋律,而人物置身其中,无法窥见未来。《回响》透过案件展现了人性的暗角,也表明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作品以一种探寻善与恶的独特视角,将人们拖入一场人性的漩涡,给予观众选择与想象的空间,或与人物共沉沦,或与人物共面对。正如东西在小说中写道的,“研究文学作品即研究人性”[2]112。“对于东西的小说创作,最不能忽略的,应该是其寓言性、寓言品质。正是深邃的寓言品质,使得东西的文本能越过表象世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抵达人性和存在世相的纵深处。这也凸显出他基于写实主义叙事策略而极力建构、扩张文本的美学意图,更是写作的精神主体自觉的表现。”[6]可见,悬疑只是这部作品的底色,讲的是案件,谈的是感情,也是人性。十三集,两条故事线,复杂的并不是故事,是人性的本质。自私和情欲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何时都需面对的问题,砸向夏冰清的那一锤何尝不是也重重地砸在我们的心上。《回响》对于人性的探讨是透彻的。大坑案的相关嫌疑人为洗脱罪责而撒下谎言,丈夫慕达夫则为自我辩护不断圆谎,正如小说所言:“真话总是慢慢讲,谎言才会跑得急。”[2]12似乎每个人都在自我保全,欺骗与背叛贯穿整个故事,人性的弱点一览无余。当我们投射了怀疑的眼光,产生了追问的欲望,生活中的一处裂缝,亲密关系中的一句谎言,都极有可能成为摧毁平静的巨浪。而人性始终装点着我们生活的基底,牵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它暗自流动,等待着我们的考验与追问。
言说方式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文学与影视终究是两门艺术,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影视作品也给予了文学作品极大的信心,通过媒介的交融与整合,使文学作品以蒙太奇的组接方式,再现时代无法磨灭的心灵印迹和精神价值。作家东西以其自觉的审美姿态与扎实的文本功底,为读者和观众献上了一出关于人性的大戏。小说文本《回响》和影视文本《回响》构成双重交响,让我们看到作家以凝视的目光着眼当下的时代生活,以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观照人性的幽暗深处,让心灵的回响与现实的叩问在人们心中久久萦绕。然而,就观众接受程度和审美差异而言,也反映出文学改编影视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创造新的艺术生命力,延续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使其免于成为当下传播媒介的附庸,同时聚焦时代,探索人性的力量,使得文学与影视的艺术价值最大化,也成为创作者们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