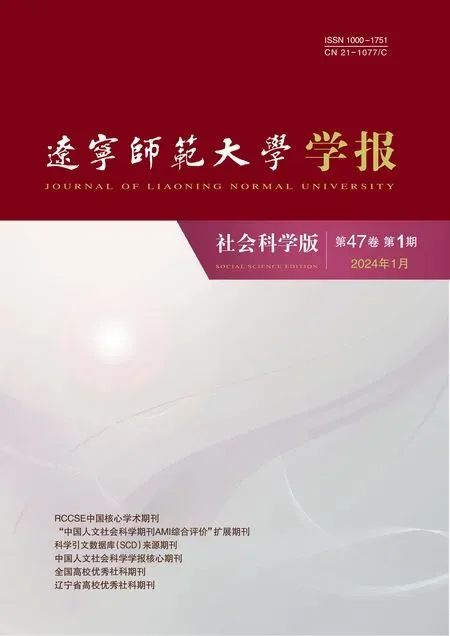摆渡人与月光澡
——迟子建《空色林澡屋》读札
金 钰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
“老女人”是迟子建的文学人物画廊中独特的艺术形象。如短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的媪高娘、《柳阿婆的故事》的柳阿婆、《守灵人不说话》的外祖母、《逝川》的吉喜、《门镜外的楼道》的清洁老太、《采浆果的人》的苍苍婆;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的“老苏联”、《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的老妇人、《鸭如花》的徐五婆、《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的云娘、《草原》的阿荣吉老婆子、《泥霞池》的老板娘、《黄鸡白酒》的春婆婆、《晚安玫瑰》的吉莲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的吉来奶奶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无论文章篇幅容量多少,迟子建均以“边缘生活者”的角度切入,用平等的目光凝望她们的喜怒哀乐与命运遭际,即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刻画出这一形象的群体风貌,以温情之手摹画出独属于“老女人”的苍凉之美。
《空色林澡屋》中“皂娘”这一人物形象无疑丰富了迟子建笔下的“老女人”谱系。但皂娘又是与众不同的,作为这篇小说的灵魂人物,皂娘秉承了迟子建笔下的女性人物气质,却也有了一定的超越,更具有“大母神”形象的精神内涵。皂娘是不幸的,她的不幸源于那张不对称的脸——“别人的鼻子,是脸颊的中界线,可她的鼻子,偏袒一方,致使左脸辽阔,右脸一派失地气象,狭窄逼仄”[1]。皂娘最初的婚姻由父母包办,但丈夫嫌弃她的长相,为了摆脱她,只身来到艰苦的乌玛山区。尽管受尽丈夫奚落和挖苦,皂娘还是带着儿子跟随与陪伴他。但后来由于皂娘帮助了一个瞎眼的算命先生,丈夫“误会”皂娘与其有染而提出离婚,儿子也因母貌丑选择父亲。伴随着“咔嚓”的剪刀声,那绺遮脸的刘海与皂娘的第一次爱情、完整的家庭都铰落在地,摔得稀碎。她脸上的那面为丈夫而竖的旗帜,就此倒下。孑然一身的皂娘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住进了林场边废弃的小屋,饱受思子的煎熬。在神秘原始森林乌玛山区,皂娘又 先后邂逅了威呼郎和老曲,成为彼此心灵上的依靠。
相比于迟子建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皂娘更加立体饱满。她虽样貌丑陋,却有着世间最清澈纯粹的灵魂。迟子建借关长河之口道出了对美与丑的不同理解——“人可真是怪物啊,歪脖垂腰的杨柳,龇牙咧嘴的花儿,奇形怪状的石头,曲里拐弯的河,都说美,轮到人呢,就不一样了,可见人多是没良心的!”[1]外貌之丑与灵魂之美的对比,使皂娘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有思辨价值。同时,她既世俗又非世俗——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在皂娘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与融合。皂娘世俗的一面体现在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以及对艰难生活的苦心经营。不同于《逝川》中那个骄傲而孤独的吉喜,皂娘是那么的“接地气”。她不在乎丈夫的嫌弃,毅然决然地追随他来到翠岭林场,只为了拥有一个家;她不在意威呼郎已有妻子,满心欢喜地与他每年在水上过半年的日子,只为了守护心中的爱情;她不在乎老曲是一个精神失常的智力障碍者,不辞辛苦地关爱着他,只为了拥有最后的陪伴。皂娘与威呼郎的结合更能体现出一种自然任性之爱,充溢着禅宗文化特有的空灵自由之美。迟子建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谴责,反而在无羁的情爱追求里添加了脉脉温情。除此之外,皂娘还能够在艰难困苦中活出人的样子。她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很有经营头脑。皂娘懂得卖女人们喜爱的小货品、自学熬制香皂来维持生计;车主经过房子时会讨水喝,皂娘也看出这是一个好商机,便把家改造成小店,后来为了避免纷争,不再提供饭食,专心经营澡屋。皂娘的世俗绝非市侩,而是以一颗热忱而纯净的心抵抗人性的荒寒与命运的不公,从容地面对人生坎坷与磨难,自如地行走在凡俗生活中。皂娘非世俗的一面体现在始终保持了一种平凡而超越的生存姿态,她是众人灵魂的摆渡者。那些在空色林澡屋中洗澡的饱经风霜的旅人,都在皂娘的船形澡盆中变回了不再逞强的孩子,甚至会痛快地哭上一场。“泪水融入散发着他们体味的洗澡水,就像汇入了世俗生活的洪流,他们拔脚出浴时,轻松了许多。”[1]皂娘用她的生命之泉给予了众生最慈悲的救济。渡人容易,渡己难。最难能可贵的是,皂娘虽在尘劳中却不为尘劳所染,本身生活在黑暗里的皂娘,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温柔的月光。
至此,可以这样认为:皂娘不是一开始就是空色林澡屋的皂娘,而是在巨大的磨难中表现出生活的韧性,确立了女性的价值尊严,才最终成了皂娘。即“女性精神变形特征是‘通过痛苦和死亡、献祭和肉体与灵魂的泯灭而达到更新、再生和不朽’”[2]。虽然这种蜕变是以悲剧为基础,但只有当她以悲悯众生的情怀超越了自我的苦痛,才从一个普通的女人转变为“大母神”,拥有了保护、温暖和滋养的功能——即便自己遍体鳞伤,仍不失善待自己和自己以外生命的爱的能量。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如同故事中的青龙河与银河,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它们在同一个宇宙中,渡着相似的人。”[1]皂娘虔诚地渡着漂泊的旅人,也渡着漂泊的自己。她用沧桑的手指搅起了岁月的波澜,褪去众人的尘垢,收纳苍生的眼泪,也抚慰了自己的创伤。
二
迟子建不畏惧黑暗,甚至有些许钟情,她的诸多小说以夜晚命名或与之紧密关联,包括《葫芦街头唱晚》《夜行船》《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兰基小站的腊八夜》《第三地晚餐》《晚安玫瑰》。而黑夜中的迟子建也并非孤独的,在柔和月光照拂中往往生发出更坚定的精神力量。于是,迟子建对于月亮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她执着地书写月光与月夜,不断延续与丰富月亮意象的文本要素意义,使其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迟子建笔下的月亮不仅拥有丰富的颜色与形态,还作为一种生命体与精神实体,具有人格化特征。迟子建是与月光一起成长起来的。如果说迟子建早期创作中的月光意象是纤尘不染的,更多的带有一种少女冥想世界中的梦幻色彩,体现她初入文坛时拒绝尘俗、远离尘嚣的创作心态。如《没有夏天了》中的这段描述:“天空被月光洗淡了夜色,天边的一些稀稀的亮晶晶的小星星,拼命地鼓起眼睛企图把宇宙望穿。……我躺在树丛下,仰着头望着夜空,望着月亮。”[3]那么成熟后的极地之女,在亲身经历了人世间的诸多苦痛、离别与死亡,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后,仍执着地创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存空间,勇敢地表达对光的追寻,深情地望向天空。在月光的抚慰下,迟子建更显平静与从容。《空色林澡屋》中,关于月亮的描写出现了16次,月亮与主人公皂娘、关长河融为一体,成为这篇小说的高频词意象与核心象征体。
一方面,“月亮”与“船”“澡盆”共同隐喻着“归宿”与“治愈”。小说中,船是与皂娘的爱情发生同时出现的。威呼郎的小船那样简单粗糙——“船是整根松木砍凿而成的,长不过两丈,中间的舱口能容一人坐下,船两头起翘,像一条贴着水面飞的大鱼”[1],却给予了皂娘生命中难以复刻的温馨与柔情。威呼郎生病去世后,漂泊一生的皂娘重新造了一条船,她守着那条不能入水的船形澡盆,如同守护自己的家:“这条小船比一般船要小许多,只能坐下一人,船头宽,有个横板;船尾尖,无桨无舱,看上去像只小脚老太穿的鞋。”[1]船形澡盆虽然不能达到河的彼岸,却让心灵有所皈依。不难发现,在整篇小说中,“船”“澡盆”与“月亮”这三个意象彼此缠绕,不可分离。关长河在小说中这样说:“太阳是做饭的大火炉,月亮是人住的屋子,星星是禾苗。”[1]屋子便是家,是理想化的精神家园,不仅是疲惫身体的栖息地,更是脆弱心灵的归宿,承载着无数个人世间悲欢合散的故事。而皂娘的船形澡盆是那样神奇。躺在其中,在皂娘手指的轻柔触碰与爱抚下,每一寸肌肤都得以滋润,每一个被阻塞的毛孔都打开了天窗。虽然洗浴过后,悲剧从来就不曾落幕,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也不会减少,但经过洗涤的人们仿佛得到了自然神的庇佑,奇迹伴随着那迷人的月光与温柔的水就这样降临了。病入膏肓的中年男子在澡屋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沐浴后,心魔不再,把生死看淡,最终竟战胜了病魔,幸存下来。因此在小说中,月光的轻抚下的空色林澡屋披上了一层超验而神秘的面纱,心灵的伤、眼角的泪、身上的灰,都于神奇的“月光澡”中觅得归宿、得以安放。“月亮”抚照下的“澡盆”成为渡着灵魂的“船”,既怀恋着此岸的光,又弥漫着彼岸的泪,不言不语、自来自去,却与人类相伴终生。
另一方面,置身于无瑕月光中,仿佛沐浴了一场天然的“月光澡”。因此,在本就以“洗澡”为主要叙事情节的故事中,“月亮”被赋予了“除尘”“净心”等象征意义,而这一主题也是迟子建在底层叙事中持续探索的。迟子建早期创作的另两篇小说《清水洗尘》《泥霞池》均以“洗澡”为主要故事情节,由此构成了前后勾连、相互对照、互为补充的“洗澡三部曲”,既从侧面呈现出迟子建的创作心理轨迹,也彰显了18年斑驳时光中一以贯之的努力。《清水洗尘》笔触宽柔明丽、温暖如诗。“洗澡”这一平凡的生活意象承载了童年世界中最强烈的愿景,且被一次一次地无限放大。而在《泥霞池》中,轻快明丽的暖色调被岁月的风尘沾染成了暗灰色,寂静的清水惹了尘埃,小男孩成长为青年男子,却在藏污纳垢中的泥霞池中迷失了自我。这个故事触摸到底层人物的生存真相,展示了卑微生命个体在现实泥沼的沉沦。在这里,“洗澡”不再隐喻对未来的憧憬,只是挣扎在社会底层弱小群体的黯淡生活的一部分,其象征意义大大减弱,洗澡的仪式感与神圣感也随着残忍真相的揭示而消失殆尽。在《空色林澡屋》中,月光这一意象再次将“洗澡”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与复杂的意蕴,尤其体现在一位暮年男子关长河身上。关长河始终怀揣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有着几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痴”和常人不能理解的“执”。他固执地追寻月光,认为“月亮也是个大澡盆,它用的是银河的水”。他更坚信皂娘的存在,空色林澡屋也因信而生、而长久。迟子建努力传达出一种基于现实的希冀,几十年如一日地书写着人性人情。面对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人心日益浮躁,精神遭遇蒙尘。因此,到大自然的月光里、到澡盆中去,洗浴人生、净化灵魂,去发掘流淌人性的清泉,去寻找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成为人们摆脱困境、安放内心的一种路径和可能。《清水洗尘》《泥霞池》《空色林澡屋》三篇作品由此构成了一种互文性意义:“洗澡”于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意蕴,象征了个体生命的心灵蜕变与精神成长——从少年时对净澈之水的渴望,到中年时于欲望沼泽中的沉溺或坚守,再到暮年时渡人渡己的超脱和净化,而这也形成了一种造微入妙却无法完全言明的生存密码与人世真相。由此可以得出,迟子建笔下的“月亮”不再仅仅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积淀着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记忆,升华为人性救赎的镜像存在,寄寓着理想恒久的精神家园。
三
除了人物形象谱系的有力接续与月光等意象的强烈隐喻,《空色林澡屋》的独到之处还在于运用了丰富的叙事技巧,拓宽了底层叙事之外的伦理主题。这篇小说是典型的嵌套结构,即大故事套小故事,而这也是“元小说”的重要特征。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尤里·蒂尼亚诺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在研究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提出了“роман романа”(小说的小说)的观点,这一概念便是文学术语“元小说”的前身[4]。在《空色林澡屋》中,“小说的小说”具体呈现为颇值得玩味的三层叙事圈套:第一层为“我”记叙了出发去森林中考察的故事;第二层为向导关长河的身世故事以及“我”与几位同事为了获得洗澡的机会而分别讲述的故事;第三层为关长河讲述的皂娘的故事。
迟子建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表明:“这篇中篇与我的其他中篇不同之处,在于可以有两种解读法。如果读前三分之二,只是关乎洗澡的部分,也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未尝不可。但岁月风雨的吹打,让我对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更加满怀期待(那里有人性寒霜的一面,有落寞和虚无),所以希望作者能读到底。”[5]这段话中的“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指向的便是勘察队五个队员在诉苦比赛中所倾诉和宣泄的生活窘境和坎坷经历。皂娘和空色林澡屋如“世外桃源”般,对于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为了获得被皂娘洗澡的机会,达到独享空色林澡屋这一目的,大家都不惜自揭伤疤,道尽自己的辛酸过往。但这场彼此袒露、掏心掏肺的诉苦却没有带给众人心灵净化的体验,而是精神重回委顿,肉身更加疲倦。小说写道:在结束考察后的一天,当第一层叙述人“我”关心小李与女友的爱情悲剧时,小李却“眨着眼睛笑了,先拱手对我说,领导对不起了,接着告诉我,他与女友间的悲催爱情故事,是被逼无奈,依照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编排到自己身上的;他还没女友呢?”据此可推断的是:勘察队一行人为了在诉苦比赛中拔得头筹,要么肆意夸大自己经历的苦难程度全力卖惨;要么选择虚构故事捏造不幸来增加获胜的概率;要么就是在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真实哀伤与屈辱被鲜血淋漓地呈现出来后,有了种难言的空虚和后悔,故而事后撒谎、矢口否认。无论是哪种原因,沾染了太多风尘的众人都在清澈的月夜里暴露出人性的寒霜,真相也在空色林最黯淡的角落迷失了方向。
此外,各个叙述层中故事亦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与勘察队的老薛、老孟、小许、小李同样处于第二层叙述的关长河的身世经历疑云密布,关长河究竟是谁?他平时生活在哪里?他为何突然人间蒸发,杳无音信?而第三层叙述中,关长河所讲的关于“皂娘”的故事亦充满叙述空白与延宕,具有无限的叙事张力。小说结尾处写道:“返程途中,只要遇见乌玛山区的人,不管他是放马的、护林的、运煤的,还是采山的、种地的、打草的,都会问空色林澡屋在哪儿。可是无一例外,他们都冲我们摇头。”[1]“我”更是一直没法放弃对空色林澡屋的寻找,“把春节的休假,放在了乌玛山区”,每到一处驿站,都要打听空色林澡屋和关长河。很多人都知道关长河,说他很难找到,但没人知道空色林澡屋,空色林澡屋只存在于关长河的追忆中。由此可以推断:在“套中套”的结构下,“他者”的回忆性言说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正如德国学者布鲁门伯格所说:“回忆中无纯粹事实。”[6]小说中提到的所有回忆故事均无法被真正完整地保留下来,每一个所谓的记忆都极有可能是被重构的。文中也借小李之口,道出读者心中的困惑与猜想——“小李见我惊愕不已,说其实关长河讲的故事,也未必真实,不然他为什么在说完空色林澡屋的故事后,不辞而别呢?因为他无法带我们抵达那里。小李还说,他也不大相信那天大家述说的委屈。真正的委屈,不是那么轻易道得出来的。而能说出的委屈,因个人处境和地位的不同,自然也做了种种修饰或伪装。”[1]事实上,迟子建在小说中不断地展现生活真相被有意或无意篡改和伪造的过程。结尾处,勘察队一行人明知关长河所说的12发子弹的使用和猎枪损毁的情况不实,却在有人调查使用猎枪的实际情况时将真相隐瞒。这一段看似与主线故事无关的“闲笔”实际上再次暗示了真与假的互相成就与转化,即人类对真相的隐瞒与替代的另一种原因——不再是出于自我的欲望与自身的利益,而是基于对事情全貌的无知,或出于善意用掩盖真相的方式来保护无辜、留存温情。甚至是因为人生中的种种落寞与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让人们宁愿选择相信谎言,相信一个美丽而易碎的梦。这种嵌套式的叙事技巧将时空秩序打破,引导读者关注事件发生本身,而不是拘泥于线性逻辑思考故事是否合理。在阅读的过程中,伴随着记忆与现实的碰撞,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越发模糊,属于读者自我内心的“乌托邦”世界逐渐清晰,由此产生了一种回荡且深刻的审美体验。
思考至此,当再次凝视这篇小说的题目《空色林澡屋》时,不禁联想到《心经》中著名的“色空之辩”,感受到弥漫在整篇小说中神秘的禅宗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迟子建并没有简单地对“真”与“假”做出价值判断,而是将所有的残忍与尖锐埋藏在“虚实相济、有无相生”的叙述中。就像真与假的相映成趣,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寒与暖、爱与痛、希冀与绝望也相依相偎。因为迟子建生活的背景是寒冷的,又因为她对人性有较高的期待,所以她的作品在苍凉之中始终带有丝丝缕缕的暖意,也就是评论家们长久以来关注的“温情叙述”。但迟子建并不允许这种“暖”绝对地遮蔽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荒寒,而是执着地记录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真正的心灵史、生活史,正如她在创作谈中所强调的:“有多少埋藏在心底的哭声,才会释放出什么样的笑声,就像有多黑的夜,就会有多动人的黎明。”[5]这种坚持正体现了迟子建一直以来写作的精神高度,她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创造了一个“现实的此岸与理想的彼岸”之间神性的艺术世界,观照着人世间最丰富的表象和最细微的心声,表达出对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与追问。在那个神性的艺术世界里,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如果命运是条孤独的河,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也许,迟子建的回答是:文学——她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