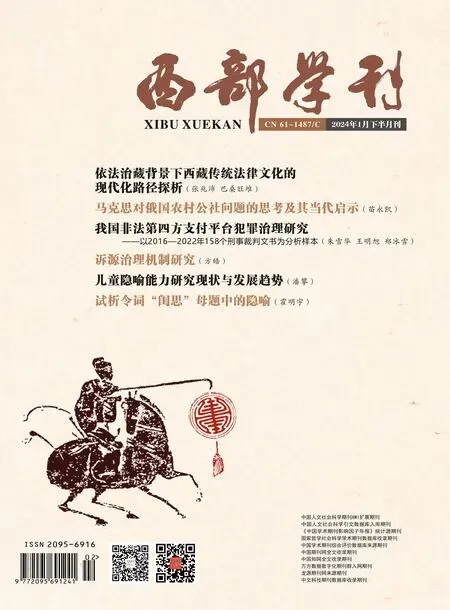试析令词“闺思”母题中的隐喻
霍明宇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通观历代的“闺思”主题诗词,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审美表达方式,一种可以看到清晰确指的人物关系,写实性的叙事,口语化的内心独白,抒情风格直露而热烈。另一种则呈现为不能指实的人物、事件,有所收敛、蒙眬模糊的情感意象。早期宋词中,那些以“闺思”为主题的小令大多以后者为审美追求,在那些未能展开的爱情线索、飘忽难寻的愁思意绪,甚至是不能确指的抒情视角中,透露着超出女性和爱情本身的更深层的隐喻和象征。
一、不宜指实的抒情模式
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唐代边塞诗,乃至元曲中的很多小令之作,都呈现着前者的抒情风格,在明确交代了抒情主客体的身份、关系及样貌特征等信息的同时,情感的表达方式也往往是直抒胸臆的。如《诗经·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1]诗歌从抒情主体女子的视角描述了丈夫,他威猛高大,执殳护卫大王,是邦国的英雄。当丈夫为国家出征,女子在家中的思念也与日俱增,以至无心旁骛。两汉乐府诗中的很多作品对人与事的交待也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确指性。如《古诗十九首》之《客从远方来》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2]诗歌用叙事的手法,描写思妇收到远方丈夫寄来的素缎后的欣喜,以及对爱情幸福的浮想,这一张素缎仿佛两人定情的信物,令女子赏玩不尽。征夫思妇的相思与哀愁是历代“闺思”主题中常见的题材,这类题材表达了在无休无止的边塞战争背景下,百姓生活受到的影响。在唐代这样的主题在诗歌中常常出现,如诗人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用凄婉的笔调描述了一位长安少妇对戍边辽阳的丈夫的思念,“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3]诗歌详细交待了女子的姓氏、居所,所思念之人的处境及两人的关系,并表达了征夫思妇天涯两隔的悲凉。元代小令中有很多作品以世俗口吻描绘抒情主体的内心活动,从而也将相思的内容写实。如元代徐再思的《折桂令·春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馀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4]从口语般的独白来看,这一位天真痴情的少女,正害了相思而魂不守舍、恍惚迷离。
与之不同的是,唐宋令词中的“闺思”之作并不呈现女子所思之人的样貌特征,相思的对象往往只是一个蒙眬的存在,对相思之人的人物关系、两人的背景经历也不做确切的交待。这里的女性是被符号化了的,被男性词人投射为某种象征性的存在,她们往往是美丽而孤独的。例如,秦观的《画堂春》一词:“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5]592这首词像一帧电影的剪辑,镜头选择的场景是暮春时节,在雨后的杏园里,满地落红铺径,一位女子独自登上画楼,她手捻花枝、凭阑而立、若有所思,最后又放花归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过程,成为宋代令词中闺思怀人的经典场景。其中女子所思何人,此人与女子的关系,他的身份样貌等都不作具体的交待,连那种哀愁也是隐约幽微、难以确指的,最后一句“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虽然将女子的愁绪稍稍点出,但若问这愁闷落寞是因何而起,却并不作具体的交待。有人说这是写离恨,是闺怨;有人说这是孤芳自赏之恨,既无人知,只有自爱自解而已;也有人联系“杏园憔悴”一语,认为这是男性词人不能杏园簪花、高中进士的不遇之恨,而托以女子相思的情事作为代言。读者能够产生如此之丰富的联想,正是由于这首小词的词义蒙眬,这与前面所举《诗经》及两汉乐府等诗词中那些大胆写实的爱的追求、被弃女子的悲歌、征夫思妇的故事有很大不同。
再如贺铸的《浣溪沙》词云:“闲把琵琶旧谱寻。四弦声怨却沈吟。燕飞人静画堂深。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一从灯夜到如今。”[5]689整首词勾勒了一位女子闲在闺中恹恹无心的样子,她时而手抱琵琶,弹出的都是沉吟哀怨的曲调;时而倚枕小睡,睡梦中全是对往事的追忆;在悄然无声的画堂里,在重重垂帘的遮蔽下,女子的春心无处诉说,孤寂无眠的长夜只有昏暗的灯烛相伴。小词以如此一番意境的描摹,引发人无限的遐思。女子为何如此百无聊赖,她的哀愁因何而起,又将如何托付?那无处诉说的“春心”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难忘的故事?因为没有明确的叙说和交待,反而令人不会陷入具体的情事之中,从而将小词中的情感与更广阔的人生维度联系到一起。人生总会面临这样的时刻,热闹繁华过后,在寂静的空间和时间之流中独自品味生命的孤独。
二、美人迟暮与贫士失职的同构关系
如所周知,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闺思”主题,特别是那些文人之作,作者多为男性,以“男子而作闺音”是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很多人将此现象视为男子借“闺思”的主题,表达人生事业的追逐与失落,所谓“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诗词中抒情主体对爱情的求之不得,对爱情消逝的哀怨,恰似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功业报复的求索。君臣、夫妇在古代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异质而同构的关系,“闺思”主题中女子对男子的思念,女子与男子地位上的卑与尊,对应于君臣之间的尊卑等级,女子对男子的衷情与爱慕,对应于男子对皇权的认同和遵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构性。
对此,前代词论家已经有所论述,他们结合词人的身世背景,对“闺思”小令中的女性和爱情所蕴含的隐喻作了丰富的阐发。清代张惠言在评论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词时说:“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6]温庭筠这首词描写一位女子晨起梳妆的过程,全词只写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不着一字点破,而正是这些描写引发了张惠言的联想,他感到了一种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的压抑。针对张惠言的这一番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史书上记载他(温庭筠)‘士行尘杂’,最喜欢那些放浪的、不正当的生活,那么他是不会有屈原那种忠爱之心的。可是你要看到,这个人很有才能,诗文都写得很好,但大家都认为他的品行太不检点了,所以他在仕途中很不得意,这是他深深藏在内心的寂寞和痛苦。也许他没有想到屈原或《离骚》,可是当他描写一个美女的孤独寂寞时,不知不觉地就把自己潜意识中那种怀才不遇的感情流露出来了。”[7]叶先生从一个士人所可能怀有的胸襟抱负,以及因为这种胸襟抱负而经历的求索历程去理解词作,得到很多超越表面文意的解读。叶先生还曾指出:“长词要铺叙,就要把当时的感情、故事都写得很真。可是令词不是这样,它用很短的篇幅写出很多的意思,这就容易使读者产生很多的感发和联想……文学作品的形式一定会影响到内容。”[8]令词以字面的男女相思之情之境起兴,引发读者关于生命的广阔联想,而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也就要超越表面的相思爱恋的意涵,生发出更深刻和多样的体悟。
稼轩词中有不少标为“代人赋”的作品,它们大多是体制短小的令词,其中就蕴含了丰富的意蕴,如《鹧鸪天》(代人赋)一词云:“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5]2425这首词上片泛写离恨。寒鸦的叫声令思妇彷徨忧虑,日暮的光景更增添了一抹悲愁,第一句以景色起兴,暗示着全词的基调。柳塘新绿透露着春光的温柔,融融绿意似乎代表着生机和希望,但抒情主人公看到它反而徒增忧伤,因为这不由得令她怀念起那远游不归的恋人。“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人间何事令人老?正是那绵绵无期的离恨。离恨恰如那柳塘的一抹新绿,即使不去刻意想起,但眼底心上无处不在,不经意间就被撩拨而起。“相思重上小红楼”,一个“重”字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登楼远眺的场景一并托出。然而这一次次的追思、期待,又是令人绝望的,因为“情知已被山遮断”,只是徒然倚阑怅望而已。作为一首“闺思”小令,词作将女子对情感的渴望和绝望写得缠绵悱恻又执着动人。而联系词人的生平经历,又与词中女子的情感经历有着很多相似。辛弃疾勇武有谋,年少时参与抗金起义,回归南宋后,屡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战守之策,是南宋朝廷不可多得的良将才人。他一生以恢复中原为愿,以建立功业为人生抱负,但却屡遭朝廷议和派的排挤,直至放废家居。这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追求而不得的怅惘,与词中女子对爱情的渴望和爱而不得的绝望何其相似!唐宋“闺思”小令中的这类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学中以“美人迟暮”代言“贫士失职”的隐喻模式一脉相承,是以女子对爱情的期望与失望,来代言男子对人生事业的求索与挫败。
三、存在的焦虑与生命的归处
在宋代“闺思”小令中,抒情主人公往往是一位美丽而忧伤的女子,她们的妆容、姿态乃至性情都带有明显的类型化和符号化特征。词中女子美丽的容颜、衷情的等待,代表着一个女子的才德,而这样的才德却无法得到爱人的陪伴和欣赏,只能孤寂空虚地划过时光,令人产生一种“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存在的焦虑。词中的她们黛眉长敛,娇羞而幽怨。“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晏殊《浣溪沙》)[5]113女子空有天仙般的美貌却无人欣赏、无人陪伴,回忆中的前事旧欢增加了今日的孤独,往事仅仅出现在梦中,一旦醒来只见帘幕低垂,一如往常的沉寂。词人特意描述女子有着“天仙模样好容仪”,转而又强调她的处境是“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此处情调的转折十分急促,突出了兀自袭来的孤独感。女子从梦中的往事旧情回到现实,只看到独自摇曳的烛火,就像自己一样形单影只。再放眼闺阁,多么希望画帘能被撩起,带来所思之人的消息,但画帘却只无情地低垂,不能体会女子心中的悲戚。这种无人问津,万物俱寂的空洞与孤独,最令人难以承受。这象征着美好的事物被弃置和忽视了,而词人塑造这样一位抒情主体,又似乎在表达着自身的某种情愫,或许词人也有着同样美好的才德与真醇的情义、远大的报负和信念,却也同样被辜负和无视,这其中投射出一种巨大的焦虑,是一种本自存在却被遗忘和弃置的焦虑,这是对自体存在感的扰动,同时又似乎隐喻着自身希望被关注和理解的渴望。这一份渴望通过词中美丽而孤寂的女性形象传达出来。
与此同时,对于抒情主体所牵挂思念的游子而言,温柔娇美的女子,在玲珑精致的居室画楼,日复一日痴情的等待、眺望,那一份相思永恒不变,给人以家的温存,当羁旅倦怠之时,那里便是回归的方向。在人们的感受中,稳定、恒常的爱能够带来安全感和可控感,它像是一种牢固的连接,令漂泊在外的游子总有一份心之所系,当顿挫流离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归处,从而在情绪上得到极大的安抚。因此,词中常常出现的那些执着“等待”所思之人的女性,往往带给游子心灵的慰藉。唐宋“闺思”小令中,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寻也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体现。她们义无反顾、执着而坚定的状貌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镜头。这份深情的画面为远游的男子传递出一种家的温暖,令其产生回归的愿望。正是因为想到有那样一份爱情的执守,才让漂泊的游子获得了内心中一处安定的存在。男性词人在“闺思”小令中不断地描述女子温暖的牵挂,正表达了词人对这样一份温馨牵挂的深情思念。“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玉楼春》)[5]169这首小词从字面来看是女子的述说,分别之后音信不通,不知道恋人所在何处,只有记忆中恋人离别时的样子,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消失在天际云边。从“代言”的视角来看,游子离开爱人所在的温柔之乡,羁旅行役,坎坷顿挫,人间冷暖尝遍,谁识天涯倦客?沧桑困厄中,唯有曾经的回忆慰籍着自己,而衷情的女子则是永恒的精神寄托。词中秋风秋夜里女子梦中的游历求索,也正像是男子寻找内心之寄托的辗转反侧。自古逢秋多寂寥,临近岁末,倦怠了世俗羁旅的游子或许也正期待着一次回归,而词中女子痴情的等待,或许正是词人心中的自我召唤。
这种等待和召唤在“闺思”小令中凝固为女子“望”的姿态,她们登楼倚阑、远望归舟:“落日水熔金,天淡暮烟凝碧。楼上谁家红袖,靠阑干无力。鸳鸯相对浴红衣,短棹弄长笛。惊起一双飞去,听波声拍拍。”(廖世美《好事近》)。[5]1188已经到了日暮时分,夜的碧色在天边弥漫,江面的舟船汀渚已经辨识不清了,但楼上的女子依然在倚阑眺望,不肯离去。不论游子身在何方,这种凝望都喻示着一种无时无刻的牵挂,促成恋人之间隐形而有力的连接。登楼凝望成为宋代令词中女子行为的类型化呈现,而“归帆”则是对等待的回应。“楼外江山展翠屏。沈沈虹影畔,彩舟横。一尊别酒为君倾。留不住,风色太无情。斜日半山明。画栏重倚处,独销凝。片帆回首在青冥。人不见,千里暮云平。”(蔡伸《小重山·吴松浮天阁送别》)[5]1322楼内别酒楼外江山,相恋的人就这样天各一方。从别后,盼相逢,女子画栏“重”倚处,相思与日俱增。虽然被重重山水阻隔,但有一份等待和召唤,也就有一份回应。女子登楼凝望之处,也正是男子“片帆回首”的方向,这份隐隐的连接藏在多少游子思妇的心中,成为他们颠沛困踬之时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