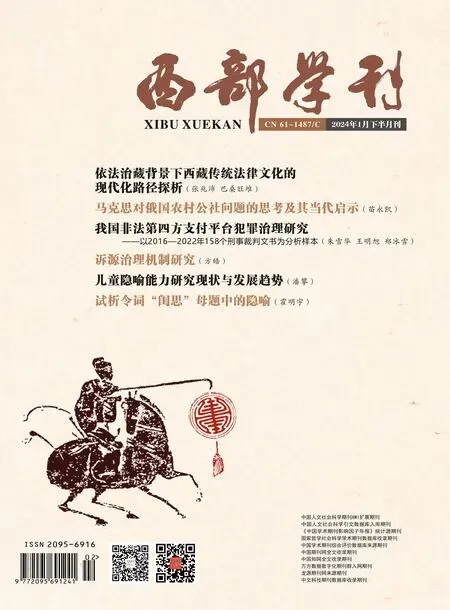现代社会空间的历史生成逻辑探析
何梦阳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苏州 215009)
随着当代产业资本的聚集,社会空间取得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生产形式,即物性化空间。物性化空间作为当代资本主义获得再增殖的起点,同时也是社会空间的历史时间构序的终点。在物性化空间的主导下,社会空间被一种同质化的重复性生产所取代,从而现代社会便在物性化空间的主导下表现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本文旨在分析现代社会空间的历史生成逻辑,来把握现代社会空间内含的物性化结构及其现实基础,并指出这一物性化空间在现代语境下的具体表现。
一、现代社会空间的起源
根据法国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定义,社会空间这一概念不同于传统经验科学与常识中的“空域”,也不是一种“没有内容的容器”[1]19,而是指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种关系性由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类活动所组织,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以一种非直观的社会存在形式参与社会的再生产。这种社会存在虽然不是指人们活动的物理场所,但却有其客观现实性。这样,社会空间便在人们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诸种精神活动所构成的总体性关系中形成,而这一总体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按照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便是生产关系。社会空间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发生重组、维持、解体或处于激烈的变革进程中,现代社会空间的起源也正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而展开。
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向资产阶级的生产与交换中心转移,社会空间的本质发生变化。随着市场化的交换逻辑对传统不动产权的冲击以及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逐步形成,传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向生产力的追逐和劳动分工过渡。在这过程中,空间具备了财产的形式,可以被出售,从而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2]。空间获得交换价值也就意味着空间进入了经济的社会形态,从而作为社会空间本质的社会关系便表现为现代劳动分工体系下的交换和财产关系。
在由交换和财产关系主导的现代社会关系影响下,社会空间的表征发生转变。按照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划分,社会空间具有三个层次。在本质层面,由社会关系组成,并在社会关系中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另外两个层次则分别为社会空间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和社会空间的物性创造物。其中,社会空间创造的物性结果便是社会关系在具体空间中的对象化表现。这一表征的具体形态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现代城市空间的生产便在这一表征的变迁中形成。通过分析社会空间的本质—表征结构,便可以追溯现代资本空间对社会空间总体的结构性影响。
二、资本空间化及其垄断
(一)资本空间化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资本转向空间生产的过渡时期,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传统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过剩,导致轻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趋向于饱和,根据相关数据统计,“1973年至1975年、1979年至1982年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3],经济危机的爆发昭示了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这一矛盾发展到顶点。轻工业市场的饱和限制了资本增殖的途径,从而促使资本不断向重工业生产投入,并深入到固定资本领域。随着对固定资本领域的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再生产的总对象便从工农产品的直接生产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转移,其中便包括固定资本、人造环境以及空间条件。空间的要素被提上资本投入的日程。
由于空间作为一种有限的刚需资源,具有相对牢靠和高利润率的特征,只要空间生产的利润率高于一般工业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资本便会不断地向空间生产投入。这便促使现代资本主义从第一阶段依靠工业产品的再生产转向第二阶段依靠空间自身的再生产。空间在资本占有的二次转向中被赋予了交换属性,通过货币的标价,而具有了价值形式。
空间的资本化以及资本的空间化推动当代城市空间基本格局的形成,在这之中,资本逻辑起主导作用。根据马克思对资本周转的分析,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影响利润形成的直接因素,当三个环节之间的周转速率提升,资本利润的形成速率也就越高,便意味着更多的利润额。因此,空间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影响资本周转速率的关键因素,生产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越近,资本周转的时间也就越短,生产资本便更易于转换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由于资本的逐利属性必然打破一切阻碍资本增殖的外部因素,对空间距离的缩短也成为资本逐利性的内在要求,这样,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产业部门之间的聚集也成为普遍的现象。产业之间的聚集促使经济中心形成,随着经济中心的产业优势不断吸引外来资本的投入,一个持续的产业汇集趋势便成为资本社会的主导。城市空间成为了不同产业大量聚集的结果。城市空间在产业聚集的趋势中得到再生产,新的空间不断被占有和集中化,而被赋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二)中心化空间对有限空间资源的逐步垄断
城市空间的集中化导致了“构成性中心”[4]的形成,城市空间的构成性中心是产业资本周转的必然结果。随着产业资本在产业部门的集中条件下向构成性中心涌流,大量配套构成性中心的二级生产消费部门便在构成性中心四周出现,其中包括商场、电影院、图书馆、学校以及医院等,从而构成性中心便转化为产业中心。由产业中心向四周扩散,离中心越远的地区所具备的二级生产消费部门便越缺乏,在其中,由于空间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作为产业中心的主要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可以就近享受到配套的空间资源,而次级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则在空间资源的竞争过程中处于摇摆的地位,普通的雇佣劳动者则长期处于产业中心的边缘,以二重化的身份参与产业中心的构成。这一二重化表现为劳动者一方面受产业中心的雇佣,通过出售劳动力的方式参与产业中心的构成,另一方面又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游离于产业中心之外,与产业中心相配套的社会资源分离。这样,城市空间的中心化便依据产业中心的产权配比,而形成一个由上到下的空间层级化结构,处于结构顶端的是生产资料占比大的大资本,凭借其对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垄断而对城市的中心空间形成较稳定的长期占有,结构的中层则由中小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而结构的底层则是大量的雇佣劳动者。随着雇佣劳动者在当代的生产中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提升,雇佣劳动者也逐渐能够享受到与产业中心相配套的社会资源,然而这样一种提升并不能改变雇佣劳动者因受产权隔离而游离于产业中心之外的事实,因此雇佣劳动者的二重化身份及其隐含的本质矛盾仍然存在。
产业资本对城市中心空间资源的垄断推生出了一个新的垄断结果,即阶层固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由于中小型资本的生产力及其对市场份额占比的不足,难以在与大资本的竞争过程中建立优势。大资本出于自身逐利的属性必然不断追求市场份额的占比,从而要求吞并中小型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和差距的扩大,大资本自身的垄断优势得到稳固,便形成阶层固化。虽然随着产业资本的增值,中小型资本的价值也获得了相应的提高,但是大资本与中小型资本之间的相对价值差却在不断扩大,这便导致中小型资本难以与大资本抗衡。产业资本的竞争扩大同时还表现为大资本建立的垄断优势使它可以逐渐摆脱同行业的竞争,从而降低获益的外部阻碍,而中小型资本却仍泥陷于相互竞争的障碍中,这便从侧面巩固了阶层固化。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03年,“日本0.9%的公司控制了86%的资本,德国109家大公司控制了64.7%的资本,英国三家最大公司控制了42.2%的资本。”[3]资本的高度集中是阶级固化的主要表现,其内在突出了社会财富被大量积聚于少数人手中,而表现为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转向,阶层固化也取得了空间的形式。当代社会空间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所占据,城市空间的形态受核心产业资本的引导,而形成有利于核心产业的空间结构。在这一变化中,产业资本通过向空间渗透,而将自身的形态赋予空间,从而扩大了产业资本的垄断面,并进而引导消费需求,使社会需求向有利于自身增殖的方向发展。正如现代城市空间的主导形态是一种经济的功能主义形态,在其中,城市被区分为互相缺乏关联的不同区块,居民的日常生活往往被隔离于发达的城市CBD区,这样的空间区隔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集中聚集,以此保证产业资本的垄断趋势。垄断面的扩大进一步保证了主导性产业的稳定优势,从而加深了当代社会的阶层固化。
应当说明的是,当代社会阶层固化的方式较过去时代有所不同。以19世纪大工业生产为首的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赚取劳动时间的差额,以此来建立资本原始积累,从而巩固资本的垄断地位。而随着当代资本空间化的发展,资本不再主要通过生产力来建立产业优势,而是通过改造社会空间的方式来创造和引导消费需求,以此占据和扩大市场。资本从过去侧重客体面的物质生产转向侧重主体面的需求的生产,通过改造主体的需求,来为资本融入扩大再生产提供动力。对主体需求的改造意味着当代资本垄断已渗透进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在当代的资本再生产中被解构和重组,而获得一种新的形式,即物性化的空间形式。这一物性化空间将遮蔽社会空间原有的社会关系,从而通过物性化的方式,来对社会关系实现重组,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这一过程予以说明。
三、社会空间本体的遮蔽和物性化空间的生成
物性化这一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们在将自己的劳动铭刻在物中时,物成为了人们的社会属性铭刻的对象,这一社会属性,也就是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5]。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在其中“人依赖于物,个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为物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6]。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社会化的生产被资本的自我增殖所主导,从而对物的生产便代替了人的生产,作为劳动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的物与物的关系,反过来成为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者,第二性的物与物的关系代替第一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上升为第一性的社会存在。从而劳动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便消失于由大量物品堆积而成的商品社会这一表象之下,物的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主导形式。
随着资本逻辑向社会空间渗透,资本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也同时渗透进空间领域。物性化空间的生成意味着现代人的生存空间被赋予了经济目的,标志着每一处城市空间都被资本所规定,被经济规律所谋划、布置,一切空间生产的领域被作为资本增殖的对象,通过控制空间的生产过程和空间产品的形态,来创造增殖的契机,人对于空间的使用价值的自然需求转变为对空间的交换价值的追逐。这同时也集中表现于休闲空间领域。传统的人类休闲是一种纯粹的、无目的的自然生息,然而随着资本的下渗,休闲空间被赋予了功能化和效率化等属性,并且被作为一种商品而加以定价。正如现代社会大量的娱乐产业被作为休闲空间来加以消费,在这些休闲空间中,时间被明码标价,人们在休闲中需要考虑身处休闲空间的成本,并要精确计量自身的休闲时间,以备重新投入工作,这便意味着人类的休闲活动被作为资本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加以计算。休闲空间的资本化意味着物化对人类生活更进一步地渗透,物性化空间对人的精确分工一方面将碎片化的分工赋予人,另一方面也将人分化,以此来满足碎片化的生产需求。人的每一部分都被精确地计量和预判,从而人不再根据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资本的需要,来作为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部件推动资本的增殖。
资本通过对人的空间需要进行重新编码,通过规制人的空间需要,重塑人的偏好等方式,来制造现代人对物性化空间的消费欲求,这便引发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在其中,人的现实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作为抽象货币积累的资本却全面实现了自我增殖,从而导致社会空间的主体由人转移为资本。在物性化空间占据社会空间的当下,物性化空间解构了社会空间的社会关系本质,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物性化空间所掩盖,作为商品形式的空间之间的交换关系代替生产者与总劳动的关系,而成为主导性社会关系。人们依据物性化空间的价值关系来建立普遍的社会活动,从而人类的社会结构便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一个环节,附属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当代社会空间及作为其表征的城市空间的内在历史生成逻辑分析,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空间在被赋予了商品属性而被纳入中心化的阶级秩序中时,也受到物性化空间的全面宰制。社会空间的本质,即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隐藏在物性化空间这一表象背后,并在物性化空间的经济秩序主导下被解构,社会空间的本质属性被下降为第二级的属性,而代之以物性化空间的主导形式。物性化空间的生成正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拜物教阶段,是现代社会空间在当代资本空间化发展下的最终形态。现代社会空间正是经由了“资本的初期渗透—垄断性的空间聚集—物性化空间生成”这三个阶段,而以“物性化空间”作为其最终的经济垄断结果,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增殖。
应该说,物性化空间对社会空间的主导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这一发展在具体的生活生产领域中不仅表现为社会的消费化转型以及诸多的物化形式,同时也引发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深刻冲突。其中为首的便是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由于物性化空间的产生,以“中心—边缘”逻辑为起点的物性化空间结构必然带来中心对边缘的吞噬效应。城市向乡村的扩张,对乡村土地的占据以及对乡村劳动力的吸纳,都是城市的物性化空间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大量的乡村土地空间以及劳动力空间被物性化结构所渗透,而作为低级的生产加工部门加以保留。由此便引发了一系列的连带问题,如人的城镇化问题、土地城镇化问题、乡村衰败问题,以及工业污染、消费主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在本质上,都是物性化空间的单向度开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于社会空间本身是一个具有丰富差异性的结构,在其中社会的各个生产环节由具有不同时空构序的部门所组成。然而在物性化空间的主导下,各个不同的部门之间被统一的经济秩序所衡量,这便意味着现代社会空间在物性化空间的主导下被纳入进一个同质化的空间结构之中。社会空间的时间性“仅仅被专门的测量仪器所记录,被钟表所记录,这些仪器就像时间一样被孤立化与功能专门化了”[1]140,从而差异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时间被重复的同质化空间所取代,社会空间的历史也在物性化空间的生成中达致其终点。然而,社会空间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时间序列也正是社会空间所本有的内在有机构成,这一有机构成在物性化空间的主导下,必然会以不同形式的剩余物形式出现。从而,社会空间正是在其历史的终结处开启了自身的历史时间序列。这样一种转型,将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来实行,并且必然要求一种总体化的社会运动。社会空间的历史时间构序将在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中与物性化空间发生重组,以此来推动社会空间的历史生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