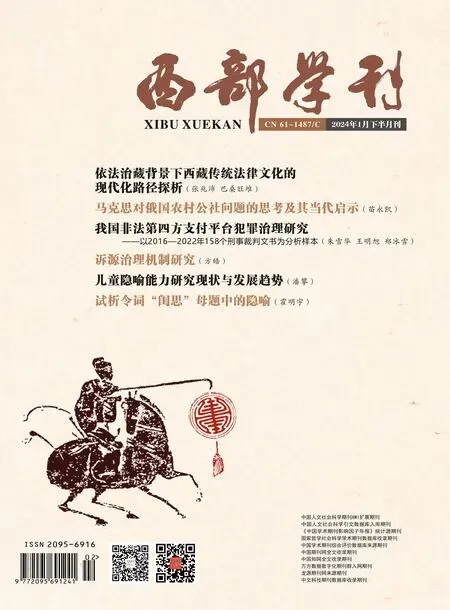东德难民和20世纪50年代东德政治现状研究
——基于布迪厄身体政治学中的象征性权力
王嘉丰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美、苏、英和法分区占领。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很快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原因分歧增大,最终使得德国统一的可能性破灭。1948年6月,原属于西方三国的占领区逐渐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行动在当时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但随着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失败,苏联也宣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立。从那以后,德国保持了40多年的分裂状态。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学习了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快速治愈了战争创伤。但是由于苏联战后一直对东德进行经济资源掠夺,如对于东德工厂的强制性拆迁和稀缺资源单向出口,1952年开展了过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使得其反而陷入灾难之中[1]125。
在政治、经济压力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东德就出现了大量难民外逃。这种情况在50年代中后期甚至60年代初期变得越来越严重。东德居民对于政府的失望甚至导致出现专门的德语词汇“Republikflucht”(fleeing the public),来代指东德人民对于政府失望想要“叛逃”的态度。在那段时期,东德难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当时的乌布利希(1)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1973):男,东德政治家,国务活动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950年7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三届一中全会上,乌布利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53年,此后改为第一书记。东德实际的当政者。政府及其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科里·罗斯(Corey Ross)看来,东德难民的逃离不仅改变了自身,也影响了东德政府和当时的冷战格局[2]。
本文通过运用布迪厄生成性结构主义来分析当时东德政治状况,并且通过象征性权力(2)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权力的象征关系,倾向于再生产并强化建构社会空间之结构的那些权力关系。象征性权力是一种神圣化或启示的权力,是一种神圣化的或已经存在知识物的权力。象征性权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权力,它强加并灌输各种分类系统,使人把支配结构看作自然而然的,从而接受它们。赋予了身体及其实践行为以独特的地位,将东德难民的“逃离”与统一社会党减弱的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一权力变化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情况,也导致了国际政治的动荡。
一、布迪厄理论中的“身体”及对东德难民的全新解读
在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元论后,身体就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心灵和精神总是比身体更为重要。在中世纪时,教士提倡人们禁欲,洗清身体的罪恶。而到了工业、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理性才是人们最为珍视的,因为只有它能带领人们领悟科学的真谛。与中世纪排斥贬低身体相比,到了现代社会,身体索性不存在了,变得无足轻重。在漫长的岁月里,身体一直被人低估、被人排斥甚至被“不存在”。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身体只是灵魂和大脑的附庸。
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被重新解读,发起了一场“身体”革命。身体成为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命题[3]。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学者主张用现象学的方法认识世界,认识自我,降低了心灵的功能,提高了身体的地位[3]。
布迪厄(3)布迪厄:通常译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男,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这部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990年,布尔迪厄80年代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内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则发表于1992年。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学术影响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上升的,进入90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在他的理论中,身体不只是精神或灵魂的附属物,恰恰相反,“肉体是比灵魂更神奇的概念。”[4]125对于布迪厄而言,身体成为了我们理解世界、建构和解构世界的关键性钥匙,作为权力斗争的外在现象,从身体中我们就可以窥见权力结构。身体,“行动着的身体”,可以是整个社会、整个历史的载体[4]43。而身体的实践感或者说世界的准身体化意图就是惯习,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关系。“社会世界将其实践活动的紧迫性通过实践感强加于我们,从而对不得不做、不得不说的事物进行控制。在惯习当中,社会世界呈现了完整的身体。”[4]43正是依赖于惯习,象征性权力得以在身体之中体现。
惯习及其代表的象征性权力是一种极为“神奇的魔法”,它不是有意识遵从,而是一种潜意识、无意识服从。对于国家而言,这一魔法具有极强的稳定作用,这种“非意识控制之下的运筹,超越于意识控制外对实践产生作用的原则”对于布迪厄而言才是支持场域(官僚制国家)运作的主要力量[5]。
这就是布迪厄极为新颖思考方式,他跳出了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构建了一门关于象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将过于僵硬的强调结构的社会物理主义和单纯强调主观认知的社会现象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生成结构主义”,从而将社会结构和内在的心智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一双向的纽带赋予身体惯习以极大意义,它既是世界的身体体现也是控制身体的象征性权力。布迪厄的理论和方法是对于“世界如何形成”(world-making)的一种全新的解读,在其概念和认知的基础上,再来审视战后东德难民的流动,就可以跳出原有的、对于难民认知的框架,得出全新的理解。
二、象征性权力的作用和20世纪50年代东德政策的失败
东德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在克林姆林宫批准社会统一党的战后经济计划开始的。战后,重建人们的生活是东德政府一大要事。从1952年起,乌布利希就开始了其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私有财产公有化以及在乡村进行集体化运动。但是很快困扰着苏联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也出现在了东德。东德政府学习了苏联的计划指导经济,政府的计划范围超过8 000多个工业、农业和服务型企业,最终造成了出台经济计划的不准确性;同时,由于民主德国的国内物价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以及生产成本的无法确定等一些列后果。大量原材料和人员的浪费、资本生产率低等因素都阻碍着东德经济的复苏,推行了新经济计划后的东德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以及通货膨胀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也并没有减轻东德的赔款压力,截至1953年,东德已经支付苏联超过40亿美元,但仍然亏欠苏联以及波兰27亿美元。东德每年还需支付苏联约2.29亿美元的占领费用[1]86。战争的赔款对于东德人们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相反,同样遭遇战火的西德却出现了经济奇迹。联邦德国人生活水平迅速上升,加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1950年联邦德国的人均GDP水平为494美元。到1960年,已经上升到1 309美元。1952—1958年是西德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年均增长率为7.6%,远高于美国(2.2%)、英国(3.2%)和法国(4%)[6]。
两相对比,东德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动摇了统一社会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执政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缺失在民众无意识的身体中展现无遗。身体会自然而然映照出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东德难民的“逃离”活动就是最好的显示。“逃离”这一行为本质上就意味着一种变化。变化永远是“惯习”的敌人,而“惯习”对于政府合法性而言意义非凡。
“故土难离”是一个社会最为基础的“惯习”。故土是一个具有特定边界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长期生活、居住的人民都会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内化外在结构,形成一些无意识的社会实践行为。以国家为例,长期生活在特定国家区域内的居民会熟悉国家内部的法律以及一些潜规则,会了解国家的语言、物价、场所分布以及各种机构的运行模式。虽然并没有刻意去思考,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国家里如鱼得水地活着,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找什么机构,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这些都是“惯习”实现的。
法律由于人们遵守才存在,机构由于人们求助方成立,惯习的存在可以维护权威的稳定,使得国家机器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无意识”意味着避免了“反抗”以及“削弱”。这种机构—身体的互动模式才是国家最健康的状态。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惯习是场域既得利益者极为需求的“神奇魔力”[5],其损失会对社会结构构成巨大颠覆。
据统计,从1951—1953年,有将近50万的居民从东德逃亡西德。到1961年,有超过260万的东德难民进入了西德,当中超过一半的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并且还有一半是25—45年的中年人。他们有专业工人、农民、义务兵,甚至还有许多社会团结党和青年联盟的成员[1]85。一个更为细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显示,从1954—1960年的难民中包括4 334名医生、15 536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738名教授、15 885名其他级别的教师和11 700名大学毕业生[7]。他们都是东德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离去不仅阻碍了统一社会党七年计划的完成,也是对“信任政府”这一传统惯例的反叛,是象征性权力的流失。对于任何场域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而言,参与者跳出“惯习”就意味着“察觉”。察觉到结构的不合理,察觉到利益的矛盾。这些本来深埋于民众心中的“服从”减弱后,会出现“质疑”和可能出现的与既得利益者的讨价还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这个超然机构得以生产某些具有合法性头衔和制度的权力,损失这些权力对于国家管理而言是灾难性的[4]144-145。为了应对这一灾难性局面,东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决策。
东德政府为了解决难民问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停留”“信任”的培养。合法性既然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因此最终解决之道需要扎根于新的信念培养以及心智结构,这显然是政府也难以快速做到的。但布迪厄的理论显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既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身体上有交叉,培养身体惯例成为了影响心智结构的可行方法。通过一些约束性政策使得居民形成特定的习惯,最终便能无意识内化成为合法化的信念。很多时候我们说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但是布迪厄的理论使得先留人再留心有了可能。
1952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东德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东德难民的“逃离问题”,一个新的委员会被建立。该委员会制定了解决难民问题的三条基本准则,一直适用到1961柏林墙建立之前。其中一条是为西德返回东德的公民提供合适的工作和住房,尤其是对于那些专家学者、有技能的工人。通过吸引高技术人才返回居住,东德政府希望通过他们“返回”的行动重新确立政府合法性。除此之外,东德政府在1957年发现,大量东德难民是通过合法访问西德的时候逃离的,统一社会党停止了签证的自由发放,同时在50年代末制定了针对难民的、更为严格的政策,包括阻断难民家属教育和求职的机会、斯塔西机构(东德国家安全部)对于可能的逃离者进行监督控制,并且在地方设置更多委员会遏制难民逃离现象[2]。在1957年11月甚至制定法律剥夺非法移民在东德的财产。这些意在阻止外逃的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减少“逃离”行为来确保更多东德居民一起维护固有的惯例,留在东德,支持新的东德政权。
构建身体“惯例”是维持结构稳定的一种方法,但是想要真正达到内化的效果,心智结构还是需要社会结构作为基础。不符合社会结构的惯例、信念无法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服从。东德政府虽然采取了以上一系列的行动,最终结果却是“1959年的问题与1955年的问题差不多”[2]。
东德政府的问题在于乌布利希政府片面地将东德难民逃离的原因归结为“Abwerbung”(wooing-away),就是资本主义商人或者西德相关部门有组织的策反活动。1953年后这一单词就被广泛用于东德社会,不管是报纸还是内部报道,都会提到Abwerbung,并且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经常是通过信件或者飞行器诱发的,有时候是由于与西方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当然更广泛的原因是因为西德的媒体。Abwerbung到1953年底已经被归纳为官方话语,不仅在官方宣传中出现,在内部文件也是如此提及[2]。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很容易被归纳为根本原因,但事实上通过对于“个人”层面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在1966年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1961年前迁移的东德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1979年,即使是联邦政府全德事务部的结论都是“离开的人相对较少因为‘尖锐的政治危险’,反而被更高的生活水准所吸引。”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东德居民而言,生存才是最要紧的事情,他们并不关心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是更多地关心经济状况如何。
东德政府则将这一切归为意识形态因素,随之辅以了大规模的思想斗争。显然,单纯地通过控制身体、改变思维是无法使“惯例“化作潜意识的,象征性权力也就无法发挥出其超越于意识控制外的强大力量。以高层与基层官员之间的政治观点冲突为例。官僚体系内部成员作为政策的第一批接收人,理应是首先形成身体惯习的那一批人。但实际上在东德基层官员的阳奉阴违则屡见不鲜。基层官员往往更同情渴望逃离的东德人,为其离开而举行欢送会,并且认为对此一味地国家干预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活动只会激化难民问题[2]。但在高层看来,难民问题不时出现是因为基层官员没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责怪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瞎子”(politically blind)。
象征性权对于合法性而言十分重要,东德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国家稳定而言并无错处,只是忽视了与其对应的社会结构的要求,导致象征性权力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使东德居民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加到身上的政治压力。
三、结束语
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学的讨论一般都会集中在有意识的政治活动之上,如竞选、协商、投票等。但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环,其任何活动都带有一定权力的影子。
就像本文对于东德难民的分析。该群体本身并没有在国内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足够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其出现时间的有限,另一方面也很难以其作为主体进行政治分析。东德难民的逃离活动与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4)Me too(我也是)运动:是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2017年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借此唤起社会关注。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WGA(美国编剧工会)游行显然并不属于一个性质。那些游行的团体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及影响力,以期获得让他们满意的结果或者利益补偿。但那些逃离东柏林的人群显然并不是将“逃离”当作了“手段”,意图改变政府行为以期获得更多的利益。“主观意愿”的有无是两者最大的区别,但是其无主观意愿的行为难道没有带来权力上的更迭吗?那也并不是的。
象征性权力更多的体现是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力量。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大到对国家的仪式、法规和各种政策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也可以小到对于我们平时一些无意识的习惯有新的认识。很多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也是我们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象征性权力是维护一个国家、民族稳定必须的因素,不容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