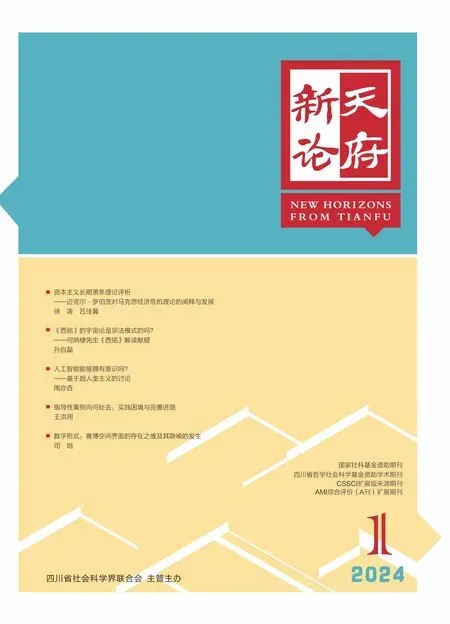从官僚范式到干部范式:重新界定中国的治理主体
朱怀洋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代领导人都将干部作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需要干部的奋发进取来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习近平也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1页,第412页。。可以说,干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所在。
而中国共产党也极其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拥有丰富的基层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一个基本条件;德才兼备则是中国共产党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1页,第412页。。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这些要求,显然与我们社会科学理论中广泛引用的韦伯式官僚概念迥然不同。
然而,中共干部的鲜明特征一直以来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重视。在理论研究上,我们往往将中共干部与官僚混为一谈,而忽视了中共干部与官僚之间的显著差异。其原因何在?一是学术界受到西方制度研究范式的影响,将焦点放到了政府组织体制、政府间关系和政府行为等方面,而忽视了对于干部这一关键政治主体的研究;二是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将韦伯式官僚制作为政府组织现代化的唯一价值目标,并以此为尺度来理解和评价中国政府及官员;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采取理性选择主义的预设,将中国官员或者党的干部假定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虽然这些理论研究为理解中国政府及官员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视角,但它们主要源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实践,对于真正理解中国官员仍然存在着许多偏见和不足。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干部不同于官僚的特性,并主张摒弃以往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官员上的官僚制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干部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政治传统来重新理解中国的干部群体。而这些研究启示我们需要深入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和历史文化,置身于中国政治的本土场景,从干部这一群体本身出发,去重新认识中国的治理主体和能动者。
一、理性化官僚范式及对其的反思与超越
在考察政治能动者的研究中,政府组织机构中的官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讨论政府组织中的官员时,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被视为国家组织体系理性化的标志和一个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而韦伯式官僚也成为社会科学理解政府官员的经典理论和模型。
韦伯认为,在一种充满理性规则和规范化的组织体系中,身处其中的官员首先需要的是将官职作为一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担任官职意味着官员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义务,即忠于该职务所规定的目标和行为规章。韦伯认为,即便是具有意识形态光环的主教、祭司和传教士等教会人士,在成为官僚制中的官员之后,他们也会变成服务于功能性目标的官僚,而这种目标是非人格化的,不再意味着对某个人的忠诚。(5)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第226页。在官僚制的原则下,官员取得的任职资格来自官员的教育文凭和专业训练,同时又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严格遵守法令和专业是官员获取官职和行政权威的基础。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组织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在于它的技术优势和理性化程度,而一个精确、迅速、明晰的,有着连续性、统一性以及严格的隶属关系,并可以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而严谨独断的官僚制组织,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官僚。(6)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7页。他们接受了专业训练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有关执行行政事务的丰富知识,他们能够按照纯客观的要求去考虑和贯彻行政职能专业化的原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按照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职责,而“无需看人下菜”。韦伯认为,这种可计算的规则就要求官员的“非人化”,即消除在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成为不带感情的、严格而客观的专家。
总之,在韦伯的概念里,官僚是在官僚制组织里忠诚地履行职责而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人”。韦伯认为,官僚制促进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理性主义也成为官僚们思考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支配结构的推动下,官僚们基本上就是属于“理性地就事论事”的职业专家。(7)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第226页。而这样的一种官员类型,也被称为“韦伯式官僚”,它是我们辨别和理解官僚品质及其行动逻辑的理想形态。
然而,韦伯的这一概念在解释现代社会和构建良好政治秩序上也存在局限。在韦伯式官僚制那里,官僚最明显的特征是理性的技术专业化和训练,他们处理事务的终极价值就是理性的行政管理,其性质类似于在工厂中的机器式劳动。而面对现代国家的这种官僚化趋势,韦伯晚年也十分忧虑,“一部无生命的机器就是一种凝固了的精神”(8)马克斯·韦伯著,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和超越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概念。
一方面,韦伯晚年就对这种官僚制和官僚制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危险——官员统治社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引入了政治家的角色,用以约束和控制不断膨胀的国家官僚系统。这些政治家以政治为职业,奉行信念伦理,领导着国家为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而奋斗。(9)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126页。韦伯进一步指出,来自政党官僚组织的政治家,不仅掌握了现代行政技术的知识,而且他的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可以使他成为引领国家和政府的领袖。(10)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阎步克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6—37页。西方国家的政府组织基本上遵循了韦伯的这一套解决方案,即政府官员分为通过选举产生或政治任命的政治家与政务官,和具备专业知识、负责专业化执行政策法律且终身领薪的事务官。然而,这似乎也并没有解决官僚体制缺乏活力、政府官员能动性不足的问题。
“谁在外面?”病房里的人听见门口的动静出声询问。雷染君回过神,抹干眼泪站起来,看见姜祈缓缓下了床,艰难地挪动到门边。雷染君推开门,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他病服袖口之外的缠着纱布的双腕上。她紧紧抿住嘴唇,双手局促不安地握在一起。头发束成的马尾也像失去了往常的活力,毫无生气地耷拉着。
另一方面,“韦伯式官僚”的概念首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将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引入政治机构的官员之中,摒弃了韦伯所设想的循令而动的非人格化官僚假定,认为官僚化的官员不仅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且他们追求复杂而多样的个人目标,包括权力、收入、声望、安全、服务公共利益的渴望等关乎个人利益的事物。(11)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第72—73页。
在韦伯的官僚制中,官员的任职和晋升以功绩为标准,同时法定程序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这些保证了官僚制的非人格化特征,使得官僚们可以不受到社会等级、财富、裙带关系和其他个人特点的影响。然而,在唐斯看来,官员对于行政事务做出带有个人情绪和喜好的回应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官员受到个人效用最大化动机的驱动,这不是规则所能预设的。(12)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第72—73页。
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则进一步发展了唐斯的理论,他将经济学里有关人的假设行为完全置入政治生活之中,并把官僚等级组织体系中的官员称为“政治人”。在塔洛克的概念里,“政治人”是指那些有头脑和抱负的官员,他们以职位晋升和攫取权力为政治目标,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理性来实现自利的目标。(13)戈登·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37页。塔洛克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着自利目的和抱负的人,官员更是如此;他们只有当完成任务可以达到自身目的时,才会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并且会根据情况改变任务的执行以符合自己的目标。总之,官员不是只会按照指令做事的机器人,而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人,这些也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官僚体制政治的重要基础。
而代表性官僚理论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点。它认为,官员自身的特点,包括性别、族群、地理区位和支持的特定理念等方面,会影响官员所关心的利益和目标。性别、族群和理念的差异会带来不同“身份”的认同,这些都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官员加入政府机构,是为了提升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地位,或是拥护他们所持有的理念与政策。(14)有关阐述代表性官僚理论的文献,可参考J. D. Kingsley,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Yellow Springs:Antioch Press,1944;S. Krislov,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74;F. C. Mosher,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J. G. March,J. P. 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oronto:Free Press,1989;K. J. Meier,“Latinos and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3,No.3,1993.与韦伯所强调的奉行政治中立的官僚制不同的是,代表性官僚制部分地赋予了官僚一种政治上和价值上的责任。正如美国学者莫舍(Mosher)所指出的,每个官员应当尽力去实现他所应当代表的利益,而不管他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人民的某个部分。(15)F. C. Mosher,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12.尽管这种政治义务只是覆盖某种特定群体,但它确实挑战了韦伯式官僚制的原则。在韦伯式官僚那里,官僚是非人格化的职业专家,他们严格依照法律从事,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来自哪个族群,肤色如何,支持哪个党派,都是同质化的行政人员,负责一视同仁地处理公务;而代表性官僚则将官僚的社会背景作为官僚行为的基础条件,官僚具备主动代表特定群体的能动性,能够在行政决策和执行中积极回应自身所代表群体的利益,从而减少了韦伯式理性官僚制的行政冷漠。
此外,另一种研究官僚行为的重要派别则是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它强调,从事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成员具有某种利他的动机,这种动机驱使官员做出对公共利益有贡献的行为;这是一种官员的内在性动机,意味着官员认可公共服务理念、追求公共价值、保持着向社会奉献的渴望,而这些与组织为实现其目标和利益所提供的激励无关。(16)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研究,可参考E. B. Staats,“Public Servi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8,No.2,1988;J. L. Perry,L. R. Wise,“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0,No.3,1990;J. L. Perry,“Bringing Society in:Toward a Theory of Public-Service Motivation,”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10,No.2,2000;P. G. Scott,S. K. Pandey,“Red Tape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Managers in Stat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ies,”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Vol.25,No.2,2005;J. L. Perry,A. Hondeghem,Motiv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The Call of Public Serv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可以说,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以强烈的权力追逐、丰厚的金钱报酬和明确的绩效奖惩为出发点的官员行为,尽管在政府机构之中无法避免,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相信,这样的情形显然在公共部门不是普遍存在的。
可以说,自从韦伯式官僚制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态之后,韦伯式官僚也成为人们期望政府成员应当达到的理想形态。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代表性官僚理论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则从政治机构的现实和责任伦理层面,对官僚的动机及行为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官僚行为的不同侧面。对于整个官僚群体而言,每一种观点都或多或少观察到了官僚群体中某些子群体的特色表现。无疑,这些考察官僚的不同角度突破了人们看待政府组织囿于韦伯式经典模型的束缚;官僚体制下的官员,尽管受限于法律规则的程序化和等级体系的命令,但人们仍然无法将之完全等同于那些只关乎行政机器有效运转的“齿轮”。官员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理性、对于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社会群体所葆有的同情和献身公共事业的政治责任,都意味着官员的世界观和行为与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而这不是官僚制本身所能决定的。
不过,这些研究虽然肯定和突出了官员的个体动机和责任,但其理论基点主要建立在两个预设之上,即严格遵守法令的行政责任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尽管这几种理论模式在这两个预设之间选择了不同程度的立意和假设,然而“就事论事”的韦伯式官僚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官僚仍然是它们研究政府官员的两大主要模型。
二、官僚理论引入中国及其不适应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改革,韦伯式的官僚制概念才开始在中国学者中流行起来。在有关中国政府组织体系的研究中,韦伯式的官僚制基本上成为学者们认知、批判和理解中国政府体系及成员的参照系,因而韦伯式官僚也是学者们考察和研究中国官员的重要概念。
有些学者认为,官僚制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现代化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基础;而中国政府体系在官僚制化程度上还远远不足,因此中国制度革新的重要方向便是建立一套符合理性科层制的现代官僚制。(17)艾子校:《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行政论坛》2005年第2期;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冷涛、周雅颂:《中国官僚制何去何从?——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在他们看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政府体制已经从一个革命性集团转型到了现代官僚制,当代中国政府已经是一个建立在理性官僚制基础之上的现代政府。(18)竺乾威:《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陈剩勇:《官僚制、政府自利性与权力制衡——对行政权与立法权配置失衡问题的思考》,《学术界》2014年第4期。美国学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职务名称表制度是控制和管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的主要工具,并随着1984年开始推行的“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权限改革,扩大了下级机构的自主权限,也为建立公务员制度提供了基础和保障。(19)J. P. Burns,“China′s Nomenklatura System,” Problems of Communism,Vol.36,1987;J. P. Burns,“Civil Service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Vol.18,1987.
而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正式颁布与实施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正式建立,更是体现出中国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一些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发现中国政府更多地开始建立一种以绩效和激励为导向的政府官员管理模式,如目标管理责任制、晋升锦标赛、政治淘汰赛等(2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第7期;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李国强:《地方政府维稳绩效的前期考核——以T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体系已经明显表现出一种以明确的规则和功绩制原则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精神,而这种运作机制也很明显地符合科层制组织的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革命干部的官僚阶层。徐湘林认为,中国新时期带来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原先注重意识形态和革命信念的干部逐渐被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所取代。(21)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美国学者李鸿永也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群体在改革新时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家干部,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为技术官僚;从1980年代开始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大量知识分子干部受到重用,一个新的以专业技能为特征的技术官僚阶层崛起。(22)H. Y.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然而,许多学者开始发现,在采用“官僚制”概念分析中国政府体系和官员时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官僚制作为一个现代政府的价值标准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更多来自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现实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官员正按照一种迥异于官僚制的政治逻辑治理着国家,并带领人民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于是,一些学者借鉴欧美国家对于官僚制的批评,开始反思韦伯式官僚制作为衡量现代国家政府体系唯一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并从超越官僚制的角度,探讨中国行政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比如,理性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理念的结合,将新治理手段引入官僚制之中,或者主张公共行政要增加责任、民主、公平、参与和透明等价值。(23)靳永翥:《西方官僚制发展历程与后官僚制改革——兼议当代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与创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0期;陈国富:《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10期;祝灵君:《从“打破”官僚制到超越官僚制——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另一种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还有一些学者从韦伯式官僚制与中国政治体系的现实比照中,总结和阐述了中国官僚组织某些异于理性官僚制的鲜明特点。比如,荣敬本等人提出,中国传统的官僚动员体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环境下演变成一种“压力型体制”;(24)《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渠敬东认为,中国官僚组织表现出一种以项目的方式来促使整个国家社会体制联动的“项目制”特征;(25)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张璋则认为,中国政府组织在特有的治理传统和政治体制下形成的是一种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复合官僚制”。(26)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年第4期。
一些学者发现,单纯依靠韦伯式的官僚体制无法有效解决中国推进现代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中国政府组织除了官僚制之外,还结合了其他要素和治理手段,尤其是政治动员手段;而正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杂糅,才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官僚体制的缺陷。比如,冯仕政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传统的影响下中国构建了一种革命教化政体,而革命教化政体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催生出一种政治官僚制的政府组织特征,而不是韦伯式的理性官僚制;(27)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周雪光也认为,中国的政府组织不能简单使用韦伯的官僚制概念来描述,而是由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统一起来的一种政府组织形态;(28)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徐湘林则通过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和进程发现,中国的治理体系呈现出的是科层官僚制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体制共存与互动的局面。(29)徐湘林:《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中国地方改革浪潮的出现,中国地方官员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在推动地方创新上的积极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官员具有强烈的积极进取的政治热情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使命感、责任感,而这些特征与韦伯式官僚那种就事论事的风格完全不同。“政治企业家”和地方“战略性群体”则成为其中描述中国地方官员较为流行的两个概念。政治企业家,是指在政治领域中,具有私营企业家般的改革创新精神,能够改变政治方向和政治流程的个人;(30)M. Schneider,P. Teske,“Toward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Entrepreneur:Evidence from Local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6,No.3,1992.他们拥有权力,并且能够洞察那些潜藏的政治机会,同时他们又是理性的自利动机者,他们愿意抓住各种机会来改变当前的制度规范,是能够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的企业家。(31)杨瑞龙、邢华:《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普遍拥有一种政治企业家精神,他们有着积极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动机和作为;正是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特征,许多学者提出了诸如“地方政府企业”(32)A. G. 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2,1996.、“地方公司”(33)J. C. Oi,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赢利型与保护型经纪人”(34)纪程:《集体经济支撑、“保护型经纪”主导下的村庄治理——山东省临沂市刘团村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彭善民、陈相云:《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地方政府自主性”(35)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概念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和舒耕德(Gunter Schubert)则将中国的县乡领导干部称为“战略性群体”,他们具有地方精英的自我认知,并倾向于以目标导向的合作来实践中央政府的意志,他们相对于上级和社会具有较高的政治自主性;县乡领导干部在其辖区内形成一个战略性群体,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相对自主权和政治权力以及凭借政绩和官位晋升来谋求升迁而在地方政策和发展战略上通力合作。(36)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透视中国地方政府战略能动性的一种新方法》,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杨雪冬主编:《“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7—64页。这些研究多数采取了一种将中国地方官员视为理性经济人的预设,认为官员的自主性源于官员个人自利的动机,中国分权制度改革创造了他们自我逐利的空间,或者说一套上下贯通的功绩制和晋升等级机制给官员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比如,周黎安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官场的政治企业家和市场的私营企业家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治企业家的产生则来自官场的仕途竞争。(37)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
上述研究为我们考察和理解当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性质和特征提供了诸多具有创见的观点,也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官僚体制那些与众不同而令人困惑的种种面貌。这些研究总体来看仍然是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为尺度来分析中国的官僚制度,尽管批判了官僚制的缺陷或深刻发掘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特性,但他们基本上是从官僚制这一典型组织模型来讨论中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和表现,而对于中国官僚组织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运作逻辑缺乏足够深入的思考。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官员的角色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模糊的位置,他们被当作组织和制度的附属物而很少被提及;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官员在隐而不彰的研究预设中,他们要么被视作理性官僚制下的韦伯式官僚,要么被当作符合理性经济人行为的自利官僚。而对于中国官员所表现出来的既具有政治热情又具备行政技术角色的特性,则缺乏合理而深入的解释。正如周雪光所指出的,这种被称作“又红又专”的矛盾,尽管在中共观念里将其视为党的官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不断被强调,但是在实际中这种要求在官员个体层次上如何体现出来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影响,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重视,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38)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因此,尽管政府官员被假定为理性化的科层官僚或者追求自我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是有些学者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只是用以官僚制组织为基础的理性官僚视角来对待中国的官员群体是有不足的,与中国的现实政治也不相适应。中国的官员不仅是国家公务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正是这种党的干部的身份,使得干部具备不同于官僚的品质和特征。那么,接下来本文将着重考察那些从干部视角出发来探讨和理解中国政治的研究。
三、走向干部范式:确立干部的类型学地位
正是由于官僚范式研究在解释和理解中国政府及成员上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中国本土历史传统和政治实践出发来理解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干部是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能动者;他们的品质、特征和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成败具有重要的影响。
部分学者在制度层面注意到中国干部体制异于官僚制组织的特征,并将中国干部组织视为一种区别于官僚体制的国家体制或政府组织类型。王海峰从中国革命、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的内在权力运行逻辑出发,发现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关键,干部支撑和维系着中国共产党、军队及其政权的权力运行;干部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执行和运作架构起了中国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并由此形成一套政党、军队和政权的国家体系,他称之为“干部国家”体制。(39)王海峰:《干部国家——一种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16页。瑞典学者博·罗斯坦(Bo Rothstein)则基于“中国发展悖论”(40)所谓“中国发展悖论”,主要是指中国政府较低的政府治理质量得分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认为政府行政能力和机构质量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他们通常以韦伯式的理性官僚制行政组织作为政府行政能力和质量的衡量指标。的讨论,详细地考察了中国政府组织与韦伯式公共行政组织的差别,认为:中国政府组织是一种“干部制组织”,而不是韦伯式的理性官僚制;这种干部制组织既不是基于正式或精确规则的指导,也不是基于法治价值的指引或经济激励的诱导,其运作基础是干部对组织具体政策学说的强烈意识形态承诺;干部具备与韦伯官僚同样要求的专业水平、教育和技能,而不同之处在于干部对于技能的运用,他们能够根据现实具体情境灵活运用资源来实现组织政策目标。(41)B. Rothstein,“The Chinese Paradox of High Growth and Low Quality of Government:The Cadre Organization Meets Max Weber,” Governance,Vol.28,No.4,2015.
然而,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一个显著的局限,即一些以中国干部为主题的研究尽管突出了中国干部及组织的特性,但还是从制度和组织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干部的特殊之处,并没有将干部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主体来看待。而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中国干部自身的历史生成过程,中国干部这些特质的形成,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组织制度变革时才开始的,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就开始具备一种兼具技术官僚和革命政治家的风格;二是将目光放置在干部组织制度上,没有深入分析干部主体本身的特征和行动逻辑,也就无法进一步深入讨论干部与官僚不同的原因何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干部在共产党政治中所形成的组织制度与韦伯式官僚制之间不只是政策执行和运用的差别,这种差别只是一种制度性或技术性的区别,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干部这个主体本身与官僚的不一致。可以说,在科层制技术或行政技术方面,干部组织与官僚制组织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异质性,干部组织的官僚制化水平比韦伯式官僚制的科层化水平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因如此,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干部本身与韦伯式官僚的区别。他们从中国干部视角入手,试图重新构建起一种理解中国政治及政府成员的新范式和新路径——干部范式。
第一,中国干部在概念和范围上就与欧美国家的文官之间存在差异。“干部”一词被认为最初是由日本译介过来的外来词,意指枝干、团队或公司的首脑以及军队中的中下层士官(42)日本大辞典刊行会编:《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五卷),小学馆,1973年,第427页。。后来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早期民国时期一些政治人物的使用和传播,“干部”开始逐渐被用来指政党、政府或社团的主干机构,以及指称军队、政党和社团中的骨干人员。(43)李美啸:《观念与制度:理解干部概念的两个维度》,《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党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干部”一词,“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44)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第13页。在这里,“干部”用来指称中国共产党内的骨干分子。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在革命年代,干部这个概念比革命领导者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干部是献身革命理想和革命目标的人,他们并不是一项专门的职业或专业。(45)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王海峰则明确指出,从中国干部群体的历史发展和变迁历程来看,中国干部所涵盖的范围和职责与欧美国家的官僚、文官或政务官等具有明显的区别:干部是作为党组织的骨干分子;干部献身于党的事业,是人民的公仆,被赋予一种强烈的为民服务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使命感;干部既是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又承担着党和国家事务的行政管理职能,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行政技术人员。(46)王海峰:《干部国家——一种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2页。
第二,中国干部与韦伯式官僚具有不一样的表现和特质。一些学者发现,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就展现出一种特殊的品质和行动逻辑。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就详细地分析了中共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纵向的干部双重领导体制以及干部的“下乡”运动和整风运动对于中共干部所造成的影响。(47)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这些不仅要求党的干部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能够领导动员群众,还要求掌握阅读、写作、算账、战术等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研究延安时期中共锻造干部的努力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旨在协调解决干部的“自觉行动”与党组织要求的完美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48)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室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69页。费正清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在干部管理上的这一特点,“这两项政策(精兵简政和下乡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49)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92页。。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和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同样发现,1949年以前的中共干部,“要求对群众的直接领导和联系,高度的政治觉悟,以及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灵活运用中央指示的能力”(50)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并开始推进国家建设之后,党的干部仍然保留了这种革命传统,并把它带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中。美国社会学者舒尔曼(Schurmann)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中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不仅是组织中担任正式领导职务的人,也是战斗领袖;干部既要当专家,又要当政治上党性合格的“红人”。(51)F.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65,p.163..另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相比于前苏联的干部,在领导风格上具有很大差别(52)F.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65,p.163..,中国干部多了一层强调政治道德和伦理的内涵。一些学者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力精英和阶级结构演变,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革命家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融合,中国产生了一批专业技能与政治忠诚性相结合的新政治精英,他们共享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并具备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53)X. W. Zang,“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Recruitment in Post-Mao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Vol.26,No.1,1998;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何大明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展现出了当代中国干部的独特性质。俞可平在研究中国干部的培训体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庞大而持久的干部教育培训工程,旨在提升党的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而不只是简单的行政技能。(54)俞可平:《中共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包涵川在关于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中也发现,中国党政干部所被赋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面对重大风险危机时展现出模范行动和表率行为的特质。(55)包涵川:《“模范式行动”:理解中国应对重大灾害的分析视角》,《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5期。美国学者Orion Lewis等在研究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人格中也认为,中国地方领导人中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公民导向型人格(56)在该研究中,公民导向型人格指的是一种更加重视社会支持、考虑地方民众实际需求而进行政策创新的人格特质。,而非权威主义人格;同时,这种公民导向型人格使得地方官员即便是面临强大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压力,也能够持续进行政策创新的努力。(57)O. Lewis,J. C. Teets,R. Hasmath,“Exploring Political Personalities:The Micro-Foundation of Local Policy Innovation in China,” Governance,Vol.35,No.1,2022.姚中秋则认为,中国干部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与官僚不一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行使的是一种领导权的权力形式,而这种领导权由中国干部掌握和行使,具体可表现为制定战略决策、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道德修养并教化群众、发现和培育干部、动员与组织、自由创制、整合社会与国家权力等。(58)姚中秋:《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政治学研究》2022第1期。这些研究从干部培训、干部行为、干部的政治人格及权力行使方式等不同侧面,显现出了中国干部与韦伯式官僚不一样的特征。
第三,中国干部是一种区别于韦伯式官僚的官员类型。鉴于中国干部的特性和典型性,也有学者开始将中国干部视为区别于官僚的能动者类型而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姚中秋在《干部作为政治能动者的一种类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通过详细考察中国式干部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干部所具有的与韦伯式官僚不一样的品质和行动逻辑。在他看来,干部作为党的双重先进分子,超越了“理性经济人”模型;他们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性治理者,统合了教化者、政治家和官僚三种角色;干部以示范和教化的方式来行使领导权;干部的行动具有任务导向,努力在组织性和创新性之间保持平衡。(59)姚中秋:《干部作为政治能动者的一种类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姚中秋认为,中国干部的根本属性在于其先进性,这体现在知识、政治和道德等各方面先进于群众和普通党员的品质,而这种先进性则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质和精神,这样的一种历史脉络形成了以领导性治理者为特征的政治传统和国家治理逻辑。(60)姚中秋:《领导性治理者:对士大夫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阎步克和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同样也指出中国古代士大夫在知识和道德层面上的引领和先锋队的角色作用(61)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现实。这些对于中国干部品质和行动逻辑的深度描绘,为我们理解干部这一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能动者提供了创新性和具有历史视野的理论启示,同时对于我们进一步构建中国干部这一独特群体类型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因此,在有关中国干部的研究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强调制度逻辑在中国政府及成员行为上的决定性影响,一套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塑造了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并导致了中国干部们的具体行动。(62)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9页。然而,这种研究路径将中国干部问题局限在中国组织制度研究的框架之内,把组织功能理想化——组织意愿可以随时得到认可和响应,而忽视了中国干部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直面中国现实中的干部群体,从概念、群体性质和不同层面都展现出了中国干部异于理性官僚的特质,并试图从治理主体的视角来对中国干部群体进行理论化。这些努力和进展表明,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干部从那些错综复杂的组织制度关系中抽离出来,把他们作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能动者,作为政治运转的核心部分而非组织制度的附属物,尝试着将中国干部作为一种新的官员类型来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和传统,构建基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干部理论体系。
四、总结:从官僚范式到干部范式
中国干部集合了中国共产党官员所被赋予的政治化和专业化属性,既区别于“官僚” “文官” “公务员”等韦伯式官僚的行为特质,又植根于中国本土传统和现实的政治语境与实践场景。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干部既肩负着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又负有为民服务的政治责任;他们对于国家现代化改革、历史任务、文化传统和革命遗产的看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治行为,展现出的正是一种独特的官员类型。因此,只是单纯将中国干部视为韦伯式的理性官僚,或者纯粹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都是不太妥当的。
当然,中国干部的这种特征和行为模式也并不是中国干部所特有的,它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民族主义政党干部,以及欧美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中国的干部具有某些类似之处。但中国干部不同于一般的地方,主要在于中国式干部的典型性。中国式干部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决心打造一个与官僚完全不同,富有政治远见、战斗精神和纪律严明的干部群体;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党,在整个党组织或政府机构中对其所有领导成员进行如此坚决有力、锲而不舍且成效卓著的干部学习教育,以防止干部蜕化为墨守成规、形式主义的官僚。因此,干部本身这一概念就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及成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今天的中国,由庞大的党政干部群体来治理。而对于重新认识干部这一群体,恰恰需要我们深入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现实,并在一个国际比较的普遍性意义上来审视它的角色和功能;这种认识和理解不仅可以有效地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也挑战了以往以韦伯式官僚为基础的官僚理论,对于我们构建有关中国治理主体的基础理论——干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的国家治理,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就需要走出以往的官僚范式,并建构一种新的干部范式。
总之,干部这个角色在中国所展现的特质最为全面和稳定,因而也可以说,干部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能动者类型在中国的形态最为完备,更接近于构建“干部”的理想类型概念。中国的干部研究,为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推进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化,以中国为方法,深刻理解中国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