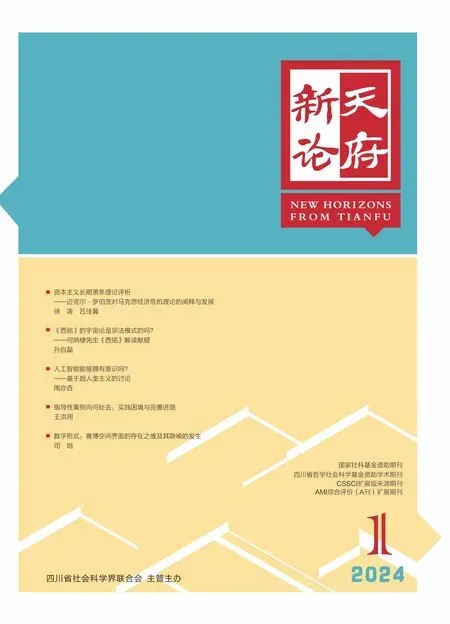毗邻而和:媒介传播与乡村社火筹演的再组织化研究
——基于晋南X村的田野调查
李 鹏 陈梓鑫
一、引 言
2023年2月16日(正月廿六),粉娟接到五组组长引平的电话,嘱咐她隔天清晨前往村委会大院进行鼓乐排练。这是粉娟加入社火表演队伍的第五年。2008年,她在北京打工时结识了其丈夫周杰,来到位于晋南的X村。常住人口为2 582人的X村是周边最大的村落。每年二月初二,适逢“龙抬头”,村里会固定进行社火表演,从1997年至今已然持续了20多个年头。这其中既有2008年的狂欢盛况,也有疫情之下的冷寂萧条。但总体而言,其演进脉络始终呈现组织化面貌,不仅征召时长缩短、筹演流程渐次成熟,参演人数逐年上升,节目形制也逐年日臻完备。于是乎,一些问题不禁浮出水面:为什么盛大的社火筹演活动发生在了X村?在历史发展脉络里,又有哪些因素统合了社火筹演的组织化进程?而作为联结手段的新媒介,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与功能?
二、提出问题:媒介传播与乡村文化的再组织化可能
在变革激荡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传播媒介始终被视为行之有效的治理工具,以国家符号形象嵌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具体到不同的研究面向:技术乐观主义者将乡村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科技扶贫与媒介赋权,以发展传播学视角分析各色媒介下乡带来的整体变迁,认为其既可以消解农民的“观念贫困”,撒播现代化的农业知识与致富信息(1)黄艾、熊皇:《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互动与现实路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实现农产品品牌传播与产业振兴(2)张晓锋、鲍姝辰、李广修:《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新媒体时代农产品品牌传播策略——以阜宁生态猪肉品牌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亦可以充当上下“中间人”与“对话者”角色,桥接起触达基层治理末梢的传播网络,实现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有机整合(3)高晓瑜、李开渝:《媒介化时空:县级融媒体重构乡村共同体研究》,《编辑之友》2022年第12期。;人文主义学者沿袭费孝通的“乡土性社会”观念,聚焦媒介传播中农民的社会交往与权力变迁,认为乡村信息网络正重构着村民的生活空间、人际网络、亲子关系与家庭文化。(4)冯强、马志浩:《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1期。通过接触与使用各种现代媒介,农民一面获得新的谋职方式与社交渠道,积极调适城乡生活;一面又因文化资本与权力等级的固有限制,成为加速数字鸿沟与城乡分化中的弱势成员。(5)曹晋、梅文宇:《城乡起跑线上的落差:转型中国的数字鸿沟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2期。除此之外的第三类视角,则是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析媒介传播与村民政治参与、家庭增收、文化动员之间的调谐关系,如关注公共传播何以能激发村民的政治讨论与选举兴趣(6)闫文捷:《作为公共传播的民主商议及其意义——一项针对浙江基层商议实践的问卷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1期。,观照“数字下乡”进程中的资本何以进行组织生产、科技如何真正内嵌适配(7)唐伟:《科技下乡的社会基础——以Y省J村柑橘品种改造过程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以及最为重要的一环——探究媒介传播与乡村各色文化活动的互构及适应。
《汉书·艺文志》云:“礼失而求诸野。”如若将乡村视为现代化治理的基本单位,文化振兴则是其中的“铸魂”工程。对于农民而言,以乡土性、群众性和参与性见长的民俗文化,不仅是滋养闲暇生活的精神养料,更是其寻求存在感与身份认同的地方印记。从《资政新篇》中移风易俗以求“教导我民”的理想愿景,到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期和平改造农民身体、智慧与道德观念的伟大设想,再到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创造新文化、救活新农村”的改良观念(8)周朗生:《洪仁玕、严复、梁漱溟的乡村文化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中国乡野,文化始终是振兴发展的智慧源泉、根基灵魂与精神动力。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乡土社会所依的规范,重在礼俗而非法理,中国乡野仰赖礼治而非西方的“法治思维”。萌于农时、长于技艺、兴于节庆的各色乡村文化,不仅承担着延续耕种策略、传播制度规范、濡化道德观念的个体培植作用,更能够有效地聚合群众、凝聚共识,塑造村庄交往与村务磋商的公共空间。(9)高瑞琴、朱启臻:《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基于〈把根留住〉一书的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伴随着1950年代以来发生在农村的土地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四次重大变迁,原先稳定闭塞的“熟人社会”渐次走向开放流动的“陌生人社会”(10)范建华、秦会朵:《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曾经烜赫一时的基层群众动员与公共文化活动,也在“离乡”潮流、“空心化”环境与“老龄化”问题的拥趸下濒临消解(11)刘天元、王志章:《稀缺、数字赋权与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基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3期。。与之对应,在沙垚的讲述里,以“关中皮影戏”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表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组织化与系统化的主体生成阶段,以1956年农民戏班的登记改造为典型。(12)参见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第110页,第127页,第133页。在此之前,乡村文化生活的联结主要依靠春祈、秋报等祭仪,农民通过参与反规范性的世俗狂欢活动获得精神纾解,并在此过程中自发凝结成文化共同体(13)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二个阶段是规范化与政策化的“人民性”整编阶段,此过程的重点是加速文化体制与农民表达的有机融合。(14)参见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第110页,第127页,第133页。通过国家性话语自上而下地触达乡村,原先自发组织的农村文艺实践,在“人民性”的呼吁下逐渐蜕变为一种“说教”与“灌输”,内生性的文化表达遭遇动摇。第三个阶段是公共性文化活动的大面积凋敝阶段,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队的解体与80年代初现代媒介的涌入,集体性文化实践与文化动员日渐衰微,农民艺人也逐渐回归个体化的表演模式。(15)参见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第110页,第127页,第133页。第四个阶段则是千禧年以来,伴随着“非遗保护”的政策性话语逐渐复归的文化再组织阶段。(16)参见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第110页,第127页,第133页。
为了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环;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明确提出要“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有鉴于此,传播学界开始重拾对乡村“文化治理”议题的关注,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两种趋势。一是怀揣功能性视角,关注媒介赋权之下农民的文化参与及文化表达,如关注短视频的“去中心化传播机制”与“高参与性互动机制”如何推动乡村网民的文化参与(17)刘汉波:《从土味实验、空间生产到媒介认同——短视频浪潮中的乡村空间》,《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6期。,关注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秩序及“共同场域”的建构(18)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聚焦乡村青年媒介使用行为对地方文化景观的再造(19)陈瑞华:《“地方再造”:农村青年媒介行为的文化隐喻》,《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以及思考新媒介赋权所带来的乡村数字建设及“重新部落化”现象(20)师曾志、李堃、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9期。。二是以批判眼光审慎思考乡村文化实践中媒介传播诱发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吴鼎铭看来,栖身短视频平台的乡村用户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诱惑、剥削与压迫下逐渐沦为被动的数字劳工(21)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杨萍则直接指出,在流量经济下,乡村土味文化大有迎合受众审丑心理、渐趋低俗化的倾向(22)杨萍:《赋权、审丑与后现代:互联网土味文化之解读与反思》,《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3期。;对于公共性文化活动衰落这一核心命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网络互动引发的家庭隔阂与个体化倾向,认为在线沟通阻碍了公共交往及生活空间的形成(23)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
可以看到,既有的研究路径多呈单一性思维,聚焦乡村文化实践的某一面,或是以正向视角对媒介传播予以颂扬,或是以批判思维对媒介传播加以指摘;更进一步,无论是积极地将新兴媒介视作乡村文化“弱者”的武器,还是消极地将新兴媒介视作对既有社会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固化与深化,皆是以媒介为中心,将农民视作媒介景观中的一员与“亟待拯救”的社会对象,缺乏内生性视角下对媒介传播与乡村文化互构过程的辩证性思考。有鉴于此,撷取群众自发的、基于自身生产的文化活动,成为媒介传播视角下寻求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一种手段;发现潜在的群众文化活动,以辩证思维探讨媒介对其的正向影响与负面作用,不仅是农村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乡村治理的应有之义。如王维佳所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前路是克服西方舶来理论的窘境,重新续接马克思主义道统,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与活力源泉。(24)王维佳:《新时代的知识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1期。故此,本文延续沙垚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将手机等媒介作为渗透至乡村文化发展各阶段的内生工具,以社火筹演这项传统文化活动为观照对象,意图剖析其后的社会结构与世道人心,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Q1:为何乡村文化活动的再组织化能够于20世纪末复归?
Q2:作为内生力量的乡民何以被动员与凝聚?
Q3:在此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媒介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与功能?
三、复访河东:以参演者身份进入
作为观照对象的X村坐落于晋南河东(今山西运城)地区,处于其所在的闻喜县最北端,素有闻喜县“北大门”之称。从“晋文侯成师”(《史记·晋世家》)到“秦伐魏,改曰左邑”(《战国策》),此地见证着中原军事、文化力量的征调与消长变化。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省级重点推进村,X村建置面积庞大,单是耕地面积就有5 000余亩,与之对应的常住人口更是多达2 582人,分居于塬上、塬下的5个生产组。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本村的社火筹演提供了充足动力。自清末起,“闹社火”便是村内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每年二月初二是社火表演的固定时间,在乡民的传统认知里,“二月二,土地诞”,农户需要在这一天通过表演抬阁、锣鼓、高跷、花车等社祭节目朝拜土地公,祈祷新年农业丰收与宗祀安稳。
20世纪70年代,因“移风易俗、破除封建”的政策需要与生产队解体、农业结构变动等社会因素,X村的社火筹演活动一度告停,直至90年代末复又重启,并在村委会与乡民的组织下逐渐扩大。2023年,因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管理与“闰二月”的特殊性质,X村的社火筹演达到20年以来的最大规模,不仅筹措资金高达20万元,节目时长与演出规模更是突破村政纪录。
为了详细了解20年X村社火筹演活动的组织化过程,笔者分别于2022年2月15日至4月1日、2023年1月28日至5月5日先后两度进入田野,以《器乐大合奏》鼓手身份参与社火筹演队伍中,意图通过参与式观察爬梳筹演活动的历时脉络、动员流程与组织化成因。
参与式观察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孕育并拓展出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其核心题旨是将调查者长期置于被调查的社区中,以求其能熟悉当地发生的事件,在被当地人信任的基础上获取一手资料。(25)马翀炜、张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沙垚认为,在进入田野观察的过程中,要竭力避免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将文化研究的触角尽可能延伸到在地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中,实现深层次的视野拓展与学科对话。(26)沙垚:《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问题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以此为基准,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以微信群为代表的新媒体并非作为单一对象被观照与解释,而是渗透至筹演的各个环节,作为观察工具内嵌于调研流程中。具体实施过程如下:2021年2月,笔者作为观众第一次接触到X村的社火展演,庞大的表演规模与完备的节目形式,让笔者对社火筹演的流程与管理模式产生好奇。于是,在2022年2月16日,笔者通过亲戚介绍加入X村的鼓乐表演队伍,成为开场秀《器乐大合奏》的一员。在此过程中,笔者接触到了以戏迷学梅、板胡手天明为代表的5位农民艺人,以及负责动员的核心骨干五组组长引平。通过交流,笔者初步了解到X村社火筹演的历时演变。2023年2月,笔者再次以参演者身份加入表演队伍,由于2023年活动规模的扩大,笔者接触到了更多的联络组长,并结识了秀彦、银虎等负责征调物资的实体从业者,以及粉娟、丽霞等特殊的外乡媳妇表演人群。通过长达4个月的走访调查,社火筹演的组织化进程终于得以明晰。
四、何以可能:从信仰到仪式的空间共同体
(一)庙宇整合与筹演队重建
在X村大部分村民的印象里,1997年是全村社火筹演活动的一条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村委会也曾动员农民艺人进行过几场表演,但其规模较小,多是本家“老汉”靠权威性和影响力拉拢来的参演人员,内容上接续明清以来的“闹社户”传统,以“抬阁、柳木棍、妆演戏目和游行街衢”为主,钲鼓喧阗,村民主要充当巡演时的“看客”。1997年的流程则不同,已初具组织和规模。据村文艺宣传队的板胡手天明回忆,那一年二月初二的“社火大闹”缘于村土地庙的翻新。“那几年天旱得可以,塬上头的地收成特别差,村里人光景不好,我父亲和几个村委老汉就合计,说干脆拜拜老土地爷、闹闹社火祈福。”(27)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刘天明,1961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28日。地点:村委会大院。1994年,X村所在的闻喜县遭遇特大旱灾,全县小麦减产3 260万公斤,与之邻近的裴社乡更是发生严重的蝗灾;到1995年,全县的降水总量降至其十年最低值,仅有354.8毫米。(28)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闻喜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49页、第67页。恶劣的生产环境让村负责人世安在内的乡民冀盼于传统的“春祈”,希望借由社祭祈祷本地五谷丰登,社火筹演由是有了再组织化的可能。
1997年的筹演过程共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土地庙的整合与翻修。作为社祭载体,庙宇寄托着乡民的土地信仰、繁衍祝祷与公正祈盼,是以农为业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9)赵世瑜:《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寺庙文化初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彼时X村的常住人口已逾2 000人,分居塬上、塬下的五个生产组,建置传统使得本村庙宇众多,土地庙、阎王庙、娘娘庙、十字庙及泰山庙据地而建,依人口密度排布于不同地域。1997年的一大变革就是这些社祭对象的统合,在村委会主任克义的牵头下,“不可遍敬”的神祇被共置于翻修后的土地庙中,重新“封土立社,示有土尊”。庙宇空间的聚合,驱使村民结成了共同的祭祀圈,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生活秩序也随之联结。其次,为了维持每年二月初二的“春祈”仪式,村负责人世安动员各组负责人先后成立了“土委会”(土地庙管理委员会)与“火委会”(烟火管理委员会)两支自治队伍,由他们负责每年的节目筹划与人员调配。自治小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自生产队解体以来社火筹演工作中的组织“真空”(30)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使村务活动得到了有效管理与监督。最后是征召与安置各组的锣鼓队与文艺宣传队。2023年69岁的翠玲曾是第四锣鼓队的击钹手,她回忆说:“那个时候锣鼓队挑人细发得很,要眉眼俏、个子高、还要有点劲儿,学东西快的人,进了队以后有镇上的老乐手教,1997年闹社火前我们学了半个月就能合奏了。”(31)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陈翠玲,1954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5月4日。地点:翠玲家中。锣鼓队的重建,复现了百年来“游春祈、庆丰年”的仪式传统,但其内在并非因循守旧、凝滞保守的“后喻文化”心态。事实上,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的涌入,社火表演的内容与形式已发生巨大变革,不仅涌现出《欢庆锣鼓》 《黄河船夫》等咏叹现代生产精神的表演曲目,由血缘联结向业缘联结的互助协作也更具组织和规模。
(二)务工潮下的“同龄人捐款”
筹演活动的第二次规模化扩张发生在2005年。彼时,离乡务工成为村内热潮,农民不再是困囿于“普遍贫困”、被迫卷入宏大结构的边缘群体,而是作为能动主体内嵌于城乡二元结构中,成为“半工半耕”的双向流动者。为了满足生存消费之外的人情礼仪、面子竞争等社会性消费,“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大部分青壮年农民谋求收入增长的主要手段。(32)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与此同时,在手机等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下,农民开始自发地调配社会资源,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跨地域关系网络,由血缘、地缘结成的手机互动式求职模式逐渐取代过往的偶遇式谋生,村民的“计价还价”能力得到了有力保障。三组村民、2023年67岁的俊成回忆说:“2005年前后村里出去找活儿的人是最多的,那几年南方要盖的房子多,大部分人去了无锡、东莞和广州当小工。哪里有活儿、挣钱多,村里人就会打电话吆喝着叫过去。”(33)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周俊成,1956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1月27日。地点:俊成家中。那一年,全县流动人口增长到了9 938人,县政府不得已重新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34)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闻喜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83页。。也是在那一年,如俊成一般的农民工对乡情的信赖与渴望达到最大值。俊成说:“以前从来没有在外面待过那么长时间,最多也就在临县干过两个月,那次在无锡当小工一干就干了半年,想娃想得不行,也总想回村里看看,多亏有几个同村人互相照应着。”(35)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周俊成,1956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1月27日。地点:俊成家中。在丁未的观察里,务工潮的背后是新媒介加持下传统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的放大,在这个网络中,有村民值得信赖的信息,有接应反馈、互帮互助以及乡情的慰藉。(36)丁未、宋晨:《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尤其在节庆时期,曾受该网络裨益的归乡、回流村民也更愿意为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005年社火筹演,俊成捐款2 000元。他说,那年家里的5亩地,种的黄芩和远志卖出去得了2万多元,他去无锡当小工也攒了3万元,在村里光景算好的,又赶上是自己的本命年,所以“同龄人”捐款的时候他给的比较多。2005年社火筹演的一大创新,就是时任村委会主任庆财组织发起的“同龄人”捐款事宜。在X村村民的传统认知里,28岁、36岁、49岁是所谓的“门槛年”,有“不掉骨头掉块肉”之说。村民普遍认为,度过了“本命年”,生命就会出现新一轮如同草木的生长熟亡过程。因此,当服务于春祈祝祷、庙宇修缮的“同龄人”捐款倡议被提出时,大家才愿意响应。在此之前,村务筹款体系多以乡村精英为主体,他们大都是村中的富户耆老,在社祭活动中兼任纠首一职,既要带头捐款、召集募化对象,又要管理捐金开支,负责人员调配(37)赵新平、王超宇:《村庙与众生:清朝代州村庙修缮与村落生活的互动》,《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事务繁杂,且缺乏现代化的组织流程。“同龄人”捐款制度落实后,进出流水开始交由“土委会”负责,会内不少成员曾任生产小组会计,业务能力强,大大缩短了社火展演的筹备周期。“同龄人”的积极参与,让村务组织管理的对象更加具体化,也让参与筹演的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借此时间维度的人生仪式与空间维度的村落仪式得以耦合,社火筹演成了乡民崇神敬祖、节日狂欢与个体记忆的融合载体,活动过程由是更具组织化。
五、何以联结:面子为里,乡缘为媒
(一)作为动员媒介的“新乡贤”
在渐次谋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脱胎于官僚—继嗣时代的文化传统与“乡贤”体系并未完全消弭,反而在中国社会渐呈“回归”之势。一则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造就了民间社会对旧的家庭模式的新需求,致使“传统家族意识”复归;二则 “集体机构”力量衰减,社区生产和生活因缺少组织者和社会资源,不得不寻求旧式家族房祧关系、地缘关系作为联结方式与庇护手段。(38)王铭铭、王斯福:《乡村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由是形成的“民间权威”在社火筹演过程中亦得到了传承,只是身份特质有所改变。李红艳认为,在相对封闭的现代乡村,人际熟络仍旧依赖于身体的在场和传播,由之形成的“熟人”关系也更加密切与稳定。(39)李红艳、冉学平:《以“乡土”为媒:熟人社会内外的信息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这与笔者对5个组长的询访资料基本一致。五组组长引平说:“在实际筹备过程中,手机一般只起到信息通告作用,细致的村民动员和节目策划,还是要靠挨家挨户地劝说。”(40)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张引平,1970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23日。地点:村委会办公室。不仅如此,“筹演也基本不建微信群,能打电话都靠电话通知,再不然就是排练当天商量好以后什么时间演、还缺谁来演。”(41)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张引平,1970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23日。地点:村委会办公室。
当然,几个组长也并非孤军作战,他们通常会在动员初期找一些帮衬的副手,由他们协助完成组织工作,水生超市的老板娘秀彦就是其中一员。秀彦2023年52岁,2009年自家商店扩建之后,她便取代“火委会”成了社火表演服装、烟花等物资的调配者。秀彦说,几个组长之所以选她,是因为她“在村里做了几十年生意,认识的人多,别人也都信得过。演个节目啥的知道谁更适合,村里大部分人不管在哪儿也都能联系上。”(42)访谈资料。访谈对象:行秀彦,1971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12日。地点:水生超市。如秀彦一般的人被胡鹏辉定义为“新乡贤”(43)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知识文化,有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时间及行动力;同时,十分熟稔乡村社会的交往原则,有强烈的“在乡性”服务意愿。
在X村的社火动员队伍中,新乡贤共有三类:第一类是如秀彦一般,从事实体经济的“商铺老板”,他们大多属于乡村中的“经济精英”,人脉广、资财足,具备长远的市场眼光与较强的统筹能力,因而在村务组织工作中有较高的话语权;第二类是原村委会的退休人员,包括历届村支书、妇女主任,以及原生产队的保管、会计等,“土委会”的负责人世安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类则是以戏迷学梅为代表的农民艺人。三类新乡贤在社火筹演过程中主要承担辅助型角色,作为村委会的解压阀,他们的职能包括社会治理、行政辅助与监督质询,是文化服务与村务项目落实过程中的关键一环(44)姜亦炜:《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新乡贤组织的演生及其类型学》,《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3期。。与传统缙绅相比,这些现代新乡贤具有较强的平民化特征,他们虽然不能以“德业学行著于世”,但皆知晓礼仪教化,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规了然于心,并熟谙地方事务和群众心理,能妥善协调乡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45)张兆成:《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既是乡缘网络中的能动主体,也是乡村自治与发展的内生力量。具体到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是使乡民能够归心乡村、安心乡村,以期从根本处解决乡村精英流失的现代化困境。在数年的打磨之下,以新乡贤为主体的筹演班组已趋于稳定,由他们组织策划的《器乐大合奏》 《舞动新春》 《骑驴闹春》与“抬阁”,也成为固定的表演节目,每年仅在表演形式和人员配比上有所创新。
(二)挣面子:一种内生动力
在中国乡野,“面子”构成了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累积的前提。《汉书·项籍传》即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鲁迅更是在《说“面子”》一文里直言:“找准了面子这个概念,也就找准了中国精神的纲领。”无论乡村内外,由“挣面子”生成的荣誉观念都是维系基层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无形纽带,是联结个人尊严与社会价值的有效介质。(46)姜亦炜、吴坚、晏志鑫:《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研》,《浙江学刊》2019年第4期。当秀彦一类的统管能手被村委会征召为筹演活动负责人时,他们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极大认可。于他们而言,成为社火体系的管理者,既是为民众办事的光荣之举,也是能彰显自身能力、在之后的村务活动与社会交往中获得话语权的有利途径。秀彦说:“村子就这么大,都互相认识,你说个啥别人愿意听、也能听进去,就说明你在村里为人不错。”(47)访谈资料。访谈对象:行秀彦,1971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12日。地点:水生超市。感受到荣誉感和内生动力的新乡贤,在承认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更愿意用柔化的手段,通过身体传播激发和共享自己的荣誉观念,以期调动起普通民众的服务意识。振邦就是在此过程中被劝服的一员。他说:“原来没想着捐钱,秀彦来我家转了好几次,说我多半年不在村里待,屋里都是别人给照应的,再不拿点钱人家都笑话哩,我抹不开面子就给了1 000块钱。”(48)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杨振邦,1974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3日。地点:振邦家中。
和振邦不同,二队的建伟在2023年的筹演活动开始前,就联系村委会,与妻子各捐了1 000元。建伟2023年53岁,2008年去绵阳包工程干活儿后,他有十多年没在村里生活。当被问及捐款缘由时,建伟坦言:“村里人都有落叶归根这个说法,年龄大了回到村里,还得邻居朋友们照应,出钱给大家做点事一点问题都没有”(49)访谈资料。访谈对象:燕建伟,1974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7日。地点:村委会大院。。对于建伟一类的回流村民而言,X村既是其生于斯也将逝于斯的社会公共空间,也是舆论压人、“面子”有价的熟人交往空间。在此空间内,“面子”扮演着社区性货币一角,其存量多寡不仅决定着村民的个体效能感与社会评价,更直接影响其子孙后代的社会交往与社区声望。(50)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赞赏和肯定,村民们需要长葆“挣面子”的动力,将面子内化为自己的桑梓荣誉感,这也是建伟愿意和妻子自发捐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夏柱智的勾勒里,离乡农民的家庭角色共分四个阶段:成年前读书升学,弱冠年务工婚配,而立年经商育子,等到五十岁知天命,便开始渐退城市,重新回流乡里。常年离土离乡的经历,让回流村民的心理漂泊感与孤独感无法排遣,对宗族与乡土归属感的渴望,亦驱使他们急切地想要借助集体活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基于此,年终祭祖与社火筹演成为众人获得荣誉感的舞台,这也就解释了建伟为何愿意为“社火”——这项日常生活之外的村务活动捐献大额资金。
(三)外地媳妇的融入需求
除了离乡村民以外,社火筹演中的另一个典型,是如粉娟一般的外来媳妇们。粉娟2023年34岁,来自甘肃天水的郭川镇,2008年她在北京一家饭店做帮厨的时候,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周杰,二人于2014年回到X村完婚。和粉娟几乎同一时间嫁到X村的,还有来自无锡的丽霞。2023年的社火表演环节,包括粉娟、丽霞在内的24个外地媳妇组成了一支锣鼓方队,联袂献演了鼓乐《黄河魂》。粉娟说:“我在村里没啥认识的人,平常都不怎么出门。我也是被人家叫去演节目的时候,才知道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儿有这么多。”(51)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郭粉娟,1988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23日。地点:粉娟家中。
在晋南乡民的传统认知里,“业成之后,筑宝买田,养亲娶妻,必在故乡”。然而,伴随着2005年以来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增长,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传统婚姻圈地域限制的解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庞大跨省婚姻群。在陈讯的观察中,跨省婚姻打破了传统的通婚圈,加剧了其与传统婚姻伦理、婚姻规范的脱嵌,在其维系过程中,“外地媳妇”一方面因与娘家相距较远,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性身份较弱,缺少利益联盟与互助合作,婚姻功能丧失公共性;另一方面也因传统文化和宗族力量的影响,遭遇身份、宗族和代际间的排斥,不得不重构社会交往与家庭生活。(52)陈讯:《多重排斥、价值嬗变与农村跨省婚姻研究——以东莞宗族型X村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9期。
此现象在“巨村为镇”的内陆山西更为明显。明朝的《泽州府志》便称河东(今运城地区)“表里河山,藩屏中国”,是华夏的腹心地区,与外界限隔。赵世瑜在考证晋南地区的聚落与认同观念后,更是认为这里的乡民据社联结,能够形成稳定的“市场共同体”与和“地缘共同体”,且不会随里甲废弛、战乱破坏和人员流动而解体。(53)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以及山路盘桓导致的交通不便,造就了晋南乡民孤立保守的社会意识,也让生活于此的X村村民形成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54)乔润令:《传统民俗与山西社会的区域特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在此情形下,以“社”为组织单位的社火展演,成了粉娟一类的外来媳妇寻求社会认同、业缘融入与荣誉满足的主要纽带。粉娟说:“人家叫我表演,我挺开心的,觉着自己成了村里的一分子。公公婆婆也觉得面子上有光,跟我说好好敲鼓,趁着演节目和村里人多认识认识。”(55)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郭粉娟,1988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23日。地点:粉娟家中。社火狂欢的全民性与反规范性,极大地冲淡了乡缘网络中的“同心圆”观念,使得外来移民能够“大聚乐戏于沙丘,盈街溢巷,与本村相合”。被卷入筹演活动中的外乡媳妇们因鼓乐表演被嵌入乡村公共空间中,成为内携荣誉观念的一员,心理认同感与组织凝聚力由是增加。
六、何以发展:媒介赋权还是减权?
从1994年以来“金农工程”与“村村通电话工程”的落实,到2005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及“十一五”规划中对于农村信息化工作的重点部署,再到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数字传播与乡村振兴的现代化联姻,借由数字技术赋能乡镇公共服务与村务治理,以新兴媒介触达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活力,始终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环节。(56)左停、旷宗仁、徐秀丽:《从“最后一公里”到“第一公里”——对中国农村技术和信息传播理念的反思》,《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7期。然而,需要警醒的是,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新兴媒介传播并非呈现出单向度的乐观态势,而是与礼俗社会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着诸多龃龉。具体而言,就是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礼俗社会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57)杨嵘均、喻包庆:《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这一特征在X村社火筹演的流程中亦得到了印证。
(一)作为赋权工具的新兴媒介
如若以赋权视角审视乡村社火筹演的具体流程,会发现整合传统文化禀赋、在云端聚合起的“数字礼俗社会”在实践中仍能清晰可见(58)邱新有、陆锦华:《微信群中的数字礼俗社会:一项关于壮族山歌媒介化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1期。。比如,延续传统“族权”动员美法村陈氏家族,民间权威组织石碇村妈祖信众,乡村广播唤询东祝村公共意识(59)沙垚、张思宇:《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9期。。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在社火筹演过程中同样扮演着知识工具、展演载体与互动空间三重角色。首先,对于参演群众而言,短视频不仅是进行自我表达与精神纾解的便捷路径,更是追念乡土记忆、接触外界资源、学习先进经验的一种发展手段。2023年62岁的天明是村文艺宣传队的板胡手,2016年从县文化馆退休后,他被村委会主任建国委派为鼓乐教员,负责教“萌新乐手”敲出完整的曲子。虽和学梅同为农民艺人,但天明并不负责演员征召,他说自己“脸皮薄,嘴皮子不灵泛,就是手艺还行,所以村里的表演活动少不了自己。”(60)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刘天明,1961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28日。地点:村委会大院。2019年,村委会大院扩建之后,社火表演的内容和时长被要求增加,为了编排新节目,天明开始求助于时兴的“抖音”。刷到心仪的眉户曲子,他会吆喝队里人学样排练,刷到同城的干板腔或者花鼓曲,他则干脆跑到定位的村子里向人家直接请教。除了充当知识工具外,抖音还是X村社火直播的重要载体。2020年,经过村民倡议与各组组长的走访合计,“土委会”决定拨出部分捐款用来进行表演录影,同时增设抖音直播以满足离乡村民的观赏需求,并在“票圈”小程序里跟进回放。此举得到了中年村民的热烈赞许。四组队员贵英说:“那年美着哩!我在市里带孙子就说不回来了,结果刘翼(笔者注:贵英的儿子)发了个链接给我,我一点开发现人家弄得还挺全活,比站那儿瞅着都清楚。”(61)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徐贵英,1963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5月2日。地点:贵英家中。借由直播展演,社火从村民印象里“可读的流传物”升级为“可看的流传物”(62)柴冬冬:《被展示的流传物: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俗叙事”及其表征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在网络桥接的跨时空观看场域内,在地民俗得以不断记录,并催生出新的情感民族志与集体文化记忆。
除了上述功效外,作为筹演基础设施的“网格群”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小觑。2020年7月,X村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需要成立“网格居民群”,此后村务活动开始大批量地转移到线上,包括户籍管理、警情通报、防疫动员,以及每年最重要的社火筹演等事宜均在群内开展。村委会主任建国说:“建群一开始,我就跟村里人讲,说这个群是国家开会说要建的,是很正规的群,以后村里啥事都会在这个群里落实。”(63)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李建国,1978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19日。地点:村委会办公室。群内的管理员仍由建国担任,村政讯息运营则交由妇女主任鸿云负责。相较于从前,现在的社火筹演过程因网格群的嵌入更加有条理与成熟。每年的正月末,鸿云会先以“通告”形式在群内发布社火筹演信息,号召各小组负责人动员群众准备节目,同时附上历年表演的视频链接供村民参考。之后,由村委会主任建国出面发起“同龄人”爱心捐款倡议,告知用款事由和截止日期。与此同时,鸿云会不断公布捐款名单及对应的款项金额,小组负责人也会不断地在群内告知新加入的表演人员和节目形式。“细事细治”的信息运营搭设起村务管理的“在线公共空间”,将互相熟稔的邻里亲朋置于彼此的“凝视”之下,原先隐蔽的筹演过程变得可见与公开,致使在无人发言的聊天环境里,部分尚未出力的村民依然能够感觉到来自“他者”的压力(64)蒋建国:《微信群:议题、身份与控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受集体观念驱使加入募捐与表演队伍,其结果便是社火储备资金与参演节目的逐年递增。
(二)作为矛盾中心的新兴媒介
尽管在社火筹演的过程中,新兴媒介赋予了乡村个体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继而统筹集体行动、联结村落精神的现实可能,但仍要看到,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媒介所诱发的负面影响。首先,被多数村民视为学习路径的民俗“短视频”,其本身便是被主流文化收编与重塑后的产物,至于村民们竞相模仿的秧歌舞曲与锣鼓钹镲,也多是城市潮流拥簇下经过拼贴、戏仿与解构的产物(65)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与村庄内部的民俗惯习存在龃龉。2020年《骑驴闹春》的退场即与此相关。老村支书申娃回忆道:“那年捐大头的十几家都在外地跑着,就嘱咐说,找个镇上的婚庆公司给他们录个全一点的相,好回来看。”(66)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安申娃,1951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10日。地点:申娃家中。为求稳妥,把关任务被申娃分配给了村委会的3名年轻干事;在排演最忙碌的当口,因为敲不准表演细节,三人决定向抖音取经。临近集体彩排,“学有所成”的他们突然要求《骑驴闹春》的表演人员取消“毛驴过河”和“过桥洞”两项传统表演,理由是画面看起来太过分散,不利于镜头捕捉,且形制和抖音上看到的宁夏、河北“列队式”骑驴不甚相符。此举引起了《骑驴闹春》负责人巧珍、雪娥的强烈不满。巧珍说:“他们几个娃娃家懂啥嘛,网上看一点别人弄的,就说我演了十几年的东西要改,我一下子就火气了,干脆撂挑子不演了。”(67)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张巧珍,1964年生。访谈时间:2023年2月17日。地点:村委会大院。在巧珍的授意下,表演团队的16人在即将登台前尽数离席,成了那年社火表演的一大缺憾。
除了巧珍的退场外,同年发生在网格群里的村民退群事件也同样值得注意。2020年,X村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需要开始进行线上筹款,逐日公布捐款人员与数额明细的做法引起了云生等待业村民的极大不满。云生说:“那两年疫情弄得人寻不下活,手里没有一点儿钱,但邻里亲戚的,不捐又实在抹不开面子。这还不算,以前是挨家挨户地聊着天鼓动你出钱,现在是靠群消息施压,我觉得少了很多人情味。”(68)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李云生,1973年生。访谈时间:2022年3月2日。地点:云生家中。2020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收入同比下降5.31%,长期停工大幅削减了村民们的就业机会。(69)叶兴庆、程郁、周群力等:《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评估与应对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3期。对他们来说,过往集体性、狂欢性的娱神仪式不仅未能缓解其时的生存焦虑,反而因网格群与线上筹款活动的嵌入,加剧了人情交往与面子负担。即如郭金秀所观察到的那样(70)郭金秀、黄政、龙文军:《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本命年的云生因为拿不出钱,遭到了组长的点名教育,并在土地祭仪、村路修缮等重大事项的讨论中被置于边缘,最终不得已退出了网格群。
上述事件均可视作新媒介下乡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巧珍的退场,折射出乡村媒介空间的“内外区隔”。在现代媒介架筑起的“去地方化”网络中,外部讯息虽然重塑着村庄的文娱情境,但乡土性礼俗的赓续留存与村民运用资源禀赋的现实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公共空间的扩张。至于云生的退群则是乡村媒介空间“公私龃龉”的最好佐证。从宗族耆老勒令乡民参事,到生产大队解体后“行政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坍缩,村庄内部的原子化及个体化倾向不断显现,其结果便是村落认同的淡漠、地方记忆的凋敝与集体行动的式微(71)吴海琳、周重礼:《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以D村“行政外生型”网络空间为例》,《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在此背景下,以国家话语搭建如网格群一般的“行政外生型”公共空间,虽然能够起到助推协商、双向监督的治理功效,但也极易引发个体的不适乃至反感。要借由媒介重建在地团结,便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性话语,还需要充分考虑在地资源、亲情伦理、礼俗秩序与最为重要的个体诉求,如此方能实现有效聚合。
七、结语:在媒介中看见乡村
从弹丸之地到都会名城的各个层面,新兴媒介的效用价值均被反复提及,可问题是: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其是否能如预期一般承担起赋权之责,又是否能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永葆正向价值?通过对X村社火筹演活动的参与式观察,本文发现媒介传播在乡村文化再组织过程中呈现出摆荡情形:一方面,传统媒介如身体、乡缘借由荣誉观念勾连起村民身体的“共同在场”与情感的“共振共鸣”,新兴媒介如抖音、微信群通过充当知识工具、展演载体与互动空间实现了村干部、在村村民与离乡村民的组织化协商;另一方面,新兴媒介在耦合在地资源、实现集体动员的过程中,却常常因制度性力量与外部市场资源的嵌入,未能真正适配村庄内部的传统惯习与日常实践。这警示我们:在推崇“资源下乡”的发展语境中,如何增加外部力量已非绝对重点,对接乡村的各项社会基础,在历史脉络与现实境况的对话中,将媒介视作了解传统习俗、地方知识与乡缘氛围的治理工具,也许是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可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