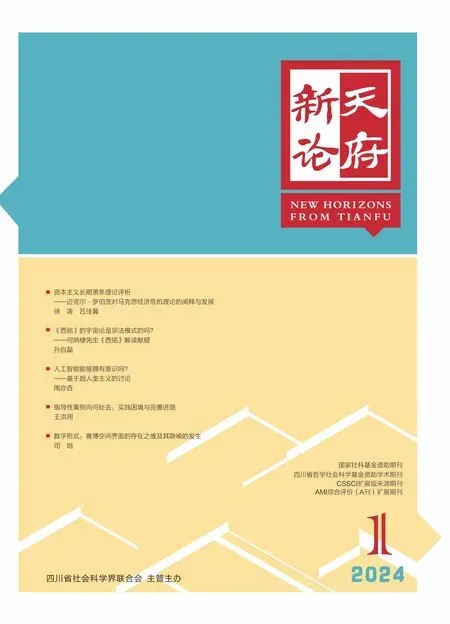走向陌异化的情感-记忆:塞巴尔德作品的相片物质性考论
丁鹏飞
不同于快乐、悲伤、愧疚、愤怒等有其价值结构的情感样态,是否存在一种难以类别化却又可被主体间共享的匿名式情感?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溢出传统情感结构的陌异性情感形态?在当代欧美文学批评界中心地带异军突起的流散作家W.G.塞巴尔德(W.G.Sebald,1944—2001)(1)被称作“当代乔伊斯”的W.G.塞巴尔德获得了1994年柏林文学奖、1997年莫瑞克文学奖以及2000年海因里希·海涅奖等众多文学奖项,并于在世之时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关注度很高的作家。桑塔格、詹姆斯·伍德、库切等众多评论家都表达了塞巴尔德在文学领域难以量化的重要性。的艺术风格,实际与此问题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2)在情感学的研究谱系中,霍根区分了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与情感科学(Affective Science)两种研究进路,前者强调体验维度,后者强调经验维度。这两种研究取向比较典型地呈现在晚近德勒兹与努斯鲍姆的相关著作中。本研究即将探讨的陌异化情感,不属于这两种研究思路所勾勒的情感轮廓。相反,通过对塞巴尔德作品的分析,本研究试图思考这种无法结构化的匿名性情感与其触发机制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由此提出情感学的媒介物质性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感研究》 (Affect Studies)中“文学情感的普遍性和陌生性”(The Ubiquity and Strangeness of Literary Feeling)部分,霍根以古希腊悲剧和莎剧为例,说明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悖论性情感,如爱与死、悲悼与满足同时共存的现象。霍根虽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探究,但这一现象与本文研究的陌异化情感有潜在的学理互动性。除此之外,艾舍与格罗斯等研究者注意到情感与“校准”(Calibration)以及分配“经济学”(Economy)之间的关联,这些都与情感自身的模糊度及其流态化特性有关。陌异化情感既与这些特性有潜在的关联,但又有其更深的学理地层。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塞巴尔德文本的分析,切近这一复杂性情感,以及由此复杂性揭示塞巴尔德的创作所关联的文学传统。参见 Patrick Colm Hogan,“Affect Studies,”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31 August,2016(available online at
根据对塞巴尔德作品的整体考察,如何让徘徊于可言说和不可言说间的情感得到显影,实际须借助相片在稀缺与过量间游戏的现象学特性来“实现”。在采访中,塞巴尔德说道:“我向来喜欢图像-文本的关系。在70年代,苏珊·桑塔格、罗兰·巴特、约翰·伯格写了许多关于摄影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感到与这些评论文章所说的话之间有一种直接的亲近感……而这(相片)是一个可以帮忙的小手段。”(3)Deane Blackler,Reading W. G. Sebald:Adventure and Disobedience,New York:Camden House,2007,p.139.那么,是什么让相片在特定时刻对读者的感知,进行着一种陌异化的情感施演(Performance of Affect / Emotion),并进而让难以回忆之物得到了“保存”?
实际上,端赖于线性逻辑的日常语言所传递的记忆,总会在福柯所言的知识话语中被简化,而缺少相片所具有的即刻让线性时间失效的情感冲力。而这种即刻性情感冲力,又正是由相片本身变幻莫测的物质性底色所施演的(4)值得注意的是,赫绪提到了相片的施为性问题(performative regime of the photograph),但并未从物质性切入这一问题。参见Marianne Hirsch,“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Poetics Today,Vol.29,No.1,2008,p.117.。故而,不再是将相片作为功能性图示的静态对象,而是借用相片所独具的破除具象的物质爆破力,才能“施演”一种真实的历史情感。正如自海德格尔以来到伊格尔顿的晚近哲学对艺术与物质性关系的深入推进思考所示,物质性总体而言指的是一种不为精神活动所把捉,但却能触发精神活动的陌异性力量。(5)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页;Terry Eagleton,Materi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22.由于它是一种独立于人之意志的、有着低饱和度的运作之物,也即一种在解蔽的同时遮蔽自身的存在,因此它就与主体自身认知活动未被发现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相连。不同于形而上学传统中与伦理总体化动机关联于一身的诸种情感结构,这种源于物质性的有着自治功能的“非知”(6)通过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哲学发展和艺术变革的提炼式考察,巴特勒与保米斯特等批评家已经注意到艺术“生产性”与“非知”之间的互构性关联。参见Judith Butler,Senses of the Subjec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Willi Baumeister,The Unknown in Art,Trans Joann M. Skrypzak,Berlin:epubli GmbH,2013.,揭示了一种无法总体化的别样情感地形及其不断勾勒的新型记忆伦理。故而,相片的物质性表征不单局限在打断线性时间,而是在于它所激活的一种更为重要的不断增殖的陌异化情感地形及与之相伴的谜一样的时间性氛围。(7)本雅明、巴特和德里达在有关摄影现象的分析笔触中,实际已经触及情感与氛围二者间模棱两可的矩阵区间,但并未对二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也是在相片物质性所施演的这一稀缺即过量的陌异化情感地形中,记忆在主体迷失于一种时间性的眩晕中自发地涌现了出来。
“陌异”是一个既有并列逻辑又有递进逻辑的语词,前者指陌生与异常的语义杂糅所产生的复调性机制,后者指陌生化效果始终有一种认知意义上的不即性,及由此不即性而导致的时间性层面的重复化机制。二者共同织就了本研究试图探索的情感地形学所意指的极性化张力空间。这种令读者“误入歧途”的既无法锁定记忆但又能感知记忆不断回潮的陌异化物质性情感,在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主要包括三种表征方式:第一种是达弥施思考的触发摄影出现并使历史记忆动荡不安的“无意识的强制重复”(8)达弥施:《落差:经受摄影的考察》,董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第二种是不同相片间的异质性关联,是朗西埃所言的“直接与故事和历史的‘外部’相连”(9)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页。的重复曝光;第三种是相片中从背景到前景的溢出历史话语的“重复性”面容。“一个历史现象,如果得到纯粹的和完备的认识,并被化解为一种认识现象,则对于认识它的人来说就是死的”(10)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那么通过相片三种陌异化的物质性情感,重复“曝光”过量的历史记忆,就成了塞巴尔德的四部曲应对这一难题的艺术方法。
一、作为过程:从乌有到世界
按通常的理解,包括人在内的事物总会有坠入虚空的危险,记忆只是防范这一危险所特有的心理机制。虽然这一理解有其素朴的切实性,但它容易将记忆活动与诸如情感、逻辑、审美等心智活动分离开来,将记忆活动简化为阿斯曼分析的仅行使存储功能的记忆“术”(11)参见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22页。。然而,悬浮在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的相片,却揭示了作为媒介相片的物质性情感过程。借助本雅明就相片洞悉到的在光影间游移不定的灵媒化物质性(12)参见本雅明:《摄影小史》,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29页。,可以进一步推进说,相片能够在收缩观者意识的瞬间捕捉到一种陌异化的“有”,所以大规模的历史记忆,实际是在“无中生有”的情感地形学中被唤起的。
从相片灵媒化的物质性中进一步获知的作为过程的无中生有,并非依某一既定系统被赋予其存在合理性的对象过程。相反,被相片中彼此成就的无法分有的光影物质性所触发的无中生有,并不给出对象,而是在作为肉身物质性的主体与其寓居的物质世界出现难以区分的熔点时刻时,所曝光的“我”是一个稀缺性他者这一陌异化情感现实,本雅明在其中看到了实在,即“灵魂”。不同于巴特在“压抑与听觉”中,将“咔嚓”一声与性快感关联在一起的思考路径(13)参见巴特:《如何共同生活——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1976—1977)》,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116页。,摄影“咔嚓”一声,生产出了狄金森式“绝望的印痕”或“庄严的苦恼”(14)转引自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这种在相片物质性中知觉到的稀缺性他者意识,更符合拉康到齐泽克思考的“原乐”,因为其陌异化的情感极性或者“快感,就其愚蠢性而言,只能建立在某种非知、无知的基础上”(15)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6页。同时参看索莱尔:《拉康派论情感》,吴张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在《说吧,记忆》中,叙述者纳博科夫曾这样写道:“个人的种种奥秘继续引逗着回忆录的作者。我既不能从环境中也不能从遗传中找到使我成形的具体工具”(16)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9页。,而作者插入的相片“物质性”,就在于能够维持这种无中生有的奥秘。这也是为什么围绕自我之来源而升起的记忆驱力,能够自为地在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大规模运作起来的缘由。
在《奥斯特利茨》的前半部分中,当得知自己被传教士父母领养的现实并深陷身世之谜时,奥斯特利茨开始着迷于摄影技术,“从一开始我的主要关心就是分散的事物间的形状及其自足的本性,楼梯栏杆的曲线,门户的铸模石拱和一簇干枯的草丛中叶片盘绕的精密度”(17)W.G.Sebald,Austerlitz,trans. Anthea Bell,London:Penguin Books,2011,p.108.。奥斯特利茨仿佛是在试图通过摄影寻找事物从世界的背景中浮现出来的“规律”。在奥斯特利茨从其幼儿时的保姆薇拉那里获知母亲曾被关押在特雷津(Terezin)(18)特雷津,捷克境内波西米亚北部市镇,1941—1945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的历史事件后,当难以在隔离区的星状平面图与当时早已物是人非而只剩下活跃着的蛛网间作出区分时,难以通过图示化的方式“分离”出在特雷津消失的母亲,使得奥斯特利茨的记忆焦虑达到了极限。是否事物有所谓的将自身从世界分离出来的“边界”这一问题,实际在奥斯特利茨偏好相片的倾向中得到了回答。“奥斯特利茨说,在摄影工作中,当现实的影子,可以这么说,在曝光的纸片上从虚无中浮现出来时,我总是尤其入迷,一如半夜中到来的记忆,如果你试图抓住,它们会再暗淡下去一样,就像一张留在显影液中太久的洗印的照片。”(19)W.G.Sebald,Austerlitz,trans. Anthea Bell,London:Penguin Books,2011,p.109.对奥斯特利茨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一张留在显影液中的相片,浮现与消逝相偕而行,而非此消彼长,所摄对象与作为注视者的主体间存在一种潜在化的相溶性(20)See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New York:RosettaBooks,2005,p.121.。这种游弋在凝定与解体之间的流体世界,让包括人在内的事物间的界限,并没有规律可循,主体实际就是“一片混沌不清的底色”(21)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物质与精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那么,作为一张相片的世界及其无法被分割的事实,如何解释穿插相片的《奥斯特利茨》能够唤起大规模历史记忆的过程?
伊格尔顿注意到了物质的“坚固性”(Intractability),不是为万物赋予基础的人类理性,而是一种先于存在物但却又维系它们的环环相扣的陌异整全感。(22)See Terry Eagleton,Materi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p.6-7.相片的物质性,正在于它的这种使意识无力的难以屈服的柔韧性。巴特分析道:“相片属于那种叠压在一起的对象的种类,在不毁灭它们两者的情况下是不能分离出它们的两层来的。”(23)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6.没有外框与内容间的区分,如同巴特认为的黏连于一身的窗玻璃或风景、善与恶、欲望及其欲望对象一样,相片自持其特有的顽固性(24)See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76.。进一步推进巴特的这一观点则是,相片是一个背景与前景彼此相溶、明与暗彼此成就的活跃地带。它在洋溢着一个“一视同仁”的世界,“即任何叙事行为和意义跨越都无法穿透的整块”(25)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是一种谁也无法动摇的神秘整体性。穿插于《奥斯特利茨》中相片的这一物质性情感,不仅证实着奥斯特利茨已置身其中的稀缺性事实,同时也引发了由自我起源的焦虑而寻找父母的记忆活动。换言之,感受到自身即为无中生有的奥斯特利茨,不仅震惊地意会到置身其中的“我”的稀缺性,同时也在一种原乐化的陌异性情感驱力中,强制性地重复证实着其无中生有的父母之稀缺性事实。由相片物质性触发的这种“把主体作为现在还有点谜团的东西,而且人类全体成为相互之间稍稍有点不可思议(或者说未知)的存在”(26)《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或借用梅洛-庞蒂的思考,相片的这一物质性,“不是串联诸多概念,而是描述意识与客观世界的混合、对躯体的介入以及与其他意识的并存。”参看梅洛-庞蒂:《电影与新心理学》,方尔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7页。的陌异化情感机制,证明了“意义只能在某些相互连接的存在里被发现……意义和神秘不可分割,而如果没有时间的流逝,它们就都不可能存在”(27)伯格:《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杰夫·戴尔编,任悦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94页。的记忆真相。
此处约翰·伯格将本雅明对故事的理解,转换为对相片的理解,也同样是《移民》能借穿插相片唤起大规模历史记忆的艺术动因。渗透于文本间的相片物质性“灵晕”,所起到的作用也如同本雅明对故事的分析,是既能“提供把事件镶嵌到世界的神秘大进程中的一种方式”(28)本雅明:《本雅明文集》,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第311页。,又从而能让“它保留集中起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释放出来”的情感记忆。因用木炭笔作画,《移民》第四章中弗伯的皮肤出现了金属光泽,叙述者感到弗伯的存在状态仿佛海市蜃楼中的沙漠。如同奥斯特利茨,弗伯在这里也成了一张在显影液中显影难分的相片。皮肤变黑实际也让弗伯想到了曾在报纸中读到的关于银中毒的摄影助手,后者的身体因长时间吸收银元素以至变成了感光板。弗伯甚至补充道,这个摄影助手的脸和手臂会在强光下显影成蓝色。(29)See W.G.Sebald,The Emigrants,trans. 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164.在松散的情节逻辑中,出现的弗伯的这段突如其来的关于摄影的回忆,暗示了相片的光影物质性对情感机制所起的建构作用。南希分析认为,相片在诞生之时便节省自身,在洗印时又返回摄影之时,后者让我们感知到一种熟悉的即刻性。(30)See Jean-Luc Nancy,The Ground of the Image,trans. Jeff For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p.106,pp.105-106.换言之,南希的思考依然延续了相片转瞬即逝的物质性,或由其引发的稀缺性他者意识,依然确认了作为主体的弗伯即使想要隐遁于无形但却已与世界黏连于一身的感光板存在状态。它是一种“呈现被置于客观世界之中、承受着他人的目光、从他人那里知晓自己身份的意识”(31)梅洛-庞蒂:《电影与新心理学》,方尔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6页。之曝光,而这一曝光同时又是一种令主体感到焦虑不安的“无中生有”,是一种始终悬挂在他人目光上的主体之形成的事件性“过程”,它在形构着一种主体与他者之间密不可分的有其无限深度的物质性伦理关系。《移民》里相片的这一物质性的陌异化情感,通过一种接近封印的方式(32)正如列维纳斯的思考所示,“铭于存在之中并不等于铭于世界之中。从主体通向客体、从自我通向世界、从一个瞬间通向另一个瞬间的道路并不从一个存在者在存在中被置放的位置上穿过——这个位置只能由人类自身存在所唤醒的不安定感、对一向如此熟悉的‘身在此处’这一事实所产生的陌生感,以及如此不可避免、如此习以为常但又突然变得如此无法理解的对这个存在之承担的必要性来揭示。”参看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125—126页。,承认着南希所言的“我们这些人”的稀缺性,强制性地重复唤起了关于包括弗伯父母在内的死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受害者记忆。(33)值得注意的是,对“稀缺性”的感知,实际源于摄影与死亡的暧昧关系,阿斯曼描述了摄影为何能录入死亡进而引发记忆的过程。“对于死亡的突然顿悟,就像一道闪电,以超自然、超人类的图像把它埋入我的身体,就像埋入了一个神秘的双重痕迹。”阿斯曼所言的这种与相片有关的“刻印的直接性”所蕴含的双重性,导向的则是一种在死亡中瞬间瞥见到的生之稀缺性。参见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1页。赫绪(Marianne Hirsch)说道:“当我们看着来自丢失的过去的世界中的摄影图片时,尤其是那种被强力所销毁的世界时,我们寻找的不仅是信息或确认,我们也在寻找一种亲密的物质性的或者情动性的联系(material and affective connnection)。”参见Marianne Hirsch,“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Poetics Today,Vol.29,No.1,2008,p.116.这里提到了相片的物质性与情动性之间的关联。相片的物质性所揭示的作为感光板存在状态的主体,与德勒兹讨论的倏忽即逝的情动有着关联性。情动是一种时间性的呈现,可参见德勒兹在《前高原》中以洛尔迦等诗作展开的对瞬间与永恒之关系的讨论,这里不再复述。
《眩晕》第四章中叙述者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W。在早已物是人非的W及其完全变样的恩格尔维特客栈,叙述者想起在1948年或1949年间的冬天在那儿上演的席勒的剧目《强盗》的情节。这段往事给叙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强盗》露天表演时的情景,其中强盗摩尔骑马出场,叙述者记叙道:“我相信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我第一次注意到马总有着一种莫衷一是的疯狂的目光”(34)W.G. Sebald,Vertigo,trans,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190,p.190.。如其他三部曲一样,文本此处插入了一张骑着马挂着长剑的摩尔,以及在背后展开的一棵树木的相片。在叙述者的记忆中,这是在W的最后一次剧目演出。“只有在狂欢节期间演员们才会再次穿上戏服,加入到狂欢的游行中并且与消防队和小丑们一起在他们的位置上拍摄集体照片。”(35)W.G. Sebald,Vertigo,trans,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190,p.190.之后,笔锋突然一转,叙述者终于看到了在按了多次响铃后倏忽出现在前台的一个女人。
相片成了命定的过去与倏忽而至的现在间的缝合点,浮现在相片中的马、树木、演员摩尔、房子,狂欢节期间的群像与突然浮现在前台的女人间的时间分界线消失了。相片的灵媒化物质性及其走向陌异的情感地形,不仅“确认着你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感”(36)约翰·伯格:《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杰夫·戴尔编,任悦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93页。,也“生产”着一种过去与现在难分彼此的时间性眩晕,即我们仿佛都被陈放在一个时间失效了的世界中的神秘情景。这就是光影互相成就的相片物质性所具有的情感施演性,它的媒介化过程在这里就意味着它的非明非暗的灵媒化,而它的灵媒化就在于证实着一个与世界通连着的在银度和数值度间飘忽不定但却无法被分有的主体(37)See Jean-Luc Nancy,The Ground of the Image,trans. Jeff For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p.106,pp.105-106.,即令意识敬畏的“我是一个他者”的陌异化事实。如同狄金森感知到的“暗者”,是恐怖、着迷和欣喜并列共存的情感状态(38)参见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布鲁姆分析狄金森的思路,也呼应了从艾略特“消灭个性”到布朗肖所言的“和激情、性格、品行相关”的混杂性情感意识。这些实际依然可以回溯到利奥塔思考的物质与精神相互连通的思想:精神的物质性或者物质的精神性,揭示了主体只是一种“转换器”,而情感的陌异化现象,也指明了主体作为“变数”或“杂多”的本质。参见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1—11页;布朗肖:《未来之书》,赵苓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Jean-Francois Lyotard,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46.。这是一个与世界难解难分总处在扩散情势中的主体。南希分析认为,相片所呈现的永远都是一个处在效价化与趋势性中的主体(39)See Jean-Luc Nancy,The Ground of the Image,trans. Jeff For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p.168.,如同《强盗》的剧情中摩尔的身份在贵族、强盗与凡人之间游移。“呈现就是相对化,就是放在上下文和呈现的条件中,在这一情形中就是可塑的上下文与条件”(40)Jean-Francois Lyotard,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26.,但相片的物质弹性并不塑造事物从中浮现出来的条件,而是曝光事物与世界间彼此共享的事实。其中作为一个点的稀缺性主体,在分享一个不断扩展的面的世界时,是一个自身确定性不断消减,而自身他异性不断增强的情感化光影过程。这是一个在扩散中愈发坚韧的主体,是一个被世界所强制性分享的他者。因此,过去的演员摩尔、消防队员、小丑和现在的女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在伯格所言的传染着我们的世界面前消失了,而它所强制性重复唤起的则是1949年前第三帝国的种族政治导致历史灾异的大规模记忆。
同上,在《土星之环》第八章和第十章中分别插入的两张有关制糖业和蚕丝养殖业的相片物质性,也在证实着塞巴尔德的用意。虽然相片在其中指涉的是在历史进程中被束缚在田间与蚕丝板上的制糖工与蚕丝工,但它也同时揭示了“自我的古老主权”(41)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8,pp.76-77.。这同样是一种让时间失效的不受侵犯的“在那里”(42)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8,pp.76-77.。塞巴尔德说道:“它只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观看事物时的残余。”(43)Eleanor Wachtel,“Ghost Hunter,” in Lynne Sharon Schwartz,ed. , The Emergence of Memory:Conversations with W.G. Sebald,London:Seven Stories Press,2007.而这种幸存下来的更为古老的观看事物的方式,或它所意指的与物质世界无法分离的“暗者”,唤起的则是大规模的生命在求新求变求快的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被抹除的记忆现实。概言之,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灵媒化的物质性,不仅重复地施演着自我从乌有到世界这一坚不可摧的陌异化情感,也重复唤起了置身其中的“我”即南希所言的“我们”这一令读者眩晕的记忆伦理。作为无法穿透的整块化相片物质性,揭示了“我”是一个占据一片空间的存在,一种与他人共同失根的“微妙的威胁”(44)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如果说“摄影承载了一种见证,人类正在给定条件下实施自己的选择”(45)约翰·伯格:《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杰夫·戴尔编,任悦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3页。,那么由相片物质性施演的这一双重“强制性”情感机制,唤起的却是在破坏这一给定条件下出现的无数历史灾异及其难以定位的记忆矢量(46)在卡尔维诺的思考语境中,通过借鉴数学中具有大小和方向的动力含义,“矢量”一词指明了文学意义是一种介于轻重之间、若有若无的自显运动。在本文的思考语境中,相片物质性激活的“过量”记忆,实际就是一种无法从理性筛选到沉淀为静态对象的矢量化记忆。参见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1—12页。。
二、作为传导:从不谐到调谐
如果说穿插于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的相片,在一种灵媒化的物质性光影中,揭示了主体是一种无法从世界脱身而出的“稀缺即过量”的强制性曝光过程,那么,当“让技术与魔术间的差异作为一个完全的历史性变数可见了”(47)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2,trans. Rodney Livingstone,et al.,W. Jennings,et al.,eds.,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512.之后,流动在四部曲叙述流中的相片,又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整全世界的解世界化过程,即“一种不断延搁的急迫性,一种某事会在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的均等的可能性”(48)德勒兹:《〈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董树宝、胡新宇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8页。之世界。这一“世界的存在不能以任何方式停止它不可理解的性质”(49)巴塔耶:《内在经验》,程小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96页。的陌异化情感地形,往往不是由叙述途中的单个相片绘制的,而是潜伏在叙事进程中不同相片间的物质性所形塑的陌异化关联之中。换言之,这是一个在语言文本之外有着自己语言的相片文本。远景与近景的相片之间,静景与动景的相片之间,物景与人景的相片之间,或者篇首与结尾的相片之间等,以及将它们打乱后的再分配过程,没有任何意指关联的相片与相片“之间”,所生成的陌异化物质关联及其歧义性曝光过程,成了塞巴尔德的四部曲情感记忆的另一种表征方式。
《移民》的第一章“塞尔温大夫的自杀”与第二章“贝瑞特的自杀”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紧迫性”,虽然是《移民》给读者制造的智性焦虑,但也是文本能够继续下去的推力。陌异化的“紧迫性”本身,成了答案,或是答案的一种变形。除了叙述风格外,这一叙述推力还能从分布在两章的相片间的关联中找到。在第一章塞尔温大夫的故事中,叙述者讲述道:退休后的塞尔温大夫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在花园角落的一个燧石筑起的房屋中隐居。偶然的一次,叙述者看到塞尔温大夫正在用枪支瞄向蓝天,“当他最终开枪后,对我而言仿佛是一阵永恒之后,枪声带着碎裂的碰撞落下花园”(50)W.G.Sebald,The Emigrants,trans. 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11.。此时,文本中插入了一张塞尔温大夫隐居其间的燧石屋,看上去仿佛史前的遗迹,既触目又隐晦,而随着叙述的进程,塞尔温大夫最终用同一支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第二章贝瑞特的故事中,叙述者开篇便叙述他的小学老师贝瑞特在74岁生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卧轨自杀,此处配有一张近处有钢轨和云杉、远处有山脉及天空的相片。一张相片里看上去坚硬的燧石屋,与另一张相片里看上去带有铁轨的柔和风景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两个人物的自杀。两张相片构成了朗西埃所言的一种并非苦中作乐的“双重诗意”,依然保留着“美学关注的悬置可能性”(51)《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75页,第124页。的燧石屋,“充当某种直接记录在无名者外貌、衣着和生活环境上的状况的无声见证人”(52)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第20页。。因为在花园角落看上去乌黑一片的燧石屋,就是塞尔温大夫在世界中的处境:笨重、孤孑、哑然,人物自身成了物体自身,这是一张“不再是符号而是事物本身”(53)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45.的相片。而有关贝瑞特的风景照,“又充当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知晓的秘密的持有者,这是向我们提供外貌的图像所掩盖的一个秘密”(54)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第20页。。鲍德里亚分析摄影时说道:“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个景色而把它拍摄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只不过是配角而已。主体只不过是一个要素而已,作为结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是主体才使得事物显现。”(55)《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75页,第124页。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能够让景色显现自身的作为“秘密”的稀缺性主体贝瑞特(56)之所以为秘密,源于相片以其特有的物质性风格,保留了一种主体与物质间的亲密性深度,列维纳斯写道:“一旦我睁开双眼,被构造者之向条件的‘转变’就实现出来了:唯有在我已经享受景色时,我才能睁开双眼。”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页。,却在涌来的火车前闭上了眼睛。成为燧石屋本身的塞尔温大夫,与如风景一样敞开的贝瑞特,最终在塞尔温大夫用枪瞄准天空之蓝时,实现了一种大规模的曝光,一种史无前例未完成的陌异性情感姿态(57)参见巴塔耶:《内在经验》,程小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57页。,诱发了“一战”前到“二战”后犹太人流亡与覆灭的大规模历史记忆。相片间这种陌异化的物质性关联,所形成的解世界化的传导性,激烈地调谐着那些试图将其遗忘的历史所具有的不谐意图。
正像《移民》中贝瑞特的恋人海伦及其母亲最终有可能被闷罐火车遣送到特雷西亚施塔特集中营一样,《奥斯特利茨》中奥斯特利茨的身世之谜,也是通过相片与相片间陌异化的物质性关联得到曝光的。奥斯特利茨曾与好友杰拉德一起度假,观赏风景、讨论鸽子的迁徙、观察飞蛾的习性以及与杰拉德一起在夜晚飞行。当讲到与杰拉德一起在飞机的座舱中感受如浮雕般从大地浮现的泰晤士河河口与镶满各式星座的移动的天穹时,奥斯特利茨说道,“他(杰拉德)讲到有巨大范围的星际气体如同暴风云一般被聚集成向虚空发送出若干光年的浩瀚的不断翻腾的形状,在重力的影响下新的星体会在一种稳步的逐渐加强的压缩过程中诞生”(58)W.G.Sebald,Austerlitz,trans. Anthea Bell,London:Penguin Books,2011,p.163.。杰拉德的这一说法,在奥斯特利茨看到哈勃望远镜拍摄到的一张宇宙空间的相片时得到了确认。在之后的一次飞行途中,杰拉德再也没有回来。随着后起的叙述,奥斯特利茨向叙述者讲到自己前往布拉格查询自己身世档案的经过。档案馆门房的对面是一个来访者需要进行登记的地方,没有过多描述而只是给出了一张相片。相片上有一面白墙,三张参差不齐的桌具,以及稀疏摆放的表格和文档,墙壁上还挂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时钟。杰拉德的叙事情节与相隔甚远的档案馆经历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不再能从叙事逻辑中得到推导,而只能从插入文本的两张相片间的物质性关联中显露出来。
列维纳斯在分析摄影时写道:“这种在我们和事物之间安插一个事物的形象的手段,产生了让事物脱离其世界背景的效果。”(59)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5页。借助相片,需要奥斯特利茨登记并从而能接下来帮助奥斯特利茨找到其身世档案的场所,成了一个从世界背景中脱离开来的在白墙、桌子、时钟以及表格间游弋不定的存在。“图像不再是一种思想或一种情感的编码式表达。它不再是一个复本或是一种解译,而是事物说话和沉默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它进驻到事物的中心,成为无声的言语。”(60)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18页,第18页,第19页。这是一张始终处在潜势中的相片,因为它“是事物直接记录在其(奥斯特利茨)身躯上的意指,是有待解读的事物的可见语言。”(61)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18页,第18页,第19页。南希为此写道:“相片的秘密,它的迷失和偏离的最为清澈的神秘,就在于它逃进了熟悉之物最为中心的陌生里。”(62)Jean-Luc Nancy,The Ground of the Image,trans. Jeff For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p.106.这一陌异化情感还可以追溯到列维纳斯思考的“身体即置放”所引发的情感极化现象,相片的物质惰性在某种程度上摹拟着一种难以预测的灵魂之情状,它完成了某种令灵魂不适的“注册”行为,其中没有任何可能引发暴力的超越之可能。列维纳斯写道:“超越并非存在论历险的根本性步骤。后者是建立在置放的非超越性之上的。情感的模糊决不是对光的简单否定,而是为这个先行事件提供了佐证。”参看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如果说这是一张朗西埃思考的事物说话的相片,那么宇宙星云则是一张“剥下所有特性”(63)《西方摄影文论选》,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的事物沉默的相片,是朗西埃所言的“从反面向事物和存在者借鉴了无意义物的辉煌”(64)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18页,第18页,第19页。时刻。在后者的无意义生产中,诞生了一个具有身体且试图通过飞离地面而远离晦暗生活的杰拉德。两张间隔遥远的相片,通过“成为身体承载记录的进程和身体赤裸在场而又无意指的中断功能之间的转移”(65)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18页,第18页,第19页。,而实现了一种陌异化的情感机制及其曝光功能,唤起了杰拉德的关于在“二战”最后一个冬天从空中被击中并落入阿登高地的父亲到奥斯特利茨的被遣送至特雷西亚施塔特集中营并无故蒸发掉的母亲间的大规模死于战争的受害者记忆。通过相片间所产生的这一陌异化的物质性关联,近在咫尺的登记身份的桌子,与置身其中的深远星空间,哪个能够陈放更多的档案?诞生星体的浩瀚宇宙,也在诞生着一个凝望着桌子却无迹可寻的奥斯特利茨。登记在案的奥斯特利茨,与诞生在星云间的奥斯特利茨,哪个更为真确?挂在墙上静默的时钟,与旋转的天穹间,哪个更有准度?极近的事物与极远的事物间界限消失的时刻,也是世界在解开自己的时刻,因为主体所看到的总是少于主体将要看到的。这“是解开物的威力,是从未开始的东西的威力,它从未被连接过,可以将一切带进它那没有年龄的节奏中”(66)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第77页。,以一种陌异化的情感调谐方式,“让一个世界背后的世界显现出来:家园舒适后面的遥远冲突”(67)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第77页。。
朗西埃写道:“存在一种非思的思想,思想不仅是不同于非思的元素,也是以非思形式来运行的。”(68)朗西埃:《审美无意识》,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页。在相片间的物质性关联所形塑的陌异化情感机制及其曝光中,《土星之环》与《眩晕》也同样是一种解世界的过程。这一由物质性的陌异情感触发的大规模濒临消亡的记忆伦理,让习以为常地将记忆视作存储工具的物化思维自行失效。相片间陌异化的物质性关联,也在绘制着主体“误入歧途”的陌异化情感地形。可以说,穿插在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的相片间的陌异化物质关联,成了克服现代性主体将所见之物自动标准化也即遗忘的重要艺术方式。因为确如克拉里认为:“正当技术文化内的专注知觉持续不断地获得自动化形式的历史时刻,被认定为‘自动’的人类行为模式却被判定为具有病理性和社会危险性……其中‘心智器官’的最高活动出现缺失……包括‘记忆、情感、推理和自主行为’。”(69)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 Modern Cultur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p.147-148.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相片与相片间的物质性关联,所形塑的无法被稀释的陌异化情感地形,才能有其令人生畏的伦理意向——一种从不谐到调谐的曝光中的历史真相,也即解世界的传导过程,才能在文本之间发酵且蔓延。因为,归根结底,相片揭示了桑塔格所言的人们在其中的不安全的空间(70)See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New York:RosettaBooks,2005,p.6.康德认为过去蕴含着一种崇高的情感维度,而本文探讨的相片物质性,则让这一崇高化的情感更加激进化,因为康德分析的崇高与弗洛伊德思考的“多重决定”的情感机制间,存在着深度的介入关系。康德在其中写道:“如果它是展望着无法窥见的未来的,那么它就具有某些令人畏惧的东西。”参见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5页。。
三、作为悬搁:从背景到前景
从被世界分享的整全式存在感知,到分享存在的解世界感知,是相片物质性在其特有的陌异化情感显影机制中,撒播大规模历史记忆的两种方式。空间、色彩、体积、阴影、深度等关于摄影的语言游戏,揭示了相片是一种“浮现”中的物质性艺术形式,并让塞巴尔德本就离散化的散文语言,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物质助推力。本文第一节的作为过程的相片与第二节的作为传导的相片,是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两种让记忆矢量浮现的物质性情感方式。而这一节我们即将探究的,则是穿插于四部曲中的相片的第三种物质性,即相片化的物质性人脸在陌异化情感机制中浮现时,如何诱发大规模记忆矢量的过程。塞巴尔德选择的相片,绕过了巴特认为的好相片不是像这个人而是就是这个人的判断标准。更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摄影本身第一次即最后一次的物质性的悖论式定格,却成就了作品中人像面容的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的复多性浮现。相片化的物质性人脸,是总在一种定格中悖论地浮现着的他者现象。(71)对应前两章,物质性相片呈现的脸,既有着整全世界的自足性,又有着解世界的他异性。我们将会看到,四部曲中在相似与不相似间游牧的“脸”,也是塞巴尔德通过相片的陌异化物质性,曝光大规模历史的情感“地貌”。
相比于追求叙事逻辑中一以贯之的完整性,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从不缺乏对于溢出之物的执迷。心领神会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常有的感受。读者与作品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共契,得益于作品自身总会“节外生枝”的形式。而在相片系列中偶然出现的人脸,则是这一在意义与无意义间不断偏转的形式中最为节外生枝的参数。在《土星之环》第八章中,叙述者来到了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长大的地方伯奇庄园,叙述者在其简洁的笔墨中就勾勒出了菲茨杰拉德1809年到1883年的生命痕迹。本就渐趋虚化的叙述写法,直到在插入菲茨杰拉德生平唯一的一张相片时,获得了一种聚焦感。然而,这张呈现侧脸的人像相片,不仅没有使读者原本模糊的叙述视象变得清晰,反而让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描述愈加迷离。菲茨杰拉德向其侄女们带有歉意地解释道:“如果他直视着照相机,他患疾的眼睛会眨得太多”(72)W.G. Sebald,The Rings of Saturn,trans. 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206,p.89.的说法,并不是生理性不适,而是拍照过程中一种本质性的心灵失调。因为根据巴特的分析,拍照过程实质上是一种不确定的出生过程,“我感觉到按照它的变幻无常,摄影造就着我的身体或者让它腐坏”(73)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p.11.。菲茨杰拉德的眨眼,即是在出生与不出生间的短路(74)这是一种在消隐的过程中却逐渐增强的陌异化主体形态,列维纳斯对科学小说的哲学理解同样适用于相片,列维纳斯写道:“在此意义上,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人们在诸宇宙空间里把我找寻了出来,就并非科学小说之虚构,而是表达了我作为己所具有的那种被动性。”参见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6页、第254页。,而这一点又是由相片第一次也即最后一次的物质性悖论所决定的。同时“拍摄人物照片非常之难。因为对于心理焦点不太准确的人,要用摄影来聚焦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是谁,人都是表演的场所,复杂的(解)结构的场所。镜头反而无法捕捉人的性格。因为人负有太多的意义。”(75)《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人并非一个在诸多不同的意义背景中被合理给定的存在者,而关注人的面部表达的肖像照片更是如此,原因在于“人们无需解释面容,因为,一切解释都是从它出发开始”(7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第252页。。相片中溢满物质感的稀缺性人脸,让时间的老化能力,陷入了一种陌异化的情感性“停顿”。
在菲茨杰拉德的面部相片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不愿出生的过程中却不断诞生的事物,一个以悬搁的方式不断临近的曝光之物。相片上的物质性人脸自在地形成了一种让主体陷入时间性眩晕的“自旋”运动。这种相片所特有的物质性,让人脸处在聚精会神与分崩离析之间,一种令读者天旋地转的陌异化情感记忆得以被启动。这张总在飘离意义之网的脸,唤起了菲茨杰拉德痛苦的童年时期在如水晶般清澈的蓝天里隐约看到的离海岸十公里以外的白帆,以及与早逝的挚友布朗乘坐马车穿过野外,看着云朵东去,感受时间碰触太阳穴时的大规模记忆。列维纳斯写道:“面容在泄露中一直保持着神秘与难以言传;这种泄露恰恰通过它的越界的过度而证明自己。”(77)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第252页。在菲茨杰拉德这一过度曝光的相片中,由相片物质性呈现的陌异化面容就是非结构,而它所唤起的则是拥有大量财富与农奴的母亲,与征战欧洲大陆的威灵顿公爵形象彼此叠印在一起的大规模记忆,是从菲茨杰拉德1809年出生到1883年故去间欧洲大陆的所有血雨腥风。
正如《土星之环》中菲茨杰拉德的相片的物质性揭示的是一张未定型的浮现中的面容,《移民》中对菲尼姨妈、泰勒斯姨妈和卡西米尔舅舅的叙述,也插入了一张三人童年时期的肖像照片。根据菲尼姨妈的回忆,三个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从德国离开前往美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移民的一代。然而,落地生根并没有在三个人的故事中发生。泰勒斯姨妈在死前如同一个当地的陌生人一般连续几个月地四处走动,死后只留下胡梅尔制作的儿童肖像。卡西米尔舅舅在见到“我”后也难以平静,走来走去,并带“我”到一眼望去一无所有的海边说道:“我经常来这里,它让我感到我已经离开很远了,尽管我从来都不知道是从哪里离开的。”(78)W.G. Sebald,The Rings of Saturn,trans. 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206,p.89.沉浸往事的菲尼姨妈在“我”离开时从后视镜中向“我”挥动手绢,在车子喷出的雾气中逐渐变小。三个人在移居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却依然处于“无依无靠”的心灵处境,被三个人童年时期的相片进一步加剧和强化了。在相片中,我们看到曾是孩童的三人从一片以故乡风景为背景的画面中浮现出来。然而,如同这故乡的风景是人造的虚假背景一样,三个人此后的未来也再没找到为其赋予存在来源的真实的故乡背景。没有找到的原因,并不是真的要把自己融进各种关于故乡的叙事话语中,也不是在历史地理上标记出故乡的物质存在。因为正如相片中三张神态各异的脸之间含混的物质歧义性所暗示的,主体之间作为混杂的谜团,或如布鲁姆评狄金森时所言的作为诸种“斜光”或“非自然的诡异自我”(79)参见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正是通过脱离背景的物质性面容自显的陌异化情感地貌获得呈现的。
“人们期望照片可以赋予一种叙事性的象征主义,作为一个符码,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寓言,毫不含糊地表达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并增加可以明白无误地建构一个(它被假定应该承载的)事实话语的标记方式。”(80)《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75页。但呈现在这里的带有古典油画意蕴的三张物质性面容,却成了有别于虚假背景的真正风景。过了半个世纪的菲尼姨妈哀伤的面容,泰勒斯姨妈泪眼蒙眬的面容,卡西米尔舅舅忧郁的面容,彼此汇流为一张再也无法辨认的陌异之脸。相片第一次即最后一次的物质悖论性,捕捉到的只是从背景来到前景中让线性时间失效的脸,印证了“人类的脸是有待讲述的故事,是有待探索的地理”(81)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38页。这一飘忽不定的陌异化物质真相。它所唤起的则是“二战”前经济危机爆发,纳粹党人势力迅速蔓延的一张承载着过量历史记忆的脸,这张陌异化情感之脸,如列维纳斯所言的无法再现的“情节”,决定了“我们总不免堕入任何辅助学科的严格性都无法保障避免的虚空:要去命名主体,去将它归属于状态、情感、事件”(82)朗西埃:《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魏德骥、杨淳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人像相片总周转在背景与前景的关系中,相片的这种失败也是它得以被留存的原因。因为人像摄影始终面对着一张难以捉摸的脸,人像相片的物质性就是难以安放无中生有的人脸的急迫性。奥斯特利茨对叙述者讲道:“我在斯托尔·格兰奇拍摄了数百张相片,大多是方形格式,但是将照相机的取景器对准人们让我总觉得不对劲。”(83)W.G.Sebald,Austerlitz,trans. Anthea Bell,London:Penguin Books,2011,pp.108-109.人不是有一张脸,人即是脸。相片的陌异化物质性,让介于稳固与解体之间的飘忽不定的人脸,建构出一种激进化的记忆伦理。如同列维纳斯所言,“他人的面容在任何时候都摧毁和溢出它留给我的可塑的形象,摧毁和溢出与我相称的、与其ideatum(所观念化者)相称的观念——相即的观念。它并不是通过那些性质显示自身,而是(据其自身)显示自身。它自行表达。”(8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脸即是坐落在人身上的总是从背景来到前景中的他者。也因此,奥斯特利茨后来看到一张自己童年时的人像照片却并不敢触摸它的忧惧感,正源于这张在物质性氛围中从背景来到前景的陌异之脸传递着飘忽不定的情感之力,“他里面的一切都在看我,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85)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5页。,一张自我言说的宇宙“显影”。这是一张在离开布拉格六个月前,也就是1939年2月拍摄的相片。相片中的奥斯特利茨穿着一身雪白色的服装陪同母亲前去参加化装舞会。从叙述中我们得知,奥斯特利茨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护送玫瑰皇后即母亲的少年侍卫的角色,但需要守护的母亲却没有出现在相片中。就像六个月后被母亲护送上从布拉格前往英国的逃亡专列一样,被遗留在历史灾异中的却是奥斯特利茨的父母。这张从背景中突兀出来的歧义性面容,打开了一种无限的情感空间。在守卫与质询间摇摆不定的这一“情节”,证实着一种巨大的辜负感。“我经常感到这个听差男孩那刺人的探寻眼神,他要来索取他的应得之物,他在黎明的灰光中站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等待着我接受挑战,去除即将迎接他的不幸。”(86)W.G.Sebald,Austerlitz,trans. Anthea Bell,London:Penguin Books,2011,p.260.相片变幻莫测的物质性强制重复人脸的稀缺性之事实,契合了阿甘本的思考,他写道:“就像在那些照片——一个陌生人的遥远却又过度切近的脸从照片往外注视着我们——中那样,这污名的某种东西急切地要求着(esige)它的专名,在一切表达和一切记忆之外证明着自己”(87)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第31页,第36页。。
《眩晕》中的叙述者在靠近故乡W时站在一个石桥上久久地观望,“聆听着河流安稳的潺潺声,观察着现在包裹一切的黑暗”(88)W.G. Sebald,Vertigo,trans. Michael Hulse,London:Vintage Books,2002,p.183.。在与卡夫卡的《城堡》十分近似的开头之后,叙述者回想起“一战”后曾在石桥边扎营的吉卜赛人。在“二战”即将爆发的1936年,每次经过这里去往确保公共健康的游泳池时,母亲都会不自觉地将叙述者抱起来。至于吉卜赛人为何大规模地迁徙,直到叙述者翻阅战争期间圣诞节时父亲买给母亲的相册集时才恍然大悟。文本此处插入了一张于波兰集中营拍摄的一位抱着婴儿的吉普赛女人,那是一张在斯洛伐克某处偏远的角落拍摄的相片。在这里,叙述者接着叙述道,“我”的父亲和他所在的机动维修部队,早已在战争爆发前的数周前就驻扎了下来。可能是因为怀里的婴儿使然,相片截取的只是吉普赛女人平和的微笑。作为背景的集中营,并不是微笑的意义来源,换言之,这是一张有其陌异性的面容。相片无法为自身赋予意义,只能借助布迪厄认为的诸种社会感知场域进行赋意,“即使是象征性的照片,如果没有什么功能能够直接被指派到它身上,也会被拒绝,正如非形象的绘画因为无法显示出一个可以辨认的客体,即不能暗示与人们熟悉的形状的类同性,而被拒绝一样”(89)《西方摄影文论选》 (修订版),顾铮编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75页。。但这也同时说明了相片第一次即最后一次的即时性悖论特征。这种不容涂改的物质性的档案化感知形式,如阿甘本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捕捉到了审判日”(90)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第31页,第36页。。相片转瞬即逝的物质性,抓住的是历史断裂的瞬间,而这一瞬间最为醒目的来源,就是相片中从背景来到前景的有其情感地貌的人脸。吉普赛妇女神秘的微笑下,是一个正在长出一张脸或正在形成一种“情节”的婴儿,“它们要求不被遗忘”(91)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第31页,第36页。。
塞巴尔德总在偏离的叙述风格,是对总在趋同的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抵抗策略,而通过相片第一次即最后一次的悖论物质性揭示人脸即“情节”的陌异化过程,这一抵抗策略获得了更为深广的振幅。现代性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事物之复杂性的消解能力,而这一切事物的尽头,就是一张无法简化的陌异性人脸。福柯洞察道:“所有这些内容(他的知识把它们作为外在于他本人而揭示给他,它们的诞生要比他早并预料他)把它们所有的协同性都悬在他上面,并跨越了他,似乎他只是自然的一个客体,一张在历史上必定被抹去的面孔。”(92)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08页。塞巴尔德四部曲中穿插的物质性人像相片,是为了在其陌异化的情感机制所形成的差异性张力中,让被历史灾异抹去的面孔重复自身。相片的物质性所呈现的悖论的即时性,不断确认着作为情感之源的脸,是意义链上脱嵌的部分这一真理。故而,相片中强制化的“重复性”人脸,就在悬搁着所有即将对历史灾异所作的定论,让读者在避开既定历史叙述的同时,被“误入歧途”地带进有着积极模糊度的历史真相之中(93)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相片物质性作用下的事后性所引发的积极模糊度,参见Gerhard Richter,“Afterness and the Image(I):Unsettling Photography,” in Afterness:Figures of Following in Modern Thought and Aesthe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四、结语:“真理总在惶惑不安的背后闪闪发光”
本雅明分析道:“从阿特盖起,照片开始成为历史进程的证明材料。这就使它具有了隐含的政治意义。它要求某种特定的接受,对此,神游八极的冥思已行不通;照片使观看者不安,使他感到:要看懂它们,就得找到一条特定的路。”(94)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正如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方向,相片令观者“误入歧途”的原因,实际在于相片能够借助其物质性所生成的陌异化情感地形,对趋向惰性的历史意识进行重置的记忆功能。塞巴尔德在谈及相片时说道:“我认为没有照片就无法抓住在那里的某些事物……并不必须要被放入书本,而是为了一种起作用的过程。如果你足够长时间地盯着它们看,特定的事物会从这些图像中浮现出来。”(95)“Qtd A Symposium on W. G. Sebald,” The Threepenny Review,Vol.89,2002,p.20.相片不是道德说教,也不是审美快感,更不是知识确证,但是相片却在一种转瞬即逝有其模糊度的物质性中,蕴蓄着一种不断弱化主体的趋近极性的陌异化情感,是一种通过意义的回撤而裸露历史真相的撒播时刻(96)See Jean-Luc Nancy,The Gravity of Thought,trans. François Raffoul and Gregory Recco,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7,p.71.。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塞巴尔德的四部曲中,作为一种视觉性叙事的相片物质性,通过不断“生产”着一种陌异化的情感灵晕,而让作品“起作用”,也即让作品处在一种布朗肖所言的“神圣压力”之下,“以它无以言表的神圣情感,微微的情感,挑动着我的动脉”(97)参见布朗肖:《未来之书》,赵苓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塞巴尔德的这一从叙事动脉转向视觉动脉的艺术变革,实际都与20世纪初期艾略特在其文学传统中发现的取消个性和取消情感的诗学洞察形成呼应。艾略特对于整个诗学传统的提炼,并不是真的取消情感,而是揭示了情感是一种不同诗学元素的化合结果,也即本文前三节分析的,由物质性模糊度而生成的不同于常规情感形式的转瞬即逝的极性化情感结构。这一分析反过来也说明了诗学情感无法被归属到任何一种类别的情感样态中,它呈现出一种弗洛伊德所言的多重决定的陌异化地形学形态,也因此在20世纪后期被布鲁姆以“影响的焦虑”为题接续并转化为对整个文学史的考察。塞巴尔德的作品中相片的视觉物质性叙事,以一种跨媒介的艺术方式参与到这一情感诗学传统中,不仅扩展了情感诗学的地貌,也同时让“真理总在惶惑不安的背后闪闪发光”(98)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藏仲伦、曾思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498页。的情感-记忆,获得了一种潜势化的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