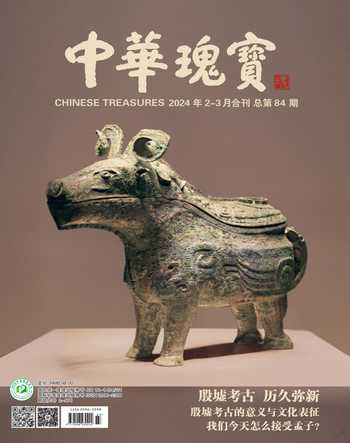殷墟甲骨文承载的文化基因



殷墟甲骨文对于今人而言有何意义?从这些早期文字中,后人可以探知到何种有价值的信息?
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包括商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两大类。其中,商甲骨文又以殷墟甲骨文为主。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在中药“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因此,1899年被视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之年,王懿荣也被视为发现殷墟甲骨文的“第一人”。
从被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就与殷墟遗址密切关联,而殷墟又是晚商时期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视为商王、某些子姓大贵族占卜的产物。由商王所主导的甲骨文被视为王卜辞。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卜辞始于商王武丁时期,经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诸王,终于帝乙、帝辛时期。由非商王的子姓大贵族所主导的甲骨文被视为非王卜辞,如著名的花东卜辞、午组卜辞、子组卜辞等。这些非王卜辞的年代均较早,多为商王武丁时期。
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商王及子姓大贵族占卜的产物,因而包含了丰富的商代政治、军事、宗教思想、社会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商王朝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我们还能根据殷墟甲骨文探索商王朝及其后世的文化传承、发展和演变关系,也就是探索殷墟甲骨文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本文即从多个方面论述殷墟甲骨文所承载的文化基因。
汉字传承渊源
中国的汉字源远流长。早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就记录了大量古文经中的篆书字形,将汉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时期。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金文对汉字传承的价值逐渐凸显,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收录有不少西周金文字体,从而将汉字的渊源追溯到了西周时期。至于西周之前汉字的面貌,则要在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后才得以知晓。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汉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简帛文字,再到汉魏碑文的完整发展历程逐渐清晰起来,由此确认了汉字至少拥有3200年的传承史。
汉字构造一般有“六书说”和“三书说”两种理论,前者如《说文解字》中提出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后者如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提出的象形、象意和形声三类。就殷墟甲骨文而言,“六书说”和“三书说”都可使用。
以“三书说”为例,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较多,如“”,像流水之形,故为“水”字;“”,突出大象的鼻子,像大象之形,故为“象”字;“”“”,像牛、羊之形,故为“牛”“羊”二字。象意字又叫表意字,甲骨文中的象意字不如象形字那般一目了然、容易辨识,需要我們去想象这个字背后的意思,如“”,以四条短画意指数字“四”;“”,表两人并立,意指“并”字;“”,以戈伐人,意指“伐”字;“”,表人睡在屋内簟席上,意指“宿”字。形声字是指有声符的字,如“”,为“圆”字,从鼎、圆声,其上的圆圈表示声符;“”,为“妇”字,从女从帚,“帚”亦是声符;“”,为“灾”字,从戈、才声,“”表示声符。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很多假借字,如常用“鼎”假借“贞”,用“亡”假借“无”,用“女”假借“母”“毋”等。总之,就汉字理论来说,殷墟甲骨文无疑是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与此后的汉字并无二致,是汉字文化的渊源。
当然,仅就字形而言,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点,就是象形字占比较大,象形程度较高,与秦汉以后的隶书、楷书差异较大。正因如此,殷墟甲骨文能够反映出商人的思想世界,为我们提供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线索。比如,中国人有龙崇拜传统,最早的“龙”字见于殷墟甲骨文,写作“”,与殷墟遗址出土的龙形遗物形象一致。甲骨文有“其作龙于凡田,有雨”的记载,是作“龙”以求雨的意思,这里的“龙”就是汉代文献中可以祈雨的“土龙”。可见,早在商代,龙就作为能够呼风唤雨的神秘生灵而存在于古人心里。
成熟的书写能力
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那么由文字所组成的典籍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内涵。《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代已有用毛笔书写的典册。学术界一般认为《尚书》中的“盘庚”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册,只是经过后人的转录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类似的还有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简牍《傅说之命》(上篇),其最初文本应该也是晚商时期的实录。
殷墟甲骨文是不同于典册的一类材料,它主要是为了占卜而产生的,典册则主要是为了记录某些事情而产生的,二者性质并不相同。不过,即便如此,殷墟甲骨文也具有某些与典册相似的特征,反映了晚商时期的人们已具备记录复杂事情的能力。比如,《甲骨文合集》137有一条号称字数最多的甲骨卜辞,全辞刻在甲骨的正反两面,从“癸丑卜争贞”至“才敦”,全辞约90字。这片牛肩胛骨刻辞还有两条与此辞相关的卜辞,三辞合计约154字,记载了某年五月、六月商王及其属下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涉及王、争、疫、左、单丁人豐、魚子豐、鬼、子潛等贵族,羌、刍等奴隶,以及奴隶逃逸、属下生病、方国战争等事项,时间、地点清晰明确,要而不繁,是较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辞。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为目的的材料,它所显示的诸如承前省略、避复等记录方法也能说明商人在书写文辞时已经懂得用辞考究,可见商人有着较强的书写能力。
类似的长篇卜辞尚有不少,如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子央坠车刻辞等,皆完整生动地记录了一个事件的经过,这说明商人记录事情的能力已极为成熟。由此,我们知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非虚言,商人是有能力书写典册的。
确立时间体系
中国人有着较为稳固的年、月、旬、日观念,这一观念最早可追溯至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商末的黄组卜辞中常见“周祭卜辞”,如《甲骨文合集补编》10943:“癸酉王卜,贞:旬亡忧。王占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册,其,唯王三祀。”这条卜辞中的时间概念有:祀、月、旬、日。
商末甲骨文中常见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并配祭先妣,遍祭一周即为一“祀”,此即“周祭卜辞”。由于遍祭一周用时为一年,故甲骨文常用“祀”表示年。至于甲骨文中的“年”“岁”二字,反而不用来表示今之年岁。因而,“唯王三祀”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祀”下有“月”,一祀可分十二月,闰年有十三月。“月”有三旬,每旬十天,商王常贞卜“旬亡忧”,就是想知道一旬即十日之内是否有灾祸。至于具体的纪日,商人已有六十干支的概念,并在一些甲骨文中详细列举了六十干支,是为干支表。上举卜辞中的“癸酉”“甲戌”,皆是干支纪日。
上述一套祀、月、旬、日的纪时体系,在商以后基本延续下来,周代以后的人们除了用“岁”“年”替代了“祀”,整个体系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今日所说的农历一年、十二月、三十六旬、六十干支日皆传承自商,这是商文化对中华历法的一大重要贡献。
完整的空间体系
商代不仅已经有了成熟的时间体系,还有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甲骨文中有所谓“四土”的概念,如“壬申卜,禱四土于□”“□申卜...四土...宗”“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又有“四方”的概念,如“其禱年四方,惠豚”“癸卯,贞:东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丁丑卜,王贞:商人受年”“西眔南比北眔东,不受年”“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七月”。
从上述卜辞中的“四土”和“四方”難以看出二者有什么区别,与它们对贞的“商”无疑是指商国,商人居于“四土”“四方”之中,故可称“中商”。“四土”“四方”即指以商国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学术界认为“四土”“四方”还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大的政治疆域。
以王所在之国(文献中称“王国”)为天下之中,以王国周边区域为“四土”“四方”,商人已形成“中心—四土、四方”的完整空间体系。这一体系在周代更为常见,如周代文献常见的“周邦”与“四方”之相对,就与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之相对完全相同。今天我们依旧使用这一空间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首著名歌曲《走四方》,其中的“四方”就完整地继承了商人的空间概念。总之,晚商时期不独在时间体系上影响了后来的文化,也在空间体系上影响了后来的文化。
五谷与六畜
上文谈了殷墟甲骨文中几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层面的概念,这里再讲一讲殷墟甲骨文中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基因。如果说晚商时期物质文化有何特色,那一定就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所谓“五谷”主要指粟(小米)、黍(黄米)、麦(小麦)、菽(大豆)、稻(水稻)五种农作物。这五种农作物,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记载。表示粟类作物的词汇有“”“”“”等字形,表示黍类作物的词汇有“”“”等字形,表示麦类作物的词汇有“”“”“”“”等字形,表示稻类作物的词汇有“”(秜)字。学术界还认为,“”可表示菽类作物。有意思的是,在殷墟遗址还发现了这五种农作物的实物材料,即小米、黄米、小麦、大豆、水稻的炭化种子遗存,这也是商人已种植五谷的证据。
所谓“六畜”主要指马、牛、羊、豕(猪)、犬(狗)、鸡六种家畜。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这六种家畜的词汇,如“”“”“”“”“”“”(或“”)分别就是马、牛、羊、豕、犬、鸡六个字。其中,马、牛、羊、豕、犬五种家畜的遗骨常见于殷墟遗址。殷墟遗址虽有鸡骨遗存,但数量较少。周武王伐商时指责商王纣宠信妲己:“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这种“牝鸡无晨”是古人长期饲养家鸡后方能得出的经验,反映了商代养鸡业的繁荣。因而,“六畜兴旺”是商代家畜饲养业的重要特征。
商代以后,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依旧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农耕基础,确保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农业还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作物和畜牧业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用。因而,殷墟甲骨文所记载的五谷、六畜,自然就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文化基础。
上文所论仅为殷墟甲骨文所承载文化基因的几个典型代表,但足以显示殷墟甲骨文所承载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文化基因,不仅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因素,还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商代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阶段,它的物质特征和精神特征深刻影响了此后3000多年的文明史,并深深印刻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之中。
王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