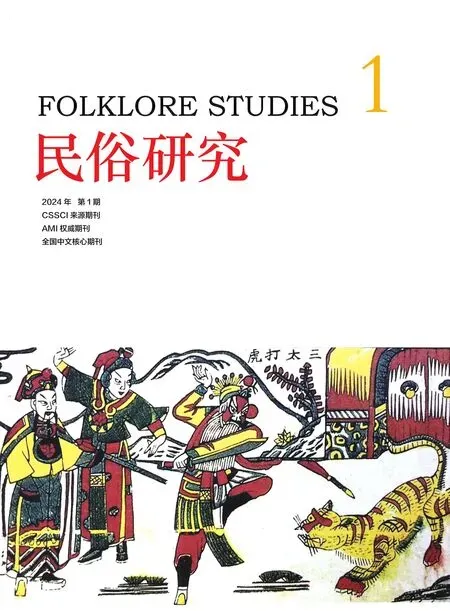“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
——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杨 华 陈祖根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不断更新和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民间信仰活动受到冲击,其中新文化运动即对民间信仰活动产生了阶段性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与“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从少数人宣扬的新思潮变为多数人践行的地方运动。(1)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近年来,新文化运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渐成学术热点的趋势。地方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进行再诠释后,将之作为付诸行动的思想资源运用到地方社会的移风易俗等事业中。
在“五四”后的地方社会中,“新文化”与作为旧文化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尤为对立。江南市镇是地方社会的代表性区域,民间艺术、庙会戏文、婚姻俗例、节日民俗、丝竹礼俗等构成了江南地方社会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的重要部分。其中,体现民间信仰的迎神赛会尤能代表“新文化”所反对的“迷信化”的“旧文化”。迎神赛会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祭祀活动。江南地区因其商业发展,出现了总管、李王、周神、猛将等民间神祇(2)[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也因其高度繁荣的地方经济出现了兴盛奢华的迎神赛会,尤以苏州地区最为著名。(3)樊树志:《盛世的投影——民间信仰与迎神赛会的记忆》,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2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0页。
苏州的吴江地区因其水网密布,存在陆会和水会两类赛会。陆会以猛将会为代表,在芦墟、莘塔、北厍一带盛行,尤以每年初芦墟庄家圩的猛将会最为出名。(4)关于庄家圩猛将会的研究,可参见吴滔:《南北三草:庄家圩庙会与乡村秩序的重组》,[日]佐藤仁史等:《垂虹问俗: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4-202页;张舫澜:《民俗学视角下的庄家圩猛将会》,[日]佐藤仁史等:《垂虹问俗: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219页。水会是江南地区迎神赛会的特色,如芦墟每年农历七月初的“摇快船”,大约有十余艘船的规模,并伴有酬神演剧活动。(5)丁逢甲:《吴江风俗记(续)》,《妇女杂志》第2卷第2号,1916年2月1日。在吴江的水会中,十年举办一次的双杨会规模最大。吴江双杨会起源于清代中期,是跨省、跨县、跨乡的水上盛会,每十年举行一次,其中有记载的4次,分别在1881、1891、1911和1924年。(6)方志龙:《清末民国江南地区跨境迎神赛会的社会空间——以吴江“双杨会”为中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双杨会源出震泽镇东北约五里许的双杨村的双杨庙。该庙正名为昭灵侯庙,供奉唐太宗十四子曹王李明,又称李明王庙。盛泽东西的城隍庙均为昭灵侯庙,同祀曹王李明。(7)周德华:《双杨会》,吴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江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第184页。双杨村附近有七十二圩,每圩需要提供会船一艘,耗资不菲。“五四”后,双杨会本该在1921年举行,但因为荒歉,经施子英等地方士绅劝阻,延期三年至1924年举行。(8)《双杨会举赛有期》,《震属市乡公报》第13期,1924年3月10日。
一些学者已注意到1924年最后一届双杨会的盛况与波折,以及所受到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9)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特别是佐藤仁史视双杨会为“作为克服对象的民间文化”(10)[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9页。事件,但均未做深入分析。从总体上看,学界多关注作为思想史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推崇科学、反对迷信的(11)如黎春晓、彭孝军:《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礼俗观念探析——以民国报刊为中心》,《学术探索》2021年第10期。,但并未关注作为社会史的新文化运动在民间信仰活动盛行的地方社会是如何传播、实践和碰壁的。在近代以来新旧冲突和礼俗互动的过程中,论者多关注清末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精英群体和国家权力对于民间信仰的改造(12)如朱爱东:《民国时期的反迷信运动与民间信仰空间——以粤西地区为例》,《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但对于1919至1927年这一“五四”后过渡时期地方社会的状况却较少论及。这些研究只是笼统地聚焦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信仰情况,并不能把握具体历史语境和时空脉络下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对“五四”后以吴江双杨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微观研究,可以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想和地方举措做对照,从而更好地反映问题背后的历史意义。
一、新旧思潮:地方新知识分子的民俗观及意义
从中国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新旧思潮不断更迭,民间信仰活动一直处在被知识精英阶层论说与改造的过程中。传统儒家思想虽然强调礼仪和道德的重要性,注重“正祀”和“淫祀”的分别,但并没有明确否定民间信仰。相反,儒家倾向于将民间信仰纳入宗教体系之中,试图通过教化、整合、塑造价值观念和规范祭祀制度等途径,对民间信仰进行改造,以实现对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塑造和引导。宋明时期,儒家以理学、心学等为个人实现道德成就的工具,不与下层信仰计较,也是祠祀中容纳各种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13)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8-189页。
清末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传统民间信仰产生了极大影响。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传入,科学理性观念的兴起,以及近代化进程的推动,使得一些传统民间信仰受到质疑和挑战,被视为“迷信”。从“淫祀”到“迷信”话语的转变,代表了晚清知识界对于民间信仰的重新定义。在“迷信”话语下,“载在祀典的祠庙也被否定”,“因为祠庙崇拜的基础——人神互益的观念开始受到挑战,迎神赛会的社会功能及其相关的传统生活方式面临重新评价甚至全盘否定”。(14)李璐:《“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民国肇建后,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壮大,开始依托报刊等城市公共舆论平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展开批评。这类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偶像破坏论》等文章中,从科学的角度表达了对“鬼神之说”的否定,将“泥塑木雕的偶像”视为“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15)陈独秀:《有鬼论质疑》,《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和旧有观念进行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反思与批判。他们不再满足于表面上的改革,而是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方式去挖掘问题的根源,并加以解剖和批判。为此,他们关注和讨论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危害性的代表旧文化的观点、事件和现象,并将其视为“热点问题”。(16)严昌洪:《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地方社会的“新文化”源自何处?“新文化”地方化的过程较为复杂,且不同地方各有其特点。如果说温州“新文化”地方化的过程主要是由“在外密切接触‘潮流’者依托学校系统另行建构的”(17)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那么吴江的“新文化”则是踏出乡关的新知识分子在上海密切接触“新文化”之后,返乡后依托报刊系统构建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一,上海“新文化”的动态迅速传递到吴江地区。“五四”前后,吴江地区不少地方新知识分子,均在本地完成基础学业后,进入上海的高等学校学习。而后,他们或是返乡工作,或是在假期回乡,宣扬新思潮、创办新刊物,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信使。在1919至1927年间,吴江地区出现了近40种报刊,其中不少报刊以吴江所辖的市镇作为发行地。这是“五四”前从未有过的现象。由此,地方“舆论社会”(18)[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第4页。因为成规模的新报刊的流播而形成,并对地方事务产生舆论影响。新文化运动不仅引发了地方新知识分子的办报风潮,地方报刊的办报主旨和所涉内容,也多与“新文化”有关。当时,吴江已经出现了“邻近市乡,均有报章问世,互通消息,从此群策群力,用以宣传新文化,造成新舆论”(19)镛庭:《新》,《新黎里》第4期,1923年5月16日。的现象。
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吴江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宣传科学,反对迷信,表达自己的民俗观。首先,大力提倡现代知识和科学精神,呼吁人们要摒弃陈旧的思维方式,增加对自然现象和周围世界的科学认识。如《蚬江声》自1921年9月创刊,常设“常识谈话”栏目,发表科普性文章《空气》《流星》《沐浴》《潮汐怎样会发生?》《鼻头舌头手指的卫生》《饮牛乳者注意》《眼睛和耳朵的卫生》《月!究竟是怎样一件东西?》等。其次,批判旧婚俗,提倡恋爱、婚姻自由的新道德。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择偶自由等观念,主张取消订婚、媒妁之言等旧俗,并推崇现代化的婚礼形式和仪式。这些观点得到了地方新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新黎里》陆续发行两期《婚姻问题特刊》,其中一些文章系统地批判旧式婚姻制度,反对“掠夺婚”“买卖婚”“童婚”“聘娶婚”,并建设性地提倡“生育节制”“儿童公育”“尊崇再嫁者的人格”“组织小家庭”等。(20)沈静涵:《婚姻问题》,《新黎里》第4期,1923年5月16日;重瞳:《婚姻制度改革谈》,《新黎里》第6期,1923年8月1日。再者,反对祭祀活动。在地方知识分子眼里,祭祀活动依赖神灵、符咒和迷信仪式,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迷信和愚昧,无法与现代科学和理性兼容。例如1924年入夏以来,吴江两月未雨,吴江县署决定“断屠”六日以祈雨。(21)廉钦:《断屠祈雨》,《吴江》第105号,1924年8月24日。对此,柳亚子认为“断屠求雨,是原人时代的迷信勾当,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当然是绝对反对的”(22)YT:《对于断屠求雨的感想》,《新黎里》第31期,1924年8月16日。。此外,地方报刊在新闻报道中,对于参加民间祭祀活动未能获得保佑反而遭遇不测者,常常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23)白虹:《迷信者之当头棒》,《蚬江声》第3期,1921年10月16日;曾:《迷信之害》,《新黎里》第3期,1923年5月1日。第四,提倡用阳历取代阴历。民国初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历法改革,以“新礼”取代阴历代表的“旧俗”,但因为“对民俗缺乏尊重和认知”(24)刘爱华:《“新礼”与旧俗的对峙: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宣传策略的误区及其阐释》,《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成效不佳。吴江地方新知识分子对历法改革的进展表达了不满,积极宣传阳历在纪节气、纪月、纪闰等方面的便利。(25)病禅:《用阳历有什么便利?》,《蚬江声》第8期,1922年1月1日。
“五四”以前,知识界对于地方社会民俗活动的讨论多来自精英阶层和城市社会,缺乏地方化色彩。“五四”后,随着“新文化”的下行,地方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看法,无论在社会空间层面还是时代脉络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的具体事务运用“新文化”;另一方面,相较于以往的城市上层知识社群,地方知识分子可以实时地、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施压。双杨会作为民间旧文化的代表,自然遭到了吴江地方报刊上新知识分子的反对。地方知识分子反对双杨会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从“新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赛会组织者利用民众的“多神教”信仰而想出了双杨会不得不举办的新理由,即“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而“不辨好歹,脑筋简单的好百姓”(26)更生:《关于双杨会补赛后之讨论》,《大分湖》第6期,1924年4月15日。才不会反对;二是从民生的角度出发,认为双杨会的举办会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双杨会所涉及的七十二圩,存在一定贫富差距,贫苦之村约有三分之一。双杨会时间长、范围广,各圩每户均要提供赛会所需柴米、费用,负担较重。(27)《双阳赛会中之花絮录(三续)》,《震属市乡公报》第20期,1924年4月28日。“双杨”有时也作“双阳”。1921年,双杨村本地“新文化”刊物《新双杨》曾短暂出版一年。地方知识分子认为,“双杨镇上底旧恶俗,双杨农民底旧思想”,经《新双杨》的指导和纠正,可以“洗刷尽净”。假如《新双杨》并未停刊,“那么对于此次赛会,一定十分努力,同本报取同一态度,为民请命底鼓吹停止”。(28)翰甫:《三言两语》,《震属市乡公报》第15期,1924年3月24日。
然而,双杨会的顺利举办表明:地方新知识分子所造就的“舆论社会”重在制造舆论和争夺话语权,无益于地方权势的获得和地方事业的革新,对于双杨会这类旧俗的改造效力有限。“五四”后地方新知识分子的“反迷信”运动,尽管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叙事在地方社会的展开(29)沈洁:《反对迷信与民间信仰的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但在“新文化”的前提下反而不易成功。地方新知识分子进而转向“党派化”和革命化(30)吴江地方报刊和知识分子的“党派化”和革命化,可参见归彦斌:《1920年代江苏省吴江乡镇小报党派化探析》,廖大伟主编:《近代中国》第3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214-232页;归彦斌:《地方报与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以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为中心》,《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形成国民党左派团体。(31)1923年末,柳亚子加入国民党。1924年春,柳亚子受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回吴江县秘密发展组织,筹组县党部,先后组成城区、同里、盛泽、黎里、平望5个区党部、13个区分部。参见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535页。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8及1929年,国民政府在广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宗教”和“反迷信”运动,活跃在地方上的国民党左派是主要推动者。(32)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91页。在“反迷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建了一系列新公民仪式,如引入新的历法和节日;禁止庙会,从而改变地方空间和仪式安排;用现代化的公墓和简化的葬礼取代以往的丧葬仪式;以革命烈士、孙中山和一系列中国过去的英雄人物为基础,通过世俗化的国家仪式,建立国家纪念体系。(33)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9.其实,这一过程在1919至1927年的地方社会中已陆续发生。这一时期,伴随吴江地方国民党组织和左派力量的不断发展,试图取代民间信仰、塑造全新认同的公民仪式和纪念体系已经开始在吴江地方展开。1925年5月3日,黎里举行孙中山追悼会。此次追悼会规模大,参与度高,《新黎里》刊发了“吴江纪念孙先生大会特刊”。追悼会当天上午,国民党党员和普通民众前来祭拜,下午地方团体前来祭拜并参加游行、演讲。(34)《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纪事》,《新黎里》第44期,1925年5月16日。在随后刊登在《新黎里》上的《雷导哀给柳亚子的信》中,雷导哀讲述了自己信仰孙中山的过程,特别是在认识、研究三民主义后,孙中山就成了雷导哀的“新信仰”,并且是“热烈的信仰”。(35)《雷导哀给柳亚子的信》,《新黎里》第45期,1925年6月1日。“三民主义”不断信仰化和准宗教化,并迅速成为个人寻求最终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
二、礼俗改造:吴江双杨会的举办风波与多方博弈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即所谓的“礼俗社会”。礼仪制度作为国家性的规范体系,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举止,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同时,地方社会也有自己的自治机制和习俗,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社会形态。这些民间社会的习俗和规则在实践中与国家政治进行互动和调整,既尊重地方的传统和习俗,又适应国家政治的需要。张士闪认为,“礼”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与国家政治相结合,“俗”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各种民间“微政治”的形态。基于这样的基础,“礼俗互动”在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平衡“国家大一统”和地方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作用。“五四”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民俗学者强调“礼”“俗”对立,此后“礼俗改造”也成为知识界、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聚焦的问题。(36)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尽管在思想史层面,“礼”“俗”分立在当时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变化,但在社会史层面,“礼俗互动”机制在地方社会的“礼俗改造”中仍旧存在。
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结构,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无论是清末新政时期、民国初年还是国民政府建立后,几波以庙产兴学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改造运动彰显了近代国家权力不断向地方延伸的过程,取得了“辉煌战绩”(37)岳永逸:《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但仍有不少庙宇如吴江地区的双杨庙等得以留存,成为民间信仰活动的中心。1911年,江苏督抚发出命令严禁举行当年的双杨会。新上任的知县得知双杨会仍计划举行,于是立即重申禁令并派人前往乡村劝导民众停止参加赛会,结果未能禁止而被当地人视为“阳示禁止之名,阴任袒庇之责”(38)《此会不可以已乎》,《申报》1911年3月14日;《公电之价值》,《申报》1911年5月4日。。1924年双杨会的举办风波,开始于《吴江》一篇引战意味颇浓的新闻《双杨会将死灰复燃》:
循例举赛双阳大会一次。请由震泽镇商会会长转请吴江县署暨水陆军警,祈予核准,给示保护,一面请求派警随会弹压。旋经该会会长迭接各镇商民商号函恳玉成。俾期振兴商业,因即据情缮呈。经刘知事准函后,以该会会长陈请举行双阳大会各节……以无论是否准行,须候省署核夺。(39)《双阳会将死灰复燃》,《吴江》第81号,1924年3月9日。
地方政府对于双杨会这一大规模的迎神赛会,也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以进行有效管理。在双杨会举办风波中,面对地方知识分子的指控,吴江县署出面驳斥,表示并未应商会的要求派水陆军警保护双杨会。(40)《来函》,《吴江》第85号,1924年4月6日。民国以来,随着现代行政力量的扩张,警察直接介入并对风俗进行改造,标志着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41)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在收到苏常道道尹、镇守使禁止双杨会的训令后,吴江县知事一方面安排警佐李涤到震泽,与各个公共团体领袖商议如何处理双杨会。李涤先后与商会、董事会和市议会等公团领袖会面。市董事会董事汤之铭和市议会沈建勋副议长均主张县知事应坐镇双杨,对双杨会负责。(42)《县委匆匆谒领袖》,《震属市乡公报》第17期,1924年4月7日。另一方面,县知事还安排警佐传唤双杨庙道士,责令解散双杨会。该道士“托词事出各圩,无能为力”(43)《捉拿赛会首要》,《震属市乡公报》第16期,1924年3月31日。。警佐只得将道士暂行拘押,后双杨庙董周心梅出面保释该道士。县知事于4月7日乘巡船前往震泽查禁双杨会,但所谓“查禁”,其实是坐镇巡视,维持赛会秩序。同时,水警厅抽拨师船四十艘,至双杨附近水域,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公共安全。(44)《禁会无效》,《吴江》第86号,1924年4月13日;《警队群来弹压》,《震属市乡公报》第17期,1924年4月7日。吴江县署原先否认派军警来双杨会,后反而改为派军警保护,实际上宣告了吴江官方禁止双杨会的失败。
随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地方士绅阶层在面对迎神赛会时也出现了分化。自辛亥以来,江苏地方实行代表地方自治的“市乡制”,袁世凯掌权后中断,“五四”后又恢复。市乡的组织包括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是市董事会,立法机关是市议事会,主要职务仍由地方士绅担任。(4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民政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页。又,关于江苏地方自治的研究,可见陈明胜:《第三领域:近代江苏地方自治研究(1905-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市镇公共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和领导力量,也由士绅阶层构成。(46)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2-263页。震泽商会认为《吴江》此条新闻实属无中生有,矢口否认,并分别写信给县知事和《吴江》予以澄清。震泽商会先是向县知事辩称“对于双杨赛会之举,绝对不予赞同”,并且“未尝预闻其事”,而后又表达了对《吴江》假新闻的愤慨,言辞激烈地希望县知事“务求彻究根源”。(47)《震泽商会致吴江刘县长函》,《震属市乡公报》第14期,1924年3月17日。随后,震泽市议事会议长龙应翔、副议长沈建勋,市董事会总董倪鸿孚、董事汤之铭,市教育会会长周积理、副会长张钟毓,震泽商会会长周积璘、副会长庄熊在给县知事的联名公呈中,强调“人和年丰之时”都不应该举办双杨会,而现在正是“民穷财尽,谣诼繁兴之际”(48)《公呈》,《震属市乡公报》第15期,1924年3月24日。,更不应举办。对于这些士绅而言,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转而依赖地方政权来领导地方事务。这些分化的士绅对于迎神赛会等传统习俗采取了与地方政府相一致的态度,并积极要求禁止这些活动。(49)何善蒙:《“迎神赛会”还是“普通烧香”?——从民国杭州三合山东岳庙会事件看政治社会变迁中的民间信仰》,王岗、李天纲编:《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对于另一些“与乡民从同一块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传统士绅来说,“礼与俗”所发生的“一些疏离”并没有取代“礼俗互动”。(50)赵世瑜、李松、刘铁梁:《“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这些士绅如双杨会首周心梅自身是双杨庙董,与双杨会关系紧密。在双杨会这类迎神赛会活动中,会首和会首团体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只要一个协会能够确保其收入来源,旁人几乎无法阻止其活动”(51)郁喆隽:《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54页。。双杨会“由震泽丝业和南浔丝业共同筹款资助,并遣该庙道士至周围各圩头化香来集资”(52)周德华:《双杨会》,吴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江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第184页。。对于会首来说,行业公会的捐资能获取超额回报,自无问题,但仍需做好本地各圩农民群体的动员工作。双杨会这类迎神赛会充满着“庙会狂欢的全民性”特征,且不同于一般限于寺庙范围的庙会。双杨会跨越乡、县、省,以双杨村为中心的“同心圆中的人们,几乎都被卷入到活动中去,从而突破了单一的寺庙前、自然村、社、城镇等空间,体现出极强的全民参与性质”。(53)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在作为话语建构的“礼俗互动”中,当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希望以“新文化”和现代性所代表的新“礼”来取代旧“俗”时,像周心梅这样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双杨会这一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思潮。这些地方士绅“在面对国家权力和民众生活时,并非完全被动的存在,而是有着极为强烈的主动性”(54)李向振:《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礼俗改造”的主要方式是将迎神赛会与乡村农业改革相联系,既可以动员地方民众参与双杨会,也因与当时社会运动的潮流相契合而可以获得外部力量的支援。1923年上半年,江苏省各道纷纷成立农业改进会。在此背景下,周心梅主持成立了双杨村农业改进会,并引入吴江之外的趋新知识分子开展农村教育事业。1923年9月7日,周心梅召集双杨村七十二圩农民至双杨庙听讲,邀请东南大学农业系教员过探先、邹秉文、黄国华参加并发表演讲,教授稻米、蚕桑知识,并预告“明年开物产赛会时,决将各种蚕种及缫丝机,携至会内,以资观摩”(55)《吴江之农业教育》,《时事新报》1923年9月11日。。过探先随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吴江分校发表演讲,提出农村改革的四点意见,认为“现在农村上的领袖人物”的“智识,大都偏于旧的方面,于新文化的智识,科学的方法懂的很少”,应在农村推行“新文化”。(56)万季直:《过探先先生讲演录》,《吴江》第59号,1923年9月23日。同时,来自双杨村的南京第一女师附属小学教员潘连奎,将双杨村农业改进会成立的消息和改进会章程寄给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57)关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可参见员怒华:《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觉悟》编辑张廷灏高度评价了双杨村农业改进会,更是将之与沈定一“五四”后在家乡浙江萧山衙前村组织的农民协会相媲美。(58)《双杨村底农业改进会》,《民国日报·觉悟》第9卷第2期,1923年9月2日。关于沈定一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返回家乡积极投身乡村革新实践,参见[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周心梅在双杨村创立农业改进会,并将双杨会改造成同时开设农业展览会的“物产赛会”,竟获得吴江外部新知识分子的认可,并成为某种“新文化”的体现。
“五四”后的地方社会,像周心梅这样的士绅在民间信仰活动上仍在发挥主导作用,并未忽视“宗教信仰与心理因素在文化网络中的坚韧生命力”(59)察应坤:《村级治理中革新力量与风俗的博弈——以翟城新政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为例》,《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双杨会成千上万的人流量,为周心梅组织的农业展览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农业展览会于双杨会期间先后在震泽、梅堰、盛泽举办,展出品共计千余件,参观农民络绎不绝。(60)《农产展览会纪》,《申报》1924年4月7日。吴江地方“新文化”报刊显然不认可这种调和式的“礼俗改造”方式,对“物产赛会”明嘲暗讽。《震属市乡公报》认为农产展览会并没有完全达到农村教育的目的,而是“做了双杨赛会中的一件点缀品罢了”,不相信“这样便是诚意的提倡农民团体底组织,可以改进农业的”。(61)《参观农产展览会以后》,《震属市乡公报》第17期,1924年4月7日。《舜湖公报》则称“假农产展览会之名,而行迎神赛会之实,双杨庙董即农业改进会会长周心梅,真是一幻术家”,“农产展览会,非绝无可取,乃一方面灌输有限常识,一方面提倡绝对迷信,蝙蝠派之行动,令人废然”。(62)培化:《关于双杨会之遗闻轶事》,《舜湖公报》第3期,1924年5月4日。
“礼俗改造”后的“物产赛会”为何引起了吴江内外新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评价?“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提高”和“普及”的分化(63)关于“提高”和“普及”之争,参见陈政:《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696期,1920年9月18日;独秀:《提高与普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一些地方趋新知识分子重视新思想的“提高”,但无法解决实际社会问题。1919年9月,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上撰文指出,“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因此对于“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这两种“文化运动”,应该进入“山林里村落里”。(64)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这种“普及”,使得“文化运动”在“社会”观念(65)杨念群:《“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得到凸显的时代转变为一种“社会运动”。周心梅所推动的农民教育和农业改革的社会运动,尽管无法摆脱与迎神赛会的结合,但的确取得了革新地方社会的实际效力,因此得到了重“普及”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认可。
三、结 语
“五四”后,吴江出现了以地方报刊为主体的“舆论社会”。这一时期的批判性舆论明显受新文化运动下行至地方的影响,不仅在内容上呈现诸多“新文化”面相,并且展开对民间信仰活动的舆论攻势。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趋新知识分子与以往知识界对民间信仰活动的批判相比,在思想上更为激进,希望对双杨会所代表的旧民俗进行快速、彻底的消灭,也脱离了地方实际;在宣传上更为全面,依托“舆论社会”以期对地方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旧式家庭、婚姻、知识观念等认识进行立体重塑。尽管地方的“新文化”倡导者擅长制造舆论,但因为无法参与到地方社会事务的治理中,并不能影响双杨会的举办。“新文化”无益于地方权势的获得,地方知识分子进而转向“党派化”和革命化,为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改造活动埋下伏笔。从空间上看,相对于当时的城市“新文化”知识分子对于民间信仰活动的思考,地方知识分子的观察、认识和宣传则更具现实意义。
地方士绅原是地方公共事务的主导者,自清季以来已经开始逐步退出地方公共领域。“五四”前,国家虽已在推动地方社会的移风易俗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仍为民间信仰活动保留了空间。在双杨会举办风波中,会首周心梅在与地方政府、新知识分子的互动中实现了对双杨会的“礼俗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地方士绅未必如趋新知识分子那样真懂“新文化”,但并不妨碍相机行事地将“新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并运用到地方事务中。相对于地方舆论中的“新文化”倡导者,周心梅这样的士绅显然可以更有能力、更具方法地推动民间信仰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变,以符合“五四”后平民教育、农业革新、社会改造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