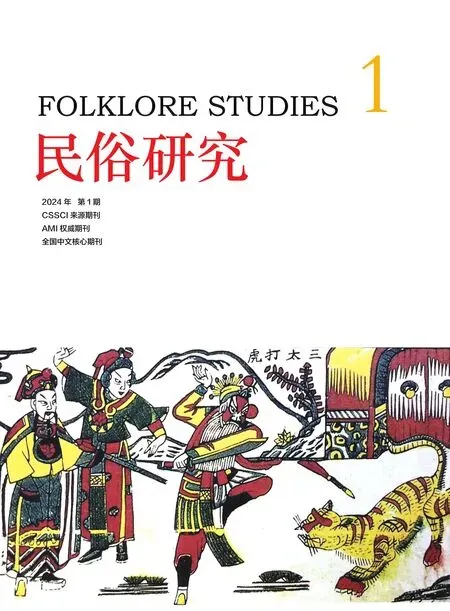滇黔桂交界地区各民族的地方礼俗传统与区域社会整合
徐祖祥 罗张悦
礼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内对“礼俗”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多年来,关于礼与俗之辩、礼俗内涵及其功能分析,学界主要从儒家礼仪、礼教思想为主的大传统及其对“俗”的规范、二者之间的互动互融以及礼俗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等方面进行理解和讨论。(1)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孙文阁、张笑川编:《张尔田、柳诒徵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9-517页;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中国文化社,1947年,第1-37页;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北)中华书局,2017年,第19-154页;王贵民:《中国礼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从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进一步加深了礼俗关系的相关研究,大多注意到了礼俗相交、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互动过程、礼治作用以及礼俗建构与社会变迁的联系。(2)刘志琴:《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赵世瑜、张士闪主编:《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齐鲁书社,2019年。张士闪将“礼俗互动”作为分析工具,提倡长时段、大区域与“微政治”以及“上下互动”相结合的视角,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与礼俗一体化的生活实践框架中,去理解中华文明内部所蕴含的政治智慧。(3)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他注意到了礼俗互动在中国政治与地方社会关系中起正向作用的机制问题,颇具启发性。赵世瑜和科大卫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都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单一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处。(4)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赵世瑜、李松、刘铁梁:《“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六卷第一、二期合刊,2008年,第1-21页;科大卫:《统一模式书写背后蕴含不同的历史进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科大卫、张士闪:《“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还有学者从礼俗传统的仪式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其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如萧放探讨了“礼”“俗”概念和传统礼仪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5)萧放、何斯琴:《礼俗互动中的人生礼仪传统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彭牧从礼俗角度思考礼与仪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民间信仰实践乃至宗教的特质。(6)彭牧:《同异之间:礼与仪式》,《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彭牧:《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最近,韩若冰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价值体现和实践路径进行了诠释,表现出对礼俗互动深层内涵的关注。(7)韩若冰:《礼俗同构与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价值》,《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李向振则论述了“礼俗互动”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8)李向振:《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大小传统的关系探究,“礼俗互动”的视角不仅有助于分析中国社会汉人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礼俗社会的研究亦有裨益。
另一方面,“礼俗互动”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表现,学界更多是从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对大传统与代表小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礼”作为“事神致福”的表达,本身便与祭祀神灵的礼仪有关。丁培仁以礼俗为例,认为好生恶死作为人之共性,道教礼仪向民俗的渗透是无法遏止的。(9)丁培仁:《道教与民俗浅议——以斋醮、礼俗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张泽洪认为,对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之间是双向渗透、相互影响的。(10)张泽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此地区中,“礼俗互动”主要指以道为主的道释儒大传统与各民族传统宗教、民俗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而礼俗传统功能的发挥,主要涉及以道教为主导的礼俗传统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学界对道教在区域社会中的整合作用,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道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被看作中央王朝基于大一统理念而实施的一种结构化整合方式,如司马虚认为,“道教包含了最具中国本质的一切”,尤其在宋明时期,道教在中央政权的边境地区开发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11)[美]司马虚:《道在瑶中:道教与华南的汉化》,巫能昌译,刘永华主编:《仪式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二是道教在区域社会中的整合作用,不再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式,而是将地方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也考虑了进来。(12)张泽洪:《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470-516页;张桥贵:《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3-152页;刘永华:《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超:《南岭民族走廊流域神灵体系与区域社会整合》,《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杜树海:《从广西左江上游地区民间宗教仪式看中国文化统一性》,《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
基于不同的研究重心,前人围绕“礼俗”以及道教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研究,但关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礼俗互动”以及礼俗传统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仍有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一是要考虑礼俗传统与道教礼仪之间的关系;二是需要进一步体察到地方礼俗传统从互动到新时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中华文化在滇黔桂交界地区的跨民族发展特点。滇黔桂交界地区位于南岭民族走廊西段,是从先秦发展至今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也是多民族互嵌的社会文化区域。本文以此区域来考察礼俗传统的建构与时代变化,即在道教为主的道释儒大传统作用下,探讨新文化模式中的礼俗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作用。
一、道教主导下各民族的地方礼俗互动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强化
在国家大一统治理下,大小传统之间的交互关系是一直存在的。早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以前,壮、瑶、苗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小传统,与以道教为主导的大传统之间就已形成了长时期的复杂互动关系。自秦汉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在岭南地区实施的一系列治理政策和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中原地区与百越民族、苗瑶民族之间的往来不断加强,在“以其故俗治”的基础上,儒释道为主的大传统作为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历代中央王朝推行礼制下行的主要内容。作为东汉时期形成的本土性宗教,道教来源于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古代宗教、民间巫术、出自荆楚文化的神仙传说等(13)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5页。,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不断地吸纳佛教和地方文化的因素,其礼俗杂糅的特征也是促成壮、瑶、苗等民族礼俗互动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不同道教教派在各民族中的传播、发展,并非仅是自上而下的礼制下行和以礼代俗的状态,交互过程中亦存在地方社会的考量与智慧选择。宗教信仰是文化系统中的深层结构部分,当道教与各民族文化发生互动时,制度性宗教与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之间是最先发生文化涵化反应的。从地方社会的能动性来看,由于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不一,加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接受道教影响的时间也不一致,故相互之间的神灵体系、宗教礼仪和教义等内容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文化涵化作用下,在壮、瑶、苗等民族中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态和相应的宗教文化结构。南朝梁时,荆湘山区的蛮人和岭南地区的俚、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14)张泽洪:《魏晋南朝蛮、僚、俚族与汉族的融和》,《楚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活动在湘州地区的蛮人,唐宋时被称为梅山蛮,大概在两晋时期便接受了道教信仰。(15)张泽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壮族道公教派亦为正一派,俗称俗家道士或火居道士,应是元代以后才传到桂西、滇东南等壮族腹心地带。(16)梁庭望主编:《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59-460页。滇黔桂壮族地区的传统宗教信仰为原生型的麽教和巫教,桂西地区的壮族道教形成后,与传统宗教之间构成了交互影响和并存的关系。黄建兴认为,在壮族麽教流播的地区,形成了“道士-麽公-巫”的关系。(17)黄建兴:《师教:中国南方法师仪式传统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238页。这种关系也符合整个滇黔桂交界地区壮族社会中道教主导下的多元宗教生态格局状况。对于以瑶族先民为主,包括苗族先民等在内的梅山蛮群体来说,梅山蛮原始宗教信仰与早期正一道融合后形成了梅山教,并体现为后来各民族中的梅山派。梅山教在蓝靛瑶中称为师边,与执行茅山教的道边一同构成了蓝靛瑶的宗教信仰结构。在盘瑶中,则是梅山教与包括道教闾山派、天心派等不同道派融合成一派。(18)徐祖祥:《论瑶族道教的教派及其特点》,《中国道教》2003年第3期。而梅山教在滇黔桂区域的苗族社会中称为武教,与源自汉族地区儒释道杂糅的文教一同构成了苗族宗教信仰的主体。总体而言,体现在宗教间相互作用的礼俗互动,不仅使不同道教教派具有了地方化和民族化特征,而且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各民族基于实际生活需要,在道教文化因素的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例如,长生成仙作为道教的核心教义,在壮、瑶、苗等民族中被改造为死后灵魂成仙的信仰,并通过各民族道教科仪化的丧葬礼俗呈现出来。
壮、瑶、苗等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形态,皆可看作各民族地方生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俗”,而“俗”与道教主导下的大传统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所谓礼俗相交,不仅有代表“礼”的大传统在此区域中的下行,也有地方社会的能动性选择与创造。如道教主导下,各民族形成的宗教文化复合体会继续与民俗文化层面发生粘连,各民族礼俗仪式的举行和传承,主要由各民族道教弟子来承担。神职人员身份的获取需要经过道教授箓仪式,民族化的授箓仪式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本质上却具有一致性。在蓝靛瑶中主要表现为几乎全民性的度戒仪式,盘瑶中为挂灯仪式,主要分为挂三台灯、七星灯以及十二台灯的不同等级;壮族社会中称为受戒仪式,等级的升高也会有相应的补职仪式;苗族中则为传度仪式。对于不同民族而言,民俗仪式会融入不同民间道教教派的教义、科仪、神灵、经书、法器、法术等内容,宗教文化复合体与民俗层面发生互动的仪式种类也并不完全一样,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的道公、师公、先生、巫师等神职人员的职能范围上。如桂西壮、瑶等民族的礼俗传统中,以家庭层面和村落层面的人生礼俗、岁时节日礼俗等为主要内容,仪式目的与个人生命、家族命运以及村寨的平安祈福有关,即与人的生老病死以及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滇东南壮族地区,则是壮族道教和受到道教影响的壮族麽教在当地礼俗传统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丧葬、补粮、解关等人生礼俗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苗族社会中武教师公主要负责还傩愿仪式,文教先生主要负责丧葬仪式,两派神职人员在其他仪式上则呈交叉出现的状态,于是以道教为主的武教和儒释道交融的文教在不同的民俗文化事象中发挥着不同的整合作用。而且道公、师公等神职人员的能动性使仪式的经书科本、唱本、仪式程序等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各民族文化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与整合过程,并非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式。于是出现了西林县壮族道公对现代学子求学需求的仪式再造,桂西地区不同的壮族道教班子在相同礼俗仪式中有不同操作环节等现象。据笔者近年的田野调查资料(19)本文所用第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2018年以来的田野调查。基于学术伦理考虑,文中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均已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西林县足别乡Q屯壮族道公主持的针对普通亡人的丧葬礼俗环节主要为:请师开坛—请水—沐浴—绕棺—走十方—散花—燃灯、灭灯—炼度—发丧—脱孝服、安神位—扫荡、封门—复山;而巴马县那社乡N屯壮族道公主持的主要环节则包括:闹坛、戴孝—开坛请圣—退堂—请水招魂—祭灵—请寿—开灯—散花—解结—绕棺十别—满灯—引灵过十殿—面圣—说戒—颁行程牒—三献—上表—开天路送灵—催灵登山—出殡—拦路—回家送寿—送圣。两地壮族丧葬礼俗仪式的环节虽不完全一致,但文化价值观念中与生命观相关的灵魂去处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壮、瑶、苗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俗”,通过与道教主导下的大传统的“礼”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文化认同心理下国家大一统层面与地方社会的贯通。地方社会在维系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时,文化认同会与国家层面之间联合起来,使民间社会的“俗”上升至“礼”的话语层面,进而在地方社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价值观念的互动与整合不仅是礼俗互动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稳定功能。
历史时期南岭走廊区域内的礼俗互动,伴随着历代统治者民族治理政策的施行、对宗教文化的推崇态度以及各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需要,影响了壮、瑶、苗等民族对包括道教在内的文化大传统的认同心理以及国家认同心理,民众通过对礼俗互动的文化想象来表达中华文化认同的集体意识。如巴马县坡月、甲篆一带的传说中,将当地盘阳河洪灾与鲧、大禹治水传说融合在一起,而盘阳河中所蕴含的利于生命长寿的铁矿物质,则是天神应龙不敌雷神后所化作的铁甲碎片。而且当地民众认为,壮、瑶、汉等民族补粮、敬老礼俗的由来,皆与道教诸神以及益寿之道相关。传说很久以前,彭祖来到桂西盘阳河流域,同当地一位老者来到甲篆乡百魔洞中,彭祖向老者传授了自己三位师父的长寿之道,分别是大宛山青精先生、宛丘先生以及推崇“无为之道”的尹寿先生,之后盘阳河长寿的故事传开后,包括皇帝都前来探寻。(20)《盘阳河的传说》编辑工作组:《盘阳河的传说》,内部资料,2010年。各民族礼俗互动过程中,包括玉帝、雷神、大禹、青精先生、宛丘先生等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对地方社会补粮等民俗的合法性和灵验性进行了文化认同的嵌入。当地民众通过承载历史记忆的传说,呈现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与国家认同心理的强化。
地方社会原有的部分民间信仰在道教主导和融入下,进入了具合法性和整合性的“礼”的层面,继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礼俗传统实践,在精神象征及行为模式上不断强化中华文化对地方社会的整合。明代作为广西战事最多的朝代,多有壮族英雄人物因战绩而得到朝廷认可。桂西地区壮族土官作为连接民族群众与中央王朝的中介,通过对汉文化的主动认同以维护其地方统治,甚至一度引发了桂西土官的“汉裔情结”。(21)黄家信、周爱传、吴先勇、吴日岗:《滇黔桂交界地区的民族结构与民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页。如岑氏土司作为明清时期壮族地区最大的土司家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巴马县定金寺原名为“岑大将军纪念亭”,始建于明朝后期,起初是为纪念明朝抗倭英雄瓦氏夫人和岑猛将军而设立的,2005年改名为“定金寺”。从2003年开始,定金寺(纪念亭)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祭,整个仪式以“玉皇大帝—岑大将军—观音菩萨—瓦氏夫人—灶王”的顺序进行。(22)陈文俊:《瓦氏夫人庙:瓦氏夫人崇拜研究之一》,《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1期。民众的心理结构是传统社会的反映,土官化身为地区性的神灵,其阶序位置则是在代表大传统文化的道教神灵之下。正如武雅士认为,神是帝国官僚的超自然化身,玉皇大帝为最高统治者,是人间皇帝的反映,而灶神是超自然官僚机构中地位较低的一员。(23)[美]武雅士:《神、鬼和祖先》,张细香译,[美]武雅士编:《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彭泽安、邵铁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7-185页。每年阴历三月三或逢闰年之时,定金寺都会举办大型庙会,田阳、田东、东兰、凤山等邻县的壮、瑶、汉等族群众都会前来祭拜。壮族道教将土官信仰纳入信仰体系之中,将周边瑶、汉等民族的信众整合进来,呈现出祭祀礼俗及神灵体系祭祀圈的扩大,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
文化认同包含了大小传统价值观念的互动与融合过程,表现为道教中的教义思想、儒家孝文化等文化价值观念与地方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整合与重塑,主要体现在贵人重生和好生恶死的世界观、生命观以及幸福观方面。如壮、瑶、苗等民族对生命观的调适,体现为各民族传统灵魂观念与道教教义思想之间的融合。修道成仙思想作为道教思想的核心,教理教义也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24)卿希泰:《道教文化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页。明中叶以后道教出现世俗化发展趋向,在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发展时,其长生成仙信仰与各民族传统的灵魂观念进行了结合与调适。各民族在接受道教成仙思想时,舍弃了通过在世修道而成仙的方法,将成仙信仰与传统灵魂观念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丧葬仪式中对灵魂去处的处理上。如壮族道教中的“积善成仙”观念,多体现在超度亡灵上。(25)粱庭望主编:《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590-591页。壮、瑶、苗等民族对灵魂去处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在与道教成仙信仰观念进行互动时,都对其中一魂进行了处理,即对于正常亡者而言,此魂是要升往神仙界的。德保一带壮族在灵魂的超度环节中,道公破狱救出亡魂后,要送亡魂升天,登上仙界。(26)黄桂秋:《壮族巫信仰研究与右江壮族巫辞译注》上册,黄桂秋、覃建珍、韦汉成采录、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西林县壮族认为人去世后有三魂,一魂在墓地、一魂在神台、一魂上天堂。西林县和巴马县蓝靛瑶道公认为,人去世后有三魂,一魂去阳州府,一魂在祖先神台处,还有一魂会上天庭。西林县蓝靛瑶将灵魂接引去仙界前,要经过破狱、炼度、超升等环节,最后由道公请三清和众神带领亡魂前往神仙界。各民族价值观念与道教教义思想的此类互动,是与祖先崇拜等地方社会的“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礼俗互动在文化体系核心层面的体现。
不难看出,历史上壮、瑶、苗等民族的原生型文化系统主要以结构松散的原始宗教为核心,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其与民俗、社会秩序等的关联性是逐渐减弱的,社会整合功能不断被解构。因此,各民族需要通过具有强大引导力的大传统与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双向影响,用礼俗互动的方式来适应新的社会整合模式,并以此发挥新的社会整合功能。“礼”作为大传统中的制度性礼仪,“俗”则是地方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27)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区域内壮、瑶、苗等民族的地方礼俗互动作为大小传统在地方社会的相互胶着,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道教教派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系统之间的整合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以道教礼仪、教义等为主的道释儒大传统与壮、瑶、苗原生型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规范,并以地方价值体系作为价值取向,将民族化的道教礼仪以及与道教仪式相关的人生礼俗和岁时礼俗等作为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壮、瑶、苗等民族神职人员则是礼俗互动中的中介力量。地方礼俗互动中,道教的民族化可视为宗教礼仪的民族化和地方化,并通过价值体系的调和与生成,成为地方生活方式的根基思想。这对于各民族集体情感的凝聚、民族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塑造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各民族乡村社会的礼俗传统实践与社会凝聚力构建
滇黔桂交界地区各民族的礼俗传统是礼俗互动的结果呈现,壮、瑶、苗等民族的民间道教组织凭借鲜明的宗族性特征和所拥有的宗教文化资本,保障了各民族道教组织传承体系的稳固和良性运行,继而成为各民族乡村社会礼俗传统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之一。1949年以来,各民族礼俗传统实践促成了各民族民间道教组织之间、不同民族之间自主自发的多维互动和协作,在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实现了民族内部和跨民族的深层交融与整合。
其一,各民族地方礼俗传统的实践离不开“依祖传教”为主的传承方式和区域内各民族道教组织之间的协作及互动。各民族民间道教的传承机制,与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叠合的。中国宗教的社会资本资源十分丰富,具有鲜明宗族性特征的民间信仰是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28)Weller、范丽珠、Madsen、陈纳、郑筱筠:《对话宗教与社会资本》,《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道公、师公和先生是乡村社会中礼俗传统的展演者、传承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礼俗传统知识、经书抄本和法器等文化资本,并熟悉仪式操作规范,这是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条件和促进各道教组织之间团结互助的基础。
该地区壮、瑶、苗等民族的神职人员以“依祖传教”和“依师传教”为主要传承方式,其中又以祖传为首选,父可传子、女婿或者家族中的其他晚辈。如巴马县壮族道公的传承,一般倾向于先传给家族内部,并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选择,故当地一个道公组织中的部分成员之间会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徒弟若想受戒并成为一名壮族道公,就要掌握神灵体系、科仪文本、仪式科仪、法器、道音、秘法、禁忌等各方面的知识。其中,礼俗仪式的仪程和规范是核心传承内容。家族若为祖传,徒弟则会有长期耳濡目染的基础;若为师传,则是自学加请教。壮族道公虽然以“依祖传教”为主,但秘法的传授必须遵守父不能传子的规定,即需要通过第三人进行传授,或可以先依照祖辈传下的经书自学,不懂之处再去请教师父。通常壮族道公的秘法师傅都是附近村屯的其他道公,相互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亲属关系,如巴马县那社乡N屯壮族黄道公的秘法师傅便是附近屯的道公,与黄道公之间不是一个家族。而且道公师父还会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向徒弟展现道公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以那社乡N屯壮族黄道公的传承谱系为例,其为祖传第七代道公,祖师牌位中间位置竖向写有“清微玄坛演教道派法派列位祖师”,下面三排主要写的是已故道公的名字,在其法名后统一以道教“真人”相称。不难看出,壮族道公的传承具有一定稳定性,对于丧葬、庙会、安龙等大型道场的礼俗仪式而言,由于所需道公数量较多,家族内部现有道公数量不足以组成一个能举行大型道场的道公班子。因此,一个道公班子内部,既有祖传道公的重新组合,也有“依师传教”的道公。这种祖传、师传相结合的传承机制,也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的瑶族、苗族社会中。民间宗教组织的制度性传承是礼俗传统功能发挥的前提,这对礼俗传统的展演和传承、地方社会的整合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民族民间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复兴,出现了各民族民间道教组织之间的互助现象,维系了社会转型下各民族地方礼俗传统的功能发挥。壮、瑶、苗等民族神职人员依托家族传承特征和宗亲关系网络,在同一民族内部出现了跨省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移植等宗教文化资本的共享现象。如西林县足别乡P屯的盘道公告诉笔者,以前全村蓝靛瑶每次度戒的人数一般为两人,改革开放后,该村蓝靛瑶与周边田林县、云南省广南县蓝靛瑶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便开始学习如何增加度戒人数的仪式流程,如今村内度戒仪式每次可度五六人。基于此前经书抄本、法器等出现了被烧毁或保存不当而损毁严重的情况,道公或师公一般会从其他家族成员处重新补齐。
其二,滇黔桂交界地区的各民族在共有文化价值观念依托下,形成了融通的区域文化生态。(29)徐祖祥、罗张悦:《乡村振兴中民间信仰重塑的文化力实践逻辑——以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H村苗族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壮、瑶、苗等民族民间道教流派神职人员及民族礼俗传统在村落秩序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民族民间道教组织不仅保证了礼俗传统的传承,也延续了各民族原有文化系统在村落内部人际互助功能的发挥。与村落生活秩序和世俗社会结构相对应的人-神关系的建构,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落内部的团结和村际之间宗亲关系网络的紧密联结。
各民族神职人员通过其宗教与礼俗传统的礼俗互动,不仅整合了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而且获得了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定社会资本,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整合提供了条件。1949年以来,滇黔桂交界地区壮、瑶、苗等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各民族民众与其他民族之间通过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长期往来,建立了以和谐、团结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互动关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礼俗传统之间不同的互动形式,在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下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整合特点。由于民族化的道教授箓仪式是成为道门弟子身份的重要途径和标识,也是各民族礼俗传统的一部分,各民族受戒仪式的跨民族举行便凸显出地方礼俗传统在区域社会中的有机整合效应。与壮族道教主要局限于本民族内部神职人员受戒相对照,道教授箓制度在瑶族社会中的民族化发展,几乎呈现为全民度戒、挂灯的现象,加之瑶族度戒仪式对壮族成员的吸收,原本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家族传承特征,扩大为跨民族的民间道教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将地缘因素中的其他民族囊括了进来。这主要表现为蓝靛瑶为壮族和汉族举行度戒仪式的现象,虽暂未发现壮族为其他民族授戒的情况,但壮族道公对于收徒并没有严格的民族限制,只要其想学道法、会说壮语、有悟性等,都可以考虑在内。在滇黔桂交界地区的富宁、望谟等地的苗族社会中,文教先生是经由汉族授戒的,神职人员兼事文教和武教的现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苗族宗教组织传承和发展的新特征,神职人员的传承及其宗教组织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民族礼俗传统的运行。
壮、瑶、苗等民族的文化资本在礼俗传统的运行过程中,转化成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良性互动及资源整合的社会资本,为跨民族的和谐互动及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重要基础,进一步发挥出更大社会范围内的整合功能,即“国家政治的礼俗一体化追求,必须借助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活实践才能实现”(30)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普通民众基于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认同心理,会选择其他民族的神职人员进行仪式互动,以此逐渐形成宏观区域社会中跨民族的社会联结。桂西地区壮族和蓝靛瑶之间通过文化核心层面、民俗层面的礼俗传统交织而产生联结,皆涉及到灵魂观念以及祖先崇拜,对民族关系的协调与社会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壮、瑶等民族之间因较多的经济、社会互动,出现了许多打老庚(31)滇黔桂交界地区各民族群众常与关系较密切的同辈之间,通过“打老同”或“打老庚”的民间习俗方式,形成互称“老同”或“老庚”的拟亲属关系。、族际通婚的现象。个人社会网络范围的扩大,也拓展了壮、瑶等神职人员与不同民族的民众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社会凝聚。如巴马县那社乡X村作为壮、瑶聚居的行政村,相互之间打老庚的现象极为常见,如X村壮族韦道公是附近Z屯蓝靛瑶李道公的老同。韦道公告诉笔者,不论家中有什么事情,李道公等瑶族老同都会过来帮忙。在各民族对道教文化的认同以及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基于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来跨民族选择神职人员是极为常见的考量因素之一。虽然壮族与盘瑶在礼俗传统互动方面没有与蓝靛瑶的程度深和范围广,但共有的宗教信仰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协调与社会凝聚起到了很大作用。如田林县利周乡F村盘瑶陈师公与邻近地区壮族民众的仪式传统互动,主要的外部因素便是基于经济往来而逐渐扩大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2020年5月,笔者参与观察了陈师公为S村壮族老同韦某举行的安祖先香火仪式。老同韦某是陈师公在山下种地时结识的,由于韦某所在的壮族村寨没有神职人员会做此类仪式,韦某将陈师公介绍给其他壮族群众,之后陈师公去壮族村寨主持了四场仪式。
黔西南地区苗族与汉族、布依族之间的民族互动与交融,则主要是通过丧葬礼俗中神职人员的同坛协作与互助,并在有关灵魂去处的终极问题上,实现了民族文化边界的跨越。从2020年8月在黔西南州望谟县进行的实地调查来看,族际通婚是促进当地不同民族之间往来的方式之一,互嵌的分布格局推动了苗族与布依族、汉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交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当地苗族和布依族主要由本民族老麽举行超度仪式。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民间信仰的复兴和重构,苗族和布依族通过移植当地的汉族文教来整合自身的宗教信仰结构。因此在苗族和布依族的丧葬科仪道场中,十人左右组成的神职人员班子中既有苗族,也有布依族和汉族,而且常出现以汉族文教的仪式传统为当地苗族和布依族举行丧葬仪式的情况。笔者于2021年1月参与了望谟县J村布依族的丧葬仪式,当地苗、布依、汉等民族群众认为,若别人家有事,尤其是丧事,自己主动、诚心地去帮忙,不仅能得到自己祖先的保佑,人家老祖宗也会保佑自己家中平安顺遂。故在丧葬仪式中,大家都会自愿上门相助。当地民众还认为商人、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职业的人通常具有较好的业缘关系,在地方礼俗仪式场域中,除了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帮助与交流,民众也会借此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自主自发的交往与交流。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协作与交融,不仅在地方社会中形成了血缘、地缘层级的互助圈,还形成了包括多民族、多职业在内的业缘一级的互助圈。苗族、布依族与汉族之间民族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各自文化边界的跨越,三者礼俗传统的共生关系则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
各民族道教组织跨民族举行的个体性、家族性、村寨集体性乃至跨地域、跨民族的仪式,皆以礼俗传统为载体,而共有价值观念的社会呈现是区域社会价值共识的体现。各民族神职人员依凭地缘优势,主持的礼俗仪式都有一定的空间范围。一般来说,主要以本村寨为中心,向乡、县、市(州)和省逐层扩展开来。如巴马县那社乡B屯的蓝靛瑶粱道公告知笔者,对壮族、汉族等的仪式范围主要包括附近所略乡、巴马县城、凤山县、南宁等地。那坡县M村由于与云南富宁一带距离较近,故村寨中的壮族道公会去富宁一带为其他民族举行仪式。礼俗传统作为一种强化群体互动、协作以及联合在一起的纽带,通过仪式交织等跨民族的良性互动方式,不仅促成了民间道教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整合与凝聚关系,而且极大提升了各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社会整合能力,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为秩序化。
三、各民族礼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共有价值观念社会呈现范围的扩大
礼俗传统的文化转型与现代性重塑,是滇黔桂交界地区壮、瑶、苗等民族社会中正面临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发展语境下,虽然乡村社会运行的部分礼俗传统发生了外在形式的过滤与功能扩展,但共有价值观念作为礼俗传统中极为稳定的精神文化因素,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对民间文化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机制,礼俗传统中的文化价值观念能够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呈现与传递,除了各民族民间道教组织、民众和政府的合力作用,学者、媒体、社会各类组织等也是传统礼俗现代重构的重要外源力量。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主体对各民族礼俗传统进行传承资源的社会整合,对于部分日渐式微的礼俗仪式的延续和传承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道教文化融入下的各民族社会生活在政府主导的区域文化事业发展中,表现出多民族友好互动情境下共有价值观念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呈现与传递。
区域内的壮、瑶、苗等民族均有被列入非遗保护范围的仪式传统,而且大部分都是道教融入下的信仰民俗。如广南“瑶族度戒”“富宁瑶族盘王节”被列入文山州第五批州级非遗项目,坡背后村苗族的还愿仪式分别以“富宁苗族面具”和“富宁红苗还愿习俗”两项被列入保护名录。笔者于2018年12月在富宁县进行调查时得知,当地文化馆为了保护和传承当地壮、瑶、苗等民族的礼俗传统,每年常到洞坡乡等瑶族村寨对度戒仪式和还盘王愿仪式进行培训,而且在保护经费的支持下,会请瑶族道公、师公为本民族民众培训和教读经书等,以此将其宗教文化资源和社会多方资本整合起来。广西区政府为推动文化产业的特色发展,自2012年起便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和意见。如2012年印发的《桂西资源富集区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充分发挥桂西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实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将文化产业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和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重点工程,并以期加快建立包括广西区河池市、百色市、崇左市,云南省文山州,贵州省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在内的桂滇黔6州市协作机制。(32)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规划处:《桂西资源富集区发展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gxzf.gov.cn/zwgk/zfxxgkzl_84988/fdzdgknr/ghxx/qygh/t10096365.shtml,发表时间:2012年12月2日;浏览时间:2022年7月4日。2013年《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发展规划纲要(2013-2020年)》中,指出需对当地包括敬老、重视生命等民俗文化在内的壮、瑶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保护。至2020年,巴马县建立了包含9大类378个项目的非遗资源档案(33)巴马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喜讯!巴马两个民俗项目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bama.gov.cn/zjbm/ftrq/t7658051.shtml,发表时间:2020年12月22日;浏览时间:2022年6月30日。;2021年,巴马县“敬老习俗(壮族补粮敬老习俗)”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且“弄亭高山神的传说”“求花”“定金山庙会”“度戒”“踩花灯”“度戒舞”等被列入县级非遗保护名录之中。至2022年,西林县共有1170个非遗信息资源(34)参见“西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简介”,笔者于2022年7月11日自西林县文化馆获得。,“西林瑶族度戒”是第六批自治区级非遗,“壮族‘三月三’歌节”则作为民俗类别被列入县级非遗。其中,补粮作为桂西北地区壮、瑶等民族礼俗传统的重要部分,每年重阳节时,巴马县会联合周边的凤山县、东兰县一起举行与敬老、重生礼俗相关的大型补粮仪式活动。为了加强对敬老、孝道意识的宣传以及补粮习俗的保护力度,当地政府还在那桃乡平林村G屯“仁寿山庄”建有“补粮”部,以供游客欣赏。在礼俗仪式的传承和实践、孝文化与贵人重生等价值观的传递方面,各民族民间道教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巴马县档案馆内非遗申报书相关资料显示,巴马县壮族补粮敬老习俗在申报区级非遗时,当地政府确定的文化传承人谱系便是依照乡村社会中实际运行的祖传壮族道公组织而定的。此道公组织的成员皆出自巴马县那桃乡平林村W屯黄姓家族,如今已传承至第六代,仪式主要传承人黄某是第五代道公,补粮礼俗依据的经书文本为《道经师宝》。当地道公组织凭借在乡村社会中的礼俗传统实践和各家族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文化资源,实现了民间道教组织、地方民众和政府部门在文化资源整合、传承及保护方面的创造性转化。
对于民众本身的生活方式而言,岁时礼俗和民族化的宗教礼仪不仅是传递价值观念的礼俗传统,也是村落秩序构建及维系的重要方式,仪式传统举行的时空成为民族内部或者族际间自主交流、交融的信仰场域。基于该区域位于三省区交界地带,除了在本县范围内举办民族节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有跨省的民族互动活动。据西林县文化馆相关资料,1985年11月26至28日,云南省富宁县举行瑶族盘王节活动时,邀请了广西区百色、西林、巴马、那坡、河池等县市的瑶族参加并表演节目。1998年3月31日下午在西林县八大河乡三江口隆重举行了滇、桂两省区的罗平、西林“三月三”民族民俗盛会。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口号下的仪式功能,并不完全由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决定,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节日效应,就民族关系的互动而言,的确促进了壮、瑶、苗、布依、汉等民族的聚集与交流。作为政府主导下的传统节日仪式,原有社会功能的发挥不再局限于某一民族内部,而是需要尽量达到多方主体功能满足的目的。
区域内壮、瑶等民族的神职人员通过对道教融入下的信仰民俗的公共性展演,将地方礼俗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呈现给大众,民族节日无疑成为各民族共享共同价值观念的场域和契机。即原本基于各民族民众生活需要的仪式传统在一些场合中逐渐被打造成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各种文化节,在现代性背景下进行了相应的重构。经过转变的礼俗传统,大多与祈求幸福生活的愿景相关,虽然都是政府主导下的仪式展演,但对强化民族团结的氛围和礼俗传统中价值观念的传递是有正向作用的。如1984年,西林县盘王节有唱盘王词和戒罪词、跳盘王舞、双人铃舞以及壮族山歌、苗族芦笙舞等节目。2015年11月27日为巴马县第二届盘王节庆典,百林乡壮族道公表演了花灯舞、金鸡拜寿,蓝靛瑶道公和师公表演的则是度戒仪式中的部分环节。(35)罗荣玉:《我县第二届盘王节庆典活动纷繁璀璨》,《今日巴马》2015年12月4日。瑶族度戒一般被视为瑶族道教的入道仪式,如今在“非遗保护”背景下,有民众将其看作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则将盘王节界定为瑶族民俗活动、自治区级或县级非遗。对于多民族在场的集体节日来说,不论是与度戒仪式相关的戒律,还是盘王节中的祭祀环节,礼俗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转变成了代表中华文化的区域性价值观念,通过各民族的交流互动在更大社会范围内进行传递。如西林县蓝靛瑶度道中的戒词有“不得呼天骂地、不得毁骂父母、不得瞒师骂友、不得凶怒凌人、不得贪财害命”等(36)西林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局:《道科书》,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226页。,这些戒言作为蓝靛瑶训诫后代的一种教育形式,在蓝靛瑶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度戒后的男子要终身孝顺师父,听从其教诲,若犯了戒言中的行为,师父也会受到众人谴责和讥笑。(37)政协西林县委员会编:《西林风物》,内部资料,2013年,第57页。壮族道公金鸡拜寿作为民间补粮习俗的节日形式,传递了地方礼俗传统中生命观所包含的伦理道德观和延年益寿的心愿。“命由魂生,魂由粮养”的价值观对于当地的瑶、汉等民族来说是相通的,巴马县汉族道公补粮时念唱的送寿歌为:“亲人面前妹开声,今唱送寿给老人;送寿给娘和给爹,安泰千年不老松。给他送寿常健在,千年万代不忧心;亲人面前妹开声,今唱送寿给老人。寿像高山擎天柱,寿像湖边千年榕;送寿给娘和给爹,安泰千年不老松。”(38)巴马瑶族自治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暖暖的村落》,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4-156页。瑶族道公的补粮疏文中亦有类似的表达:“惟愿放豪光,流演今光炁。灿烂斗坛中,错落三灾戹。解了凶病难,粮穷再补限。重添正福禄,寿命得高强。乞延求寿算,保命得延长。”(39)参见经书《一本告斗伸斗补粮》,笔者于2022年8月9日自广西区西林县那佐乡Z屯蓝靛瑶李道公处获得。虽然当地民众对节日性质的看法不一,加之学界对其“本真性”已有诸多讨论,但各民族地方礼俗传统中的共有价值观念对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无疑是有利的,即“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正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40)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不同场域中的礼俗仪式传统具有不同的功能,政府主导的民族节日对民众自发举行的仪式传统目的进行了重新设定,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塑造出更为宽泛的价值愿景,从而形成礼俗传统功能的最大适用范围。
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呈现主要体现为礼俗传统的整合作用范围上升至族际互动以及更大空间的区域社会。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各民族地方礼俗传统作为礼俗仪式和价值观念相统合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层级发挥展现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逻辑过程。在经验事实中起作用的,是在各民族之间一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内交融共生的基础上,地方礼俗传统中共有价值观念的显现和功能发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区域内地方礼俗传统的发展伴随着仪式形式与传承制度等各方面的变迁,政府相关部门、各民族道教流派神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等多方主体,在非遗保护政策下对礼俗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商,但作为共同纽带的价值观念仍在稳定地发挥着整合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滇黔桂交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呈现为不同的共居分布特点,各民族的地方礼俗互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整合过程,离不开道教融入下的南岭走廊地域文化传统背景的保障作用。儒释道文化精神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相比于儒家,道教与民间文化的联系则更为直接。(41)刘仲宇:《儒释道与中国民俗关系述要》,《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道教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壮、瑶、苗、汉等民族的地方礼俗形成、礼俗传统实践及其共有价值观念整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礼俗传统中的生命观、幸福观等共有价值观念成为维持区域内社会文化秩序的重要因素。
本地区地方礼俗传统的形成、发展及其引起的区域社会整合的客观呈现,是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治理需要、道教文化传播以及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历史时期部分偏远山区是未完全纳入地方政府管辖的编外之地,民族交融作为社会整合的深层表现,有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壮族先民、苗瑶先民和古代华夏族之间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交流。华夏民族的形成支源中就包含了百越、南蛮等古代民族,起初便具有多源性和兼容性特征,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性格。(42)张声作主编:《宗教与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这不仅影响到了之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原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1949年以来,各民族在一系列民族平等政策和地域文化传统的保障下,相互之间形成了自主、自发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状貌,总体呈现为一种稳定与和谐的社会整合形态。
壮、瑶、苗等民族礼俗传统的建构和良性运行,是不同时期的不同道教教派在区域社会中文化整合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价值体系融合的体现。作为区域社会整合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文化效应,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稳定与和谐的互联局面,带动了村落秩序的建构、维系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互动。对于某一民族来说,共有的宗教文化无疑会增加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对于某一多民族共居的区域来说,同质的宗教文化对区域社会文化有一定的塑造和整合作用。从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居地区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嵌入关系,而是中华文化大传统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调和与共适过程。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一体多元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交融提供了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