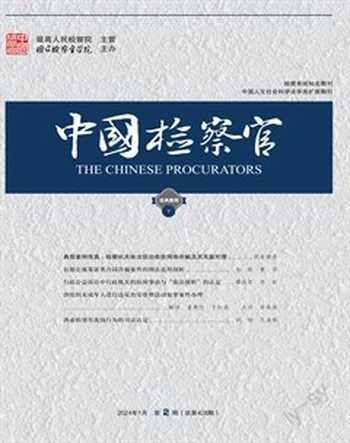线下接触型婚恋诈骗刑民边界分析
周赛 王宇
一、基本案情
2020年7月,犯罪嫌疑人奚某某与被害人徐某某通过交友软件相识。自2020年9月,奚某某隐瞒自己真实姓名及已婚事实,自称“赵某”与徐某某以“谈恋爱”名义线下交往,并营造将与被害人结婚的假象,期间奚某某多次拒绝被害人提出的“见家长”请求。交往过程中,奚某某多次索要、收取被害人财物,包括共同吃饭、看电影、购买衣物等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000余元。另外,徐某某在陷入“订婚结婚”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为奚某某线下购买金手镯花费10363元、金手链花费2829元、浪琴手表花费19788元。2020年11月,双方发生性关系后,奚某某虚构怀孕的事实,以“需要报瑜伽课锻炼”为由要求徐某某将信用卡交由其使用,后奚某某使用该卡购买减肥套餐等,消费金额共计20097元。2021年3月初,奚某某再次虚构在国外发生车祸等事由,向徐某某索要钱财未果后将其微信拉黑。2021年3月,徐某某报警后案发。
二、分歧意见
线下接触型婚恋双方之间不仅有物理空间的线下交际,而且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恋爱关系。较之于“一对多”型婚恋诈骗,“一对一”型婚恋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仅与一名被害人“恋爱”交往,对于“恋爱”过程、诈骗数额、主观故意等方面的言词证据常陷于“一对一”的困难境地,致使案件定性及数额认定方面刑民交叉问题凸显。“一对一”线下接触型婚恋案件中,双方发生的经济往来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诈骗数额该如何认定?实践中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奚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奚某某与被害人徐某某通过线下交际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恋爱关系,二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应当认定为因民事欺诈引发的婚恋纠纷,应当由民法而非刑法调整。一方面,奚某某的行为不具备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二人的经济往来属于民法范畴的“赠与”“共同生活消费”等情形;另一方面,被害人为维持亲密关系处分财产,在双方交往中的花费存在“你情我愿”的情况,其并非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进而遭受财产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奚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应全部认定。犯罪嫌疑人奚某某与被害人徐某某的线下交往,系基于奚某某隐瞒自身已婚事实及真实姓名的前提下开展。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在交往过程中隐瞒婚姻状况、真实姓名,虚构怀孕事实,致使被害人徐某某陷入“真实婚恋”的错误认识情形下给付犯罪嫌疑人财物,最终导致财产遭受损失。因此奚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应当以被害人损失数额全部认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奚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应区分认定。犯罪嫌疑人奚某某隐瞒已婚事实、真实姓名与被害人交往,其在交往期间索要或者收受被害人财物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但是这种存在刑民交叉情形的婚恋交往关系,并不应当完全由刑法进行规制,双方交往中的花费可能存在“你情我愿”的情况。对于诈骗数额的认定,应当厘清刑民边界,结合双方交往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的内容、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三、评析意见
筆者赞同第三种意见,本案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婚恋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一般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外观,对于案件中遇到的刑民交叉问题,需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实质审查,结合主观目的分析案件性质、区分涉案财物情形,进一步结合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综合认定诈骗数额,具体分析如下:
(一)本案应认定为诈骗罪,不应评价为民事欺诈行为
1. “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婚恋纠纷与婚恋诈骗的关键要素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故意地以不真实的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陷于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而诈骗罪的基本模式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认识错误,进而基于该认识错误交付财物,最终造成财产损失。
从客观上看,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往往存在重合,即行为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难以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等方面进行“量”的区分,必须从非法占有目的上进行“质”的把握。[1]从主观上看,民事欺诈导致的婚恋纠纷与婚恋诈骗有着本质区别,两者在主观故意上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婚恋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不具备与被害人结婚的条件,恋爱交往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财物。而用欺诈手段的行为人系与被害人正常交往,只是企图通过欺诈手段在交往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或解决自身某种需要,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图,也是区分婚恋纠纷与婚恋诈骗刑民边界的一个关键要素。
2. 本案犯罪嫌疑人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通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排除意思”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中的“非法”部分,即行为人占有某一财物的状态被评价为“非法”的根本原因是因其侵犯、排除了他人对自身财物的合法占有。“利用意思”则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部分,即行为人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后能进行“利用”的持续占有状态。准确定性刑民交叉案件,需要严格适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案件事实作出实质判断,并通过行为人外化的“排除原权利人合法权利”与“合理利用财物”的行为充分反推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实践中,可结合客观行为是否具有欺诈性、财物流动是否呈现单向性、事后处置是否体现消极性等客观方面实质审查认定,进而判断行为人在实施诈骗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本案从客观行为的欺诈性来看,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接触之初,即隐瞒自身真实姓名及真实婚姻状况,在无法与被害人结婚的情况下以“恋爱结婚”为名与其交往,但实际只是想“玩一玩”,在被害人陷入“真实婚恋”的错误认识后多次拒绝被害人“见家长”的请求;从财物流动的单向性来看,二人在交往过程中,双方财物往来多为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的单向流动。被害人在陷入“订婚结婚”错误认识的情况下曾为犯罪嫌疑人购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犯罪嫌疑人给付财物的价值与被害人给付财物的价值之间明显不具备相当性;从事后处置的消极性来看,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后即用于购买减肥套餐等消费支出,相关财物去向与其虚构的“用于怀孕期间锻炼支出”的用途并不一致。犯罪嫌疑人在察觉无法圆谎的情况下,甚至故意编造自己在国外出交通事故导致流产的事实,并将被害人的微信拉黑,意图摆脱被害人。
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并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即具体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系以民事法律关系掩盖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2]综合前述三个方面,从客观行为的欺诈性、财物流动的单向性、事后处置的消极性等方面实质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在交往过程中隐瞒婚姻状况、真实姓名,虚构怀孕事实,致使被害人徐某某陷入“真实婚恋”的错误认识交付财物,犯罪嫌疑人将相关财物全部用于个人挥霍消费,不仅对被害人财物具备“利用”的持续占有状态,而且侵犯、排除了被害人对自身财物的合法占有,本案从整体上看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诈骗罪,不应评价为民事欺诈行为引发的婚恋纠纷。
(二)本案应结合刑民交叉情形厘清涉案财物性质,区分认定犯罪数额
1. 犯罪数额的认定应以厘清刑民交叉情形为前提
较之于非接触式婚恋诈骗,接触式婚恋诈骗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产生物理空间的线下交际,而且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其间的经济往来多为刑民交叉情形。在刑法与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相一致的场合,刑法应当绝对从属于民法。[3]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民商法上合法的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如果某一个行为的选择在民商法上有争议,甚至该行为被民商法所允许或容忍,就可能成为“出罪”的理由。[4]厘清双方经济往来中的刑民交叉情形,是为了判断是否有必要进入犯罪的实质认定。民法中当事人的不法行为可由民事手段制裁,民事制裁具有赔偿补救的功能,相比之下,刑事制裁强调刑法严厉性、谦抑性。民事不法行为阻却犯罪的理由在于,民事不法行为尚未触犯刑法的强制性规定,行为的危害程度远不够犯罪的程度,社会危害性较小。[5]因此,本案诈骗数额的确定,首先需考察民法对于本案的基本立场。双方经济往来是否全部认定为诈骗数额,需详细剖析本案刑民交叉情形并作具体法律分析,以分类甄别涉案财物的性质。[6]
一般情况下,恋爱双方经济往来常有“赠与”“共同生活消费”“借贷”“以对方所赠资金购买礼物或发红包转赠对方”等刑民交叉情形。结合本案,在双方“恋爱”期间,被害人徐某某处分的财物可分为以下四项:一是共同看电影、吃饭等日常花销,二是共同购买衣物等小额消费,三是购买金手镯、金手链、浪琴手表等大额支出,四是将信用卡一张交由犯罪嫌疑人使用。
本案存在两类刑民交叉情形,其中第一项、第二项关涉民事范畴中“共同生活消费情形”,第三项、第四项支出关涉民事范畴中的“赠与情形”。但是,上述两类刑民交叉情形在实践中是否认定为诈骗数额存在一定争议。针对“共同生活消费情形”,一种观点认为,男女双方恋爱过程中共同生活消费,并非犯罪嫌疑人全部获利,且现实中亦无法准确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受益份额,因此该部分数额不应当认定为诈骗数额;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隐瞒已婚的真相,以诈骗他人财物为目的与他人共同恋爱消费,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该行为具有诈骗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应当认定为诈骗犯罪的犯罪数额。针对“赠与情形”,一种观点认为,“赠与情形”于受赠人而言应当评价为民事的赠与行为,只要符合民法典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行为即应当受法律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赠送方是基于双方非真实的婚恋关系处置财产,其之所以实施赠与行为,系因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欺骗行为致使其陷入错误认识。
上述情形是否认定为犯罪数额,不应孤立适用法律,单纯从形式上以民法或刑法的规定片面认定本案,而应在厘定双方经济往来中的刑民交叉情形后,对刑民交叉情形进行实质审查,结合“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这一构成要件進行实质判断,以确定是否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实质内容,进而准确区分认定案件的诈骗数额。
2. 本案诈骗数额应结合犯罪构成要件区分认定
婚恋诈骗若构成诈骗罪,需符合诈骗罪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的一般结构。[7]本案中,被害人徐某某在与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相识之初即陷入错误认识,但是本案诈骗数额的认定,还需判断被害人在具体经济往来中是否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关于该问题,实践中可结合处分财物时双方交往的过程、被害人处分财物的原因、所处分财物的实际用途、被害人陷入何种错误认识及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进行分析。
结合上文关于被害人徐某某处分财物的分类认定,第一、二项系吃饭、看电影、购买衣物等“共同生活消费情形”。上述支出均为双方线下交往过程中吃饭、看电影、购买衣物等小额共同消费,从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而言,共同生活消费并非犯罪嫌疑人全部获利,且无法准确区分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受益数额。虽然犯罪嫌疑人奚某某虚构身份信息、婚姻情况与被害人交往,但是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这种存在刑民交叉情形的婚恋交往支出并不应当全部由刑法进行规制。一方面,本案被害人徐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经过交往,事实上建立了一定的共同生活亲密关系,双方经济往来中确实存在保障日常生活的必要共同支出。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支出该部分财物系为吃饭、看电影等真实原因,不能排除上述小额消费系双方“你情我愿”的共同生活消费。因而,被害人为双方共同生活等真实原因支出的上述小额财物,无法认定其系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处分行为,不应认定为诈骗数额。
第三项支出系被害人徐某某为结婚而购买的金手镯等“赠与”情形。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实被害人徐某某多次提出要求与家长见面等事宜,且双方于此时间段内发生性关系,结合全案证据及社会常理分析,此时购买的金手镯、金手链、浪琴手表等财物,具备确立婚姻关系的传统“三金”的性质。被害人徐某某之所以购买“三金”赠送给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真实原因系为与其“订婚结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实际属于已婚状态,被害人根本无法实现与之“订婚结婚”的目的。因此“三金”等带有特定寓意的贵重物品系被害人陷入“订婚结婚”错误认识的情况下的“赠与”,应当认定为诈骗数额。
第四项虽关涉民事范畴中的“赠与”情形,但犯罪嫌疑人奚某某通过虚构“怀孕需要报瑜伽课锻炼”的事实得到被害人信用卡,并在获得被害人徐某某对使用该信用卡的授权后,消费人民币20097元用于购买减肥套餐等。被害人徐某某之所以授权信用卡给犯罪嫌疑人奚某某使用,真实原因系为其怀孕期间报瑜伽班锻炼。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刷卡挥霍的行为方式、虚构怀孕的欺骗事实、财物的实际消费去向等可以认定被害人系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该信用卡,相关消费数额应当认定为犯罪数额。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奚某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三级检察官[210031]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211500]
[1] 参见杜邈:《刑民交叉型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3期。
[2] 参见国家检察官学院编:《秉鉴持恒大讲堂》,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4 页。
[3] 参见于改之: 《法域冲突的排除:立场、规则与适用》,《中国法学》2018 年第4期。
[4] 参见周光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逻辑》,《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3期。
[5] 参见刘缨、刘宝新:《刑民交叉案件的审查认定》,《中国检察官》2019年第20期。
[6] 参见陈长福、江帆、罗晓楠:《接触式婚恋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人民司法》2021年第11期。
[7] 参见王志展:《新常态下打击婚恋诈骗犯罪问题研究 》,《犯罪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