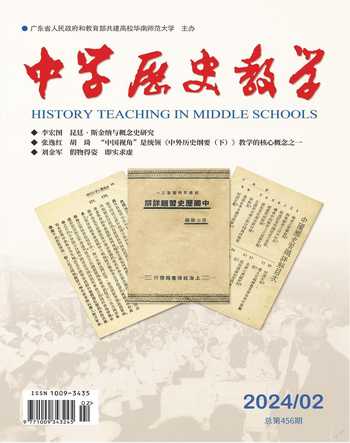昆廷•斯金纳与概念史研究
目前,概念史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也成为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工具。在这一热点中,也难免对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会产生一些理解上的误差和分歧。因此,目前亟需梳理与辨析清楚与概念史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剑桥学派”在思想史领域中的概念史研究,与德国考斯莱克以社会转型变迁为主旨的概念史研究之间的差异,从而让我们更为娴熟地运用概念史这一工具进行学术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昆廷·斯金纳概念史研究的评论
1978年,“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按照斯金纳自己的表述,此书的主旨是“我希望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1] 同时,“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到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2] 对斯金纳的这一思想史研究,著名的思想史家芬兰学者帕罗内认为,正是以这本书为标志,斯金纳“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3]并将其和考斯莱克相提并论。帕罗内还说,在斯金纳那里,其主要目标是论述近代国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他把语言行动的研究方式与国家概念化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对于斯金纳来说,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不僅是变化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成为变化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斯金纳对16世纪国家概念形成作用的论述和考斯莱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非常相同:至少大致在1800年左右以来,各种概念不仅是历史发展中的标志,而且也是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要素。
具体来说,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为起点,我们可以察觉到斯金纳历史研究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他早期关于霍布斯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仍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通过写作这本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概念史的独立地位。在斯金纳那里,他没有把各种概念看作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从语言行动的理论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们。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著述相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赋予概念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转变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就更为突出。[4]沿着这一路径,斯金纳后来持续进行概念史研究,例如对“自由”概念的讨论,和继续对国家概念的扩展性阐释。例如2010年,在斯金纳主编出版了《碎片化中的国家主权:一个竞争性概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Sovereignty in Fragment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这本论文集中,他自己也写了题为“主权国家:一种谱系的分析”(the Sovereignty State: A Genealogy)这篇文章。他说,“当我们在追溯一个概念的谱系”时,我们是在发掘这个概念早先被使用的那些不同的方式,从而可以为我们自己提供一种批判性,反思这一概念在当前被理解的方式。出于这些考虑,在接下来我将尝试速写一个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谱系。而对“自由”概念的讨论则展现在他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共和主义:欧洲的遗产》等论著中,这些研究成果被称之为“修正自由的概念史”。意为通过对在自由概念的考察改变了以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观”对“自由”这一概念定论性的内涵。另外,斯金纳对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的锡耶纳壁画进行研究的两篇长文也被看作是实践了的一种政治概念史。
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约翰·罗伯特逊也说,“剑桥学派”元老及后世研究者不仅研究理论和方法,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国家”在欧洲人观念中演变的历史。在此,我再次强调剑桥学派的主要关切是欧洲,虽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这一特点在斯金纳身上体现最多。追溯现代国家概念的起源,从而更深地理解国家的本质特征,一直被斯金纳看作首要任务,从第一部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1978)到近来尝试重建国家概念的“谱系”无不是如此。对斯金纳而言,这既是一项历史事业,也是一项哲学事业,理解历史事实是从理论上认识国家何以存在、国家对统治者和臣民提出什么要求等问题的最佳途径。目的是试图寻找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过使用这些基本概念,我们在现代西方才得以建构起“合法化”理论,当我们在谈论“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利”时我们还在继续使用这些理论。[5]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斯金纳“国家”与“自由”等概念研究的个案出发来理解其概念史研究的话,那么英国思想史研究者蒙克教授则从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来解析评价。他说,昆廷·斯金纳所追求与聚焦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动”分析的模式,以及概念史模式,使得英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之间变得水火不容——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强调需要有一种广阔的共时性语境,以便能辨明特定的概念;而在德语世界里,为了历时性分析的需要,人们则试图把个体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在英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强调人的能动性;相反,在德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则更强调历史过程。总之,正如我所希望表明的,在如何理解社会和政治概念中的历史性变化中,波考克和斯金纳代表着一种竞争性模式。[6] 思想史家保尔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六章“波考克、斯金纳与‘概念史’”中也指出,斯金纳现在将转向他自己的概念史版本,他对那些不关注概念使用的概念史不予考虑。
思想史家里克文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一书中认为,斯金纳转向了他自己的概念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版本。正是因为斯金纳的概念史和科斯莱克的概念史之间的差异,学者吉尔德伦才用“在剑桥和海德堡之间”这样的标题来区别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史流派。Jan Ifversen认为,在讨论概念变化上有两种路径,一是考斯莱克,二是昆廷·斯金纳。斯金纳是从修辞和语言行动方面展开,而科斯莱克则是从语言的交往(communication)维度上展开。
学者Sami Syrjämäki也认为在概念史研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一是考斯莱克,二是昆廷·斯金纳,斯金纳研究了诸如国家和自由的概念史。国外学者作出了很多这样类似的评述,这也表明,国际上的学者们都给予了承认,认为斯金纳是在从事着概念史研究,并且和科斯莱克一起成为了目前国际学术界两大概念史研究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如此,1994—1995年,一批研究概念史的开拓性学人,当然也包括斯金纳本人等十余位学者创立了国际性的“概念史研究小组”(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Study of Conceptual History),倡导开展概念史研究,特别是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他们举办讲习班,向全世界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开放,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概念史研究。我自己也在2006年8月在赫尔辛基大学参加过这一“概念史”暑期讲习班,亲身领略到了这一学术活动所焕发出的学术活力与开阔的视野。
二、斯金纳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可以说,在多年的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不仅实践了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对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作过很多探讨。这里引述斯金纳自己的一些表述,从中可以窥见斯金纳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这一研究独特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在接受芬兰学者的采访中,斯金纳说,概念史是由莱茵哈特·考斯莱克及其同仁最早启动的。我承认,对于概念史,我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担心它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观念史,也即把概念及其表述从语境中抽离出来,并把它们织入一个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犯了时代误植错误的故事中。但是只要能避免这种危险,那么,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去欢迎概念史的尝试,或者,正如我所强烈推荐的,我们所写的概念史应该去写“论辩中概念用法的历史”,在我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是指《自由主义主义之前的自由》)我甚至用这种立场写了“自由概念的论争史”。此外,在我即将付梓的著作中(指《Vision of Politics》),我还写了“国家概念的生成史”。[7]
这里斯金纳不仅直接表明了自己在从事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在很多文章中对概念史研究作出了阐述。例如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在对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的评论文章《一部文化辞典的观念》,以及在《答我的批评者》等文章中都触及到了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即对概念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里试举斯金纳的一些表述为例:
我遵循维特根斯坦所作出的表达:概念即工具,借助它,我可以最好地重申我的反对意见。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不但要洞悉那些表达着概念的術语的涵义,还要洞悉可能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刻上印记的长期连续性无疑在我们思想的内在模式中一直存在着;然而,我还是确信:不可能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概念在论辩中被使用的历史。同样,对于概念史而言,我们所写就的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过该概念的形形色色的多种不同的行为主体,聚焦于这些行为主体在使用该概念时的不同处境和意图。因此,在斯金纳这里,他强调和关注概念是如何被使用,以及在历史过程中如何概念化的。
斯金纳的《政治的视界》(Vision of Politics)三卷本著作被认为是代表其学术研究水准的总结性论文集。在第一卷“关于方法论”中,有很多篇目都涉及到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题为“回顾:修辞和概念变化的研究”一文中更是系统地对此进行了陈述。透过此文可以更好地理解斯金纳的概念史,以及他和德国考斯莱克概念史研究之间的差异。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这里较为完整地引述他的表达。
斯金纳写道,在本书(译者注:指昆廷·斯金纳所著《政治的视界》(Vision of Politics)第一卷《关于方法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面的一些篇章里,我已经关注到变化中的概念如何有望成为历史探究的一个独特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要书写这种历史,我们也许得集中精力专门考察一番用来描述和评价政治与道德世界(霍布斯谓之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的种种概念。这又进一步要求关注各种术语,也就是人们习惯用来表达这些概念的一整套规范性词汇。
我研究概念使用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动机,就是要质疑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和他的弟子们宣扬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洛夫乔伊称,总有一系列永恒不变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存在于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之下,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揭示并追踪这些单元。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并为思想史中存在着的更为激进的偶然性辩护。我的整个研究工程(如果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词的话)中的这一部分已经在本书第四章原文里交代过了。借用维特根斯坦在他晚期作品中的提法,我认为不存在观念单元的历史,而只有这些观念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所使用的历史。我斗胆认定观念使用的背后不复有他物,而观念使用的历史则是唯一应被书写的观念史。
这些说法中潜藏着我的一个信念,可以这样来表述:我觉得理解概念总是应该包含着理解在论辩中使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我在《观念史中的意涵理解》中首次提出这个信念时就表明了自己与二十世纪一个特殊的社会思想传统的联结。这一传统可以说起源于尼采,虽然我自己最初接触到它是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哲学里面,这一点在本书第七章(译者注:《“社会意义”与社会行为的解释》(‘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原文收录于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和斯金纳主编《哲学、政治与社会》丛书第四册,136 —157页)和第八章中有清楚论述。韦伯还有尼采都认为,概念不仅随时间变化,而且除了能提供关于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的一系列变化着的看法以外,再没有更多作用。概念是我们在理解世界的努力过程中带到世上的东西的一部分,由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不断改换的概念化行为恰恰是意识形态论争的内容。没有任何道德或认知判断可以不经由概念直接作出,而在我看来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完完全全是历史的。
不过,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质疑我一直讨论得比较少,更多是在思考,如果要富有成效地探究概念变化的现象,需要书写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还有一点值得在此一提,那就是我得出的观点同当下颇有名望的莱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在某些方面是类似的。考斯莱克和我都认为,规范性概念不应被当作关于世界的陈述,而更应被视为意识形态论争的工具和武器。我们也许都受到了福柯那句尼采式论断的影响:“承载并决定着我们的历史之形态乃是一场战争”。
我之所以觉得也许有必要像这样来厘清初衷,一个原因是我的很多批评者都认定我企图质疑的是考斯莱克的概念史。但情况绝非如此。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作先前所谈到的那几篇文章时,并不知道考斯莱克的研究计划。这一点无疑该受批评,但也的确是事实。直到梅尔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八十年代撰写论文,随后又在1995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社会和政治概念史》将其作品引介到英语学界,我才见识到他独具特色和规模的研究成果。
用考斯莱克的方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概念的历史性仍旧是一个问题,但即便有疑问,在我看来也不是对概念史书写本身的疑问,至少如果概念史是关于概念被使用的历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也尝试写过一些这样的历史。本书就收录了两个研究,其一是卷二中再版(并且大幅度修订)的写于1989年的一篇文章,有关“国家”概念的习得过程,另一个是卷三中再版的一篇与此相关联的文章,写于1999年,主题是霍布斯《利维坦》中的论述与前述传统的关系。此外我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写的也是英语世界政治理论中对于自由概念的一种独特看法的演变,此种看法认为自由不仅应被视为我们行为的做出(a predicate of our actions),还应被看做是与奴役状态相对的一种存在状态。我不认为这些研究与我写过的那些倡导在恢复概念意涵和意义的过程中需要理解运用概念能够做什么的文章存在冲突。相反,我的每个研究都有一部分目的在于指明,为什么某一概念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首次登场并流行起来,其方法就是要考察运用这个概念能做哪些没有它便做不了的事。
我的这些评论已表明,我是非常赞成身为哲学史家的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转变这一事实,还要把它作为研究的中心。道德和社会世界由于我们对因袭的规范性词汇的使用得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改变这些词汇的使用方式又是重估和改变世界的途径之一。结果就是,一切有评价作用的概念都有其谱系可循,在追踪概念使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单是社会变迁的反映,而且還是引发这种变迁的一个动因。我在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着力要表明的就是这一点。因而我一直以来也强调,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一方面会全力夺取可资利用的道德语言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忘寻找机会对传统信念发起挑战。让我咋舌的是最近竟然有批评者说我未能注意到第一种情况。本书第八章大部分篇幅就是在考察这种情况,下文要谈的修辞重述现象,目的之一也是要表明以上两者都是始终存在的。
我认为,研究概念转变现象要抓住的最根本性的一点已在第九章已有提及,这里我想再说得详细一点。严格说来,我们所能指望描绘出来的各种变化完全不是概念的变化,而是表达概念的术语在使用上的变化(这简直是有些自相矛盾的论点)。这些变化有许多种类,但我自己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中一种,即凯瑞·帕罗内(Kari Palonen)最近为我的作品所写的评论中所称的“修辞视域(rhetorical perspective)”。特定行为或事态是否允许某个有评价作用的术语对其进行恰当描述,围绕这一点所产生的争论就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虽如此,我却并不希望被人误读,似乎我将其作为概念被改变的唯一或是首要形式。因此在对修辞作进一步阐述之前,我想要介绍概念转变现象能够被历史书写所描绘的另外两种方法。
方法之一是追踪一段时期内某些特定的评价性词汇在使用范围或程度上的变化。其中又分为两种可能性:一方面,如果社会中兴起了新的行为,一般来说都会在与此相应的词汇的发展中得到反映,这些词汇对该行为加以描述和评价。我在第八章中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近代早期商业社会在欧洲的发展,特别关注了围绕节俭(frugality)、勤劳(industriousness)、守时(punctuality)、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等新兴价值而发展起来并日趋显著的评价性词汇;另一方面,已有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逐渐失去意义,社会不再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单独挑出来加以规定。这种看法上的改变一般也会在相应规范性词汇的衰落中留下痕迹。举一个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早期英语中有一套复杂词汇广泛用于描述和赞许“绅士般的(gentlemanly)”行为理想,同时贬低任何有损这一形象的行为,而在当代英语中这些已经消失。类似“无赖(cad)”、“粗人(bounder)”等概念以及与之相对的“绅士风度(gentlemanliness)”概念在英语历史词典里还存在,但因为其所评价的行为模式已经失去了社会意义,这些概念作为评价性术语就是过时的了。
这些例子有力证明了概念是有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表达概念的术语是有历史的。这些术语此起彼落,有的最终从视野里消失。但是我承认,这种概念“命运”的长时期走向的确不在我的主要兴趣之列。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其同道者的方法明显有别。他们一心着眼于时间的缓慢进展,对概念突变的点描式研究则远不及我关注得多。而我之所以对这类跨度更大的年代学研究兴趣较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种范式下变化的词汇仅仅只是更深层的社会生活转变的反映,就如前述几个例子中体现出来的一样。这就进而意味着要使概念变化的历史有解释力,必须能够在社会生活本身的层面上给出解释。然而我并没有关于社会转变机制的一般性理论,对于那些声称有这种理论的人我也多少有些怀疑。还有的理论主张时间本身就是变革的推动者,对此我更是难以苟同。约翰·邓恩(John Dunn)教授在一篇堪称经典的旧文中表示,时间促成改变的隐喻惯于以一种客观化的形态重新出现,这是有害的,会导致回到思想史中已经不足为信的一种模式,即传统总在抵抗进步,启蒙总与迷信斗争。
接下来我想结合第九章的论述谈谈概念转变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我们用于描述和评价社会世界的词汇不断发生皱折与侧滑的另一种方法。当规范性词汇对事物作出评价的能力在方向或强度上发生改变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一过程。这种类型的转变往往反映了一种改变现存社会观念和信仰的潜在企图,而后者又反过来在评价性语言中有所体现,主要形式有如下两种:其一是通常用于称赞某行为或事态的术语反而被用于表达或呼吁非难;其二则是原本具有谴责意味的术语却一反共识,声称此时的描述对象应受褒奖。
一旦这些意见被广泛接受,整个社会就可能最终变更其有关一些根本性价值或行为的态度,并据此改变其所使用的规范性词汇。因此,可以说这些例子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概念转变。然而,对于引发这些评价性术语失去评价作用或转褒为贬、转抑为扬的长期社会变迁,我仍然是关注甚少的。这方面的兴趣缺失又一次与考斯莱克形成鲜明对比,个中原因与前述相仿,我没有书写那种社会史的天赋。至于帕罗内等人对我更进一步的指责,说我和考泽莱克相反,未曾尝试研究一下是否有些情况下时间本身也需要被包括进特定概念的意涵中,我也承认确有此罪。我的确忽略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也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道理。
最后再来看看我主要关心的一种形式,即前述修辞性质的概念转变。这种变化开始于某个评价性术语对一个行为或事态的描述,而该术语通常说来不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受众相信,该术语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其原本意义是可以用来恰当指称当下这一事件的。如果成功说服人们接受这种判断,就能促使他们以一种新的道德眼光看待所涉行为。原先值得称颂的行为可能变得应予谴责,而曾经遭到贬抑的行为也可能转而大受褒扬。
这里又再次体现了我的偏好:我对上述长期变化没有对尼采所刻画的“顿悟时刻”那般兴趣浓厚。但我承认,如果想要勾勒出特定的规范性词汇在历史中的兴衰,努力考察长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帕罗内最近评价说,我的大部分研究可被视为服务于考斯莱克及其同事所从事的更具雄心的伟业中的一个方面,对此我也并无不快。考斯莱克的兴趣完全在于概念变化的整体过程,而我则主要乐于考察这个变化借以实现的技艺之一种。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工程无法兼容,希望两者在未来都能够继续发展,保持它们应有的旺盛的学术生命。[8]
从斯金纳自己的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己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也是在进行着概念史研究,在时间上,他和考斯莱克在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各自独立地进行着概念史研究,并且发展出了和考斯莱克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法,由此创立了独特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如果将两者的概念史进行比较的话,可以这样说,斯金纳的概念史是在思想史的框架中来进行,而考斯莱克是以社会变迁为主旨。考斯莱克关注于社会的长时段,而斯金纳则更聚焦于短期的急剧变化。前者关注重点为概念的历史语义探究,而后者则从语用学角度考察概念在论辩中的使用。但这丝毫不影响俩人都是在进行概念史研究,姑且可以称作为概念史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
由此,就有必要对斯金纳和柯斯莱克俩人概念史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予以说明,其实作为爱好辩论的斯金纳从来也不掩饰他的概念史和柯斯莱克之间的差异与不同,甚至有时还表现出一些不屑。那么,具体而言,斯金纳的概念史和考斯莱克的概念史在研究取向等方面有何差异呢?
三、斯金纳的概念史和考斯莱克概念史之间的差异
斯金纳自己以及一些学者如帕罗内和里克特等人都认为,斯金纳和考斯莱克的概念史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正如帕罗内所说,撰写概念史的一个条件,便是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意义,相反,一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有关。同样,“把概念的可接受性和竞争性作为它的可理解性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找不出斯金纳的观点和考斯莱克的概念史之间的差异。”[9] 英国学者蒙克教授也评论道:“至少在如下两个目标上,波考克他们与德国的概念史是相同的:第一,复原历史行为主体或作者所赋予其自身行为的意义,在英语世界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摆脱洛夫乔伊式超历史的观念,而在德语世界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抛弃历史主义;第二,把伟大文本或经典文本置于一种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以便复原意义的多元历史。”[10]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对此,斯金纳自己也毫不掩饰,多次表达过他和考斯莱克概念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当然学界业有共识,认为斯金纳和考斯莱克在不同的空间里,发展出了不同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如果说要进行一下归纳概括的话,斯金纳借助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等人的语言哲学和谱系学,从修辞和言语行为与谱系学方面进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莱克则借助于阐释学理论,从社会史的维度与现代性形成的所谓社会转型的“鞍形期”来进行概念史研究,从而将概念作为社会的显示器和推进器。对于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概念被使用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的主旨,概念的含义只有在概念被使用和表达中才得以存在与被界定,否则只是处于静态的休止状态。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也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是,不要问语言的意义,要问语言的用法,要问这些概念是用来干什么的,或者像尼采所说,将概念视为用来辩论的武器。[11] 由此,也发展出概念史研究的不同研究重点,一种是着重于在歷时性中追寻概念意义和内涵变化的历史语义学,和另外一种以运用概念和对概念展开竞争性话语表达的历史语用学。而对于斯金纳而言,显然他是更关注于历史语用学的研究路径。而对于考斯莱克式的概念史,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概念的形成,通过历史语义学这一历史演变的梳理考察,勾勒词汇如何成为了概念,其意义又如何在经验空间中被固定和界定。如果从大的学术研究领域来说,斯金纳是在思想史的范畴中进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莱克则是在结合社会史的框架中来展开概念史研究,当然这并不否认概念史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正如里希特所说:“在考斯莱克看来,‘概念史’并不仅仅服务于‘真实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目的。‘概念史’是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最好是在与解构性社会史的紧张互动中展开概念史研究。群体和运动所使用的概念框定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的行动。”[12] 考斯莱克自己也说,要把社会史和概念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它们之间彼此需要并相互依赖,但却不会合而为一。[13] 他曾经明确地说:“社会史和概念史并非同一。”[14]但他也对此详细解释道,“由于社会史和概念史具有不同的变化速率,并且是基于不同的重演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史的学术术语依赖于概念史,因为概念史能帮助社会史来查验语言形式储存下来的经验。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洞悉一去不返的现实与其语言性证据之间永远难以弥合的罅隙,概念史仍然依赖于社会史的发现。[15]
因此,面对两种不同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和路径,尽管不同的学者会站在不同的立场,甚至是偏好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但作为一种学术史的梳理和讨论,我们不能用斯金纳的概念史来否定考斯莱克的研究范式和价值;或者相反,以考斯莱克的概念史为标准来否定斯金纳所进行的概念史就不是概念史,以及无视斯金纳在概念史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从学术研究的旨趣来说,从不同的范式,不同的路径展开研究,甚至在不同研究范式相互的批评和竞争当中只会带来学术的进步,推动学术的深化。正是因为这样,斯金纳才明确承认他和考斯莱克研究范式的不同,并批评考斯莱克的概念史研究。例如斯金纳在南京大学讲学时所接受的访谈中,就这样说道,尼采曾经有句很精彩的警句,如果一个概念有历史,那它就不可能有定义。这意味着,理解一个概念的办法就是用谱系式的方式来处理它,也就是说,去发现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演变和被辩论的。我自己也试着采用这种办法。我的谱系学与尼采有不同。对尼采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一旦辨别出某种观念的根源,就意味着使这种观念变得不再可信,这就是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主要观点。因此,谱系学永远都是对你所探讨观念的谱系的批判。在我看来,这并非绝对适用,也可能存在着以赞颂为目的的谱系,或者仅仅是追踪对某个明确概念的各种相互对立的理解方式的谱系。因此,就我们决不能给出一个一致认同的定义而言,我的谱系学是尼采式的,但我并不是在试图动摇概念用途的可信度,而仅仅是在对它们进行追踪。
科塞勒克(人名原文如此——笔者注)想写的是诸概念的历史,这种看法认为,存在着所谓的“概念之历史”(Begriffsgeschichte),存在着这样一种研究,也就是对各种概念的研究。我对这种路径持怀疑态度。首先,我们研究的并非各种概念,而是概念的各种语言表达(verbal expression),因此,我们永远都要讨论语言。我已经表明,理解话语,就是对论辩中这些概念各种用途的理解,所以严格说来,这并非概念的历史,而只不过是概念可供使用的方法的历史。如果你要写的是一个词语的历史,哪怕只是这个词的语言表达的历史,像科塞勒克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学生通常所做的那样,在我看来,你必须面对的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你并未给这个词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任何说明;诚然,这个词已经出现在常用词汇表中,但是它在词汇表中是否居于中心位置,它与其他术语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是否变化?这种写作概念历史的路径并不足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从来没能真正被科塞勒克的作品说服。
在我看来,如果你成功地渗透到某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以及其中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理解中,你能取得的一项收获就是,对那些在大家看来都很重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这里又要提到另一种维特根斯坦思想了,或许这些概念中存在着的仅仅是某种“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他的原话是“Familienähnlichkeit”。如果仅仅从事实层面上看问题,我们很可能会受到误导。例如,在西方古典时代,人们谈论“共和国”和“自由”,我们也谈论“共和国”和“自由”,但是大家说的是一回事吗?因此,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给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他们谈论的“自由”“国家”(state)或者“平等”和我们的概念相比,是否是同样的概念,或者说概念之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假设我们发现,我们的历史研究向我们表明——就比如我自己的作品中也采用的一个案例:尽管西方古典时代的人们也讨论“自由”,但是他们所指涉的和我们所指涉的存在很大的出入。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甚至是现代早期关于“自由”的讨论,显然是这样的。
但是我还要简单说明的是,毫无疑问,就当前的现代西方而言,思考政治自由的標准方式就是将其视作在追求自己目标时免于干涉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去读古代关于“自由”的讨论,它们完全不是以干涉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们的基础是更加普遍的宰制和依赖关系(domination and dependence)。在思考什么才意味着自由时,首要的看法就是不受宰制和依赖。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能认识到,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理解,但这并非我们的理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我自己关于国家理论、自由理论和权利理论的作品中,我的一个心得就是,这些术语通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遵循着不同的理解道德和政治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你首先能成功地按照那个世界本来的方式将其重建,你或许会发现,存在着某些可以直接从中学习的东西。当然,这并非是说,通过反复阅读这些文本,可以发现着某种永恒真理。相反,你将会获得一种不同的思考这些基础性概念的方式,若是你对这种方式进行反思,或许会发现,这种在古代而非现代西方存在的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是一种更加有收获、更加有益的理解方式。“自由”这个问题如此,“正义”更是如此。若是我们想要利用那种“自由”理解,那么它或许会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判方式,去批判我们西方社会的组织方式,让人们认识到,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理解“自由社会是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谓人文研究的功利主义收获。
同样,在南京大学的演讲中,斯金纳在回答提问时说,“你问到了科塞勒克,科塞勒克并不关注争论者在干什么的问题。他的全部工作全都是关于概念本身的,还有概念史。我在这里想展现的是反科塞勒克的方法,我并不反对福柯,但我完全反对科塞勒克。在科塞勒克的晚年,他和我曾经同台交流,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观点不同。我们不同意对方的观点,然后我们握手告别,说我们可以等到下次再谈。科塞勒克的错误在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术语在对话中的冲突,没有意识到这些术语没有一个公认一致的含义,而认为它们的含义是融贯自洽的(self-consistency)。他编写关于术语的辞典,解释有时这个概念是这个意思,有时是那个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完全是与不断上演词语战争(war of words)的现实社会相脱离的。而且词语战争是实实在在的战争,正如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所反映的那样。”[16]
也是在2017年,斯金纳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他和考斯莱克研究主旨上的差异。他在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时说道,你提到了柯赛雷克(人名原文如此——笔者注),他致力于概念史研究。从我们之前的交谈中你能看到,我其实并不认为,严格说来,我们可以书写某种概念史。我们可以书写的历史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在论辩中的各种用法。理解某个概念不仅仅在于给出一个词典条目。柯赛雷克等人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即说明这些术语的反复出现。我们需要解释这个术语被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概念?运用这个概念到底是为了什么?它在相关论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论辩运用了某个概念,那么这个论辩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核心论证,还是一个边缘论证?他是一个受到质疑的论辩,还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论辩?在我看来,聚焦概念本身无法帮助我们了解那种我所感兴趣的历史论辩。我认为,概念是工具,而理解概念其实是要理解人们能够运用概念做什么。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柯赛雷克的研究方法。[17]
同样,斯金纳在评论一些思想家的学术贡献时所说:“他们强调的是下述观念:概念并不是有着固定意义的永恒实体,而应该被看作武器(海德格尔的建议),或者是工具(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对概念的理解部分来说不过是看谁在挥舞着它们,挥舞的目的又是什么。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在起初援引的正统观念——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分析这些道德的语言或者政治的词汇——自然也就令人怀疑了。沿用福柯提出异议的方式来说,完全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毫无变化的概念和意义的网络,等着我们去做中性的分析。”[18] 斯金纳自己在进行概念史研究中也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秉承着这一学术立场,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概念的如何被使用,由此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在斯金纳那里,概念史研究不仅仅是要追寻概念涵义的演变,还需要思考在这个社会的特定时刻概念内涵的这一新变动为何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其成功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又是什么。是一种对概念的修辞性打动了人们,从而被接受,还是被政治权力所强力确立起来的合法性,或者说,能够成功推动概念变革的主体力量是谁,同样,人们又为什么不能够抵挡这一概念内涵的变革。因此,概念内涵变革与使用概念的主体则密切关联,由此就需要研究概念的使用者。
其实,斯金纳和考斯莱克之间在概念史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不仅仅是历史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差异。在蒙克教授看来,这是关涉到如下基本问题,历史的创造者是谁,或者说,要去回答构建历史的行为主体是什么。在斯金纳看来,历史的行为主体是概念的使用者,而非概念本身。如斯金纳所说: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过该概念的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聚焦于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在使用该观念时的不同处境和意图。[19] 斯金纳也曾这样说道:“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必须总是包括从执行社会行为的行动者的角度,来恢复和解释那些行动的意义,或许甚至本身就要采取这种形式。”[20]也如蒙克教授所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行为主体各种行动的历史,而不仅仅只是各种过程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它可能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21]
实际上,这是在提醒人们,在概念史研究中,要防止一种“非人格化“的倾向,即只看到了某种概念在运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忘却了历史行为主体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犹如英国学者蒙克教授所说:在概念史那里,人类基本上是消极的工具。概念变化是一个过程,专门用来描述其动力机制的措辞是一些自然隐喻:流动、过程、现象和结构,而不是由可辨识的行为主体所驱动。[22]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呈现出差异,但在我看来,蒙克教授下述的这番话令人警醒。他说:“现在,人们倾向于把特定语言以及它们的概念和型构看作是生成了人类世界和历史,并进而倾向于否定人的能动性,认为言者、作者和行为主体都是由语言和文本所决定的。在现实的语言建构中,人们又重新铸造了某种决定主义,这种决定主义曾渗透到某种类型的物质史中。但是对于人类能动性的强调做出了相反的声音,在我看来,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人(并且正如人们所日益认识到的,女人)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语言环境中创造历史的,但他们仍然是在创造着他们的历史。而创造历史就意味着以一种革新性的、创造性的和充分能动的方式来使用可用的语言。假如人们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即便没有语言——这种语言总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人们也可以创造歷史。那么,这就等于相信:如果没有惟一的介质——也即空气,康德的鸽子将飞得更高。飞得更快,但是,实际上,正是由于空气的存在,鸽子的飞翔才成为可能。”[23]
四、概念史研究的未来
对斯金纳的这些批评,以及从语用学视角强调概念的论辩和语言行动,考斯莱克也有过回应,甚至也可以说是反批评。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个体都依赖于语言工具,如果没有语言工具,社会行动、政治争辩或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存在,但也应该看到,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显然并不能与诱发该事情或诠释该事情的语言阐释划等号。真实发生的历史与其语言性工具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言语行动并不等同于行动本身,尽管正是在言语行动的帮助下,行动才得以准备、启动和实施。历史与言说的关系应该是,没有言说,历史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历史绝不等同于言说,并且也不能化约为言说。[24]因此,我们必须判定,在过去的历史中,什么是由语言所促成的,什么不是由语言所促成的。[25]
考斯莱克的这番话的确是点明了双方在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所在,例如就其历史事件与沉淀在历史之中的人类经验而言,特别是作为历史的“社会”来说,都包括着一些非语言性的内容,象人类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等,这就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界定语言行动的边界,将非语言行动而构成的历史内容呈现出来与加以研究。
实际上,就考斯莱克的概念史研究而言,其与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不仅在于言说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差异,而且还在于,在考斯莱克这里,其概念史在社会史的范畴内还内含了这样两个核心要素,“经验空间”和“预期视域”。对此,思想史家里克特教授这样解释道:对于考斯莱克而言,经验,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前人的经验,都意指陌生新奇之物向本土寻常之物的转换。在这种关联中,空间这个德语词意指:在通往由过往经验所构成的空间而预期未来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路径。这两个范畴(经验和空间)都是时间性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大不相同。就如下面看到的,考斯莱克的假设是这样的:新时代或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在德语国家,它们是现代性的迎宾人——是由体现在传统中的过往经验和对未来的转型性特质的信念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所决定性地塑造的。考斯莱克认为新时代或现代具有一种新的时间特性,现在,时间不再被视为所有历史共有的一种中立维度,而被看作史无前例的历史驱动力。人们之所以划分世纪,不是将其作为时间的标记,而是将其作为秉有独特时代精神的历史纪元。所有这些历史时期都被置于一种不可抗拒和无法逆转的发展进程之内。当下之所以被认为是新的,是因为它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未来。于是,在经验空间和预期视域之间的关系中,遂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26]
可以说,在考斯莱克那里,历史被“时间化”了,被隔分成为过去、当下和未来,我们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态度又是如何,过去、当下和未来它们又如何进行组合,形成为一种关系,并在这样的变幻性的组合中形成了历史,赋予了历史以意义,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系列概念,以及为既存的概念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实现了转义。例如就“革命”这一概念而言,随着对时间感知的变化,“革命”这一概念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里克特教授指出:“随着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的感觉日益滋长,那种日益加速的变化感也随之滋长。因为发展被认为正日益迫近,而经验空间看上去似乎压缩了。以过去为取向的传统、习惯和规范更容易遭到贬斥和抛弃。对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变化的任何抵制,都被描述为遗老遗少们的应激反应,故而是反动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核心概念之一便是“革命”这个概念,其意涵现在已经有所改变,已由原初的循环往复之义转变为如下新义,即意指一个新型但却更好的政权和社会的出现。”[27]从这一概念个案中可以看出,概念的形成与转义与我们对时间的认知密切相关,也体现了对历史的理解,同样在这里,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概念的形成转义也密切相连,相互缠绕,但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形式,概念史研究从社会史之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两个自主性的独立研究领域。这样,在概念史研究中,“时间性”正成为概念史研究的鲜明特征。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格带着赞叹的口吻说道,在思考历史中的时间经验中,考斯莱克实际上在追寻“在每个当下时刻,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维度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28]受到考斯莱克的这些启发,目前“历史时间”正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9]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性研究,概念史依然是在历史的框架中而展开。詹姆斯·法尔曾经这样写道:“要理解概念的变化,就要求和强调用历史的眼光来理解问题。”[30] 与此同时,他也对概念史研究的进路作出了表达:“既然概念是语言的构成物,概念史就总是语言(甚至词的)历史,原因在于,概念史是我们进入政治行为人用概念所构成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31] 当然,概念是要在词语的表达中被赋予定义的,但同样,社会的实践本身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犹如斯金纳所说,“社会实践有助于赋予社会词汇以意义,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社会词汇有助于构成这些实践的特点,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32] 的确,如果在社会实践与词语表达这样的维度上来理解和进行概念史研究的话,自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式,从而可以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何进行概念史研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艰巨性任务,既需要像斯金纳这样天赋异于常人的思想史家的独自创造,也不可缺少如考斯莱克这样善于组织领导的领袖性人物,在其领导下能够组织众多学者一道展开研究,编写出版著作。诚如“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同的研究路径也都共同推进了概念史研究的深入,同样,如同概念具有竞争性那样,不同的研究路径的竞争性差异更展现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开放,而非独断与唯一。为此,重温考斯莱克为“概念史”所写的词条也可看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创始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刻的洞察力,高度概括凝练的能力和集采众人之长的那种智慧与包容,以及对推进未来研究的期盼。他说:“概念史首先询问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谁、为了谁、出于何种目的或者哪种形势、如何进行了定义。概念史经常追问的那个唯一的要求——正是这种出于具体的语言需求,在语言上用概念的方式进行了回答。期间,所有的概念不仅带来了共时性的、唯一的诠释作用,而且还总是同时呈现历时性的等级序列。在语用学上,即便仍然受到修辞方面的规范,但是它们集中于当时的需要,以寻求赞同。相反,在语义学上,上百年的体验经常被保存下来,以致某种概念的说服力既得到了扩展,又受到局限。最后,在句法和语法上,一种概念运用的活动空间虽然长期重复,但仍处于缓慢的变化中。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在每一段概念史中,共时性与历时性都被交叠于各种方式中,而不可分离。
因此,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这些概念包括:回顾性概念,即保存了旧体验,反对意义转换;展望性概念,即抢先行动,以创造新的或其他未来。在术语学上,人类的概念有:经验性概念、运动性概念、期待性概念和未来性概念。
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交错现象,使得每一段概念史都不得不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得到书写。”[33]
站在概念史研究的不同指向来看,无论是斯金纳还是考斯莱克的概念史研究,都深化了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学的一次范式创新。今天,梳理和研究这一学术流派,辨析其中的差异与共同,理解其对多学科知识的汲取接收,将会为我们未来的历史研究获得一种宝贵的学术资源。
注释
[1] [2][ 英 ] 昆廷 · 斯金纳著,奚瑞森等译:《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2、2—3 页。
[3][4] [ 芬兰 ] 凯瑞 · 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 ·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 · 政治 · 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8 页。
[5][7] [意]达里奥·卡斯蒂廖内、[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37、344 页。
[6]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8] Quentin Skin ner:Retrospect:Studying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In《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5—187. 此處内容由华东政法大学的关依然翻译。
[9] [芬兰]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38页。
[10]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49页。
[11][17]李强主编:《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5、174—175 页。
[12] [意]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9页。
[13]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39页。
[14] Reinhart Kosellek: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
[15]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41页。
[16] [英]昆廷 · 斯金纳:《西方关于“自由”的论辩》,载孙江主编:《新学衡》,第二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3頁。
[18] [英]昆廷·斯金纳主编,张小勇等译:《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2016年,第9页。
[19]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0页。
[20] [英]昆廷·斯金纳主编,张小勇等译:《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第4页。
[21] [22]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0页。
[23]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0—71页。
[24] 详见[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26—27页。
[25] [英]依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30页。
[26] [意]达里奥·卡斯蒂廖内、[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7—68页。
[27] [意]达里奥·卡斯蒂廖内、[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8页。
[28]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格著,黄艳红译:《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29—30页。
[29] 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格就承认受益于考斯莱克所提出的“经验空间”和“预期视域”这一概念,考察其中的张力、审视其与当下的关联方式,以此来探讨过去与未来,才显得特别有意义。详见[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格著,黄艳红译:《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第29—30页。
[30][31] [ 美 ] 詹姆斯 · 法尔:《从政治上理解概念的变化》,载特伦斯 · 保尔、詹姆斯 · 法尔等编,朱进东译:《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第 20 页。
[32] [英]昆廷·斯金纳:《语言与政治变化》,载特伦斯·保尔、詹姆斯·法尔等编,朱进东译:《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第17页。
[33] [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1&ZD2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