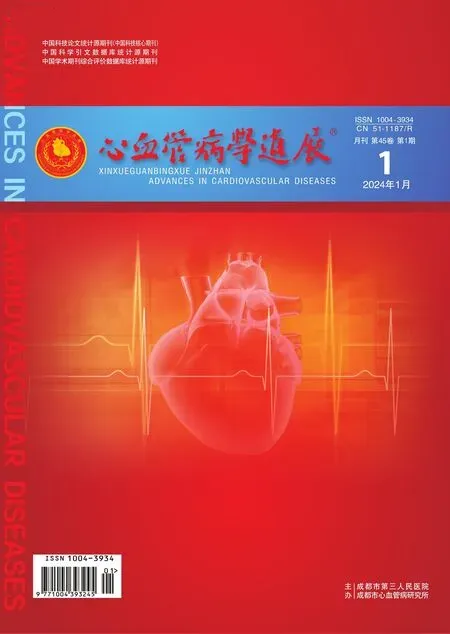高原地区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的研究进展
关璐茜 罗勤 胡海波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北京 100037;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肺血管病中心,北京 100037)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是中国发生率第一的先天性出生缺陷,动脉型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是CHD最常见且较为严重的合并症,其严重程度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由于高原地区低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高原地区CHD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平原地区,且高原地区CHD较平原地区更易并发PAH[1],如未及时矫治,PAH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艾森曼格综合征(Eisenmenger’s syndrome,ES),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及预后。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CHD-PAH)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非常缺乏,现就高原地区CHD-PAH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2-4]显示高原地区CHD的患病率约为7.21‰,明显高于平原地区。同时,高原地区CHD人群较平原地区更易发生PAH,国外研究[5-7]报道成人CHD患者有5%~10%出现PAH,国内研究[8]报道有6.48%的住院CHD患者并发PAH,而另一项研究[1]显示高原地区CHD患者中伴有PAH的占58.4%,较平原地区明显上升。另外,该高原调查报告[1]显示,海拔2 500 m、2 500~3 500 m、>3 500 m的CHD患者并发PAH的比例分别为55.2%、57.2%和68.7%,即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CHD患者并发PAH的比例增加。高原地区并发PAH的CHD患者在病种构成上,最常见为房间隔缺损合并PAH(52.8%),其次为动脉导管未闭合并PAH(23.5%)和室间隔缺损合并PAH(14.3%),且室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较房间隔缺损更早发生PAH(主要在18岁以前)。
2 发病机制
高原地区CHD-PAH的形成和发展是遗传、低氧环境暴露及心脏缺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机制十分复杂,至今尚未完全阐明。目前研究认为高原地区CHD-PAH的发病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遗传学基础
高原地区个体和人群对CHD、高原肺动脉高压(high-altitude pulmonary hypertension,HAPH)的易感性差异以及世居人群对HAPH产生的保护性适应均可能与遗传有关,这对高原CHD-PAH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
研究显示,在高原地区,藏族原住居民的血红蛋白值小于汉族高原移民[9],且青藏高原世居人群发生HAPH的风险低于外来移居人群[10-11],这可能是高原世居人群世代遗传适应的结果。迄今为止,发表的大多数基因组高海拔适应研究都集中在西藏高原人群和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通路候选基因上,EPAS1和EGLN1作为HIF途径的关键调节因子,已在多项研究[12-14]中被确定为藏族人低氧适应首选的自然选择候选基因,也被报道为其他高原人群的适应性候选基因[15-16];EPAS1基因编码HIF-2α亚基,EGLN1编码氧感知脯氨酰羟化酶,二者在低氧条件下可抑制HIF诱导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合成,从而降低了血红蛋白的浓度[9],进而使肺动脉压下降,使个体对HAPH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部分研究[14,17]也报道了可能作为HAPH适应性候选基因的其他HIF通道基因,包括PPARA和HYOU/HMBS等。
尽管高原人群对HAPH具有一定的遗传适应性,但与平原地区相比,HAPH的发生率显著升高[18]。当低氧环境的影响超过了适应能力的限度,高原人群仍将发生HAPH,这也提示了适应的相对性。此外,部分人群对HAPH的遗传易感性也是高原地区HAPH高发的原因之一。Morrell等[19]和Aldashev等[20]进行的研究显示,吉尔吉斯斯坦高原人群的ACEI/D基因多态性与HAPH的发展有关,其中ACEI/I基因型在吉尔吉斯斯坦HAPH患者中显著高表达,提示ACEI/I基因可能为HAPH的易感基因。3a/4aET-1基因多态性也被报道可能参与HAPH的发展。有研究[21]发现突变型-4aET-1等位基因的频率在患有HAPH的高原人群中显著高于健康的高原人群。需注意的是,不同地理位置的高原人群对HAPH的遗传易感基因可能不同,其遗传机制十分复杂,更多在HAPH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易感基因尚需进一步探索。
具有某种染色体模式或显著易感基因的家族或群体CHD的患病率升高,提示CHD的发生与遗传有关[22-23]。目前已发现SIRT7、FOXP1、FFAR4及CCN1等基因可能与高原藏族CHD的发生相关[24-25],其中SIRT7(c.C181G,p.Leu61Val)罕见错义突变、FOXP1基因外显子序列的rs201138716、rs202173892和2个新发现的突变位点(p.Q71K,p.T245R)、FFAR4基因外显子序列的突变位点(p.Q273R)、FFAR4基因非编码区rs10882282位点的等位基因C可能是高原藏族CHD的致病因素,而CCN1等位基因(rs3753793-C和rs2297141-A)可能与缺氧适应相关,是与降低房间隔缺损风险显著相关的保护性基因[26]。另外,EPAS1是高原最重要的适应性基因之一[27],EPAS1基因突变也被报道可能对西藏非综合征性CHD的发生具有潜在致病作用[28]。
2.2 解剖学基础
有研究[29-30]表明,高原地区居民远端肺动脉分支的肌化程度较平原地区居民更高,肺动脉管腔横截面积更小,这可能是出生后缺氧引起“胎儿模式”肺血管的重构延迟和不完全退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使高原居民更易发生PAH。低氧张力、高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及高右心室压力可抑制导管/孔道的早期闭合,从而导致导管/孔道闭合失败,最终形成心脏缺损[22,31]。
2.3 体-肺分流的影响
高原地区CHD患者由于缺损所致的体-肺分流,肺血流量增加和压力升高,肺血管承受的剪切力增加,促使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功能紊乱,缩血管因子分泌增加而扩血管因子分泌减少,平滑肌细胞增殖以及外膜纤维化,引起不可逆的肺血管重构,最终形成PAH。
2.4 高原低氧刺激的作用
长期低氧刺激可引起肺血流动力学改变、肺血管收缩以及增厚重构,均在PAH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有研究[32]提出了“ROS/Kv/HIF轴”的概念,其在低氧性PAH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的始动作用,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缺氧条件下形成,激活HIF并抑制位于肺小动脉的钾离子通道(Kv)的活性,Kv活性降低促进细胞内钙离子的增加,最终引起肺动脉血管收缩。同时,长期低氧环境下机体可通过HIF调节内皮素-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转化生长因子β等各种生长因子使肺血管重构,有研究在高原性心脏病患者的肺动脉平滑肌中检测出了较高水平的转化生长因子β,提示其在高原CHD-PAH发展中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33-37]。长期缺氧环境下机体血氧饱和度降低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也可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进而引起肺血管重构[38]。在高原环境下,长期慢性低氧刺激肺小动脉收缩,并使其管壁增厚、管腔狭窄、PVR增高,导致肺动脉压升高,对CHD形成PAH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此外,长期处于高原环境下,低氧通过诱导HIF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合成,进而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多[39],过度的红细胞增多加上肺小血管管壁增厚、管腔狭窄,最终使高原居民血流动力学具有高血红蛋白、高黏滞度和高凝状态等特点,这些特征加剧了PVR的升高,也促进了高原地区CHD-PAH的发生和发展[1]。
2.5 低温环境的影响
除了缺氧,高原地区居民的肺动脉压还可能受到低温环境的影响。有报道[40]显示,在易感人群中,长期暴露在寒冷环境中可能会引起异常的肺动脉压升高和肺血管结构重构,而在温暖的环境中肺动脉压升高可被逆转,这表明高海拔地区的低温环境也可能促进肺动脉压的持续升高和PAH的发展。
3 最新分类
根据《2022 ESC/ERS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41],临床上CHD-PAH分为4类:ES、左向右分流相关的PAH、合并小缺损的PAH和术后PAH(表1)。目前,高原CHD-PAH也沿用该分类方法。

表1 CHD-PAH临床分类
4 诊断
一般结合病史、查体、心电图、胸部X线检查和超声心动图等即可初步诊断CHD-PAH,确诊则需行右心导管检查。需注意的是,有研究[42]表明,将高原地区危重CHD的血氧饱和度筛查通过阈值由≥95%降至≥93%,可避免重复筛查和减少假阳性。在海平面静息状态下,当右心导管检查测得平均肺动脉压>20 mm Hg(1 mm Hg=0.133 3 kPa)时,可诊断PAH[41]。但对于高原CHD-PAH,目前尚无明确的诊断标准,临床诊疗中往往将居住在海拔2 500 m以上、平均肺动脉压>30 mm Hg或肺动脉收缩压>50 mm Hg的人群定义为HAPH患者[43]。
5 治疗
早期诊断并尽早手术是治愈高原CHD-PAH的根本方法。对于存在明显左向右分流但PVR无明显升高(肺/体循环血流量比值>1.5)的CHD-PAH患者,可考虑手术治疗修复缺损[44],最常用的治疗术式为介入封堵术。介入手术治疗CHD疗效较好,手术成功率较高,创伤较小且安全性高。一项对968例高原地区CHD患者行介入治疗的研究[45]报道其介入手术成功率为100%,无任何死亡病例,疗效确切,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1.55%。同时,也有研究[46]表明高原地区动脉导管未闭患者较大的缺损管径为介入封堵术增添了一定的挑战,术后残余分流和装置栓塞/移位的发生更频繁。
对于直接手术关闭缺损危险性大的ES前期或“边缘型”PAH患者,需经全面评估后确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部分患者经过充分靶向治疗后可重新获得手术机会,但确定其手术适应证较为困难,如何使更多此类患者重新获得治愈机会仍是目前研究的焦点与难题。
对于PVR明显升高(肺/体循环血流量比值<1.5)的CHD-PAH患者,尤其是ES患者,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不宜再进行缺损修复,而应根据PAH危险分层指导药物靶向治疗以延缓PAH的进展、改善生活质量[44]。目前高原CHD-PAH靶向治疗相关的研究数据十分缺乏,仍需开展更多大规模、前瞻性的长期疗效试验为高原CHD-PAH靶向药物治疗提供更多可靠的数据。
部分终末期CHD-PAH患者已采取最大程度靶向治疗后病情仍恶化,肺移植或心肺联合移植是其唯一的希望。由于供体稀缺,目前接受肺或心肺联合移植的患者数量远低于需移植的患者数量。此外,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移植价格昂贵以及感染等问题也使该治疗受到限制。
6 总结
近年来,介入和外科手术水平的提高以及靶向药物的应用,为高原地区CHD-PAH患者争取了更多的治愈机会,大多数轻中度PAH患者能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但重度PAH尤其是ES的疗效仍不理想。早期检出并尽早手术以避免PAH发展为ES是根治CHD-PAH的重要手段。此外,不同个体对低氧诱导的PAH的易感性存在差异,未发生PAH的高原居民可能存在保护性基因突变,进一步了解高原居民的遗传适应机制有利于为发掘新靶点提供新见解,未来基因治愈有广阔的前景。目前专门针对高原地区CHD-PAH的研究较为不足,尚待更多研究为其有效诊治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