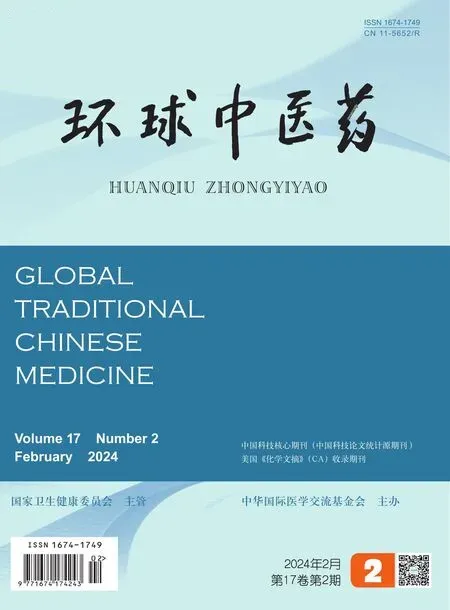浅析血证也可以巧用汗法
刘平 吴凯 赵生文
“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本是汗血关系的一种生理性认识,但后之医家在临证分析中多以“津血同源”立足,在血证的临床诊疗中更是将汗法弃而为禁,甚至逐渐贯彻为临床医教内容的准绳教条。依循于此,常将血证部分真实病机与治疗精粹湮没,尤其在一些特殊案例诊疗时常显捉襟见肘,明清医家如赵献可、王清任、唐容川等在其临床总结中,对血证禁汗的传统观点进行回顾反思,在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巧妙运用汗法在部分出血顽疾获愈上起到关键作用,并具体从病机症候学角度阐释了血证证型分化后的汗法应用范围与方式,近年来屡有诸如运用风药取汗治疗血液病的报道及研究。笔者以古籍及临床体悟梳理汗法之于血证病机学原理,从血证的禁汗缘由、危症运用、汗法机理、方药视角等方面分析架构血证下的汗法运用的合理性及理论基础。
汗法作为八法之首,是通过开泄肌腠来驱除表邪的治则。汗法由来已久,屡经发挥,渐成影响深远、内容详实、系统完整的治法,在临床实践中运用于诸多疾病。早期典籍里,汗法在血证中运用并非罕见,至宋元后渐摈弃不显,经明清两代重新审视,时至院校再为医戒,这一现象值得留意。综上,对血证的治法讨论是立论病机还是立论病证,加之病证与病机视角的应用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1 血证禁用汗法的立论缘由
1.1 津—血—汗关系下血证禁汗的机理再探
《灵枢·痈疽》述:“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表明津血的来源均为水谷精微,在其生成代谢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为用;《素问·评热病论篇》亦载:“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及《灵枢·决气》“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精”,表明汗是在精微物质的基础上所生成的沟通津—血关系的重要媒介,津—血—汗是人体生理阴液在三个不同位置上的物质表达形式。在阴分内位为血,阴分外位为津,阳分外位为汗,三者相类维持着身体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在生理关系上,此三者存在同源类性,且在内外位置上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机制。依据此理论,作用于外位之汗的干预,对于血证疾患的具体趋向变化,仍需依循具体情况分析,故基于讨论“汗血”“津汗”关系的禁汗论断稍显勉强,后世以此为论以成血证禁汗由“一病之机”到“症病之律”模糊替换。津—血—汗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汗法治疗血证的可能性提供理论基础。
1.2 血证禁汗条文枚举及病机分析
查及原文,经方体系中对于血证禁汗的立论仅仅针对于特殊病机下的特定人群,而并非以偏概全的笼统禁论。经方体系中关于血证禁汗的原因主要着重于汗可动气、汗可引热、汗可耗液三方面所致津液及阴阳气机平衡的破坏[1],但在经方临床中,对于同类病症的差异化病机下,如风客肺郁致衄以麻黄解之;虚寒气逆之吐血,以桂枝、生姜温而镇之;癥瘕引起的宮血不止,属阳气内结阴分致瘀,常用风药如羌活、白芷、藁本、桂枝散之[2]。可见无论是阐理经典的表达,还是方书的一些特殊人群禁汗案例(见表1),不足以完整支持对个体病或类病取汗与否的定性;未对涉入病机个体进行具体分析,转而直接关联药与病的简单对应关系,是有悖于辨证论治精神的。

表1 特殊人群禁汗条文枚举
故《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等关于血证禁汗本是针对单一特定病机的禁忌,后渐混淆概念,将“一病之机”混淆过渡到“症病之律”,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辨证论治和复杂病机下血证的病理表达。
2 血证危症运用汗法的枚举
《灵枢·热病》专论热病的症候、诊断及治疗等,提出了在热病治疗中以针刺泄气(热)于外,调达于经的治法思路。但同时论述热病亦有九不刺,其中便有宜汗法不宜刺之血证,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呕则上部气机上逆,不得下行;下血则下部邪气乘下,中部受损无以统血;两者并有之,则气机升降失常,当降不降,当升不升,邪气干扰内气以呈危象,此用汗法驱浅位邪气,升中阳而降阴气,亦有回阳之效。蒋元茂[3]以大青龙汤治崩漏案,在按语里专引此句以示基于上下气机的运动关系对出血重证的截断处理。又云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咳而衄为邪犯卫表,气机上逆表现时,如嚏、咳等机械摩擦,可伤及血络而呈衄状,此时刺穴泄气反致邪气内陷,汗法驱外邪以正肺卫气机,病发危机之状,若汗不至足即汗不彻,邪气不出则入营血分,或为危证。
3 汗法治血的机理探讨
3.1 外感实证,发汗止血
《医宗金鉴》载:“太阳病,凡从外解,惟汗与衄二者而已。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人受外寒,显麻黄汤主证,不以汗解,血为阴类,虽阳热上冲官窍,迫血外出而发衄血,此时血证邪热欲出,气上郁(风寒外束)未解,仍可以麻黄汤发散外寒,一解外郁[4]。陈修园注:“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其衄点滴不成流,虽衄而表邪未解,仍以麻黄汤主之,俾玄府通,衄乃止,不得以衄家不可发汗为辞。”陈修园明确指出了此类情况“不得以衄家不可发汗为辞”,还对此种类型的衄血特点(点滴不成流)做了说明。重庆医生毛得宏多次发文论述此类鼻衄伴外感者,必以发汗驱邪,视邪气内闭之程度,予以麻黄、桂枝、荆芥等发其汗,再辅以补益之剂处理[5]。申泽忠[6]提出“夺汗者夺其毒,夺血者是夺汗之源”之论,认为治血用发汗法,使毒热散,血自安;故在临床遇鼻衄咳血、便血、子宫出血等皆配以汗法俱有奇效。而申认为亦可以血治汗,常见刮痧一法应用普遍,正是以血治汗的佐证。
3.2 外感虚证,升阳止血
唐容川于《血证论》中述:“血家最忌感冒,以阴血受伤,不可发汗故也。然血家又易感冒,以人身卫外之气生于太阳膀胱,而散布于肺,血家肺阴不足,壮火食气,不能散达于外,故胃气虚索,易召外邪,偶有感冒,即为头痛、寒热、身痛等证。”唐容川点明血家外感的原因根于阴血不足,胃气虚弱,无力鼓动内气排出外寒,处以麻黄人参芍药汤治[7]。全方着眼于散太阳补太阴,合仲景小建中汤、麻黄汤之功,成后世治血证外感之典范。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经方研究中,从药证思维和病机本位思想新解麻黄人参芍药汤,以太阳风药为升举太阴阴气的关键,认为风药沟通内位气血与营卫之气,是阳分枢机药,在里可去阴邪,在上可升阳,通阴气,实津液。唐荣川在《血证论》中言:“盖必知血家忌汗,然后可商取汗之法。”可知在缜密的辨证论治基础下血家亦为汗治[8]。
3.3 中焦虚衰,燥浊止血
李杲也在其《兰室秘藏》中记载治疗经漏不止者,留有升阳除湿汤配伍防风、荆芥、羌活、藁本等发散之药;升阳除湿汤为脾虚湿盛所设,中焦虚损无力统血,血溢脉外,加之湿邪流注,携离经之血下流无度,病发崩漏之状[9]。唐荣川言:“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未尝不病血。”血病、水病常相互累及,而致水血同病。血水为阴类,同气相亲,在发病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层次性。本方以黄芪、升麻上升脾气,但升阳药物甚少,多以独活、苍术等燥湿运脾,辅以发散之物下除湿浊,再防风本有上升脾胃之功,起引经之用,使脾胃之湿浊尽除。全方虽升阳药物甚少,但以中下焦分治湿邪,脾气自升。发散药物多为温性,温可燥湿,或从内小便而解,或从外汗出而解,然此病本脾胃虚损,无力散邪气,多为无汗或少汗状,故而在临床上汗出而解者并不常见,但亦不失为汗法在血证疾病治疗的衍生。
3.4 浮阳无根,发越止血
《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述:“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麻黄升麻汤主之。”此病为外感后期,正气亏虚,妄投下法,阳邪内陷,无力振奋以驱邪气,已成阳邪郁闭,故发厥逆之症;又厥阴经循咽喉,贯膈注肺,邪扰血络,而发咽喉不利吐血之症。张仲景书常汗出而愈,邪郁而作,邪出而愈。此方发浮越阳气,上资肺阴,下缓脾寒,寒温并用,充中焦气血以托邪外出;阳邪浮越于上,借麻黄桂枝外散,以避郁闭脓成。浮阳得散,再投以门冬、葳蕤之品以资阴液,平衡阴阳,孙思邈之“千金葳蕤汤”配伍思想与此方亦有类似,在今临床中治疗肺咽齿喉疾病引起的唾血、咳血等应用较多。
3.5 真阳极衰,补阳止血
赵献可在《医贯》中述:“六淫中虽俱能病血。其中独寒气致病者居多,……俱易以感寒……经中之水与血,一得寒气,皆凝滞而不行。”赵献可从病因学明确表达,寒气乃致血证大病机下的首要病因,汗法又为解寒的首选治法,故从治法和病因学上论汗法在血证疾患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赵献可记:曾治一贫者冬时衣衫单薄,居大室中,饱饮严寒,上逆血出于口。意阳虚者太阳伤寒证当汗不汗,遂成呕血,与麻黄汤发汗遂愈。此病者寒冬单衣居于陋室,阳气内耗,表阳重虚,外受风寒侵袭,体虚无力驱外来之邪,阳虚而里热无以外展,邪热丛生妄动;再者机体无力以制气行,气机肆逆上行,携血而上出于口以成呕血。汗法以动阳气,复深浅位置上气机升降之律,调动深位阳气升至上部以实表阳,破风寒闭阻,以释内热。此以汗剂调里阳以补虚阳,实为急症及考虑患者经济之最好选择,后世固然有再造散等补阳解表之流,但在此病机表达下以汗法补阳治血是血证治法的又一亮点。需注意的是此病机下后续治疗必须处方以补津液固阳气以绝亡津及虚阳妄动之象。刘东汉等[10]曾以知柏地黄汤加用补阳益气之品治疗血汗一病,屡有奇效。
3.6 方药视角下的汗法运用
除开从辨证思路与治法变通的角度,一般传统意义的取汗药,或汗法中常使用的风药药物及方剂本身就具有止血功效,如孟诜《食疗本草》中谓“葱白”止衄血,《本草纲目》中载治“妇人妊娠溺血”。如白芷在《神农本草经》里载“主女人漏下”,《药性论》里谓“主女人血崩”;一味防风在《校注夫人良方》中为“独圣散”方,“肝经有风,血崩不止”。苏叶在南宋《履巉岩本草》中载能“止金创出血”如此类等[11]。胡红林等[12]在其研究中将我们认为能取汗的发散风药进行现代药理学分析,认为除开炮制因素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直接止血作用,提出假说可能是抑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的表达而实现的。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提出细辛、羌活等发散止血的作用应与其发散外邪有紧密联系,可以佐证本文所提汗法止血的机理,亦合叶天士之“治风先治血”之论。
4 王清任之论血化即汗之误
王清任为清朝医家,因常疑古人所论,实操解剖,自绘脏腑图画,还原人体解剖学的原貌,提出多个新奇而不叛道之论点,引人深思。时人曰:汗在皮肤是血,发于皮肤外是汗,言汗即血化。王清任从解剖所得的生理结构角度论述:气血为两个不同生理管道运输,气管沟通皮肤,在表有孔窍以排泄有形汗液;血管沟通皮肤,在表无孔窍无法直接与外相通。故病在血者必借气之通道以驱病邪,血证相关疾患可借汗孔在表而发泄邪气。王清任兼引外科疾病举例:气管发毒者,如生疮破脓,每日流脓水,而皮肤不红;血管发毒者,瘟毒发斑、小儿出痘等,色虽红而不流液。外科病种在肌腠层次上的不同外现形式辅助说明血汗两者在生理层面上运输、排泄的差异。王清任以解剖结构和功能运用立论,论述血汗的循环代谢,证明血汗并未为直接转换而来的,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津血同源的直接性联系,为血证者使用汗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5 分析和思考
汗法非血证疾患正解一论,由来已久,后世医者以津血同源为理论基础模糊概念,偷换病机,以成血证禁汗之训;笔者以津—血—汗关系立论,厘清三者异同生成关系,总结发汗止血、升阳止血、燥浊止血、发越止血、补阳止血等治法在特定病机下和临床实践和理论支持,汗法在上述治法中或为主则或为辅治或为病邪外出形式,均在血证生理病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全汗法在血证诸多病机下的特殊运用,丰富血证病机原貌。
血证的汗法运用当为医家所熟知重视,特别是在常规治法治疗无效或疗效不显时,可在谨守病机的前提下运用汗法或取风药思路常可收不意之效。血证汗法运用的讨论和分析进一步还原血证在病机病位和药证思维下的病理生理原貌,一定程度上裨益于临床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