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璀璨时光
叶克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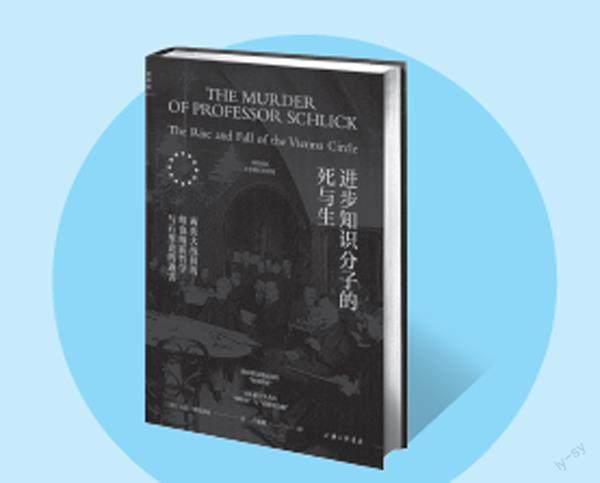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英]大卫·埃德蒙兹著
许振旭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
维也纳是一座怎样的城市?除了“音乐”这个人尽皆知的标签之外,它还有怎样的特质?
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许振旭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一书中写道:“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赫兹尔、凯尔森、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施尼茨勒、穆齐尔、卢斯……那么其中显然发生着重要之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渴望革除陈腐,他们崇尚科学,拥抱进步,希望荡平旧时代的等级制度。当然,他们中也有人走上极端之路,为人类带来浩劫。
一战后、二战前的维也纳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奥匈帝国的解体,货币贬值,经济凋敝,但维也纳的文化却迎来繁荣期,科学、哲学、文艺和政治思想领域都达到新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倡导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维也纳学圈”,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学派”。所谓逻辑经验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将数理上的逻辑方法,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合,主要目标是取消“形而上学”,建立一种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类是经验科学命题,可以由经验证实;一类是形式科学(数学和逻辑)命题,可以通过逻辑演算检验。
一八七九年出生于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的汉斯·哈恩(Hans Hahn,1879-1934),是维也纳学圈的发起人。作为哲学家与数学家,他享誉国际,至今仍有几条复杂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如“哈恩嵌入定理”“哈恩分解定理”等。一九○七年起,他开始与一群常居维也纳的哲学家定期聚会,思考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和宗教问题”。这些哲学家一般是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具有科学倾向,他们聚会地点通常在咖啡馆。
当时除哈恩之外,还有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和当时才二十三岁的后辈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1884-1966)。科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1883-1953)是哈恩和弗兰克的好友,偶尔也会加入他们。他们的兴趣在于—
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语言、科学的主张和地位,以及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他们希望划清经验科学—牵涉实验和证据的那些—与其他形式探究的界限。他们还对几何学和数学的基础感兴趣,也希望弄明白如何理解概率的意义。他们都同意,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有着毫无必要的神秘性,往往是无意义的胡话。他们都认为,哲学和科学应该展开更多合作,更紧密地相互联系。他们希望哲学能澄清科学的旨趣,从而对科学有所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大体偏左倾。我们将看到,这种政治观和这种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
一战后,莫里茨·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1882-1936)与纽拉特等学者恢复了不定期聚会,并使得圈子逐渐扩大。爱因斯坦、伯特兰·罗素、维特根斯坦、鲁道夫·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1891-1970)、卡尔·波普尔、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等留名于历史的人物,都是这一圈子的成员。一九二九年,文章《科学的世界构想:维也纳学圈》发表,号召人们“以理性的方式重塑社会生活”,维也纳学圈由此进入公共领域。
埃德蒙兹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中写道:“1907-1912年间,维也纳学圈的先驱(哈恩、弗兰克、纽拉特,以及不经常参加的冯·米塞斯)相聚之际,有着美丽穹顶和拱门的中央咖啡馆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地点,尽管他们可能太过沉迷于相对论带来的哲学问题,而没太注意这里的常客:其中有论战家卡尔·克劳斯、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以及流亡的俄国人列夫·布朗斯坦,他在那里下棋消磨时间……”
科学与哲学是学圈的目标,咖啡馆则是学圈的载体。直至今天,维也纳的咖啡馆数量和名气仍在欧洲城市中靠前,象征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创造性,也承载着无数历史。对于维也纳学圈而言,维也纳大学里的研究、讲座和提供的薪酬,当然是学术的基石,但大学同时也带来了烦冗制度和沉闷氛围。因此,在维也纳学圈正式成立后,咖啡馆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聚会之地。“帝国议会咖啡馆、苏格兰门咖啡馆、拱廊咖啡馆和约瑟夫咖啡馆都很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玻尔兹曼巷的约瑟夫咖啡馆。”
相比秉持着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圈,同样汇集于咖啡馆的存在主义者们更为人们所熟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成员更具“网红”气质,也有更多的逸事可供猎奇。不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成员们也有许多趣事被记录下来:一九二一年,已经成名的爱因斯坦进行了一次摇滚明星式的巡回演讲。为保护爱因斯坦免遭不必要的关注,菲利普·弗兰克提議让爱因斯坦住在他的公寓中,做一个“沙发客”。弗兰克后来回忆他们一起吃饭的情景:他的妻子厨艺有限,准备用本生灯加热小牛肝,爱因斯坦见状突然跳起来,问:“你在干吗?难道你要用水煮牛肝?”得到弗兰克夫人的肯定回答后,爱因斯坦说道:“水的沸点太低了,你必须用沸点较高的物质,比如黄油或脂肪。”弗兰克后来写道:“爱因斯坦的建议挽救了这顿午餐。”弗兰克还记录道,在一次宴会上,当人们都在等着爱因斯坦分享思想时,他却拿出小提琴说:“如果我不发表演讲,而是为你们演奏一首曲子,也许会更愉快、更容易理解。”随即便为大家送上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
这些逸事颇具艺术气息,也贴合维也纳学圈大本营的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当口,各种学说在维也纳碰撞,共同成就了一个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自由天堂。小牛肝与小提琴,都是这自由气息的注脚。
在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维也纳是老欧洲的文化中心,也被视为美好的象征。当时的维也纳人沉浸于歌剧、交响乐、博物馆和咖啡馆。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多元化,使得维也纳人超越了种族、语言和国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世界。在一战之前,日渐衰落的哈布斯堡王朝奉行开明专制,同时也因为较低的行政效率,带来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各国的政治异见者纷纷流亡于维也纳。而在一战后,这种文化氛围得以延续,配合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突破,共同造就了维也纳学圈的形成土壤。
除了哈恩与石里克这“两任”组织者之外,维特根斯坦也是维也纳学圈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中写道:
学圈内部有个充当维特根斯坦固定听众的小团体,这其中,石里克和魏斯曼始終对他最为拜服,在所有棘手的问题上都听命于他。对石里克和魏斯曼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和正确的立场,就像晨星和暮星一样,是同一个。魏斯曼甚至开始下意识地模仿维特根斯坦的说话模式。石里克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原创观点归功于维特根斯坦,尽管这些观点在他还没有读到《逻辑哲学论》之前就已经表达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都属于家境显赫、衣食无忧的主儿。事实上,整个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家境都不差。也正是优越条件,使得他们有动力和时间触碰人类思想的高峰。
思想不但没有止境,路径也非唯一。维也纳学圈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在内部封闭和垄断思想,反而充满包容性。石里克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包容心,比如他一方面批评波普尔为人粗鲁,哗众取宠,但另一方面又在维也纳学圈中传阅波普尔的早期著作《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并进行引荐和翻译出版。埃德蒙兹在书中写道,石里克将维也纳学圈“形容为哲学家的工会。他认为学圈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相聚切磋问题,但不应失去各人的独立性:他们的小组不是什么帮派或队伍。他不喜欢冲突,也反对煽动:他认为追求真理就够了,并乐观地认为真理终将胜出”。
但也正因为这样,石里克对《科学的世界构想:维也纳学圈》这一宣言始终持保留意见,也并不愿意过多介入社会生活。因此,这份宣言无疑是维也纳学圈的一个高峰,同时也让学圈就此陷入分裂。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也让奥地利的经济陷入风雨飘摇,右翼趁机崛起,维也纳学圈也因此遭到敌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刚刚开始便以失败告终。
一九三四年,维也纳学圈被强行解散,定期聚会画上句号,只有偶尔的相聚。两年后,石里克惨遭杀害,凶手约翰·内尔博克是个精神不稳定的前学生,自称驱使他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但相当可疑。学圈的成员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命运,甚至对未来有着盲目的乐观。书中这样写道:“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预见到了事件的走向。要离开奥地利,有着各种理由,包括事业的发展;但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想法依然看似荒谬,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受着积极看待事态发展的诱惑,就比如弗洛伊德。一九三三年,当听说自己的书在柏林被付之一炬时,他说:‘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本人;如今,他们烧我的书就满意了。’”而在后来,他们逐渐醒来。二战爆发后,曾经的学圈成员们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纷纷流亡美国或其他国家,不再想着回到维也纳。离开奥地利后,学圈成员们普遍迅速适应了英语环境。亨普尔就告诉女儿,他做梦都是用英语做的。他们用英语交流,正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至于曾经璀璨的维也纳,此时也已经沦为缺乏思想与灵魂的空城。维也纳学圈的思想,逐渐在新世界(尤其是北美大陆)扎根。卡尔纳普成为美国哲学泰斗,并直接制造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裂变;波普尔则深深影响了撒切尔夫人……
维也纳学圈诞生时,它的成员并未意识到凛冬将至。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启迪这个世界所有的心灵”,试图重现美好时代,这样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绝非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