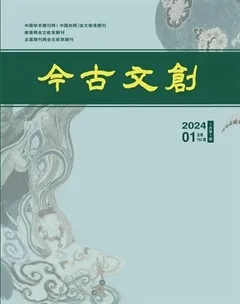不能忽视的形象
张楚钰
【摘要】《百合花》是一篇形象塑造鲜明的小说,探究主要人物形象及所蕴含的人性之美是把握其主题的关键,一直以来都是文本研究的重点。抒情主人公“我”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在结构上承担了叙事视角和情节线索的任务,在内容上又具有烘托主要形象、点化主题内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百合花》;人物形象;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04
《百合花》是一篇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叙写了通讯员、新媳妇和“我”三人在包扎所附近发生的动人故事,塑造了充满人性光辉的形象,赞美了战争时期真挚的人际关系,表达了作者在特殊年代对真情的呼唤,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究新媳妇和通讯员的人物形象,分析小说叙事手法,解读文本意象以及主题内涵几个方面。虽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对次要人物“我”的关注却相对不足。部分研究者能看到“我”的叙事作用,但对“我”在小说内容表达上的意义关注不够。实际上,准确把握“我”的形象意蕴及表达作用能够帮助读者抵达文本深层,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小说的情趣魅力。
一、从文本中解读“我”的人物形象
茹志鹃谈《百合花》创作时曾表示:“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1]作者亲历过战争,面对当时的社会氛围,无不怀念战时同志间真诚的感情。她希望以写作展现人性美好,呼唤被扭曲的亲密人际关系,那么如何以战争题材叙写人性主题就成了创作的首要问题。对此,作者选择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笔触去书写战争里的温情点化主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刻画了一个文工团的女兵形象,从女性视角出发去讲述这一清新俊逸的故事。“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参与者,文本内自然包含了“我”的主观情感。读者以“我”的视角阅读小说,首先就要理解“我”的形象特征和思想情感,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故事深层。
“我”是一个性格倔强要强的文工团女兵。从身份上看,“我”自然比不上长期四处传递消息的通讯员体力足。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因脚伤路滑走得慢,既因赶不上通讯员而着急,又不愿叫他等,怕他用性别偏见来嘲笑自己,兀自对他生起气来。这样的心理活动能看出“我”虽是女性,但面对男性的体力优势,依然不愿示弱的要强性格。除此之外,“我”看到通讯员背向我远远地坐下,“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便“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他坐下。”面对男女性别隔阂,“我”不仅没有不好意思,而且还敢于表达自己的反抗,突显出“我”作为一个女兵的自尊心和倔强。
“我”是一个活泼大方而心思细腻的女性。雖然不满通讯员的态度,但在进一步观察他,特别是知道他是自己的同乡后,“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浓烈兴趣,交流中表现得落落大方,体现了“我”性格的开朗。同时,“我”能够注意到通讯员枪筒里用来做装饰的树枝和菊花、他肩头被钩破的布片以及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憨憨地笑了一下”等一系列的微表情,都表现出“我”对通讯员的记挂与关怀,也体现出“我”心思的细腻柔和,为文章增加了几分情味,于无声之处衬托人性主题。
“我”是一个成熟稳重且思想觉悟高的革命者。面对团长的安排,“我”表示“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能够看出“我”对因女性身份而被派去战后的安排有些不乐意,但只要能为革命尽一份力足矣的革命奉献精神。这时“我”主动将革命者的身份放到首位,而女性身份则默默隐藏其后。同通讯员进村借被时,“我”能快速借到棉絮,了解到通讯员借被失败的情况后,又马上亲自去与新媳妇沟通,害怕“得罪了老百姓影响不好”,说明“我”对军民关系的看重,善于与群众沟通,在处理事情上更为稳重理性。从这些细节中展现了“我”思想的成熟和对革命的热情,是政治思想觉悟较高的革命者。
二、从叙述结构上看“我”的作用
《百合花》是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的第一篇小说,其单元导语明确写到“把握小说叙事和抒情的特点,体会诗歌和小说的独特魅力”。本篇小说在叙事上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主流的战争宏大叙事,即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小叙事”[2]。这种“小叙事”来自作者对小说情感主题的准确把握。她无意去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只想探寻生活本身,挖掘人性中深层次的光辉,带给读者真切的审美体验,因此对生活本真的细致刻画才是其创作追求。事实上,将“我”作为叙事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情感变化作为叙事线索,从空间上把故事舞台限制在包扎所这一小地点,从时间上将一天中三个非连续的情节片段串联在一起,正是作者达到写作目的的巧思。
(一)“我”是叙事视角
小说几乎是从“我”的视角来叙写的,属于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第一人称“我”的使用,将叙述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缩小,增加读者对人物叙述内容的信任,给读者真实感和代入感,增加了人性主题的表达力度。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三种聚焦模式,他认为“内聚焦的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可用‘叙述者=人物’的公式来表示”[3]。这种叙事视角的选择限制了读者信息获取的范围,所了解的只源于“我”的见闻,从而造成了小说一定程度上的叙事留白,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例如通讯员初次向新媳妇借被时,由于“我”的参与缺失,导致这次互动一笔带过。通讯员为何第一次没有借到被子?他和新媳妇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谈话?这些读者都不得而知,只能根据“我”与通讯员的互动推测两人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尴尬,想象还原两人初次见面的对话,填补小说的隐藏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英雄牺牲情节通常被作为故事高潮,但本文别出心裁地通过限制视角将这一情节省略,由担架员的转述简单告知读者情况,转而精心刻画通讯员牺牲后众人的反应,自然而然地突出人物的情感碰撞,增加了主题表达的力度。
对《百合花》而言,内聚焦叙事除了能增加小说叙事留白,由于“我”特殊的人物身份,还起到了限制故事发展空间的作用。由于女性身份,“我”被派到包扎所工作,导致故事一开始就被锁定在战场后方,实现了战争题材小说对正面战场回避,舒缓了战争紧张的氛围。茹志鹃曾说:“我特别注意从生活中发现富有深刻思想的有闪光的东西。”[4]《百合花》以“我”的视角限制故事舞台,将被战争宏大题材遮蔽的生活小场景扩展开来,开掘人与人之间朴质深沉的情感正体现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
(二)“我”是叙事线索
《百合花》主要叙述了三个故事情节,可以用三个短句进行概括。首先,“我”与通讯员在前往包扎所路上结识;之后通讯员与“我”进村借被,与新媳妇发生误会被解决;最后,他为救战友牺牲,“我”看见新媳妇将百合花被献给通讯员。可见整个故事是依据“我”的行动轨迹不断向前发展。“我”既是小说的视角人物,也是线索人物,将相对零散的情节片段串联到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故事脉络,因此“我”的见闻是小说的明线。
与此同时,小说还存在一条暗线,巧妙地隐藏在文本内推动剧情发展,那就是“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故事开篇写道通讯员总是“把我撩下几丈远”,“我”怕自己跟丢到不了包扎所而对他生气。最初由于“我”不了解通讯员,情感倾向是埋怨责备的。但后来“我”发现通讯员表面疏远自己,但实际上有着笨拙的体贴,特别是后来同乡身份的发现让心理距离得以缩短,“我”开始对他亲近起来。借被时,通讯员虽有冒失幼稚的一面,但又心思单纯地想要补救。“我”看到了他作为年轻人任性又善良的一面,“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至此,“我”对通讯员的感情经历了生气、好奇到最后喜爱的三个阶段,随着“我”对他的了解越多,感情愈加浓烈,也就为后来情感高潮做了铺垫。
在内视角下,“我”的情感变化,也就是读者的心理变化。叙述者在叙述时有主观情感注入,那么“读者也会顺着叙述者的情感倾向产生认同,进而把握人物形象及心理情感。”[5]“我”的情感流动是故事发展的暗线。读者在“我”的引领下逐渐认识通讯员,最终取得窥见小说的情感主题内核。
三、从表达内容上看“我”的作用
《百合花》的三个主题,即军民情深、人性美好和青春生命都集中体现在通讯员和新媳妇的交往中。小说的高潮结局也都围绕两人展开,他们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是理解小说主旨的重点。但“我”作为小说的次要人物,在内容表现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阅读时同样值得关注。
(一)烘托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的存在,将主要人物形象衬托得更加鲜明。”[6]“我”对通讯员形象的衬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反衬出他性格中的青涩忸怩,二衬托出他对革命的热情。在“我”与通讯员互不认识的情况下,通讯员因性别隔阂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当“我”靠近并同他对话时,他“立刻张惶起来”,“脸涨得像个关公”一连串神态描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清纯羞涩的小战士形象。此处“我”的侃侃而谈与通讯员的坐立不安形成鲜明对比,更衬托出他未经世事的青涩。作者借“我”之力将通讯员的普通一面塑造地越生动,当他牺牲时展露出的英雄品质就越令人动容。其中那震人心魄的感染力才能唤醒最纯质的人性美好。
其次,当“我”邀请通讯员同去时,他踌躇地答应了。“踌躇”的神态能品读出通讯员的心理矛盾:他因性别关系不想与“我”单独行动,但又从大局考虑选择答应。即使借被受到委屈不愿再见新媳妇,但被提醒群众影响后,他又马上“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这些行为细节都能反映通讯员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革命大局观。作者不仅用细节塑造了“我”的革命形象,还突出了通讯员识大体顾大局的革命精神。从不同层面对他进行性格塑造,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充满人性光辉。
对新媳妇的衬托,首先体现在她腼腆的女性形象上。“我”与新媳妇同为女性,但与通讯员的相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对他是毫不拘谨地开玩笑,新媳妇是不好意思地扭着头笑他,两相对比足以表现新媳妇的羞涩腼腆。对于帮伤员擦身的事务,我是“做这种工作,当然没什么,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都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这里“我”与男性的接觸自然,更反衬出新媳妇的保守思想,与她后来超越性别隔阂为通讯员擦身的行为形成反差,为人性主题的表达埋下伏笔。
其次,同为女性的“我”更能观察到新媳妇的内心世界,从细节中表现她纯粹的人性美。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洞”。此时“我”看到新媳妇的动作是“细细地、密密地、一针一针地”,这些形容词足见她对待此事的极度认真。新媳妇表面在缝补破洞,实际是在表达内心的愧疚与敬意。她没想到这位害羞的“同志弟”能有这样的勇气,后悔对他的调笑,后悔没有为他补衣服,更对鲜活生命的仓促消失感到痛心。这些情绪对内心震颤的新媳妇来说难以言表,只能通过行动来表达。新媳妇与通讯员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却能真诚待他,尊重这个勇敢的生命,这是新媳妇至纯至美的真情流露,充满了人性的光辉。面对小同乡的离去,“我”同样悲痛不舍,与新媳妇产生了情感共鸣。这样心思细腻的“我”比周围人更能察觉到她沉默行为背后的汹涌澎湃,从而捕捉到“细细、密密、一针一针”等饱含情绪的细微动作,从而点化新媳妇如百合花般的纯美形象。
(二)点化情感主题
小说围绕着“百合花被”叙写了一则战争中的温情故事,表面上体现军民情主题,深层则歌颂人性之美,奏响了一曲青春与生命的赞歌。小说故事中“我”虽然是次要人物,但也能起到点化主题作用。
对于军民情主题,“我”充当了军民间交流的桥梁。由于“我”拜托通讯员进村借被,他才与新媳妇有所交际产生后续故事。在两人产生误会时,“我”开导通讯员,并同新媳妇解释借被原因,才化解了两人误会。正是因为“我”的调解,两位军民代表才能进一步产生情愫,军民情主题才能自然呈现。
对于人性美的歌颂,除了新媳妇那超越物质的人性光芒外,“我”对通讯员的复杂情感也能增加人性主题的厚度。“我”和通讯员仅在中秋节这天有所交际,尽管时间短暂,但却产生了深厚情谊。文中写到“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称呼中的“小”字暗示着“我”将他作为小辈看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7]因此“我”所说的爱,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类似于长辈关爱晚辈的亲情。通讯员牺牲后,小说对“我”描写不多,但从细节看依然能体会“我”的痛心。“我强忍着眼泪”,“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眼泪深藏着对战友牺牲的悲痛,对同乡勇气的敬佩和对生命早逝的叹息。作者曾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1]仅一面之缘的新媳妇与通讯员是如此,“我”和通讯员的情感也是如此。虽从表达效果上看,两人间的感情并不是小说刻画的重点,但依然能点化人性美的主题。
“我”虽然不是核心人物,但却能成为理解小说主题内涵的突破口。读者从“我”的视角去阅读小说,把“我”的见闻作为理解线索,解读三人的形象特征,品味人物间真挚的人情美,还能从叙述层面去解读小说,搭建起理解小说主题的双层阶梯。可见,探究“我”的文本作用能够找到小说情感密码,从而领会作品文字下涌动的绵绵情思。
参考文献:
[1]茹志鹃.《百合花》的写作经过[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6,(05):3-4.
[2]徐志豪.论《百合花》中的“小叙事”[J].今古文创,2022,128(32):19-21.
[3]申丹.对叙事视角分类的再认识[J].国外文学,1994,
(02):65-74.
[4]茹志鹃.生活经历和创作风格[J].语文学习,1979,
(01):15-17.
[5]卢昶波.《百合花》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赏析[J].名作欣赏,2021,739(35):128-130.
[6]郜元宝.无材可去补苍天——怎样看小说的次要人物[J].小说评论,2015,(05):31-36.
[7]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研究专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