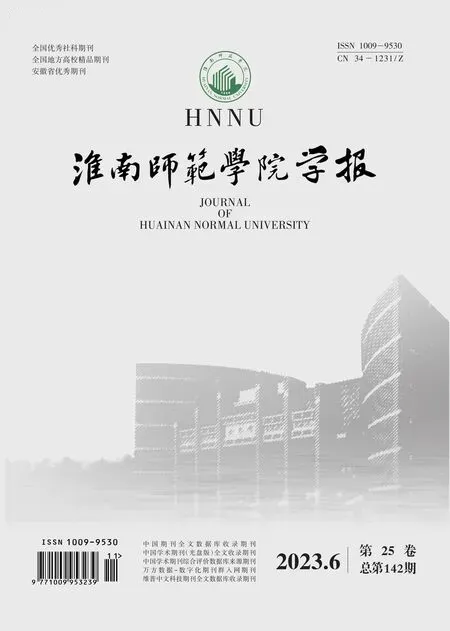《淮南子·原道训》“以治为本”的义理结构探析
吴天寒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前 言
由于参与写作与编篡《淮南子》的人数众多,因此其内容实际融杂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并且书中各个篇章分别出自多人之手,很难将《淮南子》当做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去探究其义理结构。而纵观《淮南子》现存的22篇文章,首篇《原道训》一文集中呈现了《淮南子》全书涉及的基本哲学问题,也奠定了《淮南子》整本书以老庄思想为宗的基调。基于同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理应出自一人之手的推论,本文旨在对《原道训》的哲学思想进行一个结构化的分析整理,以使其问题意识与思想主张能更清晰呈现,亦可管窥《淮南子》全书的哲学思想。
总的来看,《原道训》涉及谈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境界论、治道论等①,也有学者以本体论、生成论、实践论、境界论四方面提炼其问题意识[1](P111)。从各问题涉及的篇幅来看,可以发现作者的问题意识集中在政治上,即提倡一种“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这一结论的得出除了根据相关内容的篇幅多寡来判断,也基于作者开篇所论“道”体便落到了政治问题上。开篇在论述何为“道”本体之后,紧跟着出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2](P2)一句,形上之道落实到形下之治,并总结此二皇之所以能治天下是因他们“无为为之而合于道”[2](P2),这便是该文的思想主旨。当然,除了能从文本本身见出《原道训》对治理问题的关切外,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亦能得知治理问题当是汉初士阶层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经过秦朝的苛政与楚汉混战的动荡,致使西汉建国之初的政治主体从上至下皆有厌战情绪并共有休养生息的愿望。如何符合其时的历史情境,提出“合于时用”的解决方案?《原道训》提供的解决方案,便是一套“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
推行这种治理思想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得以在现实中落实?该篇文献通过本体论的论述给予了“无为而治”治理策略的应然性,借由本体论推演出的人性论给予了“无为而治”的切实可行性,这两部分架构起此治道思想的理论地基。再加上一系列心性修养的操作工夫与理想人格的境界工夫等工夫论部分的论述,指明了在这种治道理想下的政治主体所应努力的方向与途径,使现实中残缺的政治主体已然成为这种治道理想下完满人格的主体,此为“无为而治”在实践中顺利推行的必要条件。当然,与道家学派其他文本相似,该篇文献中也有一些宇宙论部分的知识,但这部分知识并未着意要解决物理层面的世界存在相关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价值意识的本体论意义上言说的宇宙本体——“道”,因此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认为可将其囊括进本体论部分的问题意识中来呈现其意义。
二、无为而治——本体论下的治理总则
(一)本体论进路的宇宙论知识
《原道训》篇名“原道”这一概念是就道体终极价值的本体论面向来谈的,而非在宇宙论的问题意识下展开的分析,因此《原道训》一文谈论宇宙论知识不如《淮南子》中其他篇章如《天文训》《俶真训》《精神训》等明确与丰富。一般来说,宇宙论是关于外部现象世界构成及其存在者生死原理的相关知识,尽管这部分的论述是作为哲学理论始基问题建构中必要的一环,但不是《原道训》一文所关切的治理思想需对准的理论问题。当细究文中有关宇宙论知识的表达,便可发现此为本体论进路下的宇宙论知识。文中最典型的宇宙论表达应属开篇对“道”体的描述,文中有言: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2](P1-2)
从“夫道者,覆天载地”至“甚淖而滒,甚纤而微”都是对“道”这一宇宙本体的存在样态进行的描述,总体上对它的空间形态作了定位,即承载天地的“道”无限广大,不可测度,他的形态变幻莫测,近于虚空,它是无形寂静而玄远的。而最后一句“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到“凤以之翔”,便直接从本体论的进路把“道”置于根源性的地位。这里的“以之”应释义为“因为它”,故无论是山渊兽鸟,还是日月星历,都是因为“道”才得以成为其自身,简言之,这里说明了“道”是万物所成其是的原因,是将“道”界定为世界本体的典型表达。既然道是本体,也具有创生万物的功能,文中有“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2](P27)“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2](P3)这都是在讲“道”的创生功能。但值得留意的是,“不有”与“弗宰”的特性说明了这宇宙本体尽管创生万物却不带有自我的主观意志,不采取任何认知立场,因此这里也是从价值意识的本体论进路去谈的关于创生宇宙的知识。
此外,这一宇宙本体还具有感应万物并与之同化的功能,文中言:“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俛仰兮”[2](P4),这一句描述了道体以虚空之状化于万物之中,由于道体能够全然地融合不同的情境,配合外境而变化自身。这一特性便有更深层次的价值指向,即泯除世俗的喜好,推崇无有偏私的价值意识。这样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的宇宙本体,决定了人类世界的本质应与此本体的价值保持同一性,所以人类活动的理念也应与其保持同一。以此为前提,作者所推崇的“无为而治”思想才能顺利导出,无论是泰古二皇还是禹,皆因循道而治,实现长治久安。
《原道训》中关于现象世界的解释,除了对作为宇宙本原的“道”进行了相关界说,也对现象世界中有限个体的生命运动机制原理作了说明。例如文中最后在讲形、气、神三个范畴之关系的时候,同时说明了这三者如何构成了个体的生命活动,即“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2](P36)。在作者看来,形体是生命安顿的躯壳,这个躯壳由气的流动充盈其自身,而对生命具有主宰作用的是神。尽管三者对于个体生命在现象世界的活动缺一不可,但从价值的重要性序列来看,“神”还是处于根本性地位的,可见作者依然将价值意识的精神本体视为其理论系统的核心。
(二)价值意识的本体论——无为
“道”本体作为一种存有概念可有不同面向的意义解读,上文从宇宙论的视域考察了自然大道生成万物的规律极其存在形态,在这个语境下的“道”之意义对于人类世界而言是寂灭的,唯有将此本体置于人的意识世界对存在界做意义与价值的体会,从而转为生命的智慧与行为的蕲向,这一本体的意义才会在人类世界中朗现出来。因此,本节使用“本体”一词的意涵主要是就终极价值而言。
《老子》中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P90),老子哲学将“无为”之价值意识界定为道的价值指向,《原道训》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无为”亦即“无偏私”,指从精神上革除世俗的感官欲望,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只以成就最终的事业为目的。而“无为”作为“道”这一本体的核心价值意识,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中有不同侧重。文中有言,“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2](P26),亦有“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2](P10)这些表述表明了道体至少包含了清静、柔弱、虚无恬愉、不争等不同面向的特质。总之,随外境的不同,道体在“无为”这一终极价值意识下会呈现不同侧重的表现。
除了对“道”这一本体的作以价值意识的直接界定外,作者还着重引出“一”的概念来阐释道体在人世间的秩序原则,“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2](P26)道本体是无形无状的,但它在知性层面可用“一”来概述。“道”因是本体,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作者以“一”来指称道体的这一抽象性征:“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2]27接着又论道:“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渊,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2](P27)这一万物依循的原理无论如何神秘缥缈,但作者最后依然将其落实到“常后而先”这类言说价值意识的表达上,故此“一”之宇宙运行原理不过也是“无为”价值意识的作用下的规律道理。本体论是关于此学派中关于终极价值的论述,而这种价值意识的本体之所以是终极的,就体现在它的独立自足性以及永恒实在性上,文中在形容道体的特征时,有言:“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斵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2](P4),“道”不会因他物而影响自身的完整,因此它是独立自足的;“道”也不会因外境的迁移而消殆,因此是永恒的。又因为作为本体的“道”独立而自足,永恒而实在,决定了本体指向的“无为”价值意识也应当是遍在而永恒的,因此,政治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依然应以“无为”的价值意识为圭臬,推行“无为而治”的治理方略。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说,作者在文中一再从本体论的高度强化“无为”的价值意识,实际就是为“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提供应然性的理论支持,即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奠定的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三)本体论下的人性观——虚静之性
然而,同样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反思,仅仅从本体论的高度确定“无为而治”治理思想的应然性似乎还尚存缺憾,因为政治作为全权由人参与的活动,如何确定人能够切实推行这种政治实践呢?作者在本体论进路下进一步阐释了人性的问题,便为这一潜在风险提供了人性论的保障,也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原道训》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治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2](P10)此处不仅界定了“人”的本性是虚静的,也反思了人在与外界接触时,心神撼动而遗失了“虚静”本性。《原道训》在此关于人性的表述与《文子》如出一辙,可谓是直接继承《文子》的人性主张②。 至于为何要预设一种虚静的人性主张,这与《原道训》的政治关切不无相关。由于作者倡导“无为而治”的治理方略,这便意味着君王应顺任民众自我的意愿,让他们过率性自然的生活。然而这种治理方式就必须同时预设另一个前提,即民众的心性修养层次同样达到了“无为”的高度,否则就会出现荀子所担心的人们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导致社会悖乱不治。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主体的应有虚静无为的精神状态。作者便从理论上预设“人生而静”来锚定政治实践主体实现清静无为的可能性。既然人的本性是虚静的,如果违逆人的本性,推行“峭法刻诛”“棰策繁用”的苛政,那么容易面临前朝“秦”二世而亡的局面,由此理应推行顺应人的虚静本性的治理方案。可见在这一人性的预设下,作者同时又强化了推行无为而治治理方案的应当性。
三、“反于清净”的工夫论——治理理想的具体实现
“人生而静”是从理论上保证了政治主体践行无为的可能性。而就现实情况而言,“虚静”的本性往往被遮蔽,所以现实中的大多贪名好利,就文中所说:“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治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2](P10)。由于人容易被外境诱惑而使其本性受到了损害,因此若要使无为而治的理想在现实中得以开展,除了“生而为静”的人性保证外,必须要求后天的工夫修养,于是作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夫心法来具体面对这个问题。政治主体若按照参与政治活动的支配与被支配角色来划分,大概可以分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就古代的实况而言,前者便是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层,后者即被统治的普罗大众。在《原道训》里,作者分别就这两部分群体分别阐述了其对应的工夫论。
(一)一般个体的工夫修养
针对大众的工夫修养方法,可称之为“一般个体”的工夫修养,因为这部分工夫论讨实际也涵盖了对治理者的要求,是作者就参与政治生活的全部实践主体而言的工夫论。在文中对这部分工夫修养方法的阐述不仅借由“得道者”这类理想人格呈现的至高境界来予以鼓舞人心,同时也给出了一些革除世俗感官欲望以重获心灵虚静的具体心法。
1.得道者的境界工夫
关于“得道者”这类理想人格,文中有体道者、达道者、得道者、圣人、至人等不同表述,但都共同呈现一个特点,即因“无为”成就了根本事业。例如:“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2](P21)以及“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 ……莫能与之争。”[2](P24)文中描述了理想人格在达到极高境界时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如“圣人处之,不为愁淬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2](P34)又如:“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2](P28)得道之人内心不起过度的忧乐之情,通达平和,摒弃了感官带来的欲望好恶,因此在内德性具足,在外呈现出宁和虚静、平淡纯粹的状态。文中大量描绘不同得道者的神妙精神之态,一方面为了激励人们按照道家修养的路径调整身心,并使其在现实中符合无为而治理论系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作工夫自我检验是否到位的参照标准。
2.修道的具体工夫心法
既然得道者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人格,那么人们如何修养身心朝着得道之圣人靠拢呢?纵观《原道训》中给出的修养方法,不难发现其主要路径便是心理修养的工夫。
其一,作者用“反”与“内”来指明作工夫应当着力的方向。“反”这一工夫表示往后收敛的方向,作者在文中多有表达,如“还反于朴”“反于清净”“殷然反本”“反己”“反诸性”等。“反”实为“返”,指返回到本来原初的状态。由于就人们的日常认知而言,皆习惯于往前谋划考量,而这在作者看来却是不利于身心养护的。人们应该“往后”用力去作工夫,如此才能还复自然纯净的本性;另外,也应向“内”的方向致力,如“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2](P29)表达了作者认为圣人之所以神妙的原因在于内在精神的充盈,这便是“内修其本”,强调作工夫的方向是由内而外去浸润。文末还有:“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2](P37-38),从锚定内在精神的主导性来进一步倡明向内的心理修养工夫进路。
其二,“反”与“内”的方向明确后,应具体如何修养呢?作者提出从观念上纯粹化自我的价值意识,明确应追求的事业是大道而非“数”。文中把那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世俗事业称为“数”,提醒人们应该“循道而弃数”,因为“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2](P13)。人们昔日花费精力去做的事情于自我精神的养护毫无益处,实为负累。又言:“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2](P12),这是说如果想做成一件事,却不依循大道的智慧,而是动用机心巧智从自我利益得失去运营事业,则该事业不仅办不好反而会愈加糟糕。有了这种对比之后,体认大道的价值选择便进一步强化了,从而也更好地推进人们在工夫实践上的具体操作。
有了这一基本的价值追求后,作者提出守气、尚柔、不乐等工夫去养护内在精神。文中有言:“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2](P26)也有“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2](P38),圣人的精神是通过柔和气志、平稳形体来养护的,三者在工夫次第上则是“气充而形安,形安而神宜”的顺序,可见“充气”“守气”工夫的基础性地位。至于“尚柔”的工夫,《原道训》延续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运思理路,在文中谈道:“是故欲刚强者,必以柔守之。”[2](P22)与此相同的还有“讬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2](P22)可见尚柔的工夫主要针对后天形成的争强好胜一类的习性。作者提倡事事以后为上,以弱为贵,其实就是贯彻“无为不争”的价值意识,就如文中说:“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也。”[2](P19)作者用游泳溺亡和骑马堕亡的例子来比喻那些爱彰显自己的人往往得不偿失,所以劝告人们要收起光芒,懂得隐藏自己的优势才是保身之法。最后,“不乐”的工夫是直接继承《庄子》“至乐无乐”[4](P333)的观点,旨在论述情绪管理的心理工夫,强调人们不要过度兴奋,也不要过度沮丧,“其为懽不忻忻,其为悲不惙惙”[2](P30),“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2](P31)。管理好情绪,面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要大悲大喜,心境平和欣喜才是“极乐”。这种心理工夫旨在从已发的情感中及时内省自察,维持平和的心态也是养护精神的重要操作。
(二)治理者的工夫修养
对于治理者而言,第一步便是要在内心消除“治理”或“统治”之类的观念,意谓即便从客观来说是处于管理的身份,但却不能自恃这种身份而生发出想要掌控他人的私心。贯彻“无为”这一价值意识的基本心态便要求以一种无私的服务贡献心态面对自己所经营的事业。“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2](P30)及“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2](P30)两句便是直接对治理者敲的警钟,这里的“治人”实际指的是统治者的心理认知停在“治人”层面,应舍弃这种心态才可能达到“治”的结果。尽管“无为之治”倡导的是与传统“治人之治”看似相对立的两种方式,但文中所倡导的“无为”“不治”“不争”等主张,并不是否定政治,而是从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倡君王应该“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对于这类纠偏君王对“统治”一事的执念,作者有较多警示之语,如“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2](P9)刘文典先生释此处“为”为“治”,意为天下之事不可刻意去治理,只因循自然的态势就好;又如“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2](P17)意谓君王不需要刻意花心思去制定一些规范管理国家,万事万物因循它自然而然的习性就能各得其宜。为了佐证“无为之为”“不治之治”“无道之道”一类的治理思想的合理性,作者也是举出很多先王治理的典范事迹加以强化。例如,“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2](P13)又如,“昔舜耕于历山,……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2](P21)再如“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读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2](P15)可见历史上被称为圣王的神农、舜、禹皆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即懂得因循自然来处理国家事务,故而实现了天下平顺安宁。
总的来说,“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2](P21)作者强调以无为之心办有为之事。当治理者完成了第一步对治理心态改变,那么接下来就要面对具体如何做的问题。根据作者的论述,治理者除了需要完成一般个体都需致力的心理修养工夫,还有一些特定的治理智慧供需要学习,例如贵后、合时、因循应变以及公正无私。
第一个心理工夫是“贵后”。文有“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2](P22)这里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一种居后行动,事业才能长久通达的观点。因为“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颓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2](P23)从作者罗列的这几种情形中,不难看出,先行者总是吃亏受害,而后继者因有了前人经验而避免了灾害。因此作者提倡“后发”“后行”的思路其实也是一种借助历史经验治理天下的策略,反对盲目冒进的治理行为。至于作者倡导“居后”的工夫,并非故步自封,文中解释道:“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2](P23-24)治理过程中,更易致胜的法门是“合于时”,如果能掌握这个智慧,即便是先行者也能治理好天下。

最后一个工夫是直接与“无为无私”的本体意识相应的“公正无私”。文中说:“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2](P27-28)这是说圣人之治之所以能长治久安,是因他能泯除私欲,因此处理国家事务就是公正公平的,后又进一步谈道:“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2](P28),这里特指君王不能随意更改法规法度上,而“曲因其当”也揭示了“公正执法”本身也伴随“因循”的智慧,强调了治理国家要尽量依顺事务的本性去治理,就如陈徽评价此处道:“治世之要在于人君‘执道之柄’、秉物变之‘要趣’”[5]。由此亦可窥见,《原道训》对君王提出的“公正执法”的要求实际是针对君王消除个人私欲,树立“公心”的角度而发出。
四、结 语
《原道训》一文作为《淮南子》的首篇,其问题意识是“以治为本”的哲学义理建构。《原道训》的作者通过对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等哲学问题的反思,旨在对其治道思想提供理论基础。而其中宇宙论的部分并非作者有意关注的哲学问题,只是出于理论建构的整体性考虑而简单陈述了相关意见,基本上直接沿用了原始道家以“道”为本原的宇宙论知识系统。因此,当搁置宇宙论对其治理问题关切的理论关联,从上文分析可总结出《原道训》一文的义理结构运思,即作者通过对本体论的相关主张为其治理思想论证必然性,又由本体论延伸出的人性论观点为其治理方案提供可能性,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工夫论主张来为其治理思想的落实提供具体指导。
注 释:
①关于本文使用的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等术语概念,需作一个概念术语使用的约定,尤其是本体论之本体,本文是依循中国哲学经典中“本体”之意涵,不同于西方哲学Ontology本体论之意涵。文中所言宇宙论是指关于具体时空、物质、存有者类别、世界结构的意见;本体论是指关于终极意义、价值的意见。本文是依据杜保瑞学者《中国哲学方法论》中对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等概念内涵的界定来使用的。
②《文子·道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参见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第25页。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