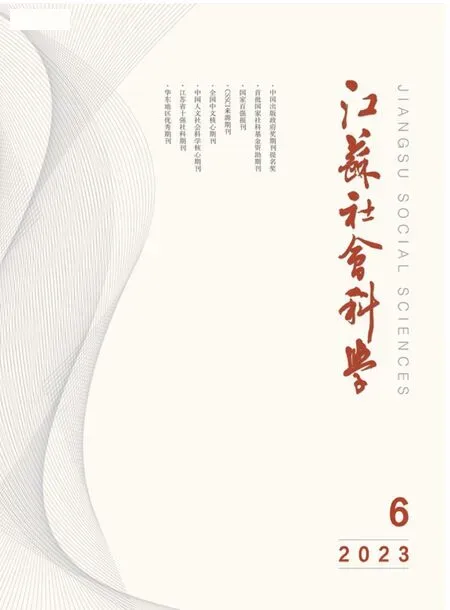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
王祥辰
内容提要 吴派是清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尊汉学、重考据的学术理念,影响了乾嘉以后学术发展的走向。然自乾嘉起,学术界给予吴派经学研究以充分关注,却忽视吴门学者的诗文创作与史学考证,此举不仅误读了吴派的治学理路宗旨,同时遮掩了吴门文、史流脉。吴派经学研究强调“证以史事”的方法,其诗文创作透露出“文好咏史”的态度,二者均隐藏以史学为根柢、实证为目标的学术脉络,直观体现吴派学人“好博尊闻”的思维模式与追慕古学的治学偏好。吴派学者以史学为串联,统摄经学与文学,落实经学注疏于史事,确立诗文创作于史书,是清代学人有意识以经、史统文的写照。而吴派以史统文,强化历史观念、史学文献之于经学研究、文学创作的作用,昭示乾嘉学术界由实学致用为主向考据还原为重的过渡历程,且显示了清代学术流变导引文学演进的内在关系。
清代学术史的主要研究范式,多从学派划分的角度出发,以学术共同体为切入点,探讨学术流变、演进的规律与价值。吴、皖两派是清代学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学派,若单论清代汉学,吴派无疑更受关注。章太炎即言:“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1]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1934年第10期。东吴三惠,尤其是惠士奇、惠栋父子,及吴门后学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江声等人,不仅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且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将推尊汉人学术的观念不断放大,引领乾嘉学风,使考据求实成为一时风尚。与吴派经学在学界被如火如荼地研究不同,吴派文学成就,尤其是经学推衍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则鲜少被提及。但不论是惠周惕、惠士奇,抑或是后来的王鸣盛、江藩,均将自己的经学观念、立场、方法浸入诗文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吴派经学家均有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故吴门学者的文学创作呈现经、史统摄,经、史、文三者合流的态势。
一、以史事为源的经典解读思路
在多数学人的认知中,吴派学者的经学观以汉儒经传为矩矱。徐仁本曾转述汪中的话,专门谈到惠士奇、惠栋父子助力汉学恢宏:“经学莫昌于我朝,我朝之经学莫昌于两江。昆山顾氏宁人,武进臧氏玉琳,长洲惠氏半农、定宇,休宁江氏慎休、戴氏东原,皆实事求是,羽翼汉学。”[1]徐仁本:《书述学后》,《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64页。《四库全书总目》谈到惠士奇《易说》,则将吴派学者宗汉理念说得更为具体:“专宗汉学,以象为主。然有意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故征引极博,而不免稍失之杂。”[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页,第240页。而论起惠士奇的《春秋说》,则直接将惠周惕至惠士奇绵延的吴门汉学宗脉表述出来:“士奇父周惕,长于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页,第240页。四库馆臣“专宗汉学”“承其家传”“考证益密”的评定,基本也讲明了以惠周惕、惠士奇等为代表的吴派经学家经解的主要立场,即多以汉学为依据,参以先秦两汉其他典籍,最终以实证为指归。尽管这种对先秦两汉典籍全面搜罗的方法,往往也被认作“失之不经”。但四库馆臣将惠士奇等的经典考证打上“赅博”的标签,还是能看出清代汉学阵营对乾嘉考证学风初起阶段惠周惕、惠士奇等先导经师的肯定。
后来学人对有关吴派学人解经特色的评定,大多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提法相类。顾千里即给予东吴惠氏家族“汉学之首”的极高赞誉:“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惠氏四世传经,为讲汉学者之首。”[4]顾广圻:《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7页。今人张素卿谈及惠士奇《易说》时进一步说:“惠士奇依准‘六经皆圣贤之语’之原则,会通诸经以解《易》,博考诂训,以象说之,而征诸典礼,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礼’成为《易》道会而通之的核心。”[5]张素卿:《博综以通经——略论惠士奇〈易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张素卿有关惠士奇《易说》“会通诸经”的提法,立足点还是吴派经师经解援引之广博,不过是看出惠士奇等人经注已将目光集中于经典内部,并为此后汉学经师解经提供了一定标准。
与其他学者视“博”为吴派学者经注理所当然的特点不同,潘雨廷提及惠士奇《易说》、惠栋《易汉学》《周易述》时,将惠士奇、惠栋等吴门学者渊博的原因用一种更为显豁的方式揭示出来:
若所说者莫不有本,且通以他经,明以《说文》,证以史事,旁及《老》《庄》《墨》《荀》,与夫《内经》《易纬》《易林》《太玄》《参同契》等。他如《楚辞》、汉赋亦时有所引,其博学盖可见焉。[6]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360页。
在潘雨廷的论述中,可以直观看出《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惠士奇等吴派学者“征引极博”的原因所在。除了征引他经以佐《易经》,潘雨廷还注意到,惠士奇等吴派汉学家的经注已经把材料搜罗的范围扩展到道家领域,甚至包括《楚辞》、汉赋等集部文献。此外,潘雨廷对有关吴派学者广采众说特征的解释,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证以史事”,用历史文献考订经学文本。
那么是否如潘雨廷所说,吴门汉学家经解常常从史事的维度出发论证儒家经典呢?答案是肯定的。以惠士奇《易说》注解《屯》六四《象传》“求而往,明也”为例:
四才柔暗,而《象》曰“明”,何也?《离》火,外明;《坎》水,内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祭有明水、明火,则水、火皆明矣。必离而始称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难之矣。汉光武失之龎萌,曹孟德失之张邈,诸葛武侯失之马谡,而萧相国独得之淮阴侯。淮阴侯乃楚之亡将,碌碌无能者耳,何所见而目为国士,且曰“国士无双”?非天下之至明,孰能与于此?《屯》难之时,天造草昧,不求国士,焉能成大业哉?[1]惠士奇:《易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在惠士奇看来,居上位者能够礼求下贤,从而得贤人以辅之,方可谓“明”。这与前人的相关解说并无二致。四居上卦,柔得正正位,以上求下,则得以刚柔并济,《屯》难局面便由此疏解。程颐谈到《屯》卦时说到:“居公卿之位,己之才虽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贤,亲而用之,何时不济哉?……知己不足,求贤自辅,可谓明矣。”[2]程颐:《周易程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页。而惠士奇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程颐等人的提法与刘秀与龎萌、曹操与张邈等人的具体史事结合,并从《屯》六四《象传》出发,回复《屯》卦《彖传》“天造草昧”,说明龎萌、张邈等人尚处事物萌发阶段,需“明”可见,使得“求而往,明也”得以落于“实象”。
除了惠士奇,惠栋、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学者,在解读经典的同时,也都会借历史事件佐证他们的观点。惠栋弟子江声在其《尚书集注音疏》中的做法,与惠士奇、惠栋等人如出一辙。江声注解古文《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曰:“太甲除丧即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礼,宗祀成汤于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从而与享焉。”[3]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儒藏精华编》第1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第231页。江声为了配合解说太甲除丧继位后的祭祀礼,引惠栋《明堂大道录》:
惠先生《明堂大道录》云:“配天之祭,百王与食。《多士》称‘自成汤至于帝乙’,‘网不配天其泽’,是其证也。”据此,则外丙、仲壬皆为王,自然与食;太丁则太甲之父、汤之冢适元子,虽未为王,不应独遗,故知亦从而举享也。[4]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儒藏精华编》第1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第231页。
江声将惠栋有关祭祀礼的论证当作结论,以期讲明外丙、仲壬、太丁所配的祭祀,与太甲祭奠成汤的礼仪相同。江声看似没有充分利用惠栋《明堂大道录》有关上古祭祀礼的考论,详细述明古代祭礼的情况。但他借着讲述太丁、外丙、仲壬隐晦地透露,他接受了惠栋《古文尚书考》中相关考辨结论,否认了孔《传》太甲直接承成汤帝位的意见,并认可司马迁《史记》的成汤与太甲之间还有太丁、外丙两君的载录。江声论证《尚书》的立足点在《史记》,是吴派学者经解“证以史事”的另类展示。
吴门学者甚至会在经注中对史事任意化用,不志出处。惠士奇《春秋说》解说《左传·昭公十三年》,谈到《左传》文辞出现“盟”与“同盟”不同指向,就有这方面特点:
襄二十七年,九国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于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当是时晋、楚分为两伯,犹后世南、北两朝。北指南为岛夷,南亦斥北为索虏。异俗、异制、异齐、异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观晋楚之盟,不言“同”,则《穀梁》“外楚”之说益信。[5]惠士奇:《春秋说》,《清经解》,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8页。
虽说《春秋》作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其文本本身就带有史学属性,但由上例依然能看出惠士奇选用史事时的别具匠心。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论说,他在阐述为何《昭公十三年》与《襄公二十七年》同载会盟提法却不一时,以南、北朝史作为具体事例,说明南、北朝习俗与制度多有不同。如若南、北朝会盟,需使两朝人统一习俗、制度,于是有“同盟”之说。《昭公十三年》提到“同盟于平丘”,实际上就是为了强调晋、楚两国各自称霸,两国习俗、制度等各方面已然不同,故若会盟,亦会着重明确需要“同”之特点。将晋、楚两国与南、北朝相比照,昭公十三年晋、楚两国国情特点一目了然。
惠栋再传弟子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特意记载了师祖惠士奇青年时一段轶事:
二十一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乃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1]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612页。
以经学饮誉清代学术界的东吴惠氏家族,却被后学江藩记录了这么一桩记诵史书的趣事,此中缘由值得玩味。江藩此记录一方面说明师祖惠士奇读书用功甚勤,且天赋较高,其经学著述广收博览与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说明惠士奇的史学功底深厚,给吴派后学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亦以此为榜样,进而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同为吴派重要学者的钱大昕,论起前辈惠士奇学术渊源时,也着重提到史学的影响:“先生盛年兼治经史,晚岁尤邃于经学。”[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11页,第612页。且此后钱大昕还着意强调惠士奇“幼时读《廿一史》”[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11页,第612页。之事。钱大昕不仅被后人视作吴派核心之一,实际生活中亦与惠栋等人过从甚密,其有关惠士奇生平的记述较为可信。质言之,惠士奇青壮年时,不单单将注意力集中在经学研究上,对史学亦十分重视,这也与江藩的讲述不谋而合。从钱大昕记述中可知,惠士奇晚年方才集中精力于经学。足见,惠士奇经学研究的方法与结论,不仅受到其青年时期学术倾向的影响,还能起到总结其学术研究特色的关键作用。如此也就不难解释,以惠士奇为代表的吴派经师经解著作带有鲜明的史学印记,且多运用“证以史事”的学术手段的原因。
二、基于“咏史”倾向的诗文创作趣味
吴派学者虽以经学名世,但诗文创作亦取得了较高成就。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谈到惠周惕诗歌成就时说:“诗格每兼唐宋,然皆自出新意。”[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页。今人漆永祥言及惠士奇之文,则表彰道:“引譬议论,左采右获,游刃有余。”[5]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2页。而清儒李绂更是作诗,记述其与惠士奇在国史馆论学、为文、饮酒的雅事:“金铺日昃影初凉,晚出蓬山笑语香。未要采丝重宛转,肯寻兰沐独摧藏。同人健笔追迁固,异事冥搜到雅苍。有酒剧怜能折简,共君痛饮论文章。”[6]李绂:《穆堂初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而对钱大昕、王鸣盛等文学创作的赞誉甚多,有清人论钱大昕之诗谓:“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屑以挦撦涂抹为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舂容渊雅,蔚为大宗。”[7]钱大昭:《潜研堂诗续集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提到王鸣盛时则说:“知其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余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8]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2页。吴派学人的主要工作虽不在诗文创作上,但他们深厚的学养为其文学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以至对他们诗文进行的褒奖都难脱离他们的学术研究而独立展开。
其实,吴派学人还创作出不少清新雅洁的诗歌作品,这部分诗作几乎看不出任何学问底色。比如惠士奇的《自石公山泛舟至消夏湾二首·其二》:
暮帆欲乱寒鸦色,秋涧长流玉罄声。夜来仍鼓沧洲枻,水清石瘦两奇绝。月上平添宝镜波,风回半卷芦花雪。孤棹洄沿兴不穷,每逢佳处一推篷。青天漠漠鸟飞去,飞上吴王辟暑宫。[9]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55页。
惠士奇此诗描写泛舟至消夏湾时所见之景色。不论是诗一开头提到的“暮帆”“寒鸦色”,还是此后言及的“芦花雪”“孤棹”,“雅洁”之感贯穿始终,尤其是“夜来仍鼓沧洲枻,水清石瘦两奇绝”此句,显然借助《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的内涵,使其独自泛舟湖上的孤寂之感,更添几分凄清,且与诗中“乱”“瘦”“平添”“漠漠”等语词运用桴鼓相应。有人认为该诗“缠绵婉约”,并认为惠士奇的这首诗作“几如梅村手笔”[1]漆永祥:《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55页。,实际上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肯定士奇诗歌创作“清新雅洁”的总体特色。
以学问家身份为主的吴派学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并非只展露文人才情,他们的很多诗作难以撇去终日为学而带来的学问底色。惠士奇在《赠宋坚斋先生三首》中就提到“数典方三世,传家在一经”[2]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6页,第251页,第251页。,虽该诗只是与宋骏业酬唱之作,但惠士奇还是特意提及家族三世传经之事,足见穷经问学在其人生中的重要位置。王鸣盛的《杂诗》也有“士不通一经,学术总荒芜。爱博反遗精,涉猎徒得粗”[3]王鸣盛:《西沚居士集》,《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页。之句,把学术追求和治学理念一一道明。当然,吴派学人诗歌所体现的学问倾向不止于此,与之经学考证“证以史事”异曲同工,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屡屡展示出极强的咏史意识:
五道通诸郡,三江绕故都。白猿终霸越,黑犬竟亡吴。人去空芳草,春来长绿芜。萧萧杨柳岸,愁煞夜啼乌……好上三台望,还从九曲行。可怜文种水,犹抱伍胥城。风雨松陵暗,烟波笠泽清。公孙今在否,寂寞久无声。[4]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6页,第251页,第251页。
惠士奇至姑胥台,即想到攻伐楚国,雄霸东南一时的吴王阖闾,同时也回忆起对伍子胥、公孙圣等人的劝谏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力主伐齐,而至吴国灭亡的吴王夫差。阖闾任用伍子胥等开创大好局面,与夫差大意听信伯嚭等的谗言被越人灭国的鲜明对照,借着惠士奇“黑犬”“公孙”等典故的运用跃然纸上。惠士奇在诗后自注道:“吴王书寐姑胥台,梦前园横生梧桐,召公孙圣占之,圣曰:‘梧桐心空,不为用器,但为甬僮,与死人俱葬也。’……公孙圣曰:‘我死,当使后世有声响。’及吴亡,三呼三应。”[5]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6页,第251页,第251页。沈德潜也发现了惠士奇的匠心独运,并特意指出该典故的出处:“黑犬及下章公孙圣事,俱见《越绝书》。”[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页。从惠士奇自注典故内容,再到沈德潜着意标出典故来历,都足以看出惠士奇咏史诗所化用《吴越春秋》之史事并不常见,侧面也表明惠士奇对史学文献之精熟。
钱大昕、王鸣盛等因为更加热衷史学,创作的咏史诗数量较之于东吴惠氏也更多一些。钱大昕对元代历史研究颇具热情,他曾经发愿重修《元史》,可惜未能如愿。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学术兴趣写入诗歌之中:“兀朱加叶总名邦,大将征西金鼓……”[7]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钱大昕以《元史》为主题,一连写下二十首诗,作《元史杂咏二十首》,将其有关元朝兴盛、灭亡的思考一同嵌入诗中,史学解读与文学趣味并兼。王鸣盛的诗歌也常围绕历史事件展开评点,他的《咏古六首》就是其中代表。他甚至还梳理出《诗经》当中的咏古诗,用以佐证经学家创作咏古诗的合法性:“盖《诗》有咏古而意在伤时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类是也。”[8]王鸣盛:《蛾术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7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页。钱林介绍惠士奇诗集时提道:“士奇诗集名《红豆斋小草》,又有《半农人诗》《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9]钱林:《文献征存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从钱林记述中可以得知,惠士奇除了现可见的《南中集》《采莼集》等两部诗集,还有包括《半农人诗》《咏史乐府》等在内至今未见的多部诗集。但即便如此,由《咏史乐府》的集名,结合钱大昕、王鸣盛等对咏史主题的重视,依然能大致看出以惠士奇为代表的吴派学人咏史怀古的诗学旨趣。
当然,吴门经士不单单在咏史诗中展示出博采史书的意识,从他们创作的其他类型的诗歌中,也经常能察觉到利用历史文献的痕迹。譬如惠士奇《夜泊庐陵》:“系缆双流岸,舟人语夜阑。推蓬千顷白,欹枕一灯残。明月鹧鸪洞,秋风苦竹滩。平生流水意,欲取素琴弹。”惠士奇在诗后自注曰:“庐陵有鹧鸪洞,见《南唐书》;苦竹滩,见《南史·周文育传》。”[1]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5页,第265页,第274页。又如《为宋药洲先生题出塞图》:“跃马过临洮,当年意气豪。首簪银立笔,腰佩玉环刀。令比三秋肃,功成一箭高。试看真学士,千骑拥旌旄。”而后,惠士奇写道:“《宋史》:‘学士簪银立笔。’”[2]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5页,第265页,第274页。由此足见,惠士奇等吴门学者的诗作不仅浸润着史学文献的印记,他们还有意将自己诗歌与史书间的联系,以自注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透露出来。
吴派经师在文章创作方面,也非常重视史论结合。漆永祥讲评惠士奇《红豆斋时术录》时,发现了惠士奇文章与宋史间的瓜葛:“所论多宋时政事,则士奇盖于宋史研究,每有心得之故。”[3]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25页。惠士奇在论析《孟子》“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时,即援用宋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请借赵宋事证之:司马光,天下之正人也。国人皆曰贤,则将可之乎?章惇,天下之邪人也。国人皆曰不可,诸大夫皆曰贤,则将可之乎?”[4]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5页,第265页,第274页。此外,惠士奇还专门以《寇准》《王安石》《高宗》等为题作文来,品评宋史。钱大昕此类文章也不在少数,虽然在《潜研堂文集》中,看到的大多是应制文,不过依然能明确看出钱大昕关联史学的良苦用心。与惠士奇相同,钱大昕也以《王安石》为题撰作文章,在文章开篇,钱大昕就旗帜鲜明地点出“世称王安石误用《周礼》而宋以亡”[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观点的错误,并结合《周礼·地官》中“泉府”职能,讲明王安石强行关联《周礼》与青苗、市易之法非正确之举。王安石变法不成功是因立法内容所致,与是否参考《周礼》无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在该文中,还特意引用王安石的诗歌“今人未可轻商鞅”之句,足见其与其他吴派学人一样,有会通经、史、文的追求。
吴派学人一直都有融史于文的意识。梳理他们的诗歌、文章亦能明显看出,咏史是其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吴派学人诗文创作中,采用史学思维、利用历史文献的观念,和他们学术成长过程中长期受前辈史学著述浸染有很大关系。惠士奇曾与惠栋共同撰作《汉书纂录》,有学者从《汉书纂录》的考证经过指出,顾炎武治史思路对惠氏父子的映射:“惠士奇治史,最取法顾炎武。顾氏《日知录》的考证内容涉及《汉书》与《后汉书》,而惠士奇对两部《汉书》的研究就以之作为梯航。”[6]赵四方:《惠栋的史学思想及经史研究关系论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惠士奇、惠栋都没有直接向顾炎武问学的经历,质言之,惠士奇、惠栋在读书积淀的过程中,主动且有意识地吸纳顾炎武等前辈学者的史学经验,并将其融入后续的经史研究。而这种经验的汲取,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诗文创作宗尚的形成,此中联系并不难说清。
三、好博尊闻之绪与经史统文之习融合
阮元在《畴人传》中介绍惠周惕、惠士奇时说:“惠氏世传汉学,今世学者皆宗之,盖儒林之选也。”[7]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63页。沈竹礽提到惠士奇也认为:“惠氏士奇,宗汉学者也。”[8]沈竹礽:《周易易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但惠周惕、惠士奇的治学特色是否能真正与乾嘉“纯汉学”画上等号,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近人柴德赓谈到东吴三惠时,就惠周惕、惠士奇是否能代表汉学发出质疑:“然三惠之中,周惕、士奇实兼词章,非专汉学。”[9]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页。梁启超论及惠士奇学术地位时讲道:“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页。在梁启超看来,惠士奇与顾炎武一样,是清代复古学术主潮的推动者。但顾、惠二人,只将学术复古运动带到六朝、唐之注疏学,并未到深入东汉郑玄、许慎之学的地步。章太炎更是跳过惠周惕,直接点明惠士奇《礼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1]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1934年第10期。
虽然对惠周惕、惠士奇等吴派先导学者是否能代表清代汉学尚存争议,但学人并没有忽略惠周惕、惠士奇等人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引领作用。与章太炎、梁启超等的观点相类,萧一山《清代通史》论述惠周惕、惠士奇之于东吴惠氏学术发展意义时,也并未专门提及士奇的汉学研究思路。不过萧一山强调,惠氏著作体现出“博闻强记”的特点,仍然为学林所重:“惠派之学注重博闻强记,此于士奇见其端矣。”[2]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565页。而事实上在多数学人的认知中,除了强调汉学以外,“尊博”亦是吴派的学术特色之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3]章太炎:《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142页。
惠周惕、惠士奇“博闻强记”的特点,其实与吴派“好古”的总体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同一性。因为嗜博必然带来的就是求之古学。就像钟文烝提到的那样:“惠士奇父子倡古学于东南。”[4]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只不过与在惠栋带领下,吴门后学江声、余萧客等将古学的主要标准确立为汉学,尤其执郑玄之学一端不同,惠周惕、惠士奇的“好博而尊闻”,并无学术源流时序谱系编列上的明确排序。《清史稿》对惠周惕、惠士奇治学特色概括得比较恰当:“于《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于《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79—13180页。赵尔巽等大致交代了惠氏解诸经的不同特色,较之于惠栋、余萧客、江声等吴门后劲,惠周惕、惠士奇的经解没有单纯指向汉学,但复古、用古企图显露无遗。在惠周惕、惠士奇的经解过程中,郑玄等汉儒之学更多起到沟通当下学术与先秦典制媒介的作用。而最能体现惠栋以前吴派学术思想框架的,是四库馆臣介绍惠士奇《礼说》的一段话:
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157页。
惠栋以前,东吴惠氏此类解经方式,看似是回归到汉人学术话语系统中,实则是想要把经学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落实,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才给予《礼说》“持论最有根柢”的品评。而这种经典研治的总体思维方式,与我们此前强调的吴派“证以史事”的经解倾向、“文好咏古”的文学宗尚,达成了微妙的统一。不论是经典注疏以史学文献作为主要支撑,还是文学创作多用史学典故追慕古事,归根结底,都是以实证为手段,是学有根柢的具体表现。而这种追求“根柢”的学术态度,亦为后来吴派后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惠栋言及诗歌时,既不谈汉学也不说考据,而是单单提“诗之道,有根柢焉”[7]惠栋:《古香堂集序》,《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326页。,其实亦是变相对吴门学术特色做出了另一种概括。而“根柢”之说,与汉学、考证学也能达成互动[8]王祥辰:《“根柢”重构、“诗史”追寻与家学接续——论惠栋的诗学旨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尽管惠周惕、惠士奇的学术研究并未明确以汉学为指归,但其“好博而尊闻”的总体学术思维框架的确立,还是对惠栋、江声、余萧客、江藩等人推尊汉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展现在惠周惕的《诗说》、惠士奇的《易说》《礼说》《春秋说》等经解上,甚至作用在惠栋文学观的塑造上。惠士奇曾经在讨论音律的时候,透露过他对诗、词、曲等不同文类的看法:
然则律何以正?曰:正以《诗》。凡人有志斯有诗,有诗斯有声,有声斯有律,有律斯有数。《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古者以六诗为之本,六律为之首,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十有二声为之齐量……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至晋而犹有《雅》乐四章存焉。后世官失其守,《诗》存而声亡。汉《郊庙乐歌》,其《风》《雅》之变乎?宋词、元曲,淫声、慢声也。[1]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8—269页。
惠士奇认为,《诗经》合乐而歌,使得声音、律吕等得以存续。至汉代立制氏世代为乐官,尚且保存住《雅》乐之声律。但晋朝时,仅存《雅》乐四章。后来的乐官,尽管有此官衔,却在其位不谋其政,致使声律流传中断。由是,存世的只有《诗经》文本,散失了合乐的音乐。汉代的《郊庙乐歌》因为制氏通晓声律,依托《国风》《大雅》《小雅》得以有音乐配合。而宋词、元曲则由于声律的散失,流为俗乐。惠士奇对于宋词、元曲“淫声”“慢声”的评价,显示出他对汉晋诗歌以后逐步兴起的词、曲之不满。
从惠士奇评论诗、词、曲的不同表述方式,以及惠周惕追溯《诗经》合乐发展的经过并明确指向汉晋的倾向中,能够看出,吴派学人好博尊闻,追慕古学,这种倾向必然使其回归经典。而以经典为根本的阐述过程,自然需要以史学发展为线索连接古今。因此,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制度层面,更接近于经典的汉晋学术,得到他们更多的关注。这种以经学理论为基础、史学脉络为线索的倾向,也作用在他们文学创作、文体使用的偏好上。惠周惕写作《过田家》、惠士奇创作包括《牧童词》《樵客行》《行路难》等在内的众多乐府诗,其实也投射了他们经学价值观念下的文学立场。在沈德潜看来,惠士奇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正是这部分乐府诗:“皆张、王体中最雅洁者。”[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5页。惠周惕、惠士奇父子经典研治的总体思维方式,也为其文学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罗时进指出,吴派自惠周惕起始有文学家数:“学术与文学兼优可以打通仕宦的道路,而仕宦又需要以学术与文学维持其社会雅誉,扩大文化交友圈。这一特点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惠氏家族数代仕宦,数代治学,余事作诗,形成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交融的文学家数。”[3]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页。
在清代朴学界,惠士奇并非首先因为音律问题而关注乐府诗的学者,顾炎武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述:“《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诗。宋以下,则其所为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285页。但即便如此,惠士奇将音律学与乐府诗关系的问题,直接落实到汉、晋,较之于顾炎武的说法,更为具体,而惠士奇的详细阐述,也影响到了惠栋。惠栋就说:“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奏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以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唐以后则有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5]惠栋:《九曜斋笔记》,《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
此后,惠栋将经学的兴盛与诗学的发展相联系,并将诗学发展的转折指向汉唐,就是在惠士奇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动。而惠栋在《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引述的一段王世禛《池北偶谈》,亦为惠士奇关注声律与乐府诗的关系做足注脚:“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今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后人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是使然也。”[1]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四部备要》第85册,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202页。可见,惠栋治经,言必汉唐,与其祖、父的综合影响直接相关。由是亦能看出,乾嘉汉学研究范式的确立,脱离不了惠士奇的作用。吴派秉持的汉学理念之所以在乾嘉后引发学界关注,的确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代人合力苦耕的结果。
胡适总结清代考据学特点时说:“清代考据之学有两种涵义:一是认明文字的声音与训诂往往有时代的不同;一是深信比较归纳的方法可以寻出古音与古义来。前者是历史的眼光,后者是科学的方法。”[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将清代考据学单单指向音韵、训诂,胡适的论断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将错综复杂的清代考据学内部关系,简练地概括成“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两面,应当说,胡适的论述基本达到了化繁为简的目的。而吴派学人“好博尊闻”的思维框架带来有关经学、文学研究的深入,强调时间发展的脉络,无疑指向胡适所归纳的“历史的眼光”。
陈平原肯定胡适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清代考据学之于古代学术发展的推进价值:“清儒为了这种学术上的‘还原’,发展出一整套考据学理论与方法,这正是胡适所赞叹不已的‘科学精神’。”[3]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能够具有好博态度、慕古精神,将学术眼光由主流宋明理学上移至汉晋学术,吴派学者实际上做到了“学术上的还原”。且这种还原并不单单定格在经学研究之上,而是依靠“历史的眼光”的串联,尊博、好古、实证气氛笼罩下的经学、史学、文学等传统学术的多个领域,在吴门学人的学术系统中,均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统一与合流。这种统一与合流的态势,从某种层面也引发了后来汉学考证渗透到学术发展的各个领域,即用一种史学还原的方法,去处理经学与文学所涉及的具体学术问题,从而在方法层面对学术的演进做出指引。这种学理层面的推动,此后又作用在经学注疏特色与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上。而经学注疏特点的巩固与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又会反过来更加稳定学术导引的意义,使得雍乾之后以秦汉典籍为根本、考证为手段的学术理念大行其道。
四、结语
自魏晋南北朝刘勰等人明确“征圣”“宗经”始,文人文学实践活动极重经学渐成主流,兼具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之人亦渐增多。但考据学风主导下的清代学坛,文学家之文风较前代仍然大有不同。学人文学创作,一方面需要展示自己文学创作的才情;另一方面,受制于考证学风的浸染,即便写作诗文,也力图做到文必有据、言必有征。而这种以实证为主的学风、文风,甚至演绎成一股实学潮流。吴派是这股实学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惠士奇直接在经注中提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仍从《说文》为正。”[4]惠士奇:《礼说》,《清经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非舍经而从传,实事求是,正所以尊经。”[5]惠士奇:《春秋说》,《清经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达成“实事求是”的目标,吴派学人以史学为线索总辖经学、文学。将经学研究落实到历史史事,以史证经、以经观史;将文学创作立足于史学文献,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吴派经学著述、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上述特性,是他们“好博尊闻”思维模式导向的必然结果。而经由吴派析论亦能看出,从事清代学术研究,不能偏执于经学家学术的某一方面。跨学科分析清代学术史,不仅能揭示个体学术特色之隐含脉络,且有助于以小见大,统观同时期学术发展之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