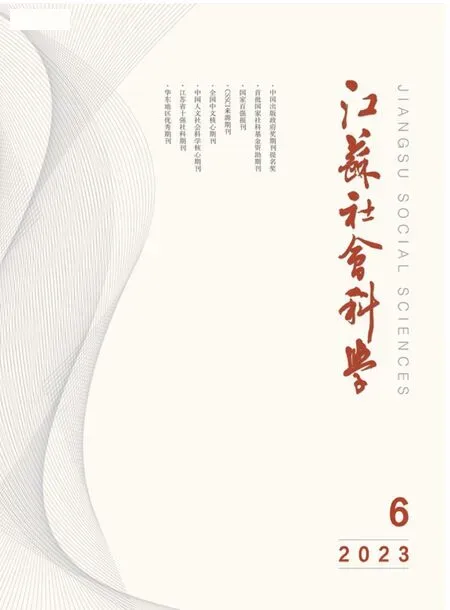构建“共同”:剧场表演中的国家认同塑造
顾高菲
内容提要 剧场表演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社会成员可通过剧场表演中的模仿、创制和净化三个环节共享历史、共通文化和共建情感,从而凝聚认同。在塑造国家认同的剧场表演实践中,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极具代表性:它模仿中国革命历史史实进行剧场创作,培育社会成员对共同历史的理性认知;它创制彰显民族性格的精神文化场域,凝聚成员对共同文化的深度理解;它净化引发集体共鸣的情感场域,唤起成员的共同情感及认同行为。以“剧场模仿—剧场创制—剧场净化”为分析框架,探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情感的构建,有助于理解剧场表演在国家认同中的价值意义,提升剧场表演实践对新时代国家认同建构的贡献。
国家认同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凝心聚力的价值与功能,剧场表演则是增进国家认同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下多简称《东方红》),是剧场表演与国家认同之间互动关联的典型案例,对于当时的国家认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东方红》的既有研究尚未就此展开深入挖掘,主流范式聚焦艺术领域,偏重考察《东方红》中的声乐曲词、民族唱法、演奏风格、舞蹈技巧等艺术元素[1]《论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第1册,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第21页;高伟:《歌唱光辉的革命历史——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新作》,《人民音乐》1964年第12期;焕之:《八月桂花遍地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曲》,《北方音乐》2007年第8期;胡果刚:《舞蹈艺术的一次检阅》,《胡果刚舞蹈论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相对忽视这一剧场表演的政治文化功能;新近的文化研究虽关注到《东方红》的认同价值,并从记忆、文化认同、身体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1]黄卫星、翟翊辰:《史诗〈东方红〉记忆与价值共同体及传播意义》,《当代传播(汉文版)》2014年第5期;陈小眉,冯雪峰:《演绎“红色经典”:三大革命音乐舞蹈史诗及其和平回归》,《华文文学》2014年第1期;闫桢桢:《身体的记忆政治与文化认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审美策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张素琴:《主体叠合与权力转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身体政治》,《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但未能提供系统解读的理论范式。本文尝试对《东方红》剧场演出构建的“共同”进行理论分析,解读这一剧场表演对表演者、观演者及周边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增进国家认同。
一、剧场与认同:分析的理论基础
就词源而论,“剧场”原指“观看之场所”[2]李亦男:《德语国家剧场艺术学概览》,《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即现实中演出发生的物理空间。发展至今,“剧场”已成为一种艺术形式[3]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它通过演员表演和观众参与来传递故事、表达情感,在主体的认同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界对于剧场表演与国家认同的关联性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领域,国外学者多青睐借用剧场表演模式来研究社会、政治乃至国家[4]剧场表演研究囊括表演艺术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研究者主要从演变历程、理论框架、方法以及实践性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参见R.Cohen, D.Sherman, Theatre Brief,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7;P.Pavis,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erformance and Contemporary Theatre, London: Routledge, 2016;R.Bharucha,Theatre and the World: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2003。。欧文·戈夫曼将表演研究从剧场拓展到日常生活,以“虚拟戏剧”研究社会互动[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5页。。维克多·特纳通过“社会戏剧”说明社会的变化与延续[6]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10页。。理查·谢克纳将剧场表演样式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之中[7]俞建村:《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克利福德·格尔茨则以令人“目眩神摇”的仪典象征,分析和展现了尼加拉如何通过公共戏剧化成为“剧场国家”[8]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赵丙祥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页。。这些研究将剧场表演与人类社会、政治及国家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连接。近年来,国内学界也越来越关注剧场表演中仪式、集体身份等与国家认同关系密切的议题[9]周传斌、韩学谋:《剧场、仪式与认同——西北民族走廊唐氏“家神”信仰的人类学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6期;杨晓:《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意义:以赛亚·伯林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学海》2021年第1期。施旭升:《民族身份与社会认同——论香港话剧的文化矛盾》,《戏剧艺术》2008年第1期;王良范:《认同形塑——民族与国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多以《诗学》作为解读剧场的权威理论基础,《诗学》关注的模仿、创制和净化这三个关键性环节,被视作剧场理论研究的历史范式[10]剧场艺术学家里斯多弗·巴尔姆所认为,德语国家剧场艺术理论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性的概念:模仿(mimesis),剧作(poiesis,亦被译为创制),净化(katharsis),感知(aisthesis)。参见C.B.Balme,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6-37。。循着这一范式,剧作者通过“模仿”,将历史事件“创制”成为艺术作品,由表演者演出于舞台之上,对观众产生“净化”作用,即为一场完整的剧场表演。尽管模仿、创制和净化这一组关键性概念中未出现“认同”二字,但在由它们精准建构的想象空间(剧场)中,原本指向“个体建构的自我与他者之间认可、赞同关系”的认同[1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无处不在。
从模仿与认同来看,所有呈现于舞台上的事物,都被视为对现实的模仿。这一模仿不仅涵盖历史故事在时空层面的全景演绎,也包括人物细节等仿照呈现[1]克里斯托弗·巴尔姆:《剑桥剧场学导论》,李竞爽、孙晓雪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版,第91—93页,第94—98页。。柏拉图以批评的口吻指出模仿具有认同作用[2]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列举了模仿的数重“罪状”,欺骗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模仿之所以能打动(欺骗)人,是因为“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在这里,满足和迎合实际上便是诗人在对认同进行建构。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4—407页。,社会心理学则从正面指出仿照现实的行为是认同产生的前置条件[3]A.B.彼得罗夫斯基、M.T.雅罗舍夫斯基:《心理学辞典》,赵璧如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6页。。循此而言,剧场表演从创作之初的模仿就暗含认同的建构,这是艺术拥抱真实的最直接途径。对已有印象或是心灵上本性部分的模仿性再现,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它将被模仿事物中蕴含的力量施加给观众,从而起到认同乃至同化的效果。
从创制与认同来看,剧场表演中的创制是以“存在之物”为对象进行情境或故事情节建构,关涉的是故事在剧场表演中如何叙述或再现等问题。后戏剧剧场的代表人物汉斯·蒂斯·雷曼认为,剧场创制的中心在于情境建构,其依据是具体日常生活的物[4]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131页。。巴尔姆则指出,决定观众认知和情感反应的关键在于剧场创制能否引发观众认同[5]C.B.Balme,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6-37.。就此而言,剧场创制中的认同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创制蕴含的认同首先来源于对“具体日常生活的物”的模仿;二是在以观众接受为目标的剧场创制中,剧场对故事情节的组织、情境的建构都要考虑观众的认同反应。
从净化与认同来看,净化通常在剧场表演过程中产生,受到剧场模仿的客观事件、创制的故事情节与情境以及舞台上的表演行为等诸多因素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净化看作对模仿引发的相应情感的疏导[6]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65页,第229—230页。。后续研究拓展了净化的意涵,增加道德洗涤与教化等内容[7]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65页,第229—230页。。无论是原初的净化还是被重新释义的净化,关涉的都是以观众为中心的观演关系,认同始终暗藏于其中,巴尔姆将之称为“被认同驯化的净化”[8]克里斯托弗·巴尔姆:《剑桥剧场学导论》,李竞爽、孙晓雪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版,第91—93页,第94—98页。。
剧场表演天然蕴含认同这一基因,表明关涉国家内容的剧场表演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可能。《东方红》便是剧场演出与国家认同之间互动关联的代表,它在模仿、创制和净化中对其创作时期国家认同的贡献亦可圈可点。将《东方红》作为研究个案,依循剧场理论与认同的关系,重新审视剧场表演等艺术媒介在塑造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情感中的功能,可以为新时代增进国家认同开拓新视域。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模仿—创制—净化”三个环节研究《东方红》剧场表演与国家认同塑造之间的关联。首先,讨论《东方红》如何模仿中国革命历史全景以推动形成“共同历史”的认知;其次,分析《东方红》在创制中怎样创设历史情境、刻画国人民族性格以形塑“共同文化”的认同;最后,揭示《东方红》剧场演出所激发的“共同情感”以及由此唤起的更广范围的国家认同。
二、共同历史:剧场模仿中的史实再现
中华民族的屈辱、沧桑和荣耀,在代代相传中沉淀于每一个成员的意识深处,成为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认知[9]洪宏:《如何寻找“我们的东西”?——韩国大片建构民族认同的四个维度》,《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但这一认知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因而,需要时常重温中华民族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在逼近史实的基础上强化成员的历史认知,激发成员亲近民族和国家,增进国家认同。
在剧场表演中,模仿先行于创制,是创制的先导和前提基础,并贯穿于剧场表演的始终。《东方红》对中国革命历史史实的模仿,主要立足于呈现历史全景和复刻历史细节,旨在培育社会成员对“共同历史”的理性认知。
1.历史全景重塑认知
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以来国家四分五裂和人民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获新生的中国人发自内心地歌颂和传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英明神武,却选择性淡化了敌人的强大、战争的残酷和革命的艰难等。一种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向往皆大欢喜。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苦难的回避,古来有之。无论是哪种原因,在时间对历史的消解中,人们关于中国革命的认知与记忆不可避免发生偏差,如21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抗日神剧”违背历史、违反常识,无限夸大甚至神化党和人民的力量,贬低敌人的智商[1]杜彩:《电视可以娱乐,历史不容调侃——再论“抗日神剧”的是是非非》,《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置于娱乐狂欢的语境之中[2]李一君、史博公:《“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传播效应及创作反思》,《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这不仅传播了扭曲的历史观和错误的价值观,而且严重损害了民族尊严以及革命先烈形象,削弱了国人对革命历史甚至是新中国的认同。因而,无论是历史认同还是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都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历史全景认知的基础之上。据此,《东方红》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模仿,须融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视角,既涵盖完整的中国革命历程,包含开端、发展和结局,又呈现中国革命历史的多面性,有胜利与欢喜的一面,也有惨烈、艰难的一面[3]金冲及:《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0页。。
从历时纵向的维度而言,《东方红》对中国革命的模仿,囊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两次国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完整革命历程。以“黑沉沉的天、黑沉沉的地”迎来“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开启了中国革命艺术叙事的开端;“燎原的星星之火”催生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展现了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红军不怕远征难”,历尽艰辛“自力更生”,拼死都要“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在不懈努力中,抗日战争发展成为人民的战争,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百万雄师过大江”“天亮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呈现的是中国革命的结局。依据国民课堂里的历史教科书,《东方红》对中国革命的历时性模仿,既体现了“历史感”,又达到由此支撑的“客观性”效果。
在横向维度,《东方红》将生动、形象的革命历史置于共时视角下,不仅包含令所有中国人欢呼鼓舞的一面,如克敌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等,还通过《就义歌》《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等重现了党在幼年时期因缺乏经验招致严重后果的另一面,相应的朗诵词直接指明个中原因,如“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得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4]参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等。传统的行为学理论认为,占有资料信息越全面、越真实,人们由此形成的认知和判断也就越理性,且越稳定[5]费多益:《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东方红》的全景模仿旨在引导人们全面、真实地认识革命历史:首先,中国革命远不止豪情壮志和节节成功的一面,更不存在“手撕鬼子”之“神力”或“绝技”。其次,革命最终的胜利是不计其数的鲜活生命前赴后继,以无我、忘我的精神浴血奋战、艰苦奋斗铸就而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换来的,“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6]参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才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写照。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维度,《东方红》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模仿,不仅让未亲历过革命战争的人们看到了革命的全景,体会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还真实呈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多面性,包括旧社会的黑暗、底层的苦难、敌人的强大和战争的残酷。在此基础上,生在红旗下的人们才能与饱受苦难的中华儿女感同身受,理解先辈们在万般曲折中的不懈抗争,热爱他们曾拼死保卫的这个民族国家,从中形成对中国革命历史以及新中国的理性认知。
2.细节元素凝聚认同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历史的真实感往往体现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在剧场创作的模仿中,细节对客观历史的还原度直接影响着剧场表演的可信度和观众的认同感。作为以教科书为蓝本进行的模仿创作,《东方红》除了在舞台上构建宏大的中国革命历史远景,在剧场布景、人物造型、舞美道具等细节元素上也下足功夫,通过细节照应历史真实,凝聚观众认同。为了让剧场表演更具客观真实感,《东方红》剧场中的所有元素,如事件发生的地理空间背景、不同革命阶段的人物造型和角色身份、舞美道具等都与真实的历史相匹配[1]周恩来要求《东方红》的创作排演一定要符合历史史实,并对初排中出现的不符之处做了修改指示。参见周恩来:《对修改排练后的〈东方红〉的意见(1965年3月5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枪、炮类武器道具是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最为常见的细节元素。通过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是党和人民在革命中的武器补充方式之一[2]张胜:《新四军建立初期武器装备问题研究》,《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可以说,枪炮武器的演变记载着中国革命的每一步发展。《东方红》很好地运用了“武器”这一细节元素来体现其模仿的真实性。譬如,在《秋收起义》和《打土豪、分田地》中出场的北伐革命军、工农赤卫队和红军使用的是土枪、洋枪、梭镖、大刀和松木炮等;到了《飞夺天险》时,战士们除了有短枪、大刀等,还用上了步枪、手榴弹;在《游击战》中,最先出场的游击队员们基本使用的都是大刀、铁锹、梭镖、土枪和土炮,也有赤手空拳的,但当他们“炸碉堡”胜利之后,每个人手上都有了新武器,大部分队员拿上了带着刺刀的歪把子枪,传神地演绎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真实历程。处处贴有“历史真实标签”的细节元素,与剧场情节发展环环相扣,展现着中国革命历史齿轮转动的痕迹。
与此同时,《东方红》对细节元素的处理也让剧作者和演职人员对这部作品的历史感和真实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并自觉以更为严谨的态度对待《东方红》的创作、排演工作。尤其是在反复的排练演出中,“呈现真实历史”的目标意识,不断“渗入”并“浸润”演员的身体——从唱腔到唱法,从语音到语调,从眼神到表情,从肢体到动作。最终在国庆舞台上,这些努力将演员们“塑造”成为中国革命穿越时空的鲜活载体。进一步而言,这些可观、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细节符号承载着客观史实,与宏大的革命历史全景相呼应,让剧作者、演职人员包括台下的观众对从“长夜难明”到“雄鸡一唱”的《东方红》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不仅强化了他们意识深处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认知,更能使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判断,从而产生理性认同,那就是:先辈们用生命拼出来的新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国家,中国革命历史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
三、共同文化:剧场创制中的文化形塑
剧作者按照对客观世界的特定认知框架,在舞台上创设包含表演场幕、事件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在内的表演情境,并期待观演者能按照其设定的认知框架接受和理解信息,这在剧场理论中被称为“创制”[3]C.B.Balme,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6-37.。如果说《东方红》的剧场模仿是为了引导社会成员对共同历史形成理性认知,那么在舞台上创设中国革命历史情境、刻画人物形象与民族性格,则是为了让社会成员在《东方红》中“共同经历”革命,“亲身”进入拥有共同民族性格的精神文化场域,形塑“共同文化”,进而增进国家认同。
1.“共同”的革命经历
“悲哀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们要求共同努力。”[1]厄内斯特·勒南:《国族是什么?》,陈玉瑶译,《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厄内斯特·勒南的这一观点赋予“屈辱的历史”另一层含义,即民族成员共同从屈辱走向荣耀的经历,更能成为成员延续历史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东方红》对表演情境的创制则聚焦于“共同经历”这一关键。
根据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东方红》的剧场演出创制了八个场幕[2]《东方红》第七场《祖国在前进》、第八场《世界在前进》的主题是“建设新中国”。根据毛泽东“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的意见,这两场在1965年电影拍摄时被删除,因此,通过电影传播至今的《东方红》,能看到的实际只有建立新中国部分。:《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这展现了中国人民在近代的经历:三座大山的压迫→个体的反抗→党领导人民一起抗争→历经挫折→奋斗→不懈奋斗→人民的战争→革命胜利→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了将党和人民从饱受屈辱走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抗争史,创制成为革命后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文化记忆,《东方红》选用了革命时期流传最广的金曲、金句、民间小调以及舞蹈等进行再加工创作,用以表现相应的革命时代以及相对应的历史事件。能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的艺术元素,必定是凝聚了时代意识、人民情感和艺术家审美理想的结晶,镌刻着深深的时代文化印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例如,当人们听到《南泥湾》的旋律,眼前就会浮现八路军第359 旅开荒的景象,听到《保卫黄河》就会想起全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年代,听到《游击队歌》就能在脑海中浮现地道战、地雷战等智取制胜的场景。当这些熟知的音符、画面重现在《东方红》的剧场情境中,必然会勾起观众(尤其是革命的亲历者)对相应历史的回忆和联想,引发强烈共鸣。在《东方红》公演的观众席上,当《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音乐响起,一位妇女跟着节拍小声地哼唱起来,旁边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侧过头问:“妈妈,你会唱呀?”妇女回答说,“这是我上学时的校歌”。紧随其后的旋律是《到敌人后方去》,她对小姑娘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路唱着它去到敌人后方的。”[3]黄卫星、佟佐尧:《尊重艺术规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导专访系列之四》,《舞蹈》2014年第7期。
《东方红》通过选用流传最为广泛的词、曲、旋律等艺术元素精准呈现中国革命历程,一经演出,便“收获”了大批粉丝,不仅唤起了亲历者的革命记忆,而且建构了非亲历者关于革命历史的文化想象。无论是否亲历过革命战争,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在《东方红》创制的逼真情境中,均产生了与先辈“同荣辱、共进退”的真实感受。他们穿越时空,一道面对旧中国的黑暗曲折、国破家亡,共同“经历”了拿起武器、奋起反抗直至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在剧场中响起的那一刹那,台下的掌声、欢呼声以及激动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这沸腾的情形,就像是场内的所有人刚刚一起亲历了中国革命一般[4]莫伟鸣、何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由来》,《人民音乐》2006年第12期。。在时间的流逝中,《东方红》逐渐沉淀为数代人关于中国革命的记忆,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一生。譬如,曾随父亲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公演的冯秋生,被充满革命激情的表演以及观众的热血沸腾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当年只有十四岁的他,长大之后学了声乐,并在建党80周年时,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再次将《东方红》搬上舞台。在他们的回忆中,1964年的《东方红》将他们“传送”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让他们受到了如亲历革命般的精神洗礼,这种“亲历感”,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5]《记得那年东方红第七集:我们的歌声传四方》,2015年12月8日,https://v.qq.com/x/page/n01753huoca.htm。。
2.共有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天然联系。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固有的品格秉性,它在长期发展中积累,并经由代际传承,最终沉淀成为该民族成员普遍共有的精神,而“民族成员对民族精神的确认”则被视为文化认同的本质[1]王希恩:《关于民族精神的几点分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东方红》在人物形象创制中,紧扣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性格特征,展现了可供民族成员确认的普遍共有精神。
舞蹈《苦难的年代》将卖儿鬻女、码头工人被欺压、抓壮丁等事件串联在一起,呈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身插草标任凭买卖的女孩、被迫卖女生存的女人、背着沉重木箱的码头工人,他们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普遍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民族。对飞来的皮鞭、子弹的无力反抗,更是刻画了那个年代社会底层百姓消极忍让、忍气吞声的性格特征。“老婆婆手持血衣控诉地主罪行”的场景,生动再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抱定“世代的仇人,千年的怨,万载的恨,今日要偿还”的老婆婆,在红军战士的引导下却给了地主改造的机会,充分刻画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性格特征。尽管民族性格的本质特征很少发生变化,但近代以来的遭遇重塑了中华儿女固有的民族性格。《东方红》创设的人物群像,展现了中国人民从消极忍让、无力抗争,到尝试反抗,到最后自力更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争到底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对苦难的忍受力被淬炼成为战胜和超越一切苦难的行动力,这些支撑中国人民历经剧烈变革,最终走出苦难、走向辉煌的性格品质,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沉淀成为中华儿女的共有精神,并在代代相传中形成稳固且具有革命属性的独特民族文化,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2]在剧烈变革中重塑的民族性格文化,它们的“共有”及“稳固”特征会显著增强。参见游品岚:《神话精神与民族个性——中希神话英雄对各自民族性格生成的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在战争结束后,国家进入相对和平的稳定阶段,在剧烈变革中重塑且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或许会沉入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但当身处相似情境,譬如置身于《东方红》创制的表演情境中,这些无意识便会随情境“重现”而显现,并因其“共有”及“稳固”特征引发各时代成员的认同与共鸣。因而,《东方红》在舞台上刻画的民族性格就像是台下观众的自我镜像。观众不仅能从中体验民族曾遭受的屈辱、感受民族性格在反侵略反压迫的不懈抗争中的重塑,还能透过剧场情境,体悟和思考自身与剧中先辈相近的思维、相像的性格等。通过镜像体验,革命历史形塑的民族精神的共有性,在“中华儿女成员”这一视角得到了普遍确认,由此也强化了个体对民族共同文化的内在认同。
四、共同情感:剧场净化中的情感塑造
国家认同植根于情感体验[3]菲利普·施莱辛格:《媒体、国家与民族》,林玮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219页。。理性的历史认知、共有的革命文化,通过切身的情感体验,更能激发成员对民族国家认同情感的投入。在剧场表演中,净化关涉的是观演者对剧场表演的情感反应以及相应行为,而情感是理解剧场净化的入口。基于剧场模仿和创制,《东方红》将表演者与观众组织在共同空间、共同活动以及共同的情感场域中,通过对“压迫→控诉→反抗→屠杀→革命→镇压→继续革命→胜利”这一完整历程的表演,激发观众体验和疏泄屈辱、悲愤、恐惧、无畏、乐观、自豪等情感,并以此引发相应的认同行为。
1.精湛表演与情感卷入
对于剧场表演而言,观众的情感体验大多由真实感引起。高度复刻革命历史的表演情境、最大限度贴近历史真实的故事情节,这都需要结合表演者的精湛表演,才能让观众从外部的观演者转化为有代入感的“内视者”,这是剧场表演激发观众产生情感体验的重要环节。
为了达到“重现革命历史,传递革命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预期目标,《东方红》除了选用全国顶尖水平的表演者,如郭兰英、王昆、才旦卓玛等[1]《东方红》的创作、排演集中了全国当时最优秀的歌舞创编、排演力量。刘秉义回忆:“都是全国各地各省的尖子,就是所有唱歌的,唱得好的都来了,所有名指挥家、所有舞蹈家里杰出的、出类拔萃的都在这!当时是全国的一盘棋,干这个活。”参见《〈国家记忆〉(周恩来与〈东方红〉系列 第二集 举国之力)》,2018 年5 月15 日,http://tv.cctv.com/2018/05/15/VIDEEZnIRhBlNRHnPbaXEvvd180515.shtml。,还在模仿创制中通过重塑理性认知、凝聚历史认同等,加深表演者对中国革命以及相应角色的认知、理解及表达。中国革命的曲折让他们体悟到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是他们奋斗的动力,这些认知与情感引导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投入表演中。以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当下的演出,成为他们践行革命精神的直接行动。因此,在排演中,表演者们完全将自己“上交”给了角色——他们以英雄先辈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行动标杆,一点一滴领会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体悟先辈们的革命情感,一遍又一遍练习台词、唱腔、舞蹈动作和表情神态,为的是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以及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带回来”。
在剧场表演中,表演者与剧场情节、角色情感相融合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剧场表演的认同。换言之,只有当表演者表现形体的真实与精神的真实相统一,才能营造出极强的历史感与真实感,让观众体验到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当观众认同表演者对角色的诠释时,舞台上的一切就被套上了“真实”的光环。在这样的氛围中,观众更容易被剧场演出的情节吸引,不由自主地向剧场情感靠近,并逐步被带入乃至沉浸于舞台创设的情境及故事情节中,直至自己的情感体验与舞台上的表演进程完全同步,即随着舞台上的革命风云变幻而同喜乐、共悲伤,在与剧中情感的相互交织中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台上台下情感共鸣的体验顶峰——观众情感卷入[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瞿白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3页。。面对卖儿鬻女的穷苦百姓和挥舞着洋鞭的“三座大山”,观众通过表演者感受到与剧中角色几乎相通的悲和怨;面对残杀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大家又被激发出同样的怒和恨;面对不怕牺牲,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大家不约而同萌生出一致的敬和爱。随着革命的发展,观众与表演者一道体会了近代以来底层人民于数重压迫下的屈辱、个体反抗时的无奈、遭遇屠杀时的悲愤、全民族奋起抗争时的无畏。最终人民胜利的号角将积极、昂扬的革命情感推向共鸣的高潮,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战士“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中被扫落,从苦难中获得新生的民众的民族情感蔓延于整个剧场,呈现“台上台下都是沸腾的群众……观众的掌声、呐喊声几乎冲破大会堂的房顶”[3]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这般情感能量集体高涨的场面,无疑是对《东方红》剧场净化效果的最好“注解”。
2.情感归属与认同行为
首演之后的《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14场,场场爆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观众就约有18万人次[4]上海文化艺术档案馆:《永远的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排演全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159页。。《东方红》成为那时当仁不让的“流量剧”,人人都想一睹它的风采。一般而言,无论艺术表演多么成功,表演者的精湛表演与观众情感卷入皆存在于演出进行时段,因为一旦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都要回归现实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剧场表演产生的净化作用可突破剧场限制,渗入观众的日常生活,并影响他们的个体行为。
公演结束后,全国各地纷纷争相模仿排演《东方红》。一时间,到处齐唱革命歌,人人争说《东方红》[1]黄华:《向天阳——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州演出二百场》,《毛泽东思想的颂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州演出的经验和体会》,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人们从昨日的苦难,唱(或朗诵)到幸福的当下,《东方红》的金曲、金句突破了剧场表演的时空限制,将“新中国从哪里来”的历史认知与民族情感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
新中国从哪里来?《东方红》在剧场表演中揭示的历史逻辑告诉人们,革命胜利不是由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英雄创造,而是源自千千万万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这不仅加深了观众对中国革命道路以及新中国的国家认同,而且唤醒了中华儿女被国家需要的归属感。《东方红》的艺术呈现,让每一位观众都深切感受到了那种“同为中国人、同被国家需要”的归属情感。这种被需要能满足一个人对归属感的最大渴望,激发个体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以及他们的主人翁意识[2]吴玉军、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被国家需要”这一意识让人们在内心构建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我的国家需要我”“我是国家的一分子”。这样的情感归属意识极大地触动和感染了观演者,并成为他们规范个体思维和产生认同行为的内在动力。
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东方红》模仿排演浪潮中,人们不仅通过传唱、表演等行为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时时处处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譬如,原本在闲暇时间“扯乱谈,打扑克”的人,在看过或者参与过单位组织的《东方红》表演后,了解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伴随着《东方红》的广泛传播,“学毛著,读报纸”成为人们在工作之余更想做的事,“讲政治,求进步”成为他们设定的人生目标,“做好革命的接班人”“每时每刻都过得有意义”成为他们内化于心的使命和外化于行的行为指南[3]《参加排演的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2日。。于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以《东方红》为代表的剧场表演将中国革命历程转化为艺术,塑造了历史与人、人与人之间贯通的共同情感,又通过艺术将这种共同情感广泛渗透至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观念和行为。在剧场表演的理论范式中,这便是剧场净化蕴含的认同力量。
五、结语
献礼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教科书及档案史实为蓝本,采用艺术方式构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之场”。它模仿创制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阶级压迫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抗争历程,再现了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历史,并通过刻画中华儿女在革命历程中淬炼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精神,展现了由抗争塑造而成的民族共同文化。《东方红》对“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执着追求,在剧场演出中引发了强烈的集体共鸣,建立了共同情感交融和表达的能量场域。其公演后受欢迎的程度及其引发的剧场外“效仿行为”,表明《东方红》赢得了当时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广泛认同。进言之,这类剧场表演既促进了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赓续和剧场艺术的时代发展,也有力地承担起了增进国家认同的使命。由此,发掘剧场表演的内容和创制形式、丰富剧场表演的国家认同塑造,不仅能在历史迭代中保存民族记忆,还能融入共同记忆、共有文化和民族共同体情感,引起国民如薪火相传般的持续关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