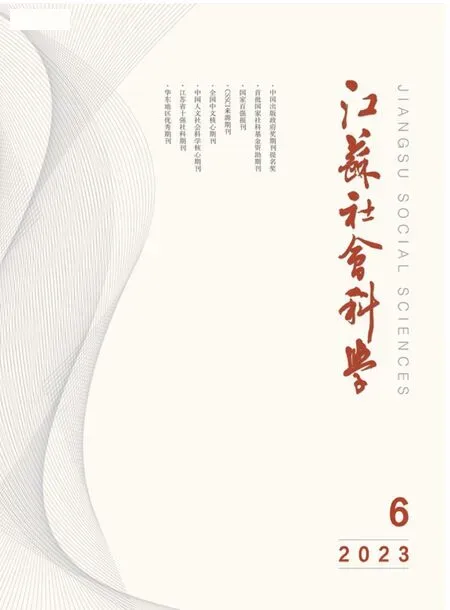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在现代转型时突出的创新性
栾梅健
内容提要 在晚清到民初期间,直接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特点的传统文人群体,在社会转型的大变动面前,没有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而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出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他们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积极创作白话小说,为现代文学的语言革新努力探求;在小说形态方面,消减传统说书人的叙述套路,尝试现代小说的结构技巧,增加心理刻画与风景描写;抛弃旧小说中忠孝节义的内容,表现人生、爱国爱民,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担当。他们温柔敦厚、含蓄内敛,在突出的创新性中还表现出和平性的特征。
对于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五四新文学工作者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1917年1月,胡适率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大主张”;同年2月,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指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1918年5月,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此同时,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茅盾、瞿秋白、郑振铎等纷纷加入新旧文学论争,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当我们在详细地研究与分析相关材料之后,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自晚清以来,中国古老的小说传统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的改造与突破、传承与借鉴、吸纳与扬弃,表现出突出的创新性。它没有五四新文学工作者那样响亮的口号、决绝的姿态,但是,它也与五四新文学工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了我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它的主要活动与重要贡献,需要我们深入发掘与公正评价。
一、白话小说的倡导与实践
区别中国小说古典与现代的最明显标志是文学语言的差异,即文言与白话的不同运用。在晚清到民初期间,小说语言经历了白话—文言—白话的几次转换,显示出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在急剧变幻的时代面前的主动面对和积极应战。
中国古代小说长期以来文言与白话并存。前者如《世说新语》《太平广记》《聊斋志异》《剪灯新话》,大多为短篇笔记小说;后者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多是话本长篇小说。在甲午战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力倡小说界革命,以图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群体或曰旧派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2]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7号。这类极富煽动性的小说革命主张,一时被奉为圭臬。重小说、倡白话,成为晚清众多文人的共同追求。
1904年,侠民在《〈新新小说〉叙例》中说:“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君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并强调“本报文言、俚语兼用”[3]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1904年第2卷第5号。。俚语,就是百姓口语,亦即白话。1906年,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小说分两大时代:一为文言小说之时代,一为白话小说之时代……白话小说亦有可观者。呜呼!为白话小说者,往往蚁视小说,而率尔为之,此白话小说之所以不足观也”[4]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小说月报》1906年第3号。。而现在则应是光大白话小说的时候了。同年,程宗启在《〈天足引〉白话小说序例》中表示,提倡新风、反对缠足,如果多用古典,卖弄才学,根本起不到启蒙的效果。于是,他坚持认为,“我想用白话的书,越土越好”[5]程宗启:《〈天足引〉白话小说序例》,《天足引》,上海鸿文书局1906年版。。以上,是晚清时期一批文学刊物主持者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他们鼓励白话创作,愿意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培育白话创作的风气。
除了刊物主持者们的呼吁与倡导,一批阐述白话理论的文艺论文也迅速出现。1907年,采庵在《〈解颐语〉叙言》中这样比较中、外文学语言的差异:“泰西言语与文字并用,不妨杂糅,匪若中国文学之古今雅俗,界限甚严也……设为白话问答之辞,形容尽致,有聊聊一二语,不叙缘起,不详究竟,而读之辄令人忍俊不禁者。语极隽妙,殊足解颐。”[6]采庵:《〈解颐语〉叙言》,《月月小说》1907年第7号。他觉得泰西小说能使读者“忍俊不禁”的原因,是采用白话写作,这正是中国作家所应补充的。1908年,一位署名为“老伯”的学者在《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中,这样表述了白话小说的重要性:“小说者,现世界风气之所趣尚也。有曲本小说,则负贩之流,得以歌曲之唱情,生发思想也;有白话小说,则市井之徒,得以浅白之俚言,枨触观念也。”[7]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6期。1912年,管达如在题为《说小说》的长篇论文中,更详细地梳理与辨析了白话与韵文的区别与功用。他说:“小说之妙,在于描写入微,形容尽致,而欲描写入微、形容尽致,则有韵之文,恒不如无韵之文为便。故虽如传奇之优美,弹词之浅显,亦不能居小说文体正宗之名,而不得不让之白话体矣。”所以他的“欲贡献于今日之小说界者:则作小说,当多用白话体是也”[8]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年第4卷第5、7—11号。。管达如将白话小说的特点说得透彻、明确。
尽管晚清时期的传统文人群体复杂而多样,但是,在主张用白话创作小说方面却很少有杂音。这是一个有着浓郁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文人队伍。当历史赋予他们重担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经世济用观念使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台前。相较而言,早在新派的胡适于1917年说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与五四新文学猛将钱玄同于同年说出“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1]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之前,已经有一批传统文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典型的创新性表现。
在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眼中,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成为革命目的已经达成的标志,小说觉民、新民、改良群治乃至倡导白话等任务已然消退,下面的工作主要在于“建设”,在于小说的雅化。“文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被发现、被唤醒。1914年,成之发表长文《小说丛话》,他如此理解文言与白话的功效:“吾尝谓中国人本有两种语言,同时并行于国中:一为高等人所使用,文言是也;一为普通人所使用,俗语是也……然以其为普通人所用之语言,故较之高等人所用之语言,思想恒觉其简单,意义亦嫌于浅薄。”[4]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3—8期。在成之看来,“吾人所怀高等之感想”,理应亲文言而远白话。同年,启明在《小说与社会》一文中也说道:“通俗小说缺陷至多,未能尽其能事。往昔之作存之,足备研究。若在方来,当别辟道途,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5]启明:《小说与社会》,《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5号。研究者决不能把这些主张理解为个人的趣味与爱好,而只有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才能洞悉其小说建设的理想。1915年,宇澄在《〈小说海〉发刊词》中认为,当此科学兴盛、时代日新的关口,文学语言必须以“隽味”为准绳,“然所谓俚俗者,要当所言有隽味有至理,不然,酒店账簿,街头市招,皆可以充篇幅”[6]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4号。。这是对一种新的小说语言的畅想,并不能因其鼓励文言而将其视为复古或者倒退。
在这方面,《小说时报》主编恽铁樵的见解较为科学与合理。“若夫词章之专以雕琢为工,而连篇累牍无甚命意者,吾敢昌言曰:就适者生存之公例言之,必归淘汰……”[7]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4号。这是就文言、骈文的弊端而言。“夫有取乎白话者,为其感人之普。无古书为之基础,则文法不具;文法不具,不知所谓提挈顿挫,烹炼垫泄,不明语气之扬抑抗坠,轻重疾徐,则其能感人者几何矣!”[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这是对白话进入文学语言的要求。他认为白话固然是小说的正格,但只有如《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白话才有可能成功。
因此,民初时期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的骈文小说创作,除了个人的趣味,其实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延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当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摆在作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男女爱情、包办婚姻、寡妇再嫁……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期。香艳绮丽、哀感顽艳、情词悱恻,正是表现当时青年男女最为贴切的文字形式。四六骈体的《玉梨魂》发表后一版再版,成为民初时期发行量最大、流行度最广的小说作品,这足以说明读者大众给予骈文小说充分的肯定。
然而,传统士子沉浸于革命成功幻想中的时间并不很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迅速粉碎了他们在小说和语言方面尝试“雅化”的企图。文言小说、骈体小说不久就偃旗息鼓,纷纷退隐。白话,重新回到尝试者的视野。姚鹓雏就是个典型,他在民初创作了《燕蹴筝弦录》《春奁艳影》《鸳泪鲸波录》等一系列中、长篇文言小说,并在回目、标题、手法等方面做出创新。1917 年,他改用白话创作长篇小说《恨海孤舟记》。他深感白话比文言更能酣畅淋漓地尽情挥洒,更能得心应手地表情达意。是年1 月,《小说画报》创刊,主编包天笑在“发刊词”中也说:“鄙人从事于小说十余寒暑矣,惟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伙而俗语鲜,颇以为病也。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言,复而为俗语之文学。”于是,从这期开始,《小说画报》全部采用白话。这一时间正好与胡适发表的提倡白话文学的《文学改良刍议》重合,而比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还要早上一年多。周瘦鹃、程瞻庐、毕依虹等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小说,在这时也均以白话的形式出现在文坛。
从晚清小说界革命时的大力提倡白话,到民初时一部分作家的崇尚文言,再到1917年前后许多作家重回白话,文言与白话交织变奏的“三部曲”记录了中国传统文人在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时留下的探索足迹。他们没有躲避,也没有后退,而是与时俱进、一路追寻。
二、小说形态的重塑与建构
白话之外,是传统文人群体对于小说形态的重塑与改造。五四时期,有些新文学工作者将传统文学斥为“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1]梁启超:《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视其为新文学运动的阻力而大加鞭挞。但是,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学群体中,尽管有的成员显现出顽固、保守、抵制的复古倾向,但大多数作家仍能顺应潮流、追赶潮流,在重塑与建构现代小说形态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首先,是传统格式的逐渐消解与引退。中国古典小说大都从话本、拟话本而来,分回标目、分章叙事,“话说”“看官”“有诗为证”“欲知后事如何?却听下回分解”等套语是常见的格式。不过,自晚清到民初,这一固定的格式逐步瓦解。晚清忧患余生(原名连梦青)的中篇小说《商界第一伟人》,直接改换传统的章节称呼和对偶回目:第一节绪论、第二节戈布登家世、第三节戈布登幼时……在这里,不用传统的“第一章”“第二章”,也不用工整对偶的回目,完全成了现代小说的章节编排与回目称呼,不能不说是大胆的改革。又如民初的《玉梨魂》和《孽缘镜》,则全部改成两字回目。前者如第八章称“赠兰”、第十一章称“心潮”,后者如第二章称“逅艳”、第十三章称“噩耗”,等等。在传统套语方面,“话说”等说书人口吻也明显减少。例如,清末二春居士的长篇小说《海天鸿雪记》,在每章结尾已不是“欲知后事如何?却听下回分解”,而是“第一回毕”“第二回毕”;民初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在每章开头已不用“话说”起兴,而是直接写道:“黄文汉这日清早动身,因到神奈川这条路,他走了多次,没有什么风景,便由品川坐电车到神奈川……”(《留东外史》第十二章)再比如李涵秋的《广陵潮》,每回结尾也是如此的新潮格式,“云麟被她这一番话,说得爽然若失,勉强笑了一笑说:‘你的话一点不错,我真佩服你。你看夜色已深,我们睡了吧。’”(《广陵潮》第六十五回)尽管在当时坚持传统的章回、对偶和套语的作家依然占有相当的比例,不过,上述小说已与纯正的现代形态小说没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是现代小说结构的尝试与运用。这是一个较为内在、隐蔽的转型,却是重塑现代小说形态更为关键的部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结构次序,往往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介绍故事与铺陈情节,而绝少采用“倒叙”的写法。线性叙事,自然是古代说书人的特点。而这个源远流长的习惯,在晚清到民初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被改变了。
设A={C1,C2,C3,C4},由定义3计算每一个覆盖Ci({1,2,3,4})的诱导覆盖Cov(Ci)并根据定义4计算Cov(A)的元素如下
1903 年,知新室主人在《〈毒蛇圈〉译者识语》中,如此比较中国古典小说与法国作家鲍福《毒蛇圈》的差异:“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1]知新室主人:《〈毒蛇圈〉译者识语》,《新小说》1903年第8号。一为中国古代小说陈陈相因之例俗,另一为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这样的比较属实可信。1914年,李定夷的长篇小说《鸳湖潮》出版,署名为鬘红女史的作者在《〈鸳湖潮〉评语》中说:“寻常小说体裁,除译本而外,大都从叙述身世开端。以序次论,自然不错,特平铺直叙,千篇一律之文字,易使读者生厌。此书从吴彤瑛一绝命书起始,实为惊人夺目之笔。彤瑛身世,后来从剑庐口里轻轻带出,便省却许多闲废笔墨。”[2]李定夷:《鸳湖潮》,国华书局1914年版,总评。这样的发现真的是令人惊喜。自晚清以来,大量翻译文学已然明显地影响我国传统文人小说创作的结构手法。
1905年,林纾在《〈斐洲烟水愁城录〉序》中说:“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其中杂沓十余国,而归氏本乃联而为一贯而下。”反观我国许多说部,“不知文章之道,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3]哈葛德:《斐洲烟水愁城录》,林纾等译,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序。。林纾的想法是因其“不期成书已近二十余种”之后的发现。我国古典小说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常会造成长篇小说结构上的松散与凌乱,《儒林外史》形似长篇、实为短篇小说集的状况,正是该种视角的弊端所致。1911年,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其“总评”曰:“新著小说,每每取其快意,振笔直书,一泻千里;至支流衍蔓时,不复知其源流所从出。散漫之病,读者议之。此书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遂成一团结之局。且开卷时几个重要人物,于篇终时皆一一回顾到,首尾联络,妙转如圜。”“[4]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版,总评。总评”指出,当时新著小说每每有散漫之习,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举一人为主”,成一“团结之局”。这与林纾的建议不谋而合。在此,吴趼人的探索与创新跃然纸上。
除了《鸳湖潮》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显带有西方小说结构影响的作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批对小说结构形式进行自主探索的小说。它们对小说艺术与技巧的尝试与思考,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1892年,韩邦庆开始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他这样表述自己对小说结构探索的企图:“全书笔法自谓《儒林外史》脱话而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则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5]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例言。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商品贸易的增加,人的交往范围迅速扩大,那种农耕文明时期单纯的血缘、亲情网络愈发适应不了现代的社会。封建家族社会的人际交往,很大程度地被限定在血缘与氏族关系之上,从而在古代小说中很难建构起丰富的人际关系。商品将全社会的人都连接了起来。《海上花列传》中“穿插”“藏闪”的有意尝试,其实正是作者韩邦庆感受到了时代转变的足音,并进而在小说结构上的自觉探索。此外,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1]颠公:《小说丛谈》,《文艺杂志》1915年第5期。,李涵秋的《广陵潮》“结构穿插,固能尽小说之能事”[2]李涵秋:《广陵潮》,国学书室1915年版,弁言。,蔡达创作《游侠外史》时的困惑是“尤莫难于穿插事迹,有骨节之联络、血脉之贯通”[3]蔡达:《〈游侠外史〉叙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4集。,等等,也都反映了他们在小说结构实践中的尝试与体会。
最后,是心理刻画与风景描写。张恨水在晚年曾经回忆过自己在创作初期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我仔细研究翻译小说……觉得在写景方面,旧小说中往往不太注意,其实这和故事发展是很有关的。其次,关于写人物的外在动作和内在思想过程一方面,旧小说也是写得太差,有也是粗枝大叶地写,寥寥几笔点缀一下就完了,尤其是思想过程写得更少,以后我自己就尽力之所及写了一些。”[4]张恨水:《我的创新与生活》,《写作生涯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因其说书人的特点,注重的是故事、看重的是情节,对于风景描写和心理刻画确实比西方小说薄弱许多。在晚清,署名璱斋的一位作者就在《小说丛话》中,发表了他对中国传统小说写“内面之事情”不足的评论:“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威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可谓知言。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语于是也。”[5]璱斋:《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7号。他在这里主要说的是心理描写。他急切希望中国文人能够迅速学习西方,以期达到更高的“小说之程度”。
对于心理描写,自晚清就有作家积极尝试。吴趼人《恨海》中描写棣华思念失散的未婚夫伯和的片段、刘鹗《老残游记》里逸云自述由男欢女爱之情证禅悟道的心理历程,都是文学研究者常举的例子,由此发现“有关人物心理的直接描写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小说上”[6]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了。学界认为,最典型的一段可能倒是《玉梨魂》第十一章“心潮”中的大篇幅描写。整章四五千字,几乎全部都是梨娘的心理活动。她“回忆夫深闺待字之年,与诸姐妹斗草输钗,簪花对镜,尔时之快乐,今日已同隔世。又回忆夫画眉时节,却扇年华,有肩皆并,无梦不双,方期白首同盟。讵料红颜薄命,今生休矣,夫复奚言?”如此的大段心理独白,绝难出现在传统的古典小说中,也是《玉梨魂》接受了西方文学影响的明证。
风景描写,在古代小说中并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因而“少得可怜”[7]张恨水:《章回小说的变迁》,《北京文艺》1957年第10期。。然而到了晚清民初时期,却得到了作家极大的重视。《老残游记》中写老残游大明湖一段,有学者认为可当《大明湖记》来读[8]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第251页。。而《剑腥录》第五章中记叙人物游超山、观梅花一段,则颇类《记超山梅花》游记[9]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第251页。。其实,周瘦鹃对于风景描写也特别看重,几乎每篇小说中都有涉及。例如,他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道:“吾夫耽静,以市居尘嚣,迁寓野外一精舍中。上下仅二三间,方春绿樾交檐,绛花蔽门,好鸟歌于树底,声长日绵蛮不断,地特幽蒨,类隐者居。屋后小园中万绿如海,间着嫣红,灿烂如锦,置身其间,如处神仙福地……”这是小说写法,又如散文笔调,显示出周瘦鹃对风景描写的在意以及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追寻。
总的来说,从叙述格式的转变到小说结构的重塑,再到对于心理刻画和风景描写的重视,到五四前后,我国传统的小说形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
三、文学主题的嬗变与现代呈现
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主题与内容,是转型期创造性转化最为内在和重要的方面。传统文人群体在这方面的探索尤为令人信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给晚清小说界革命后迅猛出现的谴责小说下过一个评语:“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1]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这一段评价不算高,甚至略带贬义,自然也就影响到后来文学史对于谴责小说的理解。不过,如果回到“小说”刚刚由闲书被推上了文学正宗地位的20 世纪初,如果想到那么一大批传统文人群体刚刚由社会的边缘群体被赋予了改良群治、启蒙的重任,那么,我们便能理解谴责小说不能够如过去讽刺小说那样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原因了。这好比新官上任三把火,当这些原来一直被视为边缘、小道的小说家们,忽然被要求扮演经世济用、救亡图存的角色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内心“入世”的冲动,努力接手过去诗人、散文家所承担的使命。
曼殊在《小说丛话》中曾经这样比较过中西小说在取材上的差别:“盖吾国小说,多追述往事;泰西之小说,多描写今人。”[2]曼殊:《小说丛话》,《新小说》1904年第11号。我国传统小说因其“小道”的地位,在主题上大都表现的是忠孝节义,在取材上常常聚焦过去的事情。而现在被推到历史前台的小说,自然必须关心现实,注重“在场”。因此,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晚清谴责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常常在小说中情不自禁地跳出来直接发表议论。“作者似乎有一股掩不住的急切,想要直接贡献己见,唤醒国民。”[3]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比如颐琐在小说《黄绣球》中说:“在本书是辅佐之文,亦是夹叙夹议之法。”[4]颐琐:《黄绣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3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辅佐”之文,是说创作的意图本为改良群治而起,而“夹叙夹议”则是为“辅佐”而生。这是谴责小说家的一种普遍心态。现在的“小说”如古代的诗文一样,应该“载道”了,“有用”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休闲、娱乐了,而“夹叙夹议”则是古代诗文的久远传统。议论文、说理诗,是中国传统诗文的一大特色,也是“载道”的主体。于是,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运用起这种独特的小说文体。而且,末世之晚清,千疮百孔、丑态百出、腐朽至极,面对如此世事,刚刚被推到正宗位置的小说家们,势必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于是讽刺以至于谩骂便自然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风格。用纯正的小说理论衡量,“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自然是缺点,然而对于才被赋予改良群治、新民、启蒙职责的这批传统文人来说,这难道不正是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心的具体表现吗?尽管有些笨拙,但也是用心良苦。
自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民初文坛一时之间泛滥起哀情小说的潮流,卿卿我我、哭哭啼啼、鸳鸯蝴蝶,充斥着大报小刊,也引起了后来研究者的批评与指责,认为哀情小说是复古、落后与反动。不过,在学界看来,事情也并不是如此简单。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时的许多维新志士误以为政治问题已然解决,而在民初最为社会所关注的事情便是男女爱情与婚姻大事。一方面,西方思潮与翻译文学的影响使得青年人惊叹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愚昧与荒唐。另一方面,强大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守旧习惯势力,又顽固地阻碍着年轻人的追求,造成了一幕幕的爱情悲剧。著名哀情小说家徐枕亚在当时的感觉是:“率皆哀感缠绵,情词悱恻,呕心作字,濡血成篇。彩毫在手,操情天生杀之权;孽镜悬胸,摄男女悲欢之影。令读者疑幻疑真,不能自己;斯人斯世,为唤奈何?”[5]徐振亚:《茜窗泪影》,国华书局1914年版,序言。悲情、惨情、痛情、忏情、悔情、苦情、哀情……也只有在民初时期,中国婚姻爱情作品中才会出现如此多的愁肠惨况。这不仅仅是当时作家的故作矫情、博人眼泪,而是对特定社会背景的必然的文学反映。徐枕亚的感慨“斯人斯世,为唤奈何?”确是道出了实情。
因此,当民初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描写婚姻爱情的悲剧性遭遇时,并不是消极避世、颓废荒唐、趣味低下,而是积极地拥抱时代、参与时代与表现时代的结果。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吴双热的《兰娘外史》《孽缘镜》、李定夷的《霣玉怨》、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花开花落》、天虚我生的《玉田恨史》、王钝根的《红楼劫》等,都留下了当时青年男女在情感世界的种种惨状,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声音。如果说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中,一批谴责小说家走向了前台,勇猛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社会弊端进行了抨击,那么在民初文坛,另一批传统文人群体则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对于中国守旧的封建道德与落后陋习加以揭示和批判。只是《玉梨魂》等发表后产生的巨大市场效应,使得一些作家一哄而上,乃至胡编乱造、煽情作假,败坏了言情小说的声誉。1914年,程公达在《论艳情小说》一文中痛心地表示:“近来中国之文士,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以放荡为风流,以佻达为名士……岂以此为卖弄文墨,足以自豪耶?抑以此败坏风俗,唯恐不速耶?”[1]程公达:《论艳情小说》,《学生杂志》1914年第1卷第6期。这种倾向,确实在当时一些作家及其作品中存在,也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迅速被读者所抛弃的原因。
不过,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格调纯正、正直正派,永远是这个群体的主流。1915年,《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如此表示:“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因此“言情小说。又安可少哉?”然而现在言情小说泛滥成灾、虚情假意,于是,他决定不再刊发此类作品:“此敝报爱读者,所以有言情小说淘汰净尽之说也。”[2]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7号。同年,《小说大观》创刊,主编包天笑也这样说道:“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诲盗导淫之风。”[3]包天笑:《创刊词》,《小说大观》1915年创刊号。再加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的时局影响,大致从1915起文坛上言情小说热大幅降温,而代之以爱国、反帝、关心民众疾苦的小说。被誉为哀情小说巨子的周瘦鹃,这时创作了《祖国重也》《为国牺牲》《祖国之徽》《双十节之哀音》《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大量的爱国小说,主题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包天笑的《战线中》《牛棚絮语》《天竺礼佛记》等篇,或表达爱国思想,或回忆早年生活,或关心民间疾苦,也都清新自然,不落俗套。这种转变在叶楚伧、姚鹓雏、陈蝶仙、范烟桥、张毅汉等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明显表现。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茅盾的一段感触颇为引人注意:“在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有‘赶潮流’了,他们不再老是某生某女,而居然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4]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吗?》,《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1号。其实,不只是在五四以后,在五四以前,传统文人已开始“为人生”“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
“传统文人”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特殊群体。他们中固然有守旧、颓废、落伍甚至反动的分子,然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爱国爱民、不甘落伍、与时俱进,这是他们的主流。在晚清到民初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他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出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从晚清的谴责小说到民初的言情小说,再到1915年以后主动创作爱国小说、反映底层百姓生活的小说,一路走来,其创新性是突出的,也是进步的。
而且,在这场现代性的转型中,中国传统文人群体的创新是和平的,没有攻击性的。除了梁启超在《小说新民论》中表露过大声的倡导与强烈的呼喊,后来他们的探寻与努力都是在各自的理论和创作中完成。他们温柔敦厚、含蓄内敛,默默地尝试着、追求着。其间也难免遇到过一些挫折、出现过一些反复,但是,最后在五四前后,也似乎是与新文学工作者共同完成了小说的古今演变,走上了一条文学现代化的道路。其中突出的创新性与和平性,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