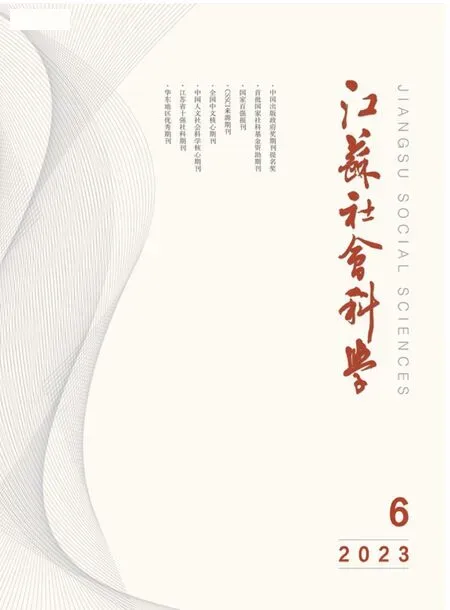柳如是“景观”的塑造与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变
张娜娜
内容提要 晚明人性解放思潮催生了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倾向和“女务外学”的女性观,明清易代的政治失序更激发了时人对“女英雄”的想象。在此背景下,柳如是以名士的风神气度及书写模式跨越性别界限,扩大性别空间,成为男性世界中的文化“景观”。男性士人在审视柳如是的过程中营造了“闲赏”的美感生活和情艺文化,并在“名妓-名士”的转喻系统中,借女性声音进行自我人格设计,彰显“深情”与“忠君”的文化理念。晚清民国,知识分子重新塑造柳如是“景观”及其背后的国族记忆,并融入了革命话语、女权思想和“恢复中华”的民族精神。柳如是同易代士人的相互“观看”,建构涉及性别互动、士人出处、隐喻诠释等问题,呈现了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变。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柳如是赞赏有加,认为她作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能有“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第75页。,实属难得。从明季诗词、野史到晚清的报刊、小说,柳如是被不断地塑造、建构,成为“侠女名姝”“文宗国士”的化身。学界关于她的研究涉及其诗词创作、性别意识、社会交往等[2]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以钱柳姻缘为线索,考察明清士人交往与生存境遇;孙康宜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围绕“情与忠”的话题考察了诗体、词体之变奏,以及柳如是的精神世界。其他相关代表性研究还有方秀洁,魏爱莲的《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值得关注的是,晚明时期,柳如是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第75页。,是男性士大夫经营情艺生活和彰显文人文化的盟友,也是他们进行自我人格设计的媒介。时至晚清,柳如是画像再度为知识分子观摩和题写,他们借此戏拟、模仿晚明历史,诠释社会、性别问题并展开对自我的检视与反思,反映出晚清民初“恢复中华”的民族精神和女界革命的“维新”思想。在“名士-名妓”这一转喻系统中,柳如是成为男性视域下的一道文化“景观”,而面对景观时,人们总会“摄取自己以为最主要、最具代表性、最符合自己需要的印象”[1]葛剑雄:《序》,安介生、周妮:《江南景观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因此,作为文化“景观”的柳如是,始终处在复杂、动态的变量联系之中,这些变量包括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因素[2]伊恩·D.怀特:《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王思思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透过柳如是“景观”被观看、被建构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晚明至晚清的文化嬗变。
一、双性名士:柳如是“景观”的生成
晚明时期,双性审美特质和“女务外学”之说备受关注,才女品藻更呈现出名士化倾向[3]比如,毛奇龄称徐昭华“不是小鬟频乞试,那知闺阁有陈思”;女诗人吴琪尤好大略,被誉为“岭上白云朝入画,樽前红烛夜谈兵”;钱谦益称沈婉君诗“无脂粉气”,“林下之风,闺房之秀,殆兼而有之”,都凸显了女性的名士风韵。。陈继儒概括道:“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4]秦望龙编著:《清言小品菁华》,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也就是说,跨越性别、社会身份约束的言行,成为文人士子欣赏的“有致”生活面相。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构成女性身份的两个因素是其内在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5]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页,第63页。。对于柳如是来说,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空间中,她“必须观察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人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6]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页,第63页。。柳如是“性机警,饶胆略”,她时常着男装,在江南一带清游、雅集,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她谈兵说剑、豪宕自负,有巾帼须眉之论;她用男性书写模式感喟国变穷途,以刀剑意象表达家国情怀,是“竞雄”[7]与柳如是身处同一时代的徐灿、刘淑、顾贞立、李因等才女都有反映世末乱离、忧思国难之类超越闺阁的言语。柳如是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以北里章台之身而具复楚沉湘之志,集名士与名妓身份于一身。的典范。一方面,内在的“观察者”身份促使柳如是按照男性审美调整自己的言行,获得男性的青睐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以柳如是为代表的女性文人也在思考己身与世变之关系,挑战了性别界限、拓展了性别空间。
1.行旅文化中的漫游与造景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业繁盛。谢肇淛说:“夫世之游者,为名高也。”旅游活动不仅开拓心胸、陶铸性灵,更是士大夫社交、娱乐的方式,故被誉为“名高”之事。士大夫甚至打造专属的“游道”,以独特的品味来彰显自身的文人身份。柳如是离开归家院之后,如同诸多名士一般,乘画舫辗转于吴越之间。她在船上读书、写字、赋诗、作画,广交才媛名士。船,是一个浮游的、无拘束的存在,无限性是其文化特征。画舫,则是柳如是身份的写照与隐喻,她同画舫一起,成为江南山水中的一道“景观”。
柳如是名声大噪于崇祯五年(1632)。是年,她赴松江畲山,为陈继儒贺寿。陈氏所居之处,亭榭数座、古梅百株。柳如是身量小巧、束腰紧身、亭亭玉立于“晚香堂”中,成为陈子龙、宋辕文、李存我等名流“凝视”的对象。陈继儒作《赠杨姬》,诗歌“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镜台”[8]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五,明末汤大节简绿居刻本,第4页。,写的是柳如是在周道登家的不幸遭遇。“颜如花”“对镜梳妆”既是闺怨诗的传统元素,也是柳如是“被观察者”身份的表现。
崇祯十一年(1638),柳如是赴杭州汪然明之邀,登入画舫“不系园”,这是众多骚人韵士雅集的场所。她“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9]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寻觅“殷勤为其启金屋者”。红妆翠微间,柳如是与西湖烟水融为一体,成为众人倾慕、游观的对象。汪然明写柳如是:“明妆忆昨艳湖滨,一片波光欲荡人……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访仙源违咫尺,几湾柳色隔香尘。”[1]汪汝谦:《春星堂诗集》卷三,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当时,需得身为“名流”“知己”或“美人”,才能够进入“不系园”,柳如是兼而有之,甚至还是神女和侠女。人们往往通过景观想象构建与事物的关系、重塑自身的社会角色。男性文人争相“观看”柳如是,或从其身上看到美色而希望贮之金屋,或于其身上投射自身理想并心生敬意。
柳如是游赏西湖的作品主要收录在《湖上草》中。杭州浓缩了晚明流韵,聚集了各方游客,而女性既是西湖景观的一部分,又是西湖景观的制造者。柳如是写道,“西泠月照紫兰丛,杨柳丝多待好风”[2]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第67页,第71页。,其中,“紫兰丛”“杨柳丝”指名媛才女;“邀人画舫留鹦鹉,游女新绫织凤凰”[3]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第67页,第71页。,则写佳人盛饰出游的场景;“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4]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第67页,第71页。写桃花得西湖美人气韵而分外娇媚,为世人激赏。可见,女性在杭州气韵的塑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琴诗为伴、漫游西湖是柳如是与一众才女有意识的举动,“她们显然深刻地体察到自己身为女性,出现在杭州西湖,对这个城市的风格与景观有多大的影响”[5]胡晓真:《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可以说,她们既在赏玩,又在造景。
2.跨越性别的“文化展示”
马克梦指出,“所谓的才子佳人是包含彼此的,其中一方具有另一方的相貌,或呈现另一方的气质,男性可以把心目中更为完美的自己投射给女性”[6]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王维东、杨彩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在这一互映性结构中,柳如是从着装到谈吐皆呈现出“学士化”“名士化”的风神气度,这是一种跨越性别的“文化展示”。《河东君小传》这样记载柳如是:“幅巾弓鞋,着男子装,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7]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着男服迎客在当时并不少见,柳如是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独特的气宇风神与怀抱胸襟,这促使她成为一道“文化景观”,乃至男性士人心目中更为完美的性别形象。
柳如是归钱谦益后,亦“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8]黄承增辑:《广虞初新志》卷二六,嘉庆癸亥寄鸥闲舫刊巾箱本,第14页。,被称作“柳儒士”。钮琇在《觚剩》中称其“有时貂冠锦靴,或羽衣霞帔,出与酬应。否则肩筠舆访于逆旅。清辩泉流,雄谈锋起,即英贤宿彦,莫能屈之”,钱谦益直呼其“高弟”“良记室”[9]钮琇:《觚剩》卷三,康熙壬午临野堂刊本,第6页。。她流连文宴,接席雄谈,俨然儒士、名士。王国维曾题写柳如是《湖上草》:“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10]谷辉之辑:《柳如是诗文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版,第256页。柳如是带给男性文人视觉与心理层面的冲击,他们认为“柳如是所拥有的,甚或多于自己,于是出于对己身‘匮乏’的焦虑,更渴望着柳如是”[11]严志雄:《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8年版,第45页。。因此才说,柳如是是“景观”,但又逸出“景观”。
当然,柳如是的男子气度是由内而外的,不仅表现在着装打扮上,更渗透在其个人性情、文化艺术风格之中。她具君子气,以经世自任、以天下为务,喜纵横之术、具文才武略。她的草书风骨嶒峻、笔力雄健,见知于当时,被程孟阳评为“书势险劲”,亦被清人翁同龢誉为“铁腕拓银钩”“奇气满纸”。几社名士常常宴集于陆氏南园,这个文学兼政治团体宴集具有时事座谈会的性质。柳如是多次参加南园雅集,经名士政论熏习,其本人亦被视为社员之一,其“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观念逐渐成熟。
3.男性书写模式和权力想象
世变之际,女子与国难的关系是男性文人一再吟咏的话题。反之,对于现实中的女性来说,男性亦是她们自我定义的一种方式。正如华玮所言,“‘拟男’在为她们突破发声困境的同时,还适可满足她们的‘权力的想象’(illusion of power)”[1]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147页。。当时女性文人的家国之论并不罕见,而柳如是除了以男性口吻营构勇武的自我形象,还采用男性的书写模式,甚至有《男洛神赋》这类直接“凝视”男性的作品。
柳如是《戊寅草》颇有云间派风味,而云间派身为几社旁系,本就担负着匡时济世的使命。柳诗超旷凌空、宏达微恣,被陈子龙赞为“绝不类闺房语”,认为其“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2]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此论体现出柳氏诗文对男性书写空间的介入。“夏服左弯从白马,铙歌清彻比乌弹。千金元节藏何易,一纸参军答亦难。我欲荥阳探龙蛰,心雄翻是有阑珊”[3]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展现了她心雄万夫、探取龙蛰的豪情,并意欲成为一名身负弓箭、驰骋疆场的英武之士;“长空鹤羽风烟直,碧水鲸文澹冶晴”[4]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中,她从直升的烽烟和远飞的仙鹤以及波涛与鲸鲨中,预见战事兵祸的到来,这般慷慨正见其性别身份的游移以及对精神自由的追寻;在后金犯边、国势阽危之际,她赞颂、呼唤“杰如雄虺射婴茀,矫如胁鹄离云倪。萃如列精俯大壑,翁如匹练从文狸”[5]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般抗敌救国的英杰;“丈夫虎步兼学道,一朝或与神灵随”[6]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被《神释堂诗话》评曰,“有雷电砰然、刀剑撞击之势,亦鬟笄之异致矣”[7]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页。,体现的正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期许。
柳如是超越婉约秀雅的女子风韵,表达世变当头,志同道合的共同悲感。比如,文人常借英豪庙碑书写忠臣、英雄的悲剧命运。柳如是承袭这一表达传统,写道,“当年宫馆连胡骑,此夜苍茫接戍楼。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8]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以田横五百士宁死不屈的壮举激励世人,呼唤孤忠劲节之士为国效力。时人评此诗:“脱尽红闺脂粉气,吟成先吊岳王祠。”[9]谷辉之辑:《柳如是诗文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版,第256页。再如,她歌颂于谦“意气吞龙荒,事业高云阁”,因其悲剧命运而发出“洒泪空夕阳,英风竟安托”的感喟,并于西湖之滨“恸哭霸王略”[10]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24页,第24页,第30页,第30页,第73页,第75页。。此外,中国男性文人常以“女洛神”作为自己寤寐求之的理想女性形象,柳如是的《男洛神赋》则“颠倒传统情诗的基桩”,写自己访求情郎的过程。她描摹“男神”风姿,“泯灭男女诗人的传统界限,打破阳刚阴柔的定见”[11]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李奭学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总之,柳如是“牵动的欲望纠结、权力运作,实则远远超过这种稍嫌‘简略’的观看之道”[12]严志雄:《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8年版,第44页。。一方面,在男性文人眼中,柳如是游走于社会伦理规范的边缘,其色、艺、才、情满足了男性的文化需求,她士大夫般的气节操守、胸襟境界、人文风采亦是男性文人自我理想的投射。另一方面,在忠明的男性眼中,名妓的命运是国家兴衰的隐喻,正所谓“名姝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13]李中馥撰,凌毅点校:《原李耳载》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而对于男性的观看,柳如是或许意识到,以男性装扮和口吻抒情言志可适度缓解“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1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的焦虑。同时,柳如是对“名士”形象的塑造也使自己远远逸出“景观”的范畴。
二、柳如是“景观”与晚明文人文化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精英阶层在科考及第或践行儒家德性之外,追求纵乐和炫耀性安逸,刻意营造美感生活。赏玩古董、珍藏书籍、游览名胜、选妓征歌等都是士人经营其美学生活的重要活动,围绕着选妓征歌,出现了独特的女色品赏文化。在此美学品味与文人文化的建构中,柳如是等明季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明中后期商人崛起的背景下,男性文人在观看柳如是“景观”的过程中,建构了与富商巨贾附庸风雅相区分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男性士人借用柳如是之类的女性声音进行自我人格设计,呈现易代之际自我身份的复杂性。
1.“闲赏”之乐:美感生活的悬想与经营
晚明时期,传统社会的“四民分业”逐渐模糊,各阶层的经济、文化行为趋同,尤其是商人的崛起,对文人精英群体的身份和地位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晚明文人致力于构建一种不流俗的、超越官能的“看妇人的方法”。屠隆曾言:“登山临水,旷望俯仰,必思佳丽。思佳丽必营楼台,营楼台必及声色。嘲风吟月必耽光景,耽光景必动才情,动才情必生欢恋。”[1]屠隆:《鸿苞集》卷三十八,茅元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由山水之美到佳丽之色,再到营建楼台,兼收山水与声色,他们悬想和经营具有脱俗之美的生活,乃至构造“色隐”的文化空间,从而安顿个人的情感和生命。
晚明士人将柳如是和建筑、山水等融为一体,塑造出一个被认知、想象的“女性空间”[2]巫鸿认为:“女性空间是一个空间整体——是以山水、花草、建筑、氛围、气候、色彩、气味、光线、声音和精心选择的居住者及其活动所营造出来的世界。”参见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页。。钱谦益为柳如是建成绛云楼,金石文字、鼎彝环璧、法书名画等充牣其中,柳如是于此“俭梳靓妆,湘帘棐几,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3]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第142页。,给观者呈现的是一道颇具意味的文化景观。类似的,徐锡胤写柳如是“舞燕惊鸿见欲愁,书签笔格晚妆楼”[4]谷辉之辑:《柳如是诗文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版,第192页。,陈文述也曾描绘道:“金石千秋书万卷,琳琅都置妆台畔。流水亲调绿绮琴,墨香小试红丝砚。”[5]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第142页。书签笔格、金石书卷、琴棋墨砚与柳如是一并构成博学文士、名士、居士的建筑空间和文雅世界。文房清玩与柳如是近乎成为一组相互转喻的概念。卫泳所作《悦容编》专论如何借美人营造美感生活,称“美人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能参透者“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6]虫天子编,董乃斌等点校:《香艳丛书》第1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第32页。。柳如是众美兼备,为文人开启了美学的、感性的、超脱的生活意境。
另外,晚明《燕都妓品》《莲台仙会品》之类的“花案”树立了品赏美色的标准,呈现“脱俗化”“传奇化”的特征。文人“描摹想象,麻姑幻谱,神女浪传……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7]冒襄:《影梅庵忆语》,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这里的美人想象及“才子佳人”传奇乃明清文人文化之特色,柳如是便被塑造为男性寤寐求之的“神话”女性。陈子龙《采莲赋》视柳如是为宋玉的“神女”、曹植的“洛神”以及《游仙窟》中的“女仙”。程嘉燧的“翩然水上见惊鸿,把烛听诗讶许同”[8]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页,第126 页,第147页,第147页。,偈庵的“杯近仙源花潋潋,云来神峡雨濛濛”[9]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页,第126 页,第147页,第147页。,亦将柳如是视作存在于洛水之上、桃源之境的传奇女性。在《东山酬和集》中,朱云子称“借问蓝桥今共室,何如鄂渚昔同舟”[10]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页,第126 页,第147页,第147页。,林若抚也道“谁知宿世蓝桥侣,即在今宵谷水舟”[11]柳如是撰,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页,第126 页,第147页,第147页。,柳如是又化身为《太平广记》中的仙女云英。他们在观看柳如是“景观”的过程中,进入神话世界的悬想。卫泳在其书中道:“古未闻以色隐者,然宜隐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须知色有桃源,绝胜寻真绝欲,以视买山而隐者何如?”[12]虫天子编,董乃斌等点校:《香艳丛书》第1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第32页。晚明文人通过柳如是建构了一个淡化名利、安置自我的美感世界和桃源之境。
2.身份认同:酬赠唱和中的相互建构
“景观”是观者与被观者相互作用而造就的结果,审美观看不仅是对被观者生命存在的探寻,也是观者自身生命状态的转化。就柳如是而言,男性士人通过对其生命风流的审美发现,进一步打开自身的存在境域。马克梦认为这种现象彰显的是“才子佳人”式的“相似性与互映性”,并且在“对诗”,即唱和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王维东、杨彩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男性文人在同柳如是的诗文往来中建构自我身份,并在文人群体中传播、确证,而柳如是也在成就“他者”的同时彰显自我人格与志向。
程嘉燧《耦耕堂存稿》中的《朝云诗》八首皆为柳如是而作。“香泽暗菲罗袂解,歌梁声揭翠眉颦”[2]沈习康点校:《程嘉燧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页,第8页。中借用淳于髡“长夜之饮”中“男女同席,履舄交错”的场景;“绝代倾城难独立,中年行乐易离群”[3]沈习康点校:《程嘉燧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页,第8页。隐含着谢安携妓和卓文君的典故。程嘉燧描摹的是同柳如是相处的情境,也在另一个层面将己身与谢安、淳于髡、司马相如之类的风流才子类比。陈子龙和柳如是的情诗对唱是一个共享事典、语典的象征隐喻系统,是双方相互观看且不断内省的结果。柳诗“紫兰荫飞盖,绛节焕华区”[4]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0页,第125页。期望陈子龙成为持红色符节的使臣成就一番伟业,自己则化身“紫兰”,为其荫护华盖。“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5]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0页,第125页。以轻生重义、急人所难的游侠相期许,陈子龙则以“不然奋身击胡羌,勒功金石何辉光”[6]施蛰存、马祖熙标校:《陈子龙诗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酬答应和。柳如是赠予友人朱茂暻的《朱子庄雨中相过》,是以塑造“他者”形象进行自我表达的案例。诗中称朱氏“才气甚纵横”“射策凌仪羽”“窈窕扶风姿”,这是对友人安攘之才的景仰,也是她个人对英雄志业的向往。“天下英雄数公等,我辈杳冥非寻常。嵩阳剑气亦难取,中条事业皆渺茫”[7]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0页,第125页。更是将朱茂暻引为同调,她意欲成为男性群体中的一员,自觉或不期然地投合晚明士人钦羡的“侠女”情节。
柳如是初访半野堂,赠钱谦益诗曰:“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8]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0页,第125页。她将钱谦益比作马融、李膺和谢安。当时,钱谦益在会推阁臣中获罪罢归,其遭遇与李膺相似,正如谢安一般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外,钱氏一向自矜博探佛藏、洞达禅理,故柳如是将自己比作捧瓶持拂、供奉菩萨的侍女。柳如是赠诗可谓“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句句道出对钱谦益的个人期许。钱谦益也在奉和诗中称柳氏为卓文君,俨然自视为风流多才的司马相如了。
钱柳二人定情之后,《东山酬和集》中有诸多文人唱和之作,他们以诗语为媒,将晚明情观中情欲的底蕴与美学、文化元素交相渗透。男性士人在与柳如是的两相唱和中相互建构,并彰显了融合诗艺与爱情的情艺文化。这些酬唱交织着两性之间的声音、态势、美学观与权力意识。柳如是并非被动地接受男性士人的“凝视”,她在时而“男性化”的角色以及红粉黛妆的女性魅力之间切换,从而获得钱谦益等异性的认可,男性士人也通过对柳如是的殷勤推崇以确认自我。
3.移情作忠:女性声音中的自我人格设计
晚明时期,海内鼎沸,然江左士大夫益事宴游,“其于征色选声,极意精讨。以此狭邪红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时喧誉,独推章台”[9]钮琇:《觚剩》卷三,康熙壬午临野堂刊本,第6页。。一方面,他们从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身上看到自身才略的无处施展,以及国族命运的风雨飘摇。另一方面,以女性为基础的情艺的经营成为忠君爱国的表现,即周铨所道:“情之所在,一往辄深:移以事君,事君忠;以交友,交友信;以处世,处世深……古未有不深于情,能大其英雄之气者。”[1]朱剑心选注:《晚明小品选注》,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14页。柳如是正是这一“情”与“忠”之社会思潮的参与者、建构者之一。
王朝覆灭以后,钱谦益等易代文人频繁追忆和一众名妓于湖山间流连诗酒的生活。胜国沧桑之艳迹,承载着晚明的文人文化,激发着文人的故国怀想,是钱谦益等文人士大夫在晚明生活的象征。于钱谦益而言,柳如是的豪侠之风、英雄之气与忠君爱国不断地促使他反观自身,是其转变为爱国“遗民”的关键助力,也是其一再洗刷污名、确立抗清志士身份的“符码”。钱谦益追怀他同柳如是旅居杭州的生活,写下“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会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2]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第91页,第9页。。故地重游,“空王法”与“肠断前尘”表示明王朝以及故明臣子身份的消逝。“杨柳”是柳如是的代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攒眉”“杨柳桃花应劫灰,残鸥剩鸭触舷回”[3]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第91页,第9页。等语抒发的是兵燹之后的“残山剩水”之感,以及对柳如是所象征的晚明生活的缅怀。顺治四年(1647),钱谦益因“黄毓祺案”下狱,柳如是孤身北上斡旋。钱氏记述道:“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4]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第91页,第9页。正是在此番遭际的影响和柳如是的感发下,钱谦益试图以新“遗民”身份开展复国运动。
钱谦益曾于晚明时期与柳如是同访韩世忠墓,二人追念梁红玉“佩金凤瓶,传酒纵饮,桴鼓之声,殷殷江流喷沸中”[5]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四(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6页。,相与感慨良久。钱谦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七写道:“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堕粉英雄气,剩水残山俯仰间。”[6]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页,第706页,第666—667页。他们以韩世忠、梁红玉自期,希冀“中兴”。沈璜与孙永祚在《东山酬和集》序中所道“桴鼓军容,尚资纤手”“援桴贾壮于从军”之语都用梁红玉事。柳如是在晚明时期就已是文人笔下“情与忠”的符码。入清后,钱谦益写下“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7]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第10页。,以梁红玉击鼓助战,暗示自己像韩世忠阻击金兵一样反清复明。柳如是赴海上犒劳抗清义师,资助神武军等事迹确为忠烈之举,钱谦益亦一度将其视作爱情与政治的联结点。钱诗中“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8]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页,第706页,第666—667页。“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9]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第10页。之语都是对柳如是壮举的感佩,而在“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10]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页,第706页,第666—667页。句中,钱谦益俨然模糊了二人之间的性别界限,他以英雄自期,更将柳如是视为同道中人[11]张娜娜:《明清易代士人“诗史”书写中的自我建构——以钱谦益为中心的探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三、隐喻晚清:钱柳故事的再度演绎
两三百年后的晚清民国,柳如是已化作荒庄拂水之畔的一座香坟,但作为文化“景观”,她的符号价值仍在被持续地征用、重塑、建构。知识分子目睹柳如是画像[12]柳如是有多幅画像存世,据陈去病记载:“柳夫人风流放诞,妩媚绝世。一时思慕者众,争图形貌,颇有团扇放翁之致。”参见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想到国士名姝东山酬唱的明末风流,感受到一代国手裹挟于舆论纷争的生存困境,以及九州尘烟、美人殉主的凄惶,他们因此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柳如是的题像诗。一方面,知识分子围绕钱柳故事,以“隐微”写作的方式,借“诗史”“隐语”戏拟历史,映照当下。另一方面,钱柳二人的生死抉择是“男降女不降”[1]“男降女不降”史事及相关研究参看夏晓虹:《历史记忆的重构——晚清“男降女不降”释义》,《读书》2001年第4期。之说的范本。这一说法在明季关涉满汉文化冲突和“华夷之辨”,在近代则与“民族主义”相融合,表面上看是“种族之见”,实际则是以“民族主义”抵制异族侵犯。他们重塑柳如是等明季女性和钱谦益等士人的形象,期望以女子的坚贞刚烈唤醒柔弱游移的男性,表达对国族复兴的期望与对尚武时代的神往。
1.钱柳并称与“隐微写作”的可能
中国古典诗学向来有“隐微书写”[2]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提出,“隐微写作”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失去言论自由的作者会以特殊的方式把情思隐藏于字里行间,这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即“隐微写作”。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的传统,钱钟书说文人常常“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以“咏史”影射时事,以“古意”诉说“新愁”[3]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虽然在政治压迫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烟幕弹”未必能避害,但是在“主文谲谏”的基础上,对于表达变局之下诗人思想之矛盾与张力等方面用处不少。钱谦益素有“诗史”诗人的称号,其前朝遗老的身份与心态尤其复杂,且与柳如是暗中从事复明运动,故其诗歌语言“灯谜交夹,市语杂出”。因此,时人在对女主角柳如是故事展开想象时,通过“古典”“今典”的映照,借用二人的姻缘以及钱谦益创作中的“隐微写作”进行时代言说,为“才子佳人”的“诗史”叙事,额外增添了末世的悲怆感以及“复国运动”的革命色彩。
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借晚唐史事书写当下,而晚清文人亦以钱柳所生活的晚明隐喻晚清,进行古今交叠的“诗史”写作。李贻德的《题河东君小像后》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钱柳二人的东山酬唱写到“忽传噩耗破金瓯,万岁山头苑树秋”的国变。“供养珍同西竺书,飘零劫比《东京录》”将柳如是故事视为对“兴”的缅怀与对“亡”的警戒,称之堪比遗民书写典范的《东京梦华录》。“只怜绝代佳人貌,谁识千秋国士心”[4]李贻德:《揽青阁诗抄》卷下,同治五年(1866)刊本,第32页。诗句中,此“国士”之心指柳如是的忠贞孤烈,亦是诗人当下心境的夫子自道。钱文选写下“义师鼓舞非甘后,异族驱除誓必先……董狐史笔存真意,烈女忠臣一例编”[5]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二(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其中,“董狐史笔”将柳如是事迹纳入历史的范畴,此时“异族驱除”的对象不再是满清,而是环伺中国的西方世界。丁传靖有《柳如是妆镜为曹君直题》一篇,“胜国沧桑艳迹多,残脂剩粉照山河”中的“残脂剩粉”是对国变后“残山剩水”的隐喻,亦是对时局的隐忧。“珠冠星灿蛾眉笑,玉辔风驰雉尾飘”是撮合野史笔记而成,而“一样苍凉可奈何”所道既是晚明,更是晚清[6]丁传靖:《闇公诗存》卷二,民国乙亥白雪庵刊本,第11页。。
在接受史中,钱柳二人往往“捆绑”出现、相互映衬,表现之一就是文人化用钱谦益诗语题写柳如是小像。入清后,钱谦益的诗歌隐语颇多,借之进行集句创作正好可以塑造迷离惝恍的诗境,影射当下。光绪朝局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之后已然失控,光绪被软禁、庚子事变等一系列事件昭示着封建王朝的式微。李葆恂在《题河东君儒服小像集牧斋句》中摘取钱谦益“秋风纨扇是前生,坐看人间沧桑更”“绿尊红烛都如昨,都是昆明劫后人”“洞房银烛辟轻寒,历历残棋忍重看”[7]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等句,大概是世变的焦虑、分裂引起李葆恂心中山雨欲来的不安,而生出“昆明劫后人”[8]释慧皎言:“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后泛指遭受巨大灾祸或变故之后的余烬。参见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页。之感。“揽镜端详应自喜,为他还着汉衣冠”是钱谦益隐秘从事复明运动后对自己“汉人”身份的审视,而诸如李葆恂之类的晚清文人又何尝不面临着满汉文化冲突,以及自我身份界定的问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红豆”意象。红豆山庄曾是钱柳秘密反清的据点,钱谦益以“红豆”为诗集名,并有多篇歌咏之作。实际上,“红豆”除了象征钱氏和柳如是之间的爱情,在明“遗民”诗中还表示对故国的思念,隐含恢复朱明王朝的心曲。“美人”“爱情”“红豆”“南国”“中华”等意象融合在一起,成为时人表达末世感伤以及复国意念的媒介。晚清潘遵祁“棐几湘帘转眼空,飘零红豆泣东风”[1]潘遵祁:《西圃集》卷四,光绪刻本,第7页。和钱谦益的“可是湖湘流落身,一声红豆也沾巾”[2]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四(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属于末世的异代同悲。费念慈“枕熟黄粱春梦短,庄荒红豆暮云凉。无穷家国伤心事,一事低回一曲肠”[3]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张云骧“红羊小劫须臾,虞山老却尚书。莫数江南红豆,年年恨满蘼芜”[4]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亦是借“红豆”的多重隐喻,抒发在个人关切与政治言说之夹缝中的无力感,以及新旧时代交接中短暂、虚无和不确定性的情感体验。一直到现代,陈寅恪作《红豆吟》,“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第4页。一句言其在抗战期间旅居昆明,从旧书商手中购得一粒据说出自钱谦益故园的红豆,二十年颠沛流离,而红豆仍在。他借“红豆情缘”窥探易代士人之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第4页。,俨然又是一重文化复兴之思。
2.“男降女不降”与“民族独立”
晚清民国论者对柳如是等明季奇女子青睐有加,原因在于她们的妓女身份与节烈行为之间的巨大张力,颇具示范性,《民立报》甚至称“吾国女革命家,当以河东为第一人”[7]塞庵:《塞庵旧话》,《民立报》1911年4月3日。。1911年《申报》的《自由谈·野史》栏目称:“女杰,一娼妇也”,“而能独其爱国思想深明大义”,“然诸多顶天立地之男子为求高官厚禄甘心卖国,绝无民族思想,与女子相去甚远”[8]参见1911 年12 月4—6 日《申报》。嘉定二我转载柳亚子《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并易名为《松江女杰小传》。。入清以来,一直流行的“男降女不降”的说法是属于汉民族的易代记忆,钱柳二人在殉国之事上的抉择堪称此说的典范。晚清文人铺陈演绎此类野史逸闻,凸显明季女性之死的意义,目的之一就是激发男子的“民族思想”,争取“民族独立”。
晚清文人宣称“明末清初之际,山川之秀不扬为须眉之气而吐作巾帼之光”[9]山渊:《余孝女》,《春声》1916年第3期。。其实,这种“男不如女”的说法在入清以来不曾间断。袁枚“可惜尚书寿更长,丹青让于柳枝娘”[10]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陈文述“婵娟都被须麋误,不作忠臣传里人”[11]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应时良“生得相随原妾幸,死无他憾为公迟”[12]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等,表述的都是柳如是的义节侠气为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晚清文人进一步融合“殉节”与“殉国”的概念,即认为柳如是的死体现出的不仅有“钱氏家难”所道的普通节烈纲常,更是“国家伦理”的价值取向。比如,吴清学“妇人能殉国,斯土亦生香”[13]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直接将“殉主”改为“殉国”,将柳氏之死拔高到家国层面。丁传靖“海虞红豆千秋艳,寂寂人间方芷生”[14]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99页,第191页。将柳如是同民元前后文化视野中的方芷生并置。方芷生在国难之际逼夫自尽,自己亦引刀而去,《申报》称其“为民族流血之英雄,增光种族之女杰”[15]嘉定二我:《方芷生传》,《申报》1911年12月15日。。正如南社领袖柳亚子在《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所说,柳如是等所引起的“男降女不降”之说,已然被奉为“中国女界之魂而决民族思想”之起点[16]柳亚子:《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女子世界》1904年第7期。。
以推翻满清统治并抵御外辱为目标的革命思想,需要一种“女军人传统”作为支撑,而柳如是的事迹恰好印证了这一“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思想。当时,《女子世界》传记栏目先后为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女军人”立传,表彰其卫国殊勋。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将柳如是视为与花木兰、梁红玉比肩的人物,故借其小像重构晚明历史记忆。李黼平“到底不惭真女士,木兰邨里斗新妆”[1]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03页。,柳亚子“红粉能谈兵,何异梁红玉。惜哉钱尚书,老去徒碌碌”[2]柳亚子:《题河东君像》,《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等等。这些诗句中所道柳如是“京口祭拜韩世忠”“劝夫殉国”“北上救夫”“自缢殉主”的情节,将其塑造为性豪侠、重然诺、尚信义的典范,顺应了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她的“海上犒师”之举更是直接投入了民族战斗的表现。张亚屏“千秋大义甘殉节,一片孤忠独犒师。志愿毁家能复国,才优咏絮且工诗”[3]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03页。,张卓人“工吟已见娴风雅,助饷尤能解橐囊”[4]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03页。,钱文选“义师鼓舞非甘后,异族驱除誓必先”[5]范景中、周书田编撰:《柳如是事辑》卷一(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03页。等诗句中所诠释的柳如是,符合当时铸造“军人之体格”和“军人世界”[6]丁初我将“军人之体格”、铸造“军人世界”作为“女子世界”诞生的首要任务。参见丁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1904年第1期。的时代要求,这也是知识分子对强权与帝国主义集矢中国而急切呼吁抵御之策的反应。
文变染乎世情,男性文人从哪种角度观赏、重构柳如是,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借助对柳如是“景观”的塑造,最终烘托及激励的是男性人格,这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尤其是男性心理投射、作用的结果。当然,晚清文人对柳如是等明季烈女的回顾与西学东渐及西方女权思想的传播有密切关联。《精卫石》录有秋瑾的《改造汉宫春》:“可怜女界无光彩,只恹恹待毙,恨海愁城。湮没木兰壮胆,红玉雄心。蓦地驰来,欧风美雨返精魂。脱范围奋然自拔,都成女杰雌英。”[7]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便是最真实的写照。时人谓“莫诞于柳如是,莫怪于吴弱男”[8]孙毓修:《绿天清话》“吴弱男”条,《小说月报》1912年第6期。,柳如是得以与“女权运动之先驱”并称。对这一理想女性的重新认定和重构,也为当时“新造中华资格之巾帼”以及“女界革命”提供了历史依据。
四、结语
晚明时期,柳如是在男性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发声方式,以漫游、造景和充满双性特质的风神气度及书写模式与男性对话,重塑了性别身份、扩展了性别空间,成为一道瞩目的文化“景观”。男性在审视柳如是“景观”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带有身份意识和性别权力的运作,营造了与富商巨贾相区分的“闲赏”“闲雅”的美感生活,“此种结合美色、情艺与情感之情色文化,乃成为明代社会文化之重要特色”[9]王鸿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赏与情艺生活经营》,《新史学》2013年第2期。。另一方面,在晚明“情观”的时代背景下,男性士人还在“观看”柳如是的过程中打开自身生命境遇的言说空间,移情作忠,借女性声音进行自我形塑和人格设计,彰显了“深情”与“忠君”的情艺文化。推及后世,钱谦益和柳如是作为“明清痛史”的典型在晚清及民国的“新痛史”中重新焕发生机。知识分子对钱柳二人的书写融合了“复国运动”的革命话语与“恢复中华”的民族精神,为“女界革命”或妇女解放者所利用,呈现了晚清对晚明历史的重构、戏拟。因此,柳如是“景观”和士人的相互观看及建构,体现了政治失序状态下性别声音的混杂,其中涉及性别互动、朝代更迭、士人出处、历史感伤、隐喻诠释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