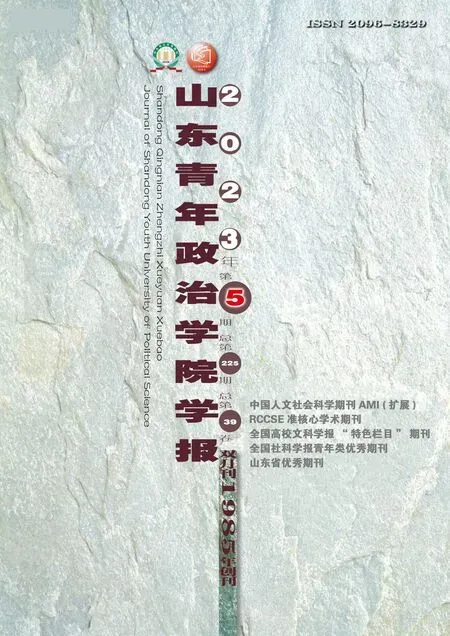从“《易》是卜筮之书”新诠看朱熹的易学观
王林栋
(山东大学 a.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b.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在朱熹的易学中,受到极大关注和争议的,便是那句“《易》是卜筮之书”。这一论断引发了较为广泛的辩论,即便是朱熹的知交好友张栻和吕祖谦也未对其表示认同。然而朱熹为何不改初衷,始终坚持“《易》是卜筮之书”的立场?卜筮之书透出了朱熹对作《易》圣人怎样的理解呢?对朱熹来说卜筮的含义是什么?他的卜筮之书与前人的卜筮之书存在何异同?其一再强调“《易》是卜筮之书”有什么现实的需要么?在他眼中卜筮有何实用价值?卜筮之书对其易学建设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希望通过细检朱熹易学的相关文本,以对此问题有所发见。
一、从四圣作《易》看卜筮之源头义与根本义
既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不能不提这卜筮之书的由来。古来对周易经传作者及年代的看法大致如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可见,汉代学者认为《周易》经传由上古、中古、下古的三位圣人所作,而具体作《易》之人,唐孔颖达在《周易注疏·卷首》中云:“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又说:“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 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并提及:“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2]
据此可知,汉唐时期,或有三圣作《易》说,或有四圣作《易》说,其差别在于卦爻辞的作者是否涵盖周公。除此之外,具体到重卦之人或认为是伏羲画八卦之后一并重卦,或认为重卦另有其人,其时代大体不出上古。概言之,在以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学者看来,伏羲画八卦,重卦之人未有定论,卦爻辞或是文王作,或是文王周公合作,《易传》是孔子所作。
时值宋代,朱熹认为:“《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3]也就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由此可知,朱熹是赞同四圣作《易》说的。那么《易》之卜筮之用是源于何呢?朱熹推想道:“盖上古之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务’。”[4]显然,上古之时,民众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伏羲等上古圣人立龟卜与筮蓍,作《易》画卦,以教与万民保全自身,驱除恐惧,最终以化成天下,以成就民族之生生不息。故而,卜筮源于上古圣人慈心爱民,有着极其深远的眼光,虽未立文字,却也蕴含着圣人之大道。由此推知,卜筮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象征意义,以及极为幽远的历史根源。
卜筮价值虽高,却也时代久远,若无后人之理解却也无法传至今日。因而,朱熹进一步申说:“然伏羲之卦,又也难理会,故文王从而为之辞于其间,无非教人之意。……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5]据此,伏羲画卦立卜筮幽微难显之大义,借由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而得以传承。至孔子之时,却也是沿此进路而作十翼,透过解释卦爻辞以言明伏羲所画之卦、所立之卜筮之义。白寿彝说:“伏義文王周公孔子底《易》,虽各有不同,但在以卜筮为主之一点上,却是相同的。”[6]不难想象,在朱熹的视域中,四圣作《易》虽各有大义,然终极目的确是为了传承卜筮之义,说其为圣人作《易》之究极目的也不为过。这样看来,卜筮不仅具有《易》之始发义、源头义,也具有核心义、根本义,《周易》经传不过是以卜筮为出发点,由卦画、卦爻辞、《易传》三者环环相套,一步步将卜筮推开来去,又一步步回归于卜筮。
具体说来,卜筮所具有的价值,与《周易》经传的价值密不可分。就圣人所作之卦画、卦爻辞、《易传》而言,周敦颐于《通书》中曾云:“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7]朱熹接此而论:“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蓄众等处,因卦以发,皆其蕴也。”[8]如此,以圣人之精蕴相分,《周易》古经所涵盖的卦画、卦爻辞为精,《易传》则为蕴。其作层次之区分,无非是为显现高下之差,明了价值之别。“精,是精微之意;蕴,是包许多道理。……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画之中,故谓之蕴。”[9]可知,“精是蕴所本之理,蕴是精的具体展现与实现,精是易道之体,蕴是易道之用。精蕴说可以视作朱熹诠释思想的的一个基本原则。”[10]相较《易传》之用而言,古经作为易道之体,其理皆已具足,只是并未显发而已。同理,在古经之中,卦画为精,卦爻辞为蕴,卦画可以开显出卦爻辞之理,以至于天地万物之理,“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说尽天下万物之理。”[11]可以说,卦画最能代表“圣人之精”。故而,《周易》经传的文字系统是由符号系统所显发,卦画是这一切的根底,这就与前文所述卜筮为《周易》之价值源头是相契合的,进一步印证了以卜筮与卦画为代表的伏羲之易的根源意义和人文价值,而非仅仅具有时间上的始发价值。
然而,就一般意义来看,来自上古的伏羲怎能具有如此高的超越后人的智慧,岂不有违常理?在此,朱子却显发了与众不同之意:“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只是借伏羲手画出尔。”[12]就此而论,伏羲显发的卦画与卜筮并非出于个人之智慧,不过是“自然”罢了,这个“自然”就是朱子所言之“天地自然之易”,“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13]四圣之前,还有“天地自然之易”,这不再是人文意义上的易学,而是最为广大久远的天地万有意义上的易学,其具有宇宙本源义、本体义上的价值,也就是邵雍所推崇的“画前易学”。不言而喻,卜筮与卦画之所以具有本根价值,是由于天地自然之易为根基,而天地自然之易是借由圣人所开显的卜筮之易为立足点。
综观上文可见,朱熹看重《易》为卜筮之书,是从卜筮所具有的源头义、根本义而言,他将四圣作《易》的时间脉络与价值脉络相重叠,以起点为根源,时间愈发久远则价值就愈发重要,以伏羲所作的卜筮与卦画为人文价值的根源。更进一步,将人文根源推至天地万有,人文便以宇宙义或本体义为根源,将易学之含括从人类视域扩大至天地万有之视域,以致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故而,卜筮之书是为朱熹易学之立足点与切入点。
二、以太极之理重构“卜筮之书”
应当承认,朱熹一句“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14],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误以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只是一本占卜之书,没有什么道理,误以为这源远流长的易学发展史,不过是流于术之小道,并无人文价值可言。不过,若是落实到具体生活世界中,笔者认为,朱熹这句“《易》是卜筮之书”是有针对性而发,针对的便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疑经思潮。
汉唐经学在经历了佛道两家思想几百年的冲击之后,时值宋代,其经典地位不再稳固,圣人制作经典的说法也备受质疑,即便是拥奉五经的儒者也开始产生质疑,由此而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疑经思潮。北宋欧阳修,作为有记载以来的首位质疑孔子作十翼的人,他指出卦画是卜筮之用,惟有卦爻辞和《易传》则是含有圣人大义的。他在《易或问三首》中提及:“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后世,用以占筮。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15]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承认伏羲之《易》是用于卜筮的,但文王作卦爻辞是出于忧患意识,孔子作《彖》《象》拨开《易》的卜筮之用,开显了文王之志,卦爻辞和《彖传》《象传》都含有圣人大义,《周易》属于义理之书。客观而言,其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对《周易》义理性质的判定,对十翼作者的廓清,以及对卜筮之用的打压,正是为了维护正统的圣人大义,维护经典的地位,也正是出于儒者的现实需要。[16]
欧阳修的观点代表了同时期大部分学者的心声。众所周知,在《周易》经传形成之后,“有了学与术的划分:着眼于哲学性的天人之学解读而运用《易》的,属于学之列;从卜筮的角度解读、运用《易》的,归于术之列。后者渐渐为主流士人所鄙薄,乃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见识,即认为将《易》视为卜筮之书乃是对这部经典的亵渎,是对创作这部经典的圣人的不敬。”[17]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这部分学者,为了维护《周易》的经典地位,想要将《周易》与卜筮割裂开来,抬高义理易而贬低卜筮与象数易的价值,这既违背历史事实,又置卜筮与象数于不顾。朱熹有着历史理性的眼光,他看重《易》的卜筮义、根本义,以及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价值,明了象数与义理的体用关系,且认为承认《周易》所具有的卜筮性质,并不会抹杀其作为经典的价值和地位,反而能寻得《易》之本义。学者们否定卜筮的性质,无非认为卜筮是非理性的,不具有人文价值,不属于天人之学,朱熹正是从此处下手,希望扭转人们对卜筮的看法,因此对卜筮之书进行了重构。
概言之,朱熹的“卜筮之书”,与传统的卜筮,有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卜筮背后的终极根基不同,二是卜筮之用不同。
首先,从卜筮的终极根基说起。先民的卜筮虽出于伏羲之手,但这种卜筮是想要通过龟甲和蓍草作为媒介,“实现人与神灵及相关物事间的感应沟通”,这是“自原始时代以来即已出现的万物有灵且可彼此感应沟通观念的一种延续与发展”,卜筮发展到殷周时期,仍是建立在对皇天上帝的绝对信仰的基础之上,虽周代出现了“以德为灵魂的天命转移观念”,其本质仍旧是“信仰优先于理性”。[18]因而,大约在战国以后,“卜筮作为算学的萌芽沦落为末技保留了天人感应的认知模式,从而被逐出人文领域,为读书人所鄙弃,这就要求《周易》必须通过自我更新与当时的认知水准相匹配。”[19]
前文提及,朱熹看重卜筮所具有的源头义、根本义,并将其与天地自然之易相贯通,更使其具有宇宙义、本体义。然而,从学理上观之,这天地自然之易是如何具有本体价值的?又是如何贯通于《易》之卜筮的?笔者认为,朱熹是以太极之理为根基来实现的。他认为“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20]可见,从本体义上言,太极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基根据,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又成为万物之性。太极在万物具体生化的过程中则需要理气关系的参与。“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21]将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转换成理气关系是朱熹理学与易学之核心。“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2]据此可知,从落实到万物生成的角度来看,理是太极之理,是形上的本体,是万物之根基;气则是构成万物形体之必须,有气的生成才有着大千世界的形成,大千世界万物皆是理与气是不相离的。一言以蔽之,这个世界就是由太极之理和气造化而成的世界,居于其中的人也是理气造化而成。
问题是,卜筮如何实现以太极为根基的呢?卜筮如何得以实现的呢?卜筮之价值又是怎样呈现的呢?由上述可知,人之所以能够通过卜筮实现与这个世界的感通、沟通,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气造化而成的,人跟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直处在以太极之理为根基、以气为媒介的变化中。以此应用于卜筮中,就表现为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卜筮的操作,去感通沟通终极根据的太极之理,感通沟通气、天地,你的疑惑就呈现在卦上,你就能够通过卦来知吉凶祸福了。朱熹对于《系辞上》中所载的大衍筮法就是作出了这样的解读,如以五十策蓍草置一不用以象太极之理等。归根结底,朱熹的“《易》是卜筮之书”,是以天地自然之易为根基,更是以太极之理为根基。正是在此意义上,卜筮不再如前人所言出于信仰而非理性,而是自然地以一种人文价值理性来接通天人,与太极之理相感通。
其次,是卜筮之用的不同。先民想要通过卜筮去预测事情发展的状况,以更好地趋吉避凶,属于“因卜筮以设教”。[23]这也是卜筮最初的意义和最基本的功用,而这种功用在朱熹太极之理的架构之下,显现为人人皆可用卜筮去感通接通太极之理、天地万物,以达到趋吉避凶、知吉凶祸福的目的,“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处”,[24]这也是朱熹所认为的卜筮之用最基本的层次,即第一层。第二层,是在日用平常中去把玩筮占,不一定非要遇事而占。“今学《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孔子所谓‘学《易》’,正是平日常常学之。”[25]学者对于卜筮之用,可以上升至学的层面,在天人之学的层面去理解体味把玩卜筮中所蕴含的道理。也就是说,将卜筮、象数层面与义理层面相贯通,而皆不偏废。第三层,也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以卜筮之用作为学《易》的基础,以此达到契入作《易》圣人的境界和天地自然之易的境界,实现对终极的太极之理的体认与回归。综括这三层,朱熹要接通学与术,以学为旨归和目的,以术为手段和方法,由卜筮之术达至天人之学。朱熹对卜筮之书的定位,是为了打通古今、贯通学术,真正地让《易》在万民和士人之间流通起来,使得易学焕发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这也可看作是易之生生的一种表现。
三、卜筮何以接通现实
朱熹用太极之理重新架构卜筮之书,接通学术,以天人之学填充卜筮之术,用理学宏大的宇宙论来支撑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由太极到阴阳二气再到气化世界的形成,太极始终以人物之性的形式存在世界之中。同时在《周易》中,由无形的天地自然之易到象数系统形成,再到文字系统形成,太极同样贯穿其中。《周易》的象数、文字系统与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体的、相对应的系统,并不仅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上,更是在实用的层面上,而二者的对接恰恰可以通过卜筮。具言之,朱熹认为卜筮之所以能实现二者的对接,一是以太极之理为根基,二是以阴阳二气的交易、变易为展开模式,三是依靠《易》之象与辞的情境性。关于太极之理为根基,前文已述,下文主要从后两部分入手。
先来看看阴阳二气的交易与变易。“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更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26]交易、变易是《周易》称之为“易”的根据,是阴阳爻所符示的阴阳二气的变化方式。“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27]
朱熹将“交易”解释为像邵雍所传的伏羲八卦圆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圆图那样,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朱熹谈及六十四卦的由来,说道:“当未画卦前,太极只是一个浑沦底道理,……及各画一奇一耦,便是生两仪。再于一奇画上加一耦,此是阳中之阴;又于一奇画上加一奇,此是阳中之阳,又于一耦画上加一奇,此是阴中之阳;又于一耦画上加一耦,此是阴中之阴,是谓四象。所谓八卦者,一象上有两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28]如此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朱熹虽未明说,但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还会无穷尽的继续下去。王新春认为:“这就是所谓交易: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而又与另一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者相互对待。”[29]即阳中无穷无尽地分阴分阳,阴中层层无尽地分阴分阳,而又各个相对。
变易则是阴阳互变。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余敦康指出“对待与流行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横,一个是直。横是就宇宙的结构而言,直是就宇宙的过程而言。”[30]变易讲述了纵向的阴阳流转之意,交易是横向的阴阳层层无尽分阴分阳的流转。朱熹认为程颐“只说得相对底阴阳流转而已,不说错综底阴阳交互之理。”[31]必须强调的是,对于朱熹而言,包括程颐在内的学者们大多只看到阴阳的流转,难以看到阴阳的互含。
合而言之,在横向上层层无尽的分阴分阳而又相互对待,在纵向上又阴阳相互流转,既是宇宙万物流转变化的常态,是卜筮能够体现实用价值的依靠,也正是八卦、六十四卦形成的根据。正是在交易、变易不断对待、流转的基础上,产生了理气运化而成的世界,因而,以易学的交易、变易理论,更能意会理气运化之精微之处,也更能理解太极与万物之感通与关联。换言之,以交易变易为基础的卜筮,是我们得以理解天地万物、太极之理及更好认识人类自身的桥梁与工具。
进而,我们再来看象与辞的情境性。《周易》古经中,八卦、六十四卦的卦画系统是象,属于符号系统,卦爻辞是辞,属于文字系统之。朱熹认为:“《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辞中便有道理。”[32]《易》因为圣人要教民作卜筮以趋吉避凶而画卦才有象,根据象而占筮,进一步形成占辞,即卦爻辞,“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33]故而,不论是圣人作卦画所取之象,还是所作卦画中蕴含的象,还是因象而虚设的卦爻辞,皆含具象形的意味,换言之,含有一种情境的意味,而这种情境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宇宙万物交易变易过程中的一段。依朱熹的观点,这种象和辞的情境性,使得“易则是个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34]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空套子”,不可把它看实了,不可只看作某一个确定的人或某种确定的史实。
具而言之,“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这里,无所不包。”[35]假托说和包含说可看做是《易》之情境性的两种表现。譬如,《周易》不是为了记述文王、箕子的史实而作,而是借着一个箕子的情境来说明吉凶祸福的情状,以及说明一种事理,这是假托。而《周易》以其丰富多变的情境性而无所不包,这是包含。一种情境可以包含好多种事,它的外延是很大的,象与辞的情境性赋予《易》之无限性。唐君毅指出:“此变化之可能无定限,然其每一可能之实现,皆有一始点,此即为一几。一事物可引起种种之变化,即有种种之几。在一变化之始点上看,其中亦有其他种种之变化之可能,聚于一变化之始点。故知几之义微,其事亦难。”[36]知几之微恰好好说明卜筮可以呈现出丰富的、无限的、超出人一般认知的各种情境,此其神妙所在。正因为象与辞无限的情境性,才能使得“《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37]
象和辞的这种情境性,落实到具体的占筮活动中,体现为一种感通模式下的情境模拟与再现。比如我们因一件事有疑惑而占筮,我们当下是有一种情境的,我们与天地感通而占得一卦,这一卦或一爻所蕴含的情境是与与我们所占之事相应的,代表可以解决事情的情境。这种解决情境只有64大类384种,而所问之事千千万万不可穷尽,两者时如何相应的呢?相应的前提是太极之理,而相应的原理是交易、变易。上文提及,交易指层层无尽地分阴分阳,这样64卦变128卦,128卦变256卦,256卦变512卦,如此成倍增加,直至无穷卦,同样384爻变768爻,变1536爻,变3072爻,直至无穷爻。换言之,64卦384爻是圣人画卦作卦爻辞所显现出的天地自然之易的一个宏观图景,其中还有层层无尽地微观的、细致的情境与我们当下占问的事情相对应,这就是余敦康所言“宇宙的结构”。那变易怎么解释呢?当一个情境变成另一个情境,一卦变成另一卦,阳变阴、阴变阳,这就是变易。我们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情境也跟着不断变化,这是变易所体现的一种绵绵无尽而又相接续的变化过程,此即余敦康所言“宇宙的过程”。当占问的情境与某卦某爻的情境相应时,将卦爻情境的吉凶及解决方法再现于占问者面前,通过对再现的情境的理解得出解决办法,这个过程也是占者了悟情境所蕴含的太极之理、易道的过程。每一卦每一爻背后都蕴含着层层无尽的情境与可能性,所以要用模糊不实的象和辞来表示,要虚着说。
综括上文,朱熹对“《易》是卜筮之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契入了天地自然之易的层面,是活泼泼地生活之易,他借着卜筮之用打通古今之易,打通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空的易,接通每个人每个事物的生命。至此,朱熹借由卜筮、太极之理、阴阳交易变易与易之情境性,重新构建起以卜筮为核心,以太极之理为根基根据的弘大的无所不包的易学视域与宇宙图景。
四、由卜筮观如何读《易》
前文已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天地自然之易是不易被人所知的,而之所以伏羲之卜筮最为根本,是源于作易之人的心境之不同:“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38]易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四个层次,而伴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的心境则越来越狭窄,不似伏羲之时宽阔。
即便是文王周公之易,也有所遮蔽,不似伏羲卦画那样圆融。说的越多,越急于说出一些道理,则遮蔽的越多,“譬如个灯笼安四个柱,这柱已是碍了明。若更剔去得,岂不更是明亮!”[39]《易》之发展史就像这个灯笼,四个层次像是四个灯柱,说的越多,则遮蔽的越多,伊川之易是说的最多的,也是遮蔽的最多的,反之,伏羲之易只有卦画,是遮蔽的最少的。故而,在朱熹的逻辑下,伏羲之易是最圆融、涵盖最广的,文王之易次之,孔子之易再次之,伊川之易则是最狭隘、涵盖最少的。这与一般学者的逻辑是不同的,一般我们会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时代越靠后的则越圆融、内容越丰富。朱熹能如此想,正是由于易是个空底物事、空套子,易的象和辞是虚设的,具有一种情境性。在一种情境中,你给定的条件越多,说明的越详细,则限定的范围就越小,那么能说明的东西就越具体也越局限。伏羲的卦画可以符示无限宏大的宇宙图景,而文王周公的卦爻辞则有了具体的人情事物的限制,符示了人类的生活场域,到了孔子之《易传》则用于推明义理,以卦爻之好坏和己德之高下结合而展现吉凶,展现出义理的场域,再到伊川之易传则完全遮蔽了卜筮之用,只留下理学的视域。
因而我们要契入伏羲的场域,就要研究伏羲之易,要契入文王周公的场域就要研究文王周公之易,以此类推。研习的过程自然是从宽阔的广大的到细致的具体的,自是要沿着伏羲、文王、孔子、王弼、程颐这样的顺序。朱熹很讲究为学的顺序:“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40]由此而知,为学应该先从讨论具体之事的四书入手,而后是孔子所雅言的《诗》《书》《礼》《乐》,最后才是《周易》和《春秋》。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日用常行到天人之理,由易到难,这是日常为学的顺序。
而《易》之难读恰恰由于卜筮,朱熹说:“盖《易》本卜筮之书,故先王设官学于太卜,而不列于学校。学校所教,《诗》《书》《礼》《乐》而已。”[41]蔡方鹿认为:“指出诗书礼乐教人以道理,故被列于学校;而《易》在当时只是为占筮而设,就其不列于学校而言,说明它的本义初不在义理,而在卜筮。推原其本,《易》以卜筮而为教化。”[42]《易》以卜筮设教,就决定了《易》“不可易读”,自不能用日常学习的方法对待,“读《易》,当明大衍筮法,‘如读《易》不曾理会揲法,则说《易》亦是悬空’。同时,他认为,要身临其境,进入卜筮活动氛围,用卜筮语境来理解《易》。‘读易当如筮相似,上达鬼神,下达人道。’就其文本而言,先解读六十四卦,再读《易传》。他说:‘熟读六十四卦,则觉得《系辞》之语直为精密,是《易》之括例。’”[43]只有以从卜筮的视角,按顺序打通古经和《易传》才终能契入易学视域之中,这是从客观上讲。
从读者自身的条件来看,“读《易》未能浃洽”,未能融会贯通,“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罗得许多义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44]读《易》之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静下心来,摒弃一切干扰,二是要有所经历,对各种各样的情境有所领会,才可有所透破。唐琳指出:“学者惟有保持内心的虚静,才能摒除外在干扰,对文本真实含义做出正确的理解,避免误读误解。但朱熹强调,对于读《易》来说,这一点又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与其他经书相比,《易》最难读,读者除了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以外,还需要以心验之,以身体之,优游涵泳,默识心通。”[45]
五、结语:卜筮贯通朱熹易学
朱熹的易学有宏大的宇宙观,是理学视域下以太极之理为终极根基的宇宙观。这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落实到具体生活情境中可以生成活泼泼的具有生命力的生活观,而这些是围绕“《易》是卜筮之书”这一论断展开的。透过四圣作《易》,朱熹开辟了一种以伏羲卦画与卜筮为原点、核心的层层推展开来的易学路径,而究其根本而言,《易》之本根在天地自然之《易》,从而在学理意义上引入太极之理作为卜筮之终极根基,置换了曾经的信仰层面的卜筮之根基。又以交易变易及易之情境性使得卜筮与气所构成的现实世界相感通接通,卜筮得以立于现实之中,并非源于非理性的信仰而是源于朱熹理学视域下的理气关系,由理气所构建出的现实宇宙社会与人生。由此,《易》之价值从人类视域推广到天地万有视域,又由跨越时空的天地万有落实到社会人生的实用层面:卜筮生来就有趋吉避凶的算命之用,却不纯是如此,《周易》以卜筮之实用为表,以卜筮之接通感通圣人境界和天地自然之《易》的境界为里,用《易》之人可不限于士人或巫觋,平民百姓皆可习得与运用,由此,人人皆可通过卜筮以契入作《易》圣人的境界和天地自然之《易》的境界,以实现对终极的太极之理的体认与回归。可以说,“《易》是卜筮之书”贯通朱熹之易学,而其贯通是以其理学架构为根基。不可否认,朱熹此“《易》是卜筮之书”一说确有所疏漏,如高怀民认为“朱子倡言‘《易》为卜筮之书’,后世知识分子多视《易》为算命之学”,朱子割断经传关系等等,[46]但笔者认为,细观朱熹的易学思想,他能凭借太极之理所重构的卜筮之易契入到如此境界,实在值得被众人所理解,学者不应一看到“《易》是卜筮之书”就着急否定朱熹,还要看到朱熹这一学说背后的种种精神与其磅礴弘大的易学视域。